影评 | 庵野秀明《巨神兵现身东京》:末日情结的当代命运
“在睡眠中,他创造了一个典型/筹划一场轰烈的革命/拥抱正在呈现的未来”
——阿多尼斯《睡眠与睡醒》[1]
《巨神兵现身东京》是庵野秀明于2012年拍摄的一部特摄片。因为它前缀于《EVA新剧场版: Q》,名称和形象借自宫崎骏的《风之谷》,绝大多数观众都从《EVA》和《风》代表的末日片传统本身出发,把《巨》看成无甚新意的致敬之作(见bilibili弹幕和豆瓣评论)。
粗看之下,《巨》的情节的确再庸常、再简陋不过了:昨日“弟弟”现身,警告“姐姐”在末日降临前逃离,当下巨神兵降临,将东京毁灭殆尽。尽管片长只有8分多钟,却有将近一半时间在“花样”展示城市陨落,加之特摄技法相比电脑特效过于原始,在口味早已被大片养得刁钻的观众看来,这实在是毫无意义。不过片中层出不穷的疑团却与观影常识格格不入,尤其是毁灭场景和静谧气氛之间的强烈对照。这些被导演有意放慢、突出、多角度展示的不协调似乎都在暗示,《巨》表面情节之下还潜伏着更深层的故事和含义。
可惜庵野秀明为了反思末日片/幻想的社会心理甚至政治意涵,采用了表里翻转的结构,把反讽意图包裹在厚厚的烂俗元素之下,自恃曲高和寡,给观众提出了过高的要求。那么,就请随着我一起解码《巨》的玄机,看看是什么意图要求庵野秀明故作隐晦。
- 叙事分析:警告还是邀请?真实还是幻想?
影片开场从“姐姐”视角呈现的对话部分出现了一连串超现实元素(火星飘飞、“弟弟”凭空消失、巨神兵现身)。在末日片观影常识中,这些都是推动俗套情节前进的常规要素,是熟悉化(familiarization)的手段,然而一旦统一起来,它们却构成了间离化(distancing)机关,提示我们“假作真时真亦假”的虚构框架已经被突破,巨神兵不是电影世界里“真实的”怪兽,而是“真实的幻想中的”怪兽。
对话中“姐弟俩”貌似心境各异、出言步步相逼,但仔细分析会发现,他们始终都在同一个频率上,“姐姐”总能立刻意识到“弟弟”的言外之意,做出准确联想,而“弟弟”的话似乎也都对“姐姐”产生了预期效果。叙述中昨日“弟弟”出场刚提到末日,当下的“姐姐”便回想起昨天在各个场合偷窥到的网络大讨论,接着她开始注意到当刻天空中火星飘飞的异象。虽然几个事件之间有一天的时间间隔,但口头叙述中“弟弟”消失后由火星汇聚成的巨神兵立刻现身却提示我们:“弟弟”、网络谣言、火星、巨神兵四个意象其实是内在统一的。可以这样推论:网络上汇聚的毁灭城市的集体意志,具象化为空中丛聚的火星意象,因为非但火与毁灭相应,火星丛聚也和网民汇聚的形态相似。实体化为火星的集体意志进一步人格化为代表地狱之火的巨神兵。而“弟弟”则是网络意志的一部分。
既然巨神兵是网络集体幻觉的投射,而它正是出现在“姐姐”的视野里,我们由此推测“姐姐”也是网络集体的一部分。但是看起来置身事外的“姐姐”有什么理由毁灭自己赖以生存的城市?影片对东京人生活状态的呈现非常有限,在纵览了他们整个社会生活和内心世界之前,我们不可能知道他们为什么对“一成不变的日常”失望至此,进而倒向毁灭幻想。但这段叙事的小细节却让我们得以推测都市人的复杂心境。比如“姐姐”颇苦于城市人际的冷淡艰难,才退守自己的小空间,甚至会因亲生“弟弟”的到来而惊慌失措。弟弟的话以黑底白字呈现,比网络聊天窗口更冰冷、更看不透,一如他在亲“姐姐”面前极尽委婉的语气。我们由此推断,“姐姐”其实因自己亟待宣泄的不满在网络谣言中找到共鸣而窃喜,却碍于一成不变的日常还可容忍、难以割舍,无法完全认同毁灭幻想,忌惮其他网民的黑暗心理,承受着剧烈的内心冲突,所以才不敢表露自己的真实心境。
现在回过头,弟弟的话也显出其用意。末日幻想正在酝酿之际,作为网络集体一员的“弟弟”来拯救处在情绪爆发边缘的“姐姐”。他的警告表面上是末日预兆,但对于意识到眼前异象和谣言关联的姐姐,这更是一场集体末日幻想的邀请。“在度过一成不变的日常之时,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预兆和警告,才是至关重要的。”“弟弟”暗示“姐姐”:要想宣泄心中的绝望,当务之急是加入集体幻想。但他也清楚,还有一个阻止“姐姐”放弃日常的强大心理障碍需要打破,因此他才说:“那么久拜托姐姐了,虽然很像在为难你,实在很抱歉”。

如果以上细节还不足以证明巨神兵是网络集体幻觉的投射,那在巨神兵在城市中走动、喷射激光的场景中,“真实怪兽毁灭真实城市”的表面情节的幻觉实质再也藏不住了。下图的场景中,尽管近在咫尺,巨神兵脚下腾起的尘埃和火花却对楼上站满的人没有任何影响,人们停下了手中的一切,呆立出神,而巨神兵也完全没有在意这些观众。当巨神兵开始向城市展开攻击时,城市突然“万径人踪灭”,成了一具空壳。天旋地转的火光、烟尘、残骸中竟然没有惨叫、血迹和残肢。伴着迷幻而陈静的音乐,我们仿佛在欣赏奇景,而非目睹灾变。你会怀疑,这场末日中或许本来就没有人的位置。

如果巨神兵是影片中“真实的”终结者,它绝不会留下一条活口,人们不可能不落荒而逃。只有一个可能:这些人并非置身末日发生的那个“世界”,他们是那个“幻想世界”的创造者-观看者。只不过,导演为了提醒我们巨神兵是人造幻象,有意让这群幻想者和他们的幻想共同出镜,就像热内·马格利特Attempting the Impossible中的画家和他笔下的裸女,也像广告中带着VR眼罩的玩家和虚拟物体。暗示过后,这些影片中的观众退出画面,形成一内一外两层嵌套叙事。虽然影片中的观众和作为影片外观众的我们同处于镜头之外,因而视角重合——我们看到的《巨神兵现身东京》正是影片中的幻想者们的幻想,但我们必须意识到,还有一群画面中不可见但属于故事一部分的幻想者正在制造我们看到的幻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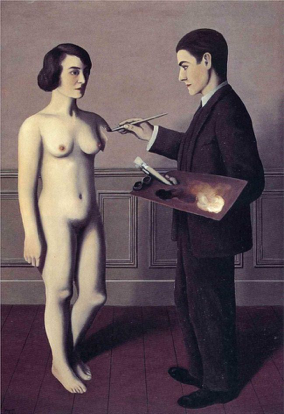

- 神话修辞和心理分析:毁灭欲的宣泄
“姐姐”转念之间就接受了“弟弟”的邀请。巨神兵着陆后,“姐姐”摇身一变为末日的解说者,论述起神的本质,连人称都从“我”变成了“我们”,似乎已经与网络集体意志融为一体。前一刻还充满疑虑的“姐姐”,为什么会突然接受末日幻想的邀请?这跟末日幻想满足毁灭欲的具体方式有关。
毁灭欲在我看来其实和精神分析所谓的“生命驱力”(life drive)是一体两面。生命有随心所欲地占有时间、空间、物质和关系来满足自身的倾向,当遭遇阻挠或抵抗时,便会有攻击性反应(reaction)。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2]中认为,人类个体和文明之间存在广泛的欲望交换,随心所欲的“生命驱力”必须被限制,以换取分工合作和集体生活的种种益处,而对束缚的挣扎反抗则表现出“文明的不满”。对都市人来说,现代生活无法割舍,对“生命驱力”一定程度的牺牲必然会作为代价(而且似乎是最轻易的代价),用于交换文明对其他欲望的满足。现代城市生活赖以维持的关键,就在于疏导“文明之不满”,避免压抑过度而触及毁灭欲的红线。对个人来说,毁灭欲的爆发则意味着放弃一切文明的既得利益——破釜沉舟、自断后路,所以必然面临无比强大的内心阻挠,很难从幻想照进现实。
正因此幻想才对毁灭欲的宣泄至关重要。只有幻想能毫无限制地调节欲望交换,制造出欲望的乌托邦,奇迹般地减轻甚至撤除对个体自由的所有压抑和限制的同时,又避免一切代价。因此,末日幻想天然地采取神话的形式。正如福柯所言:“…既然生死攸关,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反抗能够轻易地在宗教主题中找到表达和进行的方式:对超越的承诺、…、对救世主…的期待、至善的无可争议的统治。”[3]换句话说,神话为末日幻想提供了现成的欲望乌托邦的话语模板和图像样式。
“姐姐”之所以轻易就接受邀请,正是因为幻想极具可塑性,她作为网络集体的一员,可以根据心理需要亲自调整末日叙事设计,从而体验超现实的完美满足。接下来让我们从末日情节反观网络集体究竟有哪些心理需求,而他们又是如何据此来设计欲望乌托邦的。
接着上文“末日中没有人的位置”的观察,我们进一步追问:即使只是为了逼真性,不让观众出戏,影响宣泄效果,也应该在城市中投影出惨死的人类吧?尽管人的元素的缺席影响了末日的逼真性,但这是保证宣泄效果的必要代价。既然把毁灭欲投射成巨神兵,毁灭欲指向城市日常,寻求释放的幻想者绝不会允许再把自己的形象投射成末日的受害者,让毁灭欲反指向自身。主人公绝处逢生或受超自然力量眷顾是灾难片的宿命论(fatalism)。同理,只有在安全承诺下,灾难片、怪兽片和恐怖片越逼真,观众才越能获得酣畅淋漓的观影体验。
网络大众观看末日的特殊视角也服务于末日幻想的宣泄效果。注意,人们并没有透过巨神兵的眼睛体验毁灭的畅快感,代表集体视角的镜头与巨神兵拉开了一定距离,站在它身后或身侧,观看着自己投影出的替身为自己毁灭世界。这是因为,如果采用第一人称视角,人们就必须承受亲自毁灭自己仍无法割舍的日常的心理困境。只有采取一种半投入半抽离的旁观视角,把灾难归因于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超自然因素,才能一边共情巨神兵毁灭脚下羁绊的快感,一边逃避主观视角带来的心理负担和道德责任。当网络大众透过镜头看着巨神兵的背影时,他们和作为替身的巨神兵之间是一种“顾影自怜”的关系,巨神兵的形象就是他们心目中自己的形象。
影片高潮是一个极其反常的末日神话叙事,它的所有要素都服务于同一个动机——让网络大众得到淋漓尽致的休憩。这部分神话叙事的心理机制值得我们仔细分析一番。
与其说这是一场末日,不如说是一首安魂曲。末日本是集体意志自导自演,现在责任却被画外音推给世界:“世界强行召唤了他们。”灾难的道德责任被重新分配,人们不为灾难的发生负责,反而要承担延宕灾难的责任,任城市毁灭就是“我们”付出的代价。然而上天却眷顾“我们”“一味想要活下去”的愿望,让“我们”在第一日就让“人与地上的生物消失无踪”的末日中有机会逃离。这进一步证明,末日话语中出现的所谓被“夺取性命”的“人”,只是为了让末日更加逼真而添加的词汇伪装。就如上文分析到的,逼真而非真实的危险才是末日幻想/片的真谛。
接着,模仿《创世记》的庄重而不容置辩的文字,一句句穿插在巨神兵从天而降的影像间,讲述着上帝七日创造的世界按倒序一步步瓦解的天启(Revelation,即《启示录》)。这段叙事用对称手法,制造了“我们”与上帝力量相当的假象。毁灭和创造花费同样的时间,而且是原原本本倒退回去,似乎毁灭是创造、毁灭者是上帝的反面等价物。只有这个假象才能给“我们”重生的希望,才能让画外音轻巧地鼓励道:“自己创造出新的世界就好了。”这段末日叙事其实一直被构造为毁灭与重生的辩证(巨神兵从天幕降下的场景伴随着微弱的婴儿笑声),而这正是满足幻想者心理需求的终极因素。只要“我们”被构造为和神力量相当,等待在毁灭尽头的就不是永恒的虚无或重建的劳作;有了重生的希望,幻想者们才能像天启中提到的灾祸一样,在使命结束后“在安息的喜悦中静静地哭泣”(从侧面看,巨神兵们多像脸上挂着笑容,向前自由奔跑啊![4])。这样看来,影片结尾巨神兵排成人墙朝屏幕走来的画面,不仅仅是乘胜追击的死神阵列,就像《风之谷》漫画扉页构图几乎完全相同的画面。不妨说,这就是幻想者心目中的休憩。网络集体通过认同巨神兵们,已经在这幅画面中体验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人际关系——毫无牵绊(脚下的城市燃烧殆尽)、如战友般亲密(密匝的人墙)、万众一心(统一于毁灭的意志和行动)。在这个意义上,有没有末日后的重建都不重要了。末日便是重生,毁灭者已经得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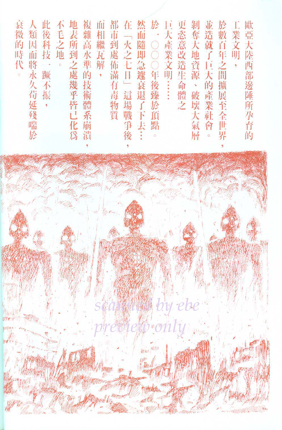

- 意识形态机器分析:作为日常的末日
末日拯救了人,那毁灭针对什么?末日的影像揭露了真相:毁灭欲指向的甚至不是在城市中进行的日常,而是城市景观——城市的物质基础。这场末日幻想是一种卢德运动式的宣泄,它的逻辑中蕴含着某种本质主义还原论。由于生活经验的限制,在日常生活中感到痛苦,人们自然会以周围的日常(景观)为万恶之源,而无心追问是什么生产方式造成了异化,什么生产关系导致人际隔绝,什么才是“一成不变的日常”的始作俑者。于是人们天真地以为,只消在物质上抹平城市,就能提炼出人际关系以及人性的精髓,返璞归真,重建人间乐园。但消灭资本主义的物质成果远非革了异化的生产关系的命,而后者正是效率崇拜、对生命的过度压抑、社会原子化、缺乏意义和成就感的劳动和生活的根源。可以想见,由于没有触及根本,末日清理出的这块“处女地”仍旧会孕育出原有的一切。
进一步,这种挑错目标的毁灭幻想在客观上反倒有助于维持既有的生产关系。集体意志正是靠互联网汇聚和维持,观望者们正是通过手机观看、记录、分享、制造幻象。这才是影片的终极反讽:否定城市生活的手段却恰恰是城市生活赖以维持的关键。电影、电视、游戏及其他娱乐产品构成了阿尔都塞所谓的“娱乐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们不仅像其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那样在常识和日常实践中将生产关系自然化、合法化[5],而是同互联网、影院、手机、电脑、电视等物质手段一起,通过生产欲望和调节欲望交换,让异化的生产关系成为都市人无法违抗的生存本能。资本主义掌管着我们的“生命驱力”:在漫长的物质发展和社会变迁史中,资本主义创造出对富足、安稳和私密的需求,让它们显得像是从来如此的本能一般。这造成了我们饱受折磨却又无法割舍现代生活,甚至对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毫无知觉的困境。同时,资本主义也调控着我们毁灭欲的发泄,甚至裹挟这种颠覆性的力量来维系资本主义社会的欲望交换。当福柯认为“所有形式的自由…无疑都会在反抗中找到最后的定位点”[6],而齐泽克认为“死亡驱力”是逃离资本主义“大他者”规训我们欲望的途径[7]时,《巨》通过戏仿末日片,以一种自反的(self-reflexive)方式提醒我们,在唾手可得的成瘾性消遣手段和逼真末日幻想的包围下,我们的反抗阈值无可避免地提高了;在道阻且长、前途未卜、不能存档重来的末日/变革,和保全了现代生活又保证可重复宣泄的日常之间,趋利避害的欲望交换原则被激活,任何成规模的反抗都从欲望和本能的层次被阻绝了。哪有什么能像末日幻想/电影那样既逼真刺激又保证绝对安全?还有什么比幻想的诗和远方更能给人苟且的希望?而压抑、隔绝、剥削的日常正是通过在幻想中拥抱毁灭,才在现实中保全了自身,得以“一成不变”的。这就是所谓“对加害自己、夺取性命的事物也会合掌、跪地、膜拜、祈祷”吧。
一个不祥的问题将在我们耳畔长久回荡:在毁灭欲被收买之后,我们的自由意志还剩什么?
(原载于微信公众号“深焦DeepFocus”)
[1]阿多尼斯,叙利亚著名诗人。此诗选自他的诗集《戏剧与镜子》(1968),薛庆国译。
[2]详见本书第VIII部分。Sigmund Freud,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W. W. Norton & Company, 2005, pp. 137-155
[3]米歇尔·福柯,《反抗没有用吗?》,王宇洁译,引自微信公众号“保马”。
[4]见影片8:13-8:29部分。知乎网友“夕颜雾见里”类比特摄片演员穿戴的皮套和能乐面具,说明了特摄片也有表现模棱两可的面部情绪的特殊艺术价值,见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4386195/answer/372550017
[5]Louis Althusser,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Revolution”,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Routledge, 1995, pp. 148-163
[6]摘自米歇尔·福柯,《反抗没有用吗?》,王宇洁译,引自微信公众号“保马”。
[7]Slavoj Žižek, “From Desire to Drive: Why Lacan Is Not Lacaniano?”, 第5-7小节。引自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