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閨蜜國慶來香港玩
大學好友曉茜在國慶假期來香港找我玩。
香港的情況,讓我們不可避免地聊到政治,儘管我們從前在一起的大多時光只是逛街聊共同朋友、工作和少女心事。
上次曉茜來香港還是7月份,那時我們一起去梅窩,在中環遇到有人遊行,曉茜說她挺支持的,覺得香港人這種為自由而戰的精神值得肯定。
就像我的其他幾個大陸朋友一樣,在逃犯條例剛引發一系列抗議的六七月,他們聽我講為什麼香港人不支持這個條例,對香港表示理解。
但當時間來到10月,當事件一步步發酵,我發現,當時在北京聽我講逃犯條例是什麼、問候我在香港注意安全、不要管微博上那些網絡暴力的友人,開始在微博上發國旗、自發表達自己作為中國人的自豪。
曉茜這次來,也展現了跟上次不同,或者說,是更全面的一些看法。一天晚上,她同我說,我不支持中國自由開放,中國這麼多人。
“畢竟,民智未開,” 她說。
接下來我們並未就中國是否要走上一條自由道路進行更多探討,也許因為我心裡,也充滿了困惑。
但我們有個一致的認知是,香港需要保留它的特色,不能變成中國普普通通的一個城市。
雖然我倆達成的這種一致裡,暗藏著許多其他的不同。這隨時能體現在——對運動中示威者口號的感受、對同一部紀錄片不同的反應。
示威口號
那是蒙面法推行的前一個晚上,我跟曉茜走在香港街頭, 太子站旁全都貼滿了各式各樣的海報。曉茜說她覺得爭取自由沒有錯,但是不喜歡“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句口號。
後來,我看到《端傳媒》一篇採訪港漂的文章中,引用的圖表也顯示,被採訪的港漂生,最不讚成的運動口號便是這句: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大概有種想回到殖民時代的意味吧。
後來,曉茜又同我說,其實所有口號里,她最最不能接受的是“十一 國殤日”這句。我問,這不算口號吧,為什麼你最反感這句?
曉茜說,作為一個中國人,國家是個很神聖的概念,國慶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卻被說成國殤,這就像你否定了自己的根一樣。
雖然我不認為“國殤日”有什麼問題,但我很快能理解她為什麼覺得有問題。
紀錄片
有天晚上,我又拉著她一起看我之前看過一遍的香港電台紀錄片《我的家國情》。
紀錄片裡的三個人物有三種不同的家國態度。第一個出場的男士,是典型的愛國代表,國慶日號召大家一起唱國歌,認為國家如今這麼強大,年輕人真不懂事。
第二個出場的阿婆講普通話,她說:“香港和深圳隔了一條深圳河,一個羅湖橋,在橋那邊,什麼人都可以罵,但不能罵政府。在深圳河羅湖橋這邊的話,你什麼人都可以罵,但是不能罵老婆。”
我注意到,曉茜在看到這句話時,輕笑了一下,好像不是非常認同。
紀錄片里有首歌,是阿婆用電腦放著《要嫁就嫁習大大這樣的人》,曉茜說,我們大陸哪有人會天天聽這個歌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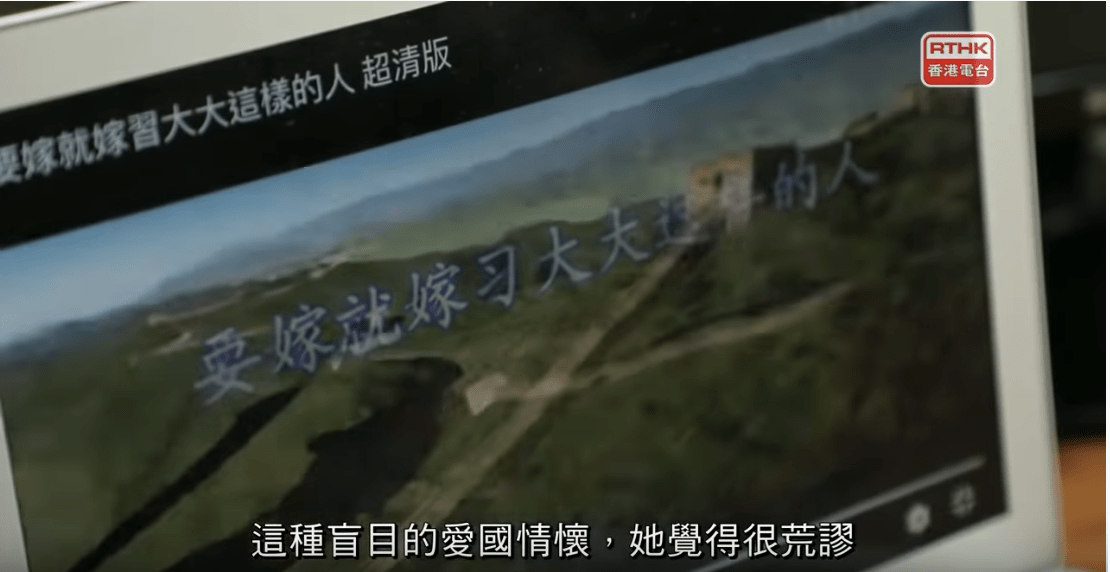
其實我自己看時,倒是很讚同、共情這位阿婆說,看到大家都在崇拜習主席,都在說國家多麼多麼好,“看到覺得很惡心、很肉麻。”
我和曉茜說,“對,你不覺得‘肉麻’這個詞用得非常恰當嗎?!”
快結尾處,阿婆說“個人的價值,自由的價值,是高於國家民族的價值。”
自己看時,我對這句話覺得理所當然,沒想到這次跟曉茜看,她卻提出了不一樣的看法。
她說:“啊,這不就是資本主義的說法嗎?但是我們從小學的都是,國家利益、民族利益大於個人利益啊。”
是嗎?我問。
對啊。她回。都是先有國再有家。
我回憶著,發現她說的沒錯,我學過的。大概是政治書上哪一頁,說國家利益大於個人利益。我說,對哦,是這樣學的,學的時候也沒有覺得不對。
小時候看電視劇,講家國大義,我也感動得不行。還記得那句話: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然後我在想我的轉變是什麼時候發生的呢?
我現在對國家這個詞所有的情感,似乎越來越淡薄。
我和曉茜的區別之一大概就在於這裡。我們都不認可對党、對某個人的個人崇拜,能分得清党和國的不同。但是在曉茜心中,國家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民族是天經地義值得捍衛的,而我近幾年,深受“國家是個偽概念”的這種態度影響。
為了更好表達我的態度和意思,我在房間裡,給曉茜念了那句阿倫特的話:我這一生中從來沒有愛過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集體——不愛德意志,不愛法蘭西,不愛美利堅,不愛工人階級,不愛這一切。我只愛我的朋友,我所知道,所信仰的唯一一種愛,就是愛人。
我的好朋友,她也覺得這段話寫得好、很動聽。
但依然對民族是想象出來的這個論點有所質疑,我跟她說起那本書《想像的共同體》,然後發現自己其實並沒有能力,去概括這本書是如何論證這一命題。我覺得挫敗。
我只能跟她描述,我自己一個關於肉麻的感受。
研究生時,上國際關係課,老師放了一個朝鮮人民送別金正恩的視頻,裡面有人追著他哭,甚至掉到河裡,我們外面的人看來覺得荒誕,但身在其中的人,感動其中。某種程度上那種感動,不就很像今日之我國嗎?《我和我的祖國》。
我找出當時為《想象的共同體》寫的讀書筆記,看到潔平在回復讀書筆記的郵件裡寫的,“對,要警惕自己為了創造物而生的“熱淚盈眶”。
在我跟曉茜表達我的看法和態度時,為了顯得不那麼偏激和對立,我也補充到,那本書里,作者也認可民族與愛國主義的高貴、可敬與合理,認為這是一種與歷史文化變遷相關,根植於人類深層意識的心裡建構,就是有敬重也有警惕。
星期六,曉茜離開香港了,在微信上跟我說,她在朋友圈發了幾張香港照片,但什麼也沒有說,因為不知道說什麼。底下很多人留言,全都是讓注意安全,都是之前跟男友一樣的感覺和語氣。(她在我家時,跟男友因為香港這個事情吵架。之前,我還跟曉茜默默吐槽,發現好像大陸的男性朋友在這件事上都體現出更強的民族主義,比女性友人更加不open-minded。)
對那條朋友圈大家的反應,曉茜說,其實他們也是對香港有非常非常深的偏見。
然後她問我,你會覺得痛苦嗎?

我起初沒懂她的意思,後來反應過來,她這幾天在香港,一直看01上關於香港的新聞,聽我拉著她講這些事情。但當她回到內地,她依然還是那個整天忙著工作和只關心個人生活充實的自己了,討論社會多麼不接地氣,沒有這個氛圍。
只想著自己的生活,自然比牽掛太多,思考太多要容易快樂,不容易有無力感。
我沒有感到痛苦,但是我也早就發現,在大陸,好像大家(我們的同齡人)也都覺得過得可以很開心很充實啊,並不覺得自己缺了什麼。社會主義國度的精緻咖啡廳裡,人們說項目談融資聊創業,追求私利也是追求努力活出自己心中理想生活。
誠然,都體會過後,比較而言,我由衷更愛香港理想主義,有公共生活和自由討論的那一面。
但,我真的不能接受另一種嗎?
去深圳投入到互聯網公司努力工作賺錢有好吃的食物和各種休閒活動不Okay吗?
這也許也是我跟香港朋友不同的一點,我多麼理解他們要爭取的, 理解他們害怕失去的,但是我卻也覺得,另一面也不是那麼恐怖的。
就像老郝的香港同事跟她說:“你們是無法感同深受的。”
老郝跟我說:“對,畢竟,我們是有路可退的。”
那邊是大陸的愛國青年,這邊是奮勇抗爭的香港青年,中間是來香港幾天有些許改變的曉茜,以及,有路可退的我。
PS:
晓茜回去後,在微信上給我轉發了兩篇關於香港的文章,一篇是港大劉榮寧的<<直到今天我們仍然無法了解香港困境的真相>>。早前我就看過。當時想著,難怪這個可以發在微信上。
她說: “昨天我看到之後就覺得這居然沒被刪,就把文章複製了下來。”
我說:這個也給刪啦???!
PPS:
我跟曉茜說,我在寫文章,回憶我倆說過的話,但是微信、微博、連豆瓣都發不了哈哈。
她:So I speak English when I talk some sensitive topics
我:English can be censored, too, maybe 阿拉伯語 okay
她:Can they understand English?They are more educated beyond my imagination.
我:don't look down upon them...they are watching you.
她:Oh, my god I am so sorry.
反應過來她在給big brother的下手道歉呢,hhhhhh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