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共和国总统与极右派“暗通款曲”
作者按:本文首发于“腾讯·大家”专栏,题为《马克龙,欧洲复杂光谱中的变色龙》,发表时有删节。本文为完整版,划线处为被删节部分,下划线处为matters版本增加部分。
想象一下,当特朗普出访归来,与他眼中“FAKE NEWS”头号大敌《纽约时报》的主编在“空军一号”专机上进行了长谈,并且在报纸上发表十余个版面的专访;又或者,如果当年希拉里如愿当选后,接受了布拉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的采访,与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谈笑风生......外人除了瞠目结舌,还会有其他什么反应?
在政治极化加剧的美国,哪怕当事人心里曾经闪过一丝这种念头,恐怕也形格势禁,无法付诸实施。然而这种戏剧化情节,却发生在了大西洋彼岸的法国。
2017年大选中击败极右派“国民阵线”(后更名为“国民联盟”)的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马克宏),胜选之后多次疾呼警惕民粹主义,近期却出乎意料地接受了一家“极右派杂志”的采访。在这篇10月31日出街、长达14页的访谈中,他回应了移民、世俗化、穆斯林头巾等一系列当下法国社会的敏感问题。
这一波“神操作”,让政坛内外许多人大跌眼镜。如果仅以立场划线,难免会让人产生“浓眉大眼的马克龙也叛变革命了”的唏嘘和愤慨。不过细读这篇访谈,正如杂志封面上马克龙难以捉摸的神情一样,让人联想到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的狡黠。相比之下,携150亿美元经贸大单归来,只不过是锦上添花,远没有政治暗战来得有趣。

《当代价值观》:哪一种“当代”?
如果说,当年因遭受恐袭而名噪全球的《查理周刊》是法国激进左翼的象征,那么《当代价值观》可以说是当下法国右翼思潮的一面旗帜。
这份创刊于1966年的杂志,前身是一本财经周刊,创刊之初也沿袭衣钵,定位于财经报道,因此有趣的是,刊名valeurs actuelles意为“(资产)实际价值”。但在其后几十年时间里,这份周刊逐渐演变为综合性时政刊物,而且跻身法国五大全国性周刊之一(其他四家分别为《观点》《新观察家》《快报》和《玛丽安娜》)。而这个刊名,也就在不经意间改变了它最初的意涵,尤其翻译成中文更是如此。
与刊名中使用的复数形式Valeurs相反,《当代价值观》并无意弘扬当代“各种”价值观,从创刊之初,它便明确持经济自由派和社会保守派立场;而从2012年以来,随着Yves de Kerdrel出任总编辑主掌杂志,更呈现出从中右向极右“激进化”的趋势。这一转向引发了内部分裂,并导致编辑部五分之一的成员离职,但杂志的发行量却一度节节攀升,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转向”的成功。
《当代价值观》倾向于所谓“墙外”右派,既不同于中右派共和党,也不同于极右派国民联盟。编辑方针转向的操盘手Kerdrel曾经描述称,这份杂志的标准读者形象,是一个“来自乡村地区、自由职业的中产阶级法国人,他对外省事务非常关注,反对政治正确和巴黎中心主义”。从这个形象不难发现,它和此前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菲永(Francois Fillon)打造的“外省保守派”形象其实非常一致,亦即共和党这个中右党派中最偏保守一翼的“硬核”右派。
但是2017年菲永因为丑闻而元气大伤并最终败选,另一位立场相近的右翼大佬、前总统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号召力日薄西山,右翼阵营中缺乏强有力的重量级人物能够凝聚起这一块基本盘,而《当代价值观》和极右翼的界限也就日益模糊。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当代价值观》近年来的激进化,却也不负其“当代”之名,因为它的确抓住了现时代的一个主旋律——极右思潮兴起、身份政治强化、民粹主义甚嚣尘上。在经济危机和移民危机的轮番打击下,2010年代的法国民意原本就已经整体右倾,而2012年来自左派社会党的奥朗德击败萨科齐当选总统,在“一拉一推”的共同作用力之下,《当代价值观》看到民意流变的走向,走上了向右的激进化之路,也算是“当代”的一个鲜活注脚。
马克龙究竟说了什么?

在马克龙接受《当代价值观》采访之后,许多法国媒体不约而同地引用了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名言——“媒介即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这句言简意赅的论断可以有多种理解,但放在这一语境中,含义不难解读:马克龙愿意接受一份极右杂志采访,并且把他的言论变成铅字印在这份杂志上,这本身就是一种重要讯息,甚至比他具体说了什么更加重要。
怎样的重要讯息?外界(尤其是左派)普遍认为,马克龙此举是“右倾”的明显例证,虽然总统任期“下半场”刚刚开始,距离2022年大选还有两年半,但马克龙已经开始隐隐进入选战状态,而向极右选民喊话笼络人心,蚕食“国民联盟”的潜在票仓,则是这波“神操作”的战略目的。同时也显示出,鉴于传统左右两大政党的颓势,在马克龙眼中,下次大选很可能仍像2017年一样的格局,即由他出马对决“国民联盟”。
但平心而论,马克龙在《当代价值观》上的访谈,其实并没有太明显的逢迎示好色彩。在一些敏感问题上,表态不乏锋芒,甚至有“踢场子”的架势。
例如,法国多年来的一个敏感话题是所谓“族群割据”(communautarisme),即少数族裔采取防御性、封闭性的姿态“抱团取暖”,拒绝融入社会主流,尤其拒绝承认自由平等、政教分离、男女平权的价值观,其中穆斯林群体受诟病最多(其实华裔群体同样不能幸免),这也是包括《当代价值观》杂志在内的右翼声音最着力攻击的标签,但马克龙对此明确表态称,他“会竭尽全力对抗‘族群割据’现象”,但不希望掉进“族群割据=伊斯兰教”的陷阱里。
针对近期的热点问题——穆斯林头巾,马克龙也有自己的思路。此前一位穆斯林母亲戴着头巾,陪同学生(包括其子在内)进行校外教学活动,参观勃艮第-弗朗什-孔泰大区议会,结果遭到一位极右议员的当场责难,后者要求这位母亲要么摘掉头巾、要么离开议会。现场视频传到网上后,引发全法国的一场大论战。政界不少人要求马克龙作为总统就此表态,但他一直避而不谈,在这篇访谈中才终于正面回应。
马克龙对极右议员的责难颇不以为然,认为后者是在“羞辱”这位母亲。“我(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戴着头巾、陪同自己孩子去参加校外教学活动的母亲......起码这一点还在:她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公立学校,还陪着他参加校外活动。”“他的母亲戴着头巾,这并没有妨碍到任何人,我们不能对她说‘你不受欢迎’,这样做是一个巨大错误。”
马克龙的基本思路,是将“头巾之争”放在“教育”这个更大框架下来审视。从这一点上说,他颇有19世纪后半叶法国第三共和时期政治家儒勒·费理(Jules Ferry)的格局。这位因为中法战争而下台的总理,固然是一个殖民主义者,却因为奠定世俗化教育的基础、从深层解决政教分离问题而名垂法国史册。而在法国革命史大家傅勒(Francois Furet)眼中,儒勒·费理的功绩影响深远,甚至可以说直到他为止,法国革命才真正尘埃落定。
回到当下,虽然马克龙说“如果她选择(戴头巾),那这就是她的选择”,似乎是一种无原则的多元主义立场,但其实不难发现,他并不认为穆斯林头巾是一种与共和价值观完美兼容的事物,他的思路是,正如当年法国天主教势力最终退场有赖于世俗化的公立学校一样,要解决穆斯林的“族群割据”现象,最终也只能依靠法国的公立教育系统,“共和体制下的学校已经知道如何教化天主教家庭的孩子们,并且让他们进入共和体制”,那么面对伊斯兰教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在他看来,与其在头巾问题上做口舌之争,不如把焦点放在如何确保穆斯林孩子进入公立学校、如何改进世俗化教育上。
因此,面对近期围绕头巾的种种纷争,马克龙颇为不屑地表示:“我们都成了两种祸患——‘族群割据’和国民联盟——的人质,这是本来应该避免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想牵涉其中的缘故。”
同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马克龙做出最为耐人寻味的表态:“当我们谈到头巾时,许多戴头巾的年轻女性是移民二代或三代,她们可不是刚来法国的......这是我们(社会)模式的失败,同时也和伊斯兰自身的危机交织在一起,这种危机导致了非常僵硬的‘政治伊斯兰’形式。”
这段话颇为均衡地把矛头同时指向了法国自身和伊斯兰信仰,而《当代价值观》也颇为买账地将“我们(社会)模式的失败和伊斯兰自身的危机交织在一起”,作为当期杂志的封面引语。但纵观全文,马克龙并没有继续将“伊斯兰危机”作为论述重点,否则杂志的封面引语,恐怕要长得多。
但说回来,在《当代价值观》的主场,马克龙的出击,未必能取得期待中的效果。
一方面,从形式上说,杂志并没有采用Q&A的问答体,而以自身的陈述为框架,将马克龙的言论片段嵌入其中。整个访谈宛如一篇“碎碎念”的长日记,马克龙的观点被严严实实地包裹在执笔人的思维前见和叙述节奏中,很难让读者窥见原原本本的对话语境,也难以确定杂志做了多大尺度的裁剪。
另一方面,在强烈的政治爱憎之下,媒体很容易失去原本该具有的持平立场,而《当代价值观》在这方面的可信度记录并不美好。2014年该刊曾经发表一项“民意调查”结果,为萨科齐的党内选举背书,但这份语焉不详的“民调”引起很多怀疑,在各方追问之下,最后发现所谓“调查”是子虚乌有,完全是为特定候选人造势的文宣产物。
有鉴于此,虽然马克龙大胆出击,试图向右翼选民喊话、从而避免将话语权白白留给“国民联盟”,但在这样一个言论阵地上,他所期待展现的说服力,恐怕多少要打个折扣。
克里孟梭式的总统,与马基雅维利式的君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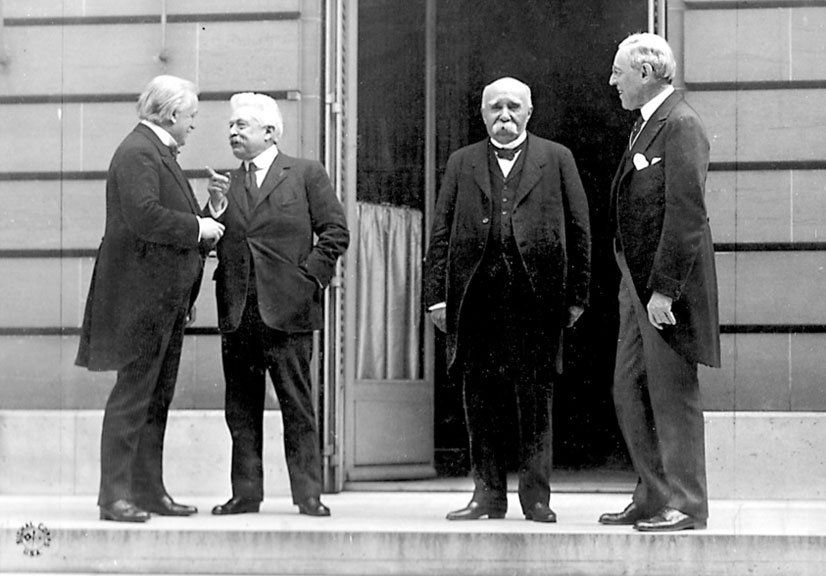
虽然思路和儒勒·费理近似,但马克龙在访谈中也丝毫不掩饰对前者最大的政敌、同时代另一位政治家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的激赏,甚至在访谈中明确声称——“我是一个克里孟梭派!”
“克里孟梭派”意味着什么?对于《当代价值观》来说,这个文化密码传递出的信息恐怕并不那么友好,它意味着激进共和立场、反对教权主义、倡导政教分离、同情巴黎公社,反对殖民主义。尤其具有象征意义的是,正是在克里孟梭创立的《震旦报》上,作家左拉针对德雷福斯事件发出振聋发聩的“我控诉”(J'accuse)。而马克龙自称“克里孟梭派”,隐含着一种与极右派从根本上划清界限的意味。
然而,道不同,未必意味着不相往来——何况克里孟梭也曾经镇压过罢工。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位“克里孟梭派”总统又颇有马基雅维利的手腕。
耐人寻味的是,马克龙的硕士一年级论文正是以马基雅维利为题目——《马基雅维利论历史中的政治事实与代表性》。当然,目前并没有足够充分的证据说明,这位总统深受年轻时求学经历的影响、始终遵循马基雅维利的教导治国,但仅就此次接受极右媒体采访的操作来看,他的确既有狮子的一面,也有狐狸的一面。
马克龙执政之初,被诟病为“朱庇特式的总统”,意即如众神之王一般高居宝座之上,严令政府阁员不得自行其事,由他掌握最终裁决权,正仿佛如马基雅维利所言,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要安全得多。但这种“朱庇特式”的风格反过来刺激了“黄马甲”的兴起,为消除不满情绪,他改变策略,一方面公布经济利好政策、通过提振购买力来“收买”民心,另一方面发起“全国大辩论”,发表“告法国人民书”,脱掉西服、卷起衬衣袖子亲自下场参与了十余场辩论,相对成功地化解了“黄马甲”的冲击。
马克龙此番直接与极右媒体对话,并非无迹可寻。如该杂志所言,马克龙政府中的经济部长、国防部长、公共帐务部长、性别平权国务秘书、政府发言人等一干重要阁员,其实早已或是接收过该刊采访、或是在该刊发表过文章、或是参与或该刊组织的活动,总之事后看来,其实一切早有布局,而马克龙本人直接发声,只是迈出了最后一步。
剥离冠冕堂皇的说辞,马克龙“向右转”的说法或许并不为过,民调专家指出,2017年总统大选中曾经给右派共和党候选人菲永投票的选民中,27%的人在上届欧洲议会选举中转投马克龙的政党;但是,同样比例的原大选中马克龙的支持者,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转投给更加左翼的党派。流失的选民群体,需要填补和巩固。
问题在于,在普选和代议体制下,极右派对手或许可以定性为施密特意义上的政治“敌人”,但他们的选民即便受到蛊惑,却绝不是敌人,而后者手中的选票,也和满怀普世理想的左派是同等权重的,这就决定了马克龙在距离选战尚远之际,不会轻易放弃这一部分选民,而通过各种“介入”手段,来引导这部分选票的流向。
马基雅维利曾将理想的君主形容为,“狮子不能够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吓退豺狼。”由此观之,作为狮子,“朱庇特式总统”一度掉进了自己挖的陷阱,但自己又爬了出来;作为狐狸,他认识到“客场作战”的陷阱,但在精心布局之后,下场踏平了这个陷阱。
对于一个严肃的阅读者来说,马基雅维利远不是坊间所认为的“西方厚黑学”大师。事实上存在两个马基雅维利,一个是《君主论》的,一个是《李维史论》的,二者各自面向不同的历史境遇,表面上的差异各有逻辑可循。最重要的是,深怀对共和体制之爱的《李维史论》作者,同样是一个真实的马基雅维利。正如有着狐狸般狡黠眼神的马克龙,依然是一个“克里孟梭派”一样。
从历史脉络来看,今天法国的左右之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中间派”与“极右派”之争——依稀仍可以看到法国革命之后不同思潮交织缠斗的影子:巴黎与外省、共和与威权、世俗与宗教......马克龙与《当代价值观》,各自占据着相应的光谱,或许可以看作21世纪初语境中的变形化身。
这本杂志在访谈导言结尾处颇为慷慨激昂地写道:“(读者)人人见仁见智,终有一天,历史将会做出裁判。”其情可哀,不过从长时段来看,迄今为止历史的裁判对他们并不友善。而一个具有马基雅维利式头脑的“克里孟梭派”,或许是当下乱世中“保持航向”的一个最不坏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