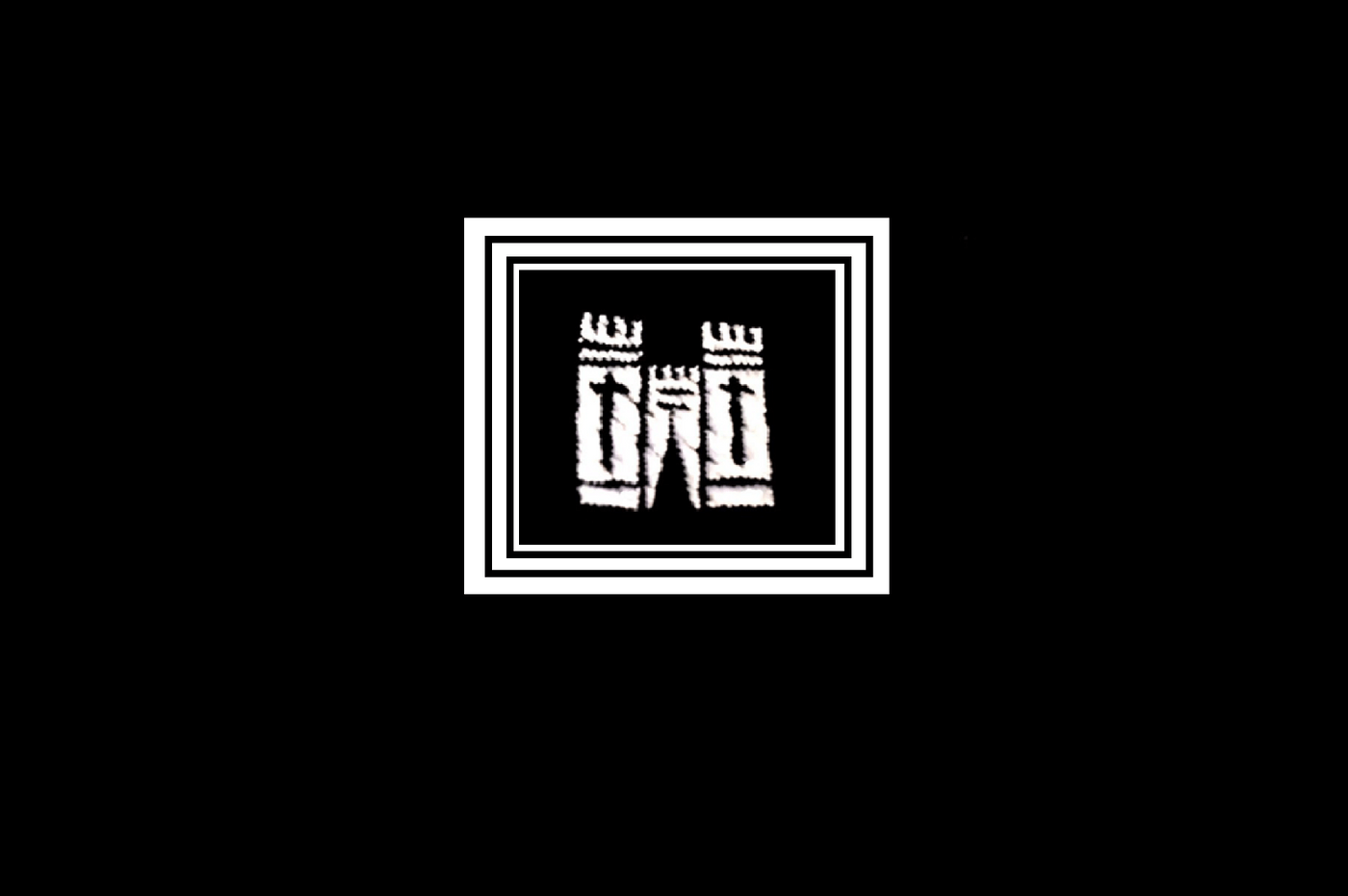谎言的统治及其敌人
两个对立的存在支撑了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力》的论述的核心:真实的生活与谎言的统治。
位于真实的生活之上的,我们常常称之为想象的或者观念的结构,对我们有如幻影般的操纵与控制力。而一旦它们与真实的生活格格不入的事实被揭露,则成为人们心目中巧妙装潢的谎言与幻象。
为大众所传唱的故事常常着眼于英雄的成功与智者的洞见;被其指引的我们也许会将那样理想化的图景代入对于现实的反抗的期待之中。可别以为大家都如开悟者或者老成的魔术师一样,一眼就将包装美妙的世界看穿。绝大多数人不过安心于一个能够存续下去,一个可以自圆其说的处境。实际上,许多人这回睁开眼睛望向操纵皮影戏背后的嘴脸,不是因为他们头一次意识到谎言的存在和真相的稀缺,也不是头一次见识到这东西害人,只不过是发现自己原先认为能和这个“谎言的体系”共存的处境,也是一个如泡沫般一戳即破的幻想而已。
哈维尔对相似情境的论断相当简洁:无论是从语意还是实践的角度,真实的生活都是反击谎言的最佳武器。但是我们仍不禁会问,在当下的环境下仍然如此吗?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把握真实来赢得这场战争吗?
首先构成当下我们面对的谎言的结构,虽然各方面有所进步,但是基本的元素仍然是这些:
一个审查制度,比以往的所有的权力的触角伸的都远。不仅牢牢把控了传统的舆论场,还将新技术产生的讨论空间“应收尽收”。
一个被神话的政治体,无比坚定的相信自己是真理的代言人。这有一套“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支撑,也有诸多话语(也即意识型态)的包裹。
(关于意识型态:简短地说,意识型态是任何掩盖社会真实本性的思维结构,我们面对政治的意识型态则近似于一种宗教。)
一个官僚主义的笼子,将一切的社会内容都分装成各级别的机关带着自己的利益考量执行的任务。
在官僚,意识型态与审查之中,人类在物质和信息的洪流中逐步失去本身的属性,沦为繁荣的手段,和机器的对象。的确,人类世界中的利维坦正像游戏中的怪物一样,随着时间越演进血槽越厚,武器越多,心机越深,而向其挑战的难度则是与日俱增。我们不仅发问,仅靠向“真实生活”的回归,仅靠重建人与人自然的联结和醒悟人的存在的基本条件,能够战胜这一切吗?
如果说我们还可以理解支撑谎言统治的不断发展的技术的细节,可以描述其背后运作的权力的结构,可以分析其动机和影响,那么哈维尔所说的真实的生活则更像是一个生活哲学的原型,甚至是一个关于人性的文学性的发挥而得来的根本态度。到底怎样才是真实的生活态度,我们应该怎样做到呢?即使做到了,它真的能如哈维尔所说的那样发挥作用吗?
如此说来,应当再重新审视一下关于“真实的生活”的理解了。
首先当然是在个人的看法内屏蔽掉谎言和意识型态对事情的扭曲。类似“桑事喜办”,将个人为社群的牺牲合理化为国家的奉献,诸如此类宣传,要在心里鄙视唾弃。牢记个人权利为基点的价值判断,比如对公权力提出批评建议永远不是恨国,不是散播“负能量”而是有关怀的公民应有之义。在这些事上,现实情况常常让人陷入自我否定——人们常不自觉地将社会规范置于个人诉求之上,中国人尤其是。如果条件不允许彰显于外部,那么在内里我们也至少坚定地相信自己的良心,不放弃自己的权利,不甘心被高高在上的话语篡改或埋没。
见到有人批判当下资本对人的压榨,使得人们在政治压迫天平的另一段仍然没有出路(见“市场-国家对立”的那篇文章,philosophia哲学社)。这只是问题的一端。40年来至少中国人越来越有个体意识,越来越不肯容许轻易地被集体性所代表,这和市场化,和在理想上资本增长所尊重的自由空间是分不开的。
在悬置扭曲人心的力量基础上,我们将重头反思人的价值和道德的涵义。宏大的价值不值得信任,那么我们就从最基本的意义开始发现我们自身:认真的看待自己的追求和价值,为自己做决定,为自己做的决定付诸努力。将外部的境遇视作自己能够利用,在之上逐渐搭建起自己存在价值的砖石。
随后,抛弃意识型态的灌输而以朴素的同理心去对待他人的遭遇。“灾难并不是死了两万人这样一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人类本能的善意可以让我们敏感地看到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诸多不公,尤其是发生在弱者,贫穷者和不幸者身上的事。在他们身上,真实的生活的力量充满了毁灭性,而响亮积极的口号从来无法将其掩盖过去。我们看到这些,如果无条件施以援手,则至少不能忘记。试图理解为什么世界是这样子,人为什么有苦难的这类问题,还是会无可避免地引入(都是由主观的一个个人提出和发展的)总体解释和概括性的理论。需要警醒,这些可能是意识型态的帮凶甚至是其本身。我们应当总是听取对人的个体遭遇和权利的侵占最敏感的那些理论和看法,以让自己不致疏忽大意失去了道德感。同时,这也有助于我们总是听到被压迫者的呼声。
有时候我们看似会陷入矛盾,而有些人会以相对主义的立场对我们加以攻击。诸如“中国的制度还是米国的制度?”,指出每一个制度都有缺陷和疏漏之后,他们会满意的说,所有政治全都是不可信的;他们还会说所有的理论全都在支撑背后某些集团的利益,所有的人都带有主观立场,所有呈现出的信息都是不可信的。道德相对主义是一种群体的癌症,而长期有毒的社会文化无疑加重了我们的病症。对于它,我们要明白,事事完美当然不存在于现实之中,可是人们对于善和良知的追求是真实的,人的感想和道德判断是真实的。所以我们不能接受人类道德的相对化,现实世界的残缺不是我们丧失道德感的原因。
也许我们应该记住加缪的批评:“如果人们什么也不相信,如果什么都没有意义,如果没有价值可以被确认,那么一切都是被允许的,一切都变得不重要。因此,不存在善,也不存在恶。希特勒既没错,也不是对的。有的人把几百万无辜的人扔进焚烧炉,有的人则全力拯救麻风病人;有的人撕裂他人的一只耳朵,却对着另一只说出安慰的话。有的人能在刚被折磨完的人面前,把房间收拾干净。有的人向死者致敬,有的人则把他们扔进垃圾桶。这些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认为一切都没有意义,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胜者即正义。”
最终我们追求的是在原初的善意和同理心之上的人们的互相沟通和对彼此尊严的尊重。要想在拒绝意识型态叙事的同时远离孤独,我们必须让怀着原初善意的人们以某种方式聚到一起,彼此沟通启发。要构建一种沟通的机制,使得任何人都无法以地位或者权力宣判某一个想法死刑,或者神话另一种看法。唯有在诚实和相互尊重的沟通中,基于良知的共识才得以彰显。
正是基于这样的愿景,哈维尔才倡导建立一个平行于官方机构的文化圈来向社会施加持续的影响。“决定在真理中生活的人们无法直接影响现存的社会结构,更不用说参加到这个结构之内,他们就开始创造我所说的‘社会独立生活’,而这个社会独立生活就开始以某种方式自行产生自己的结构。”
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哈维尔提出的解决方式面对的监督技术进化的无能为力。
虽然面对审查的压力,捷克的“第二文化”的地下活动确实一直延续发展着,直至那段历史的终结。而今天我们发现,凭借无孔不入的技术,官方的触角伸入到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只有零星的组织能够提供一个平行不受干扰的空间;而这些组织常常陷入困境,稍不注意就被“销号”或者“关停”。审查淡化了一波一波决心反抗或者建构平行文化的人的影响——他们甚至被精心地冠以恶名,被“第一文化”的信众唾骂。(我在周中发的那一句便是赠给这些人:“不管梅科姆人知不知道,我们对他的敬意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能得到的最崇高的敬意。我们坚信他是在伸张正义。事情就这么简单。”)在技术干扰和打压之下,平行文化很难维持一个稳定的网络,更遑论去稳定地向社会辐射其影响力。
与技术监督打压同时进行的,是官方对各种民间文化的收编。最近“阿中哥哥”和“江山娇”引起的争议即是其中的一个细节——官方对于年轻人二次元文化的收编和利用。引起捷克“七七运动”的正是地下乐队的反叛文化,而我们可以留心到中国的乐队受到官方的影响,无法将审查失败的作品流通入公众(至少无法同一心颂唱安全内容的歌曲相竞争)。即使有独立反叛精神的乐队在媒体上的曝光,歌词却是遭到和谐的(最近的例子是《乐队的夏天》)。实际上,官方的价值一直力图打入现代生活的每一个鲜活的场景之中,而不仅仅似哈维尔描述的那样存在于标语和官僚机构的统治之中。面对这先进的统治战略,先贤的构想似已成为了古董。
伸入各个文化角落的谎言瓦解了平行阵线的形成,却也敦促人们开发出不同的应对策略。定向的解构就如同端着匕首在小巷里和敌人短兵相接的平民勇士,拼着老命也要拉着有毒的意识型态垫背。今天我们用江山娇,你能做到吗?和如果你不喜欢猪就去自己当一头惹人爱的好猪等话语完成这种解构的攻击——如果我们的文化阵地不能安生,那么他们的宣传渠道也永远别想。
在这种情况下,无怪乎我们不能要求人们的信仰超出真实的生活的范畴。“这不仅仅是因为对公共事务的普遍麻木不仁和“更高责任感”的丧失。这不只是普遍的非道德化的结果,在这种态度里,还有一些健康的社会本能在起作用。 ……生活的目标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起码能和谐地活着,以可以忍受的方式活下去,不受官员和上司的侮辱,不受警察的日夜监视,自由地表达自己,为创造力寻找发挥的途径,享受法律保障的安全,等等。跟这个有关的一切具体事件,跟这个基本的、无处不在的对抗相关的一切,都必然引起人民的关注。关于理想的政治经济秩序的抽象计划不能使他们感兴趣。这不仅是因为人们知道它们成功的可能甚微,也因为人民觉得政治色彩较淡些的政策出于具体、此时此地的考虑。如果他们把眼光盯住抽象的未来,就更容易陷入新的奴役人性的罗网。”(哈维尔)
“我们这一代人面对着如此巨大的难题,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确信。其实,我们应从这种否定中获取战斗的力量。有人对我们说,你们应该信仰上帝、信仰柏拉图、信仰马克思,可这是徒劳的,我们并没有信仰。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是否接受这样一个世界:要么成为受害者,要么成为加害者。但我们两者都不接受。因为在心灵深处,我们了解这种区别本身就是虚设。最终只有受害者,因为杀害与被杀害,结局都是一样的。杀人者和被杀者,都会承受同样的失败之痛。”(加缪)这是人类的失败,是我们作为共同体的沦丧,但却是谎言统治的胜利。
或许无论谎言凭借怎样先进的战略和技术,它总无法在对真实的战争中收获全胜。因为生活的真实性永远存活在每个具体的个人的心中,它无法像被杀灭害虫一般就那样被消灭。可是,它也是我们仅存的阵地,我们不得不将所有的能量都倾注其中,才能勉强抵御自身的道德修养不受谎言的侵蚀。
我们只能这样得出结论:真实的生活并不是反击谎言的最佳武器,而是仅存的唯一取胜可能。把握了真实绝不代表我们就会取得胜利——只有幸运儿才能侥幸品尝到如此意义非凡的胜利——但是我们宁愿选择当高昂着头颅的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