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疫情暴发一窥否弃事实背后的心理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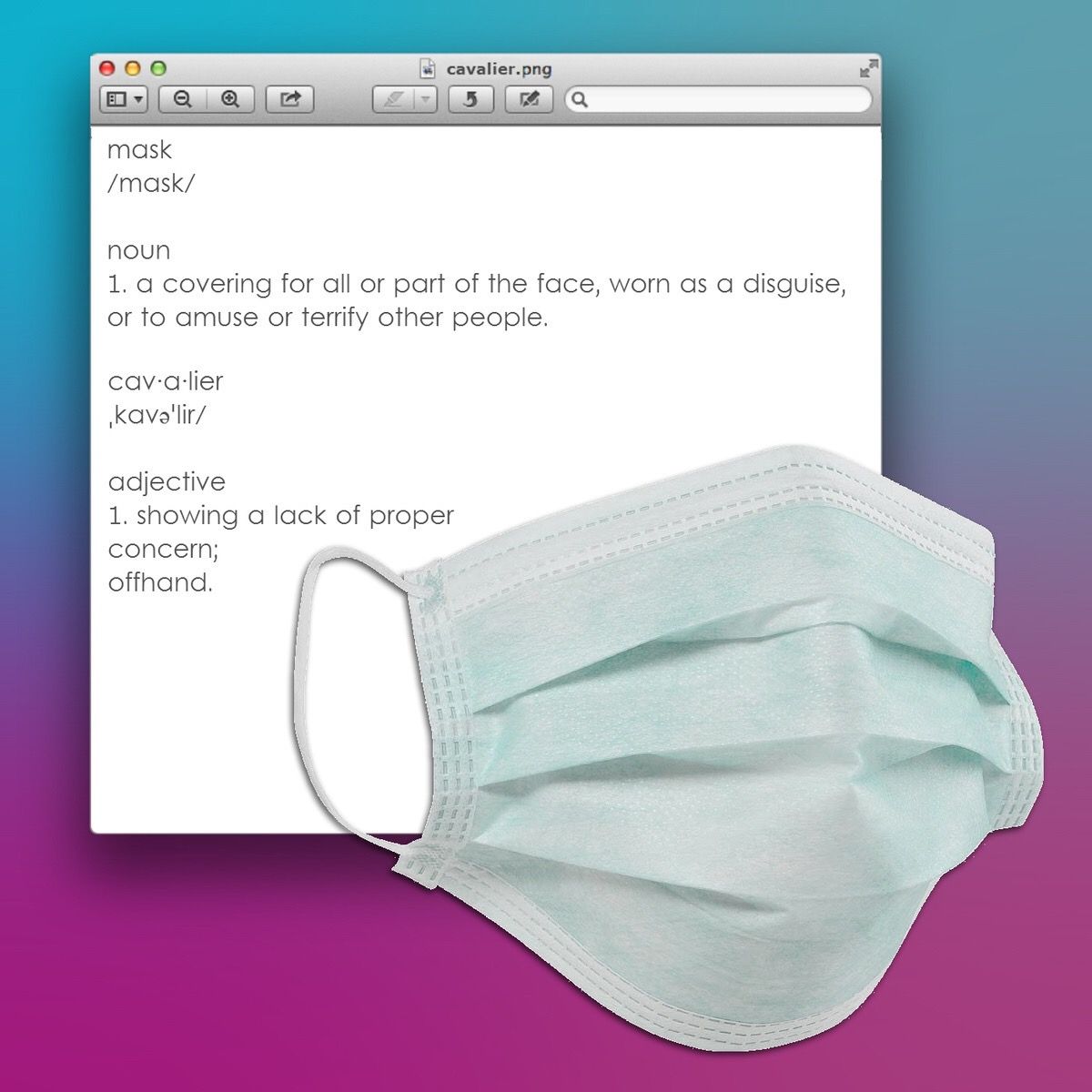
近期阅读部分文章兼观察网路言论有感,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写下本文。
首先开宗明义,我认为将对疫情的处理与国家体制的优劣挂钩是一种泛政治化的二元思维方式,某种程度上甚至到了反科学的地步。我不是说不能从政治学角度入手,这当然属于一种有意义的视角,但将单纯的流行病学措施强行上升至体制之争就有政党政治之嫌了。
与此同时,某些网友(其中有些是在特定议题上与我观点相近的盟友)拒绝承认中国在控制疫情扩散方面的某些表现值得肯定,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欧美国家未能在前期足够重视与警惕以致疫情可控性暴发这一事实也令人遗憾。为了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心理,我斗胆从下面三个角度试做分析。

逻辑谬误
不得不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有人不愿接受真相?在我看来,关键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认为接受真相不仅意味着接受“真相”,还意味着接受“真相背后的一切”,比如发现并确证真相的群体,比如可能通过真相获利的群体,比如这些群体支持的价值观。到这里,真相在他们眼中早已不仅是独立存在的客观叙事,而是掺杂各方利益争夺的主观陷阱。
代入进本次事件,坚决不认可中国抗疫成果的人并非不认可这一结论,而是不认可结论之外暗示的东西。他们在潜意识中将赞扬中国抗疫有效与赞扬中国政治体制简单粗暴却毫无关联地划上了等号,由于他们绝不想赞扬中国政治体制,于是只好也拒不赞扬中国抗疫有效。
可以看到,这种思维方式是因果谬误(casual fallacy)与滑坡谬误(slippery slope)的结合。关于各种逻辑谬误的整理与举例,友人@雲五 已经写过一篇比较完备的文章,请参见关联文章。
事实上,当然存在赞扬中国抗疫有效且批评中国政治体制的空间,因为这二者本就没有被绑定在一起。陷入两难境地的网友们醒一醒,不要画地为牢,用虚无的网把自己困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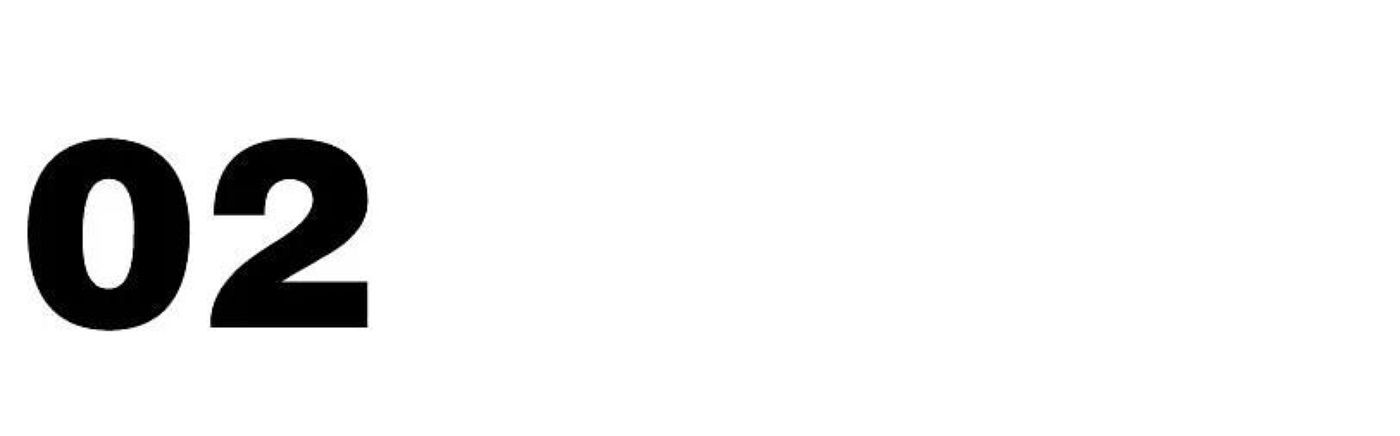
认知失调
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是美国心理学家Leon Festinger在1957年于《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一书中系统阐述的理论,经过多次实验证明后成为了社会心理学界非常重要的奠基理论。
LF首先假定每个人都希望寻求心理认知稳定的状态,而当我们心中存在两种互相冲突的信仰、理念或价值观时,精神状态便会出现不适感,即所谓的认知失调。这时我们就会想方设法寻求消除这种不适感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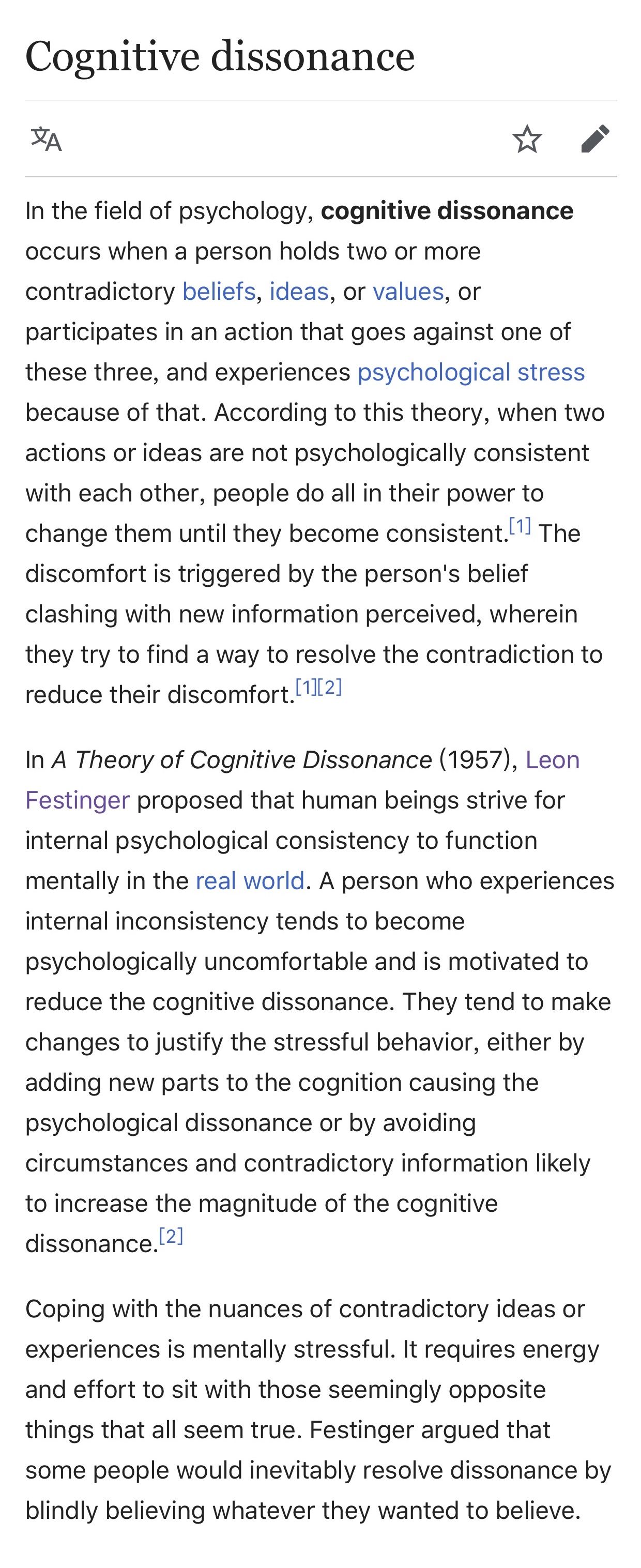
不幸的是,正如Edward Craig在《Philosoph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中所言,“一旦我们同时考虑一个以上的基本价值观,我们必定会发现这些价值观有时会互相冲突。”
举个例子,1956年,LF在《When Prophecy Fails》中首次提出了“认知失调”的概念。当时他观察到UFO末日教派的成员在“地球毁灭”的预言落空后,为了缓解认知失调带来的不适感而形成了新的结论——外星人因为他们饶恕了地球。
代入进本次事件,在已经将对疫情的处理与国家体制的优劣挂钩的人心中,他们得到的信息是部分欧美国家的抗疫不力与中国的抗疫有效(认知),但他们内心又强烈认同欧美国家的体制与价值观(行为),于是认知与行为相冲突的失调状态就出现了(未将二者挂钩的人则不会产生认知失调)。
此时为了恢复认知协调,他们有以下选择:
● 不再认同欧美国家的体制与价值观
● 意识到两者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 坚持否定中国的抗疫成果并试图找出欧美国家抗疫中的闪光点
鉴于第一项需要个体付出高昂的改变成本并面临信仰崩塌的风险,因此出于自我防御机制,个体往往倾向于选择后两者。
总结一下,为了解决认知失调所带来的不适感,个体的选项包括:
● 改变自己的行为(不再认同欧美国家的体制与价值观)
● 对自己的行为增加一项认知,从而改变它的定义(意识到两者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 改变对行为结果的认知(坚持否定中国的抗疫成果并试图找出欧美国家抗疫中的闪光点)
● 直接忽略有冲突的存在(沉默)
其中,“改变对行为结果的认知”也是本文想要探讨的重点。我们借助LF和Merrill Carlsmith在1959年进行的经典实验来进一步理解。
在这次围绕“诱导性服从”展开的实验中,学生们被要求进行繁琐且无意义的工作,包括把书翻转四分之一圈,或者在盘子里放满汤匙,然后清空盘子,再次放满汤匙,不断循环往复。其中一组实验对象拿到了20美元报酬,另一组拿到了1美元,而对照组则没有任何报酬。
当之后被要求评价该项工作时,1美元组的实验对象比起20美元组和对照组的评价显得更加正面。这被LF和MC解释为认知失调的证明。

对照组浪费时间白白做了件无聊的事,无聊和无报酬都是负面印象,并不造成冲突,所以他们不会认为有必要将实验想得很有趣。
20美元组的行为则有着外在正当的理由,因为收到了足够的报酬,这笔钱已经足够解决无聊带来的心理落差,即“虽然很无聊,但我至少赚了一笔钱”,所以也不存在认知失调。
1美元组的实验对象却被迫内在化自己被诱导表现而产生的态度,因为他们没有其他正当理由。他们收到了一点钱,但钱的数目并未大到可以抵消无聊感,所以他们只能自行调整认知,把整件事解释为“拿了1美元还做了这么有趣的事,很值得”。他们通过把无聊扭转成有趣来诠释自己的行为,平复内心认知失调带来的不适感。
显然,当个体处于社会场合中时,其观点被与自尊联结在了一起,这点我在此前的两篇文章中也有提及。为什么辩论很少出现说服对方的情况?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辩论从来不是单纯的观点交锋,更是自尊的对垒,极少有人愿意主动交出自尊。因此,比起向另一个体“支付自尊”,我们往往倾向于“捍卫自尊”,无论观点(自尊的部分体现)孰对孰错。
不过,认知失调也并非全然坏事,如果使用得当亦能出奇制胜,黑人民权运动就是一个很值得借鉴的例子。在当时,认知失调理论支持黑白同校,认为给人们带去一些认知上的冲突有助于击碎偏见。比如曾经“黑人野蛮粗鲁”的认知很难改变,但在黑白同校后,第二种认知“黑人是我友善的同班同学”出现了,两种同时出现的认知产生冲突,人们就会为了平复失调主动改变认知。
事实证明该理论是正确的,黑白同校的学校中的白人学生成绩不但没有下降,甚至还有所提升,而且普遍共感力偏高,偏见值偏低。种族主义者认为的“黑白同校会引发种族冲突”也并未发生。由此更印证了一句话,你无法改变他人的观点,是他人自己改变观点。

给敌人提供弹药
George Orwell在1945年11月写过一篇题为《穿过玻璃的玫瑰色》的散文。当时红军刚刚“解放”大部分被纳粹占据的欧洲土地,在不少圈子里,任何对解放者的批评都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GO当时供职于社会主义报纸《Tribune》,但该报的维也纳通讯员却执意要提起苏联军队对这座城市的蹂躏和掠夺,于是GO 评论道:
最近我们的维也纳通讯员的报道惹来了一串愤怒的读者信,除了骂他是傻瓜和骗子,和其他一些可以说是例行公事般的控诉,还隐含了一层非常严肃的意思,暗示他即使知道自己要说的都是事实,也该闭口不言。
一旦A与B为敌,那么只要攻击或批评A,往往就被认为是在助长或怂恿B。客观上来说,如果眼光不放长远,的确B的工作常常因此简单了。于是,A的支持者会说,闭嘴,不准批评,或者只能“建设性”地批评,后者买践起来则难免似贬实褒。这种论调再往前挪一小步,就会让掩盖和歪曲事实变成新闻工作者的最高职责。
那时战争结束不久,GO列举纳粹聪明的宣传手段时就极其生动地展现了这种过程:
在他们传播的内容之中就有E. M. Forster的《A Passage to India》。就我所知,他们甚至还不用篡改文字。正因为这本书本质上是真实的,纳粹的宣传部门就可以借它发挥。William Blake说过:
真相若带着坏心思
所有假话都难企及
一个人要是听到自己的言论在轴心国的广播里反咬自己一口,就知道这两句诗的分量了。的确,为不受欢迎的事业写作,或见证了必然会引发争议的事件,一定会体会到那种让人惧怕的冲动,就是要歪曲或掩盖事实,只因为诚实的表述里多半有一些真相会让无耻的对手利用。但我们应该在意的,是长远的效应。
坦白来说,就个人来讲,我认为这种冲动是最难克服的。如果有人不以为意,我建议大家设想一种最极端的情况,因为个体对某一价值观信仰的程度通常在极端情况下能够得到最残酷的证实。
举个例子,一名记者打算揭露一起政府高官有组织性侵儿童的案件(亦可替换为其他在你心中最不能原谅的罪行)。然而这个时候,同为记者的你发现ta曾经写过几篇有违新闻伦理的报道。假设性侵案确定是真相,曾经的黑历史也确定是真相,而你是唯一同时握有两种真相的人,在明知如果说出该记者曾经的黑历史将会大大削弱甚至彻底推翻性侵定案可能性的情况下,你还会和盘托出全部细节吗?
我不会,我相信大多数人也会默默选择隐瞒后一种真相,或者至少是延迟这一真相的呈现。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不要给敌人提供弹药”是最具诱惑力的劝告和最强烈的动机。大多数人对真相的信仰程度,都不如对立场的信仰程度,这是人之本性,无可厚非。我们也没有必要追求绝对理性,尽可能靠近理性并意识到自己带有倾向就够了。
最后附上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的一篇类似评论文章《为什么东亚对疫情的控制比欧洲有效?》(https://mp.weixin.qq.com/s/8yUrY_4vBorFCYif8lrRSw)作为延伸阅读。
我于2020.3.26写的简评摘录如下:
超级无敌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
尤其是对于发达国家的生活社会与发展中国家的生存社会(the society of survival)间的辨析相当精准——
“生存社会其中全部的生命力量都被用来延长生命。对美好生活的关注让位于对生存的歇斯底里。生存社会也对享受持敌意。健康代表了最高的价值。”
身边即世界地说,大部分我所认识的中国人都持这种观点。我却觉得只要充分地享受过人生的乐趣,在50s甚至40s死去都是可以接受的。简单来讲,当存活已经无法带给我最低限度的幸福时,其对我来说就是无意义的。
另外我也赞同韩的担忧,即病毒会做到恐怖主义都做不到的事——让西方社会最终接受东亚强度和广度的数据监控,让紧急状态(“例外”)成为常态。
确实,宪政民主制度在这次应对中令人失望透顶,然而我们绝非时刻生活在John Locke所描述“战争状态”中,而是更多生活在常态中。集体主义和专制服从天然地在处理紧急事态方面具有经验上的优越性,但这并不代表其本身优于其他制度。归根结底,能够做出整体评判的不是一千个小时中的几秒。
西方社会真正该调整的是久居领先后产生的傲慢与怠惰。重新体验陌生的危机感能够再度激发民众已经丧失大半的创造力、参与性和批评监督意愿,唯一的问题是,这种创造、参与和批评监督能否走上正轨。弱政府的传统使得我对西方政府的引导能力持怀疑态度,靠民众自发若真加深新一轮民粹就是饮鸩止渴自取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