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鲍毓明案谈“性同意年龄”等问题
(注:这是今天草就的短文,在微信公众号一直发送失败,正在不断自我检查敏感词中,也不知最后发不发得成,先在这里备个份吧。)
鲍毓明涉嫌性侵未成年养女案,想必大家都已有耳闻。前两天我就此接受了梨视频的采访,谈了一下中美两国刑法中关于“性同意年龄”等方面的规定(视频链接:http://n.miaopai.com/media/vn2A7fB6tScPh-YaRW5BVq~n7Zhnrwa~)。受短视频节目的时长限制,采访中聊到的大部分内容最终未能呈现,所以我在这里再大致地整理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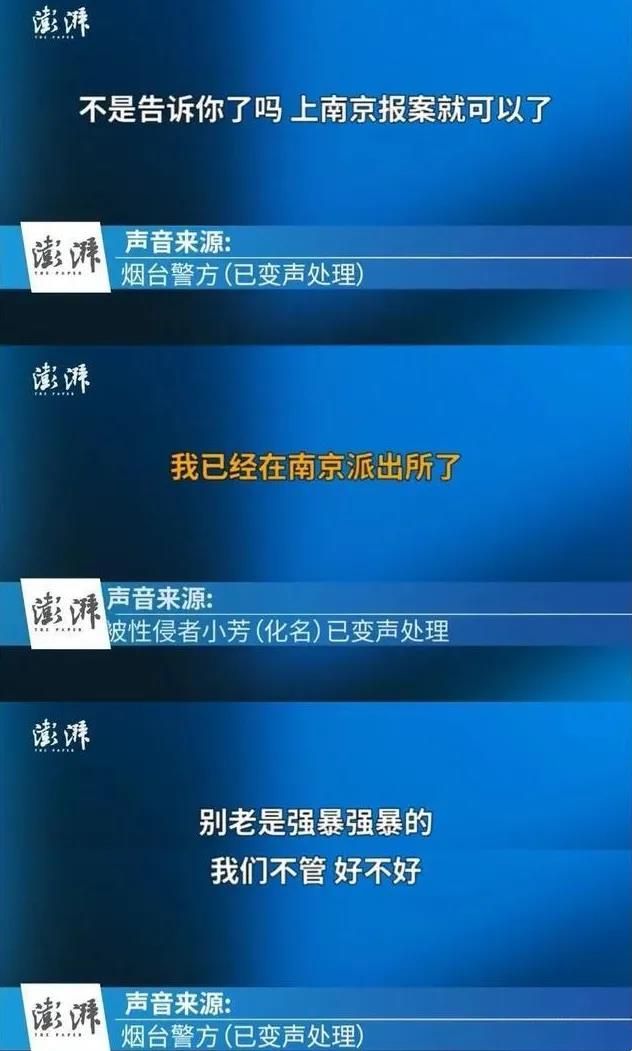
一、“性同意年龄(age of consent)”及“法定强奸(statutory rape)”
所谓“性同意年龄”,即认为年龄太小的人,由于心智与生理等各方面仍在发育过程中,太容易遭到心怀不轨的成年人的诱骗、欺诈、洗脑、威压、胁迫、剥削,因此并不真正具备“同意(consent to)”与别人发生性行为的民事能力;当一个成年人与一个未达到法定的性同意年龄的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时,即便这位未成年人声称自己纯属自愿,该成年人的行为仍然触犯了法律,构成“法定强奸”。
有人可能会觉得,不同人的发育有早有晚,凭什么法律可以一刀切地规定一个性同意年龄?以及,认为未成年人缺乏“同意”的能力,是不是家长制的心态作祟、抹杀了未成年人的自主性?对这些疑惑,我在以往批驳反同人士滑坡论述的文章中(全文下载: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452156)已有剖析,比如法律意义上的“同意”为何不等于日常意义上的“赞成(agreement)”等等,感兴趣的读者可自行翻阅。
此外,结合本案情节的更具体分析,可以参考:看理想,《鲍毓明案所谓“反转”,是社会对性侵案认知的狭隘》。
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刑法中都存在“性同意年龄”的概念,尽管各国(以及某些国家内部的各个行政区域)对这个年龄线具体划在哪里有着不同的规定。
中国目前的(女性)性同意年龄是14周岁(刑法第236条:“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在世界范围内偏低。
根据这个网站(https://worldpopulationreview.com/countries/age-of-consent-by-country/)的汇总,目前全世界只有9个国家的性同意年龄低于14岁(尼日利亚、安哥拉、菲律宾、科摩罗、日本、韩国、尼日尔、西撒哈拉、布基纳法索);其中日本和韩国虽然刑法中的性同意年龄为13岁,但民法或地方法中往往又规定了更高的性同意年龄(从15岁到20岁不等),导致事实上的性同意年龄仍旧高于中国。
此外,尽管世界上有大约30个国家和中国一样把性同意年龄定为14岁,但这些国家往往还有一些更详细的规定,以保护年满14岁但仍未成年的人。比如德国的最低性同意年龄虽然是14岁,但法律同时规定,已满21岁者不得与未满16岁者发生性关系,否则仍然视为“法定强奸”;类似地,意大利的最低性同意年龄尽管也是14岁,但法律同时规定,当双方之间存在实际权威关系(比如父母与子女、寄养人与被寄养人、师生等等)时,性同意年龄上升为16岁。
就美国而言,由于刑法绝大部分属于州法,各州在性同意年龄的规定上略有差异。目前大多数州的性同意年龄是16岁,还有一些是17岁或者18岁(参见美国卫生部的资料汇总:https://aspe.hhs.gov/report/statutory-rape-guide-state-laws-and-reporting-requirements-summary-current-state-laws/sexual-intercourse-minors)。
美国各州将性同意年龄定为16岁甚至更高,并非自古皆然。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绝大多数州的性同意年龄都仅仅是10岁或者12岁,有些州甚至完全没有相关规定——毕竟人类社会长期浸淫在父权文化之中、历史上童婚现象比比皆是。性同意年龄的提高,是20世纪初女权运动家与进步主义改革家不懈努力推动的成果。其它各国的法律修订,也与此同理。
与此相反,中国刑法的修订一直落后于时代。其实早在民国期间,1928年刑法就已经将性同意年龄定为16岁。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民国的“旧法统”,全盘模仿苏联,以“被害女性是否实际发育成熟”作为判断“法定强奸”的标准;但这个标准在实践中难以操作,导致种种问题,因此从五十年代末起,司法部门在办案中基本上都是将“发育未成熟”等同于“未满14岁”来处理。1979年修订刑法时,干脆直接将相关条款改为“奸淫不满十四岁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一直沿用至今。
除了对性同意年龄的设定偏低之外,这一条款还有一个长期遭人诟病的问题:只保护女童,不保护男童。对于男童,中国刑法中只有“猥亵儿童罪”,其惩罚远低于对女童的(法定)强奸罪。更一般地说,中国刑法整体上缺乏对男性——无论成年还是未成年——性侵受害者的保护,反映了早已过时的性别观念。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至2015年间,中国刑法中还存在一条奇葩的“嫖宿幼女罪”(1997版刑法第360条)。该条款表面上是为了保护幼女,实际上判罚远远轻于(法定)强奸罪,乃是给某些有恋童癖好的高官特地留出的后门;就法理而言,该条款等同于认为幼女有“同意”卖淫的民事能力,和“性同意年龄”背后的预设(未成年人没有“同意”发生性行为的民事能力)直接抵触,放眼世界恐怕找不出第二家。经过法学家与社运工作者近二十年的呼吁之后,这个条款终于在2015年废除,可谓中国刑法修订史上难得的一点进步。
二、“年龄接近豁免(close-in-age exemption)”及“欺压(abuse)”
对于“性同意年龄”的规定,一个常见的疑问是:这样一来,假如两名未成年人之间两小无猜偷尝禁果、自愿发生了性关系,岂不是有可能两人都属于“法定强奸”、都会被判刑?
这个问题在实践中并不难解决。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采取的是“年龄接近豁免”(亦称“两小无猜豁免”或“罗密欧朱丽叶豁免”)的办法,即规定当双方的年龄差小于一定数目时,即便一方尚未达到性同意年龄,双方之间的自愿性行为仍然属于合法、而非“法定强奸”。
注意:“年龄差豁免”只适用于双方自愿的性行为。毫无疑问,未成年人之间仍然可能存在非自愿的性行为(甚至某些体力较强的未成年人同样有可能强奸一名成年人);倘若一方胁迫另一方发生性关系,这本身就构成“强奸”而非“法定强奸”,年龄差豁免自然不适用了。当然,后一种情况又涉及新的问题,比如胁迫方可能年龄实在太小,尚未达到法定的刑事责任年龄等等;这在不同国家的法律中又有不同处理,这里不再赘述。
美国五十个州里,目前有二十多个州的“法定强奸”罪中包含了“年龄接近豁免”条款。以我目前居住的康涅狄格州为例,如果发生性关系的一方年龄未满13岁,则另一方的年龄不得超过前者2岁以上,违者将被判处最高25年监禁及2万美元罚款;如果一方已满13岁但未满16岁(如鲍毓明案中的情况),则另一方不得超过前者3岁以上,违者将被判处最高20年监禁及1.5万美元罚款。
还有一些州,比如加利福尼亚(据称鲍毓明在该州拥有律师资格),“年龄接近”并不构成对“法定强奸”的“完全豁免”,只构成“部分豁免”。按照加州的法律,任何18岁以上的人和18岁以下的人发生“自愿”的性关系,都构成“法定强奸”;不过倘若双方的年龄相差在3岁以内,则成年一方将从重罪(felony)降为轻罪(misdemeanor)、尽管并不完全免罪。
另外一些州的法律条文并不提供任何“年龄接近豁免”,但在司法实践中会有其它一些替代的措施。以马萨诸塞州为例,其“法定强奸”罪的要件之一,是一方“欺压(abuse)”了未满16岁的另一方;具体到检控上,是否存在“欺压”,判定依据包括后者是否遭到身心伤害(比如鲍毓明案中受害者出现PTSD等心理症状)、成年一方是否对未成年人利用权势施压(比如鲍毓明案中养父女之间的强烈权力关系)或采取恋童癖常用的“诱骗(grooming)”手段等等。
在现实中,由于两名未成年人之间两小无猜的自愿性行为基本不存在上述“欺压”因素,因此即便在马萨诸塞州这样没有“年龄接近豁免”条款的地方,也不会遭到起诉。
相反,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之间的性行为,在现实中往往包含这类“欺压”因素,因此检方一般将其默认为“法定强奸”提出检控。不但如此,马萨诸塞法律还规定,年龄差距过大,将作为加刑的依据:倘若一方未满12岁且另一方超过前者5岁以上,或者一方未满16岁且另一方超过前者10岁以上(正如鲍毓明案的情况),则年长一方将被判处最低10年、最高终身的监禁,且在头10年服刑期间不得保释或减刑。
三、填补童婚漏洞
前面说到,人类历史上童婚现象比比皆是;20世纪初美国的一些州在提高“性同意年龄”的同时,却由于宗教保守势力的反对,而未能同时提高法定结婚年龄。时至今日,尽管绝大多数州已经将法定结婚年龄改到了16岁或者更高,但仍有极少数州允许13到15岁的未成年人结婚、甚至完全没有任何关于结婚年龄的限制(参见:https://www.law.cornell.edu/wex/table_marriage)。
注:这里说的“法定结婚年龄”,并不等同于“法定自愿结婚年龄”。在美国的绝大多数州,刚刚达到“法定结婚年龄”的人若要结婚,必须首先获得父母、其它监护人或者法官的批准;只有达到“法定自愿结婚年龄”的人,才可以自行选择结婚。绝大多数州的“法定自愿结婚年龄”是18岁或者更高。即便是那些“法定结婚年龄”很低甚至全无规定的州,“法定自愿结婚年龄”也相对正常:比如新罕布什尔州的“法定结婚年龄”是男14岁、女13岁(必须父母与法官同时批准),但“法定自愿结婚年龄”是18岁;密西西比州不限制“法定结婚年龄”(必须父母或者法官一方批准),但“法定自愿结婚年龄”是男17岁、女15岁。
由于某些州的“法定结婚年龄”(有时甚至是“法定自愿结婚年龄”)低于该州的“性同意年龄”,因此理论上一度存在这样的法律漏洞:一个本来犯下了“法定强奸”罪的人,赶在被检方发现之前与受害者结婚(可能是通过诱骗受害者本人、也有可能是与受害者的父母达成交易、通过婚姻结合来避免让受害者的家人感到丢脸等等),从而让性行为变得名正言顺。
在女权组织的呼吁下,存在这类漏洞的州,在过去几十年间先后修订法律对其加以填补。其中最常见的方式,是将“年龄差距”规定引入婚姻法。比如密苏里州2018年修订法律,一方面将法定结婚年龄从15岁提高到16岁,另一方面禁止21岁以上者与未满18岁者结婚。这样一来,该州婚姻法与“年龄接近豁免”之间的矛盾便消除了。
四、新闻报导及公共舆论
此次鲍毓明案引起舆论哗然,除了案情本身令人发指之外,《财新》那篇全无专业水准且极其偏袒鲍毓明的报导(《高管性侵养女案疑云》,已删除)、以及随后明显缺乏诚意的“致歉”,也是重要的推动因素。对于《财新》的报导究竟如何违反新闻专业主义,已有许多专门的分析,我就不再重复了(比如:方可成,《媒体应该如何报道性侵案?以财新的鲍毓明案报道为例》)。
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财新》的报导、以及后续一些为其辩护的声音(比如有人声称网民对鲍毓明以及该《财新》记者的群情激愤,乃是立场先行的“舆论公审”;又比如《财新》在“致歉”中有意无意暗示,对其不满者只是不愿意接受“不符合人们(包括我们财新自己)的期望”的“复杂事实的真相”而已),又回到了两年前“米兔”运动兴起以来的一大争论上:如何理解公共舆论在性侵问题上的角色?
对此,我在《“我也是”:作为集体行动的公共舆论运动》一文中做了系统性的论述,由于篇幅过长且敏感词过多,无法在公众号发出,欢迎感兴趣的读者在此下载阅读: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463859
摘要:
本文是计划中一系列两篇文章的上篇,旨在对MeToo运动质疑者的各种常见观点及论述加以较为全面系统的辨析及回应。第一节以美国与中国为例,梳理反性侵扰运动的地方脉络,及在各自脉络中发展出的问题意识与面临的挑战;在此基础上,总结MeToo运动追责、赋能与促变之三重诉求,并将质疑者的论调归纳为三大类型:“群氓批判”、“弱女子批判”与“道学家批判”。第二至四节针对“群氓批判”的不同版本做出回应,第五节着力批驳“弱女子批判”,至于“道学家批判”则留待系列的下篇再行讨论。
具体而言,第二、三两节分别澄清质疑者对“无罪推定”与“舆论审判”概念的滥用与误用,指出为何质疑者将MeToo运动(以及其它公共舆论运动)视为践踏法治的群氓狂欢,乃是基于对法治原则的错误理解、以及对历史经验的错位应激。第四节与第五节各自通过对质疑者“虚假指控论”与“自我受害者化论”的剖析,包括对相关经验研究的总结讨论、以及对此类论述中概念与逻辑的抽丝剥茧,揭示性别偏见如何隐蔽而深入地扭曲着我们在性侵扰问题上的认知。恰恰是由于这种扭曲的系统性,导致我们无法以散兵游勇的方式有效反对性侵扰,而必须动员起MeToo这样的公共舆论运动,以集体行动的方式促成社会文化观念的变革,并在此基础上建设起新的救济制度。
作为公共舆论之一例,几位在美国的华人律师朋友近日起草了一份给加利福尼亚州律师协会的公开信,呼吁其调查鲍毓明事件、并撤销或暂停其加州律师资格。欢迎大家参与联署:https://forms.gle/sTg8XF93rZ24JvuBA
五、其它
由于很久没有发公众号了,这里顺便一并再提几件事。
其一,我在去年暑假期间,受覃里雯老师邀请,在《海马星球》做了一期播客,聊了聊我在耶鲁法学院参与的一些与性别平等有关的法律项目,包括家暴受害者援助、校园性骚扰工作小组、堕胎权案件等。几周前这期播客正式上线了,欢迎大家收听:《在耶鲁法学院帮助家暴受害者》(https://www.ximalaya.com/renwen/12558418/273158241)。
其二,我最近在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发表了一篇论文,Beaconism and the Trumpian Metamorphosis of Chinese Liberal Intellectuals(灯塔主义与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川化”)。杂志的正式版本还没有出刊,不过我先上传了一份预印版到网络,内容与正式版本大同小异(正式版本里纠正了预印本的一些错别字和表述上不够精确的地方),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先睹为快: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538736
摘要: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uzzling phenomenon that many Chinese liberal intellectuals fervently idolize Donald Trump and embrace the alt-right ideologies he epitomizes. Rejecting ‘pure tactic’ and ‘neoliberal affinity’ explanations, it argues that the Trumpian metamorphosis of Chinese liberal intellectuals is precipitated by their ‘beacon complex’, which has ‘political’ and ‘civilizational’ components. Political beaconism grows from the traumatizing lived experience of Maoist totalitarianism, sanitizes the West and particularly the United States as politically near-perfect, and gives rise to both a neoliberal affinity and a latent hostility toward baizuo. Civilizational beaconism, sharing with its nationalistic counterpart – civilizational vindicativism – the heritages of scientific racism and social Darwinism imported in late-Qing, renders the Chinese liberal intelligentsia receptive to anti-immigrant and Islamophobic paranoia, exacerbates its anti-baizuo sentiments, and catalyzes its Trumpian convergence with Chinese non-liberals.
其三,去年发表的唯一一篇专栏文章: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605-opinion-liberal-international-order-post-june4/
其四,去年的年终总结:《人到中年》(http://dikaioslin.blogspot.com/2019/12/201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