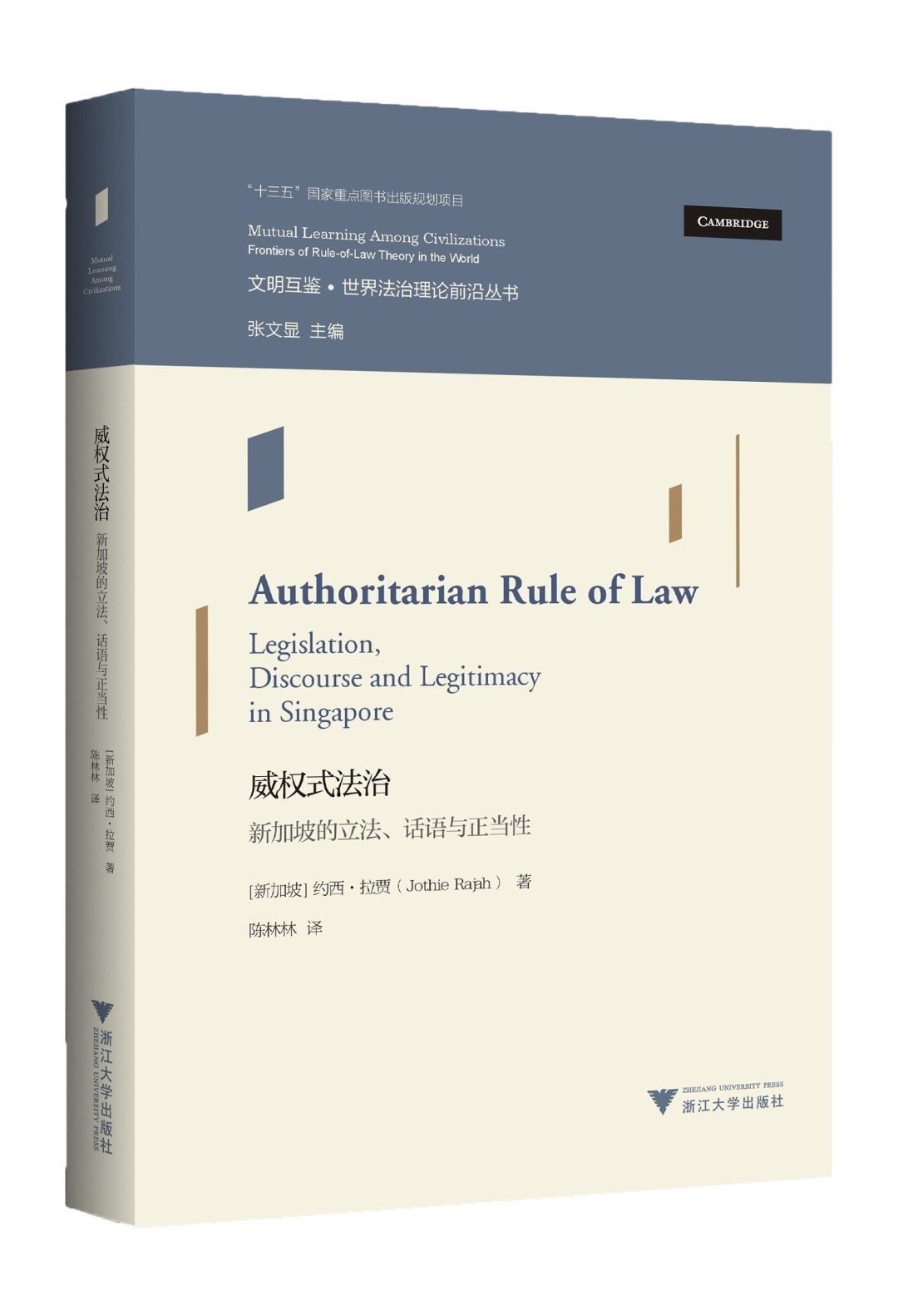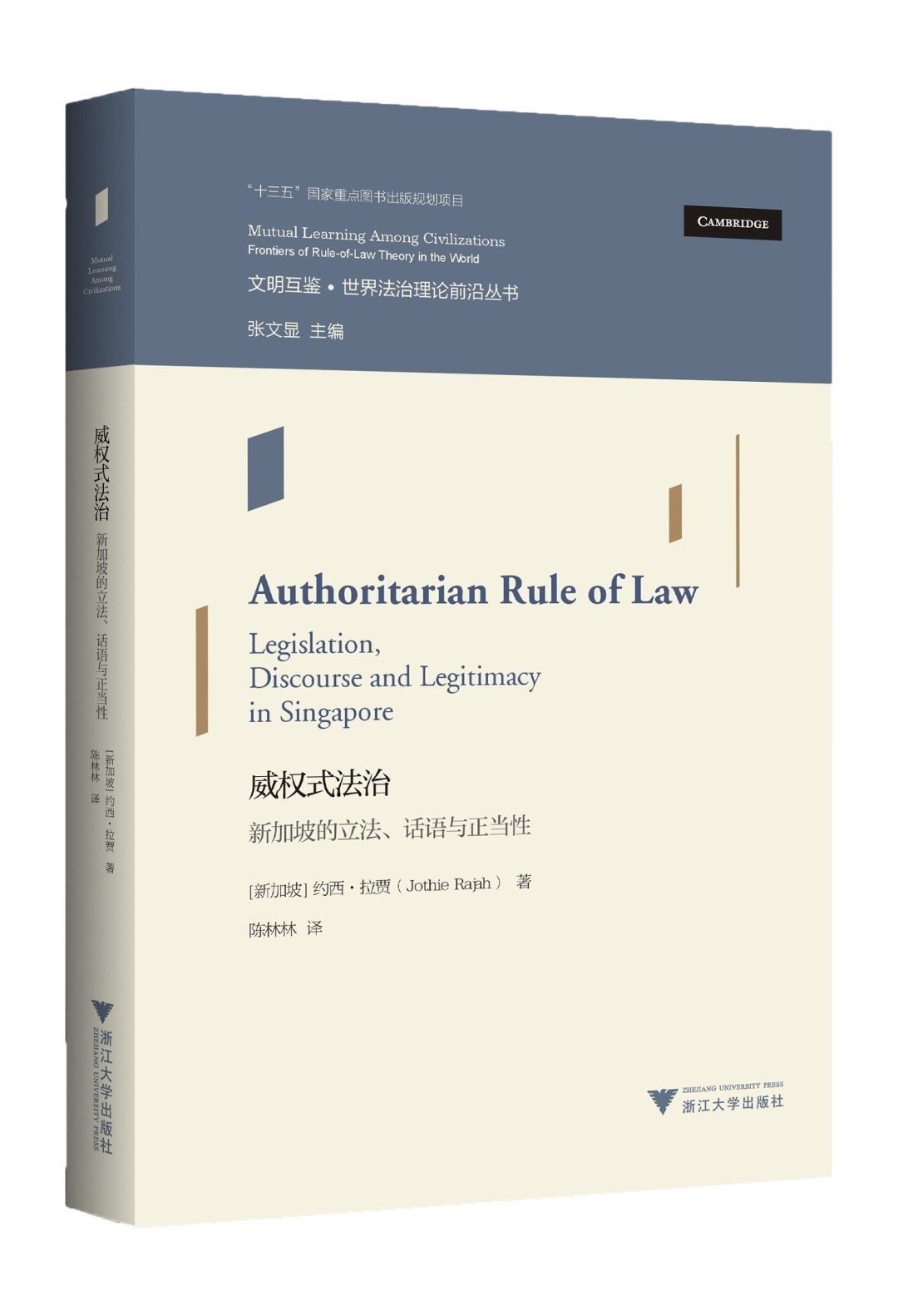 《威权式法治》封面图
《威权式法治》封面图以下为《威权式法治》一书的第七章和第八章段落摘抄。
第七章 根深蒂固的非自由主义:2009年《公共秩序法》
1.为了加强现有法律对公共领域的管理,《公共秩序法》要求下列活动必须事先获得警察许可:一人或一人以上的任何聚集或集会,只要其目的是:(1)支持或反对任何个人、组织或政府的意见或行动;(2)宣传一项事业或运动;(3)纪念或庆祝任何活动。
2.在新加坡,发起某个“运动”或者加入某项“事业的行为都被视为一种政治性犯罪,但其中的原因却是含糊的、解释不通的。
3.与其他四部法规一样,《公共秩序法》事先赋予行政机关以预防性的权力,并将国家安全当作不容置疑的正当性依据。除了《破坏性行为法》,在本书研究的五部法规中有三部法规在实施时将法院排除在外。这三部法规规定,对行政决定的所有申诉均应交由行政机关处理。
第八章 法律、非自由主义与正当性
1.政府认为,新加坡是”一个民主国家,成文宪法具有最高权威“。讽刺的是,新加坡的国家说辞又立即限制了这一主张。实际上,就实质论证而言,新加坡政府对国际律师协会人权研究所的回应是以国家说辞开篇和结尾的,政府认为这一框架是必要的,因为”你们的报告既没有理解新加坡的民主制度,也没有理解我们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政府认为,新加坡拥有特定的”民主“和”价值观“。这样一来,它就达成了两个目的:第一,它维护了自己作为法治政府的修辞性主张;第二,在没有重塑法治的情况下,它为例外主义论证奠定了基础。政府重塑了法治的基石——自由主义。这一策略表明,政府不想被认为其与传统的法治相冲突。
2.例外主义有很多表现形式:将公民幼儿化,以此证明1966年的《破坏性行为法》和1974年的《新闻法》是正当的;1986年,歪曲性地描述公众参与,以此限制律师公会;夸大种族与宗教所固有的暴力因素,通过《新闻法》1986年修正案来管理外国新闻媒体,还通过1991年《宗教和谐法》来管理宗教;1994年《破坏性行为法》通过肉刑和亚洲价值观,遏制有关国家衰退的耸人听闻的预测。
3.新加坡的例外主义话语的论证策略主要是以下两种:第一,从建国到现在,新加坡特殊的脆弱性;第二,新加坡物质成就是特殊的,它是正当的,但也是脆弱的。由于法治根植于现代治理,这样一来,新加坡的物质繁荣就能够有力地消解法治的批评。
4.如果要维持自身的法治身份,新加坡就不能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新加坡政府的回应,既抨击又认可了西方,这反应了它在后殖民世界中对自身地位的短期估量。
5.面对国际律师协会人权研究所提出的批评,新加坡政府的回应是:西方权威机构对新加坡的积极评价,予以确认;对新加坡的负面评价,选择忽视。
6.民族国家采用了殖民地时期的法律制度,将自身变为新的殖民主体,让公民居于从属地位并将其幼儿化。更重要的是,新殖民时期的威权主义被国家的家长主义所改造。政府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造福了社会的所有群体……“由此,政府实现了社会正义。
7.法律是依照法治程序制定的,这种做法掩盖了政府让公民噤声、让公民屈于从属地位的事实。
8.新加坡政府的正当性源于一种悖论式的可能性——尽管新加坡政府处于霸权性地位,但是它对权力的掌控可能是极其不稳固的。
9.法治结构是新加坡国家形象的关键支柱。为了保证政府的正当性,新加坡政府维持了形式上的法治,以防止公民寻求其他的统治方式或国家结构。
10.由于新加坡政府不知道自身获得了多少民意支持,并且它也不能冒险弄清出这一点,因此它对公共话语便会过度警觉。
11.鉴于政府在选举前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并制定法律,这就表明无法解决的问题其实是人民行动党的统治地位——是政府而非国家处于危险境地。
12.对于将自己塑造为唯一有效的超验力量的新加坡政府而言,那些具有国内、国外关系网(不论政治还是经济上)的意识形态,自然都构成了极端威胁。
13.若社会工作者与他人联合、诉诸使国家处于从属地位的宗教价值,将自己塑造为公众代言人,那么新加坡便会将公共领域中的批评视为”重大威胁“。换言之,新加坡政府并非简单残暴的威权主义。政府以一种颇为老道的方式研究了法治与法制之间的矛盾,并施行了一种有限的法治式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