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在其中耳朵被压住和熨平 | 今天的记号

早晨,正在考虑发点什么东西,哪怕随便排几个字,来为自己标记一下这个日子,就看到一个公众号上重发我译的卡内蒂(Elias Canetti,1905-1994)《苍蝇的苦痛》(Die Fliegenpein,1992)的第二节,就在盆友圈里转发了一下,作为今天的记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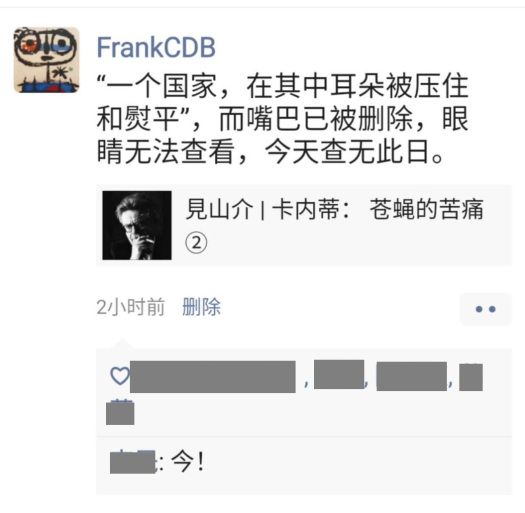
以下是转发的内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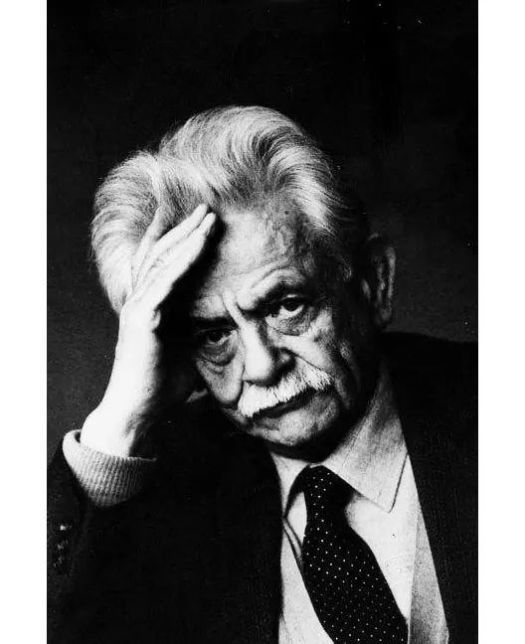
苍蝇的苦痛
笔记与符记
II
他是如此聪明,只看见发生在他背后的事。
无论是谁留下了一份自我表露的遗产都应被信以为真。一场多么卤莽的冒险呐,鉴于未来的世代绝不会显示怜悯!
一切障碍中没有一个比河流更诱人。
我自己生活的全部事实,无论是好是坏,都以某种方式困扰着我。
别人的行事方式影响我之甚一如有些人受他们食物悦人或讨厌的味道之影响。
他的名单除了省略什么也没有。
一帮哲学家为诗人拼出死亡。
我们在任何环境下都无论如何不能容许自己有某些性格上的改变,这是令人丢脸的。事实上,性格的确是由我们在那些允许我们采取的改变中所作的选择构成的。
当着一群非常熟识你的观众表演新角色的乐趣,可以说是偷偷溜出它的掌握,那乐趣是那么大,以至写作新角色,像作家与剧作者所实践的那样,比较起来显得相当乏味。这无疑是被如此想象出来的角色中有一些最佳者从没有传诸后世的原因。你如此强烈地希望是这些角色,以至对别人产生了一种看得见的即时魔幻效应,不是仅仅把它们记录与保存在纸上。它解放心灵,当你那双老手用一小会之前你还从未听到过的新语言说话之时。这是幸福的,进入一张新的脸并把旧的那张像面具一样覆在它上面。
那位著名天文学家的曾孙女接待了我。她生活在记录了北方与南方两片天空里群星的望远镜之间。我访问了曾属于威廉·赫歇尔[1]的旧屋和书房。在正对面耸立着一座现代电影院,人们在前面排成长列等候。去看看躺在赫歇尔书桌上的科学仪器与文件对于他们容易得很,但他们根本不知道存在过这么一个人。他的曾孙女像那影院一样会被大地所吞噬。
只有怀疑令他不安,从来不是实际的事实。这些事实也许是想象得出最糟的,甚至比怀疑更糟——但即使如此,它们在他心里也激不起恐惧。一个事实一旦证实了一个怀疑,他就重新获得了平静。例如,他可能对被下毒害怕得要死,但有一种克服这种恐惧的方法:他只不过得令自己相信他已经确实被下了毒,于是又一次一切都平安无事了。
他能很快把人看透,这样他更加易于成为他们的猎物,恰恰是因为他已经看透了他们。
创造悲痛的诱惑几乎是不可能抗拒的——只要它仍留存在人再一次驱除它的力量之中。
阅读寻求在我之中通过阅读来宣传它自己;我从不遵循任何外界的推荐,或者只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这样做。我想要发现我阅读的东西。无论谁向我建议一本书都是将它从我手中打掉,无论谁称赞它都令我对它扫兴许多年。我只信任我确实尊敬的头脑。他们可以向我推荐任何东西,而为了唤醒我的好奇他们所要做的只是在一本特定的书里提及某事。但别的人用他们能说会道的舌头无论推荐什么东西,它们都仿佛是实际在受诅咒。于是我便很难了解伟大的书籍,因为最伟大的著作很久以前便已经进入了平凡的偶像崇拜。人们把那些书籍及其主人公的名字挂在他们的舌尖上,他们说出这些名字时嘴巴塞得鼓鼓的——由于他们如此有意填满自己——于是便让我对我如此有必要知道的一切倒了胃口。
单句显示的模仿最少:即使两个句子放到一起也仿佛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
一个国家,人们在其中只是出于渴望而呼吸。
在英格兰人所得到的评价高低取决于他设法不打扰别人的程度。
技巧在于读得恰恰够少。
丑的缩影:一只吝啬的孔雀。
伟人时常正是那些好奇的人,他们将一种辽远的距离加于自身。
他试图遗留散乱的笔记,当作他已封闭的权利要求体系的修正。
历史从强者中制造戴绿帽子的人。
他想要每个句子出于自已的经历说话。
你认识得太久的人扼杀你愿意发明的人物。
人们避开那个总是重复自己的人。但如果他以足够轻率的无情重复自己,他们便会屈服于他的统治。
还会有多少世纪继续掠夺柏拉图?
灵魂是多层次的,但喜欢给人简单的印象。
她想要的都是些什么呀,冒险,假面舞会,盛宴,还有给她做牙签的他。
她不想了解善,而这令他恼怒无比。
当他对一个人的担忧变得不堪忍受时,他只剩下一种手段能帮他摆脱它。他告诉双方都熟识的第三方,说所涉及的那个人已经死了。他描述这个消息的性质以及它是怎样传到他这里的,以及那场他深为害怕的死亡的所有细节。他充满感情并带着适合那一事件的所有面部表情对它详加陈述,仿佛那是真的。他这样在第三方身上引发的恐惧震惊极大地安慰了他。一会儿之后他便与他谈起了完全不同的另一件事,在离开他时,他满怀绝对的肯定,那个他如此深恐会有危难的人,依然活着并安然远离一切危险。
他严肃得那么冷酷,可以与一只蚯蚓展开一场战斗。
我深为那篇有关烟囱雨燕的报道所打动,它们边睡边在极高处飞越夜空,尤其是感动于做梦与飞行是不可分割的。
他想要新闻报道像活生生的信使一样传到他这里,而他讨厌招惹他们。
一个只不过必须踮起脚尖“抓天花板上的苍蝇”的巨人。在马厩里骑兵的战马见了那巨人便惊退。“马眼大概比人眼把物体放大得多。”
一个垂死人向他的众神请假。
我会很高兴用我的几年生命来交换做一只动物的短短一会儿。
一切文学都在自然与天堂之间摇摆并爱将它们互相搞错。
人使用他的知识来保护自己免遭永恒,并在这样做时想象他正在实现它。
她打架,因为这样她就更能哭泣了。他打架,因为这样他会更加怒气冲冲。
斗争令他厌倦,因为它们偏离任何理解。
决不要告诉别人你感到多么受遗弃,甚至对你自己也不要。
一个人一直把持住自己,直到失去一切方向感。
他煞费苦心要知道得少而又少,而为了那目的他必须学得多而又多。
秋日对自己心怀感激。
人们给他们的上帝塑造了一个多么弱小的形象啊!他们愿意赋予他的一切不过是一个梦,一个创造!
但也可以说上帝是梦想一切于一瞬者。
对于我,最不寻常的诗人是那些人,他们短暂的寿命为更老得多的同时代者所超越。于是克莱斯特[2]在歌德的成熟岁月期间仍旧年轻,后者此后比克莱斯特又多活了二十多岁。
这一不均衡在诺瓦利斯与歌德之间甚至更为极端,尤其是鉴于歌德对于诺瓦利斯具有多大的意义。对于那些年轻诗人来说不随时间而逝是容易的,他们的不朽看来像一种补偿的形式:不可能想象他们会身处老年。我们倾向于相信他们早逝是为了不留下他们年老自我的单一形象。
一个在即将死去时仍然学习新词的人。
那个缺乏一切信念然而却指责别人的信念的人,总是宣称属于他有一个自己的信念,他不断改变着它以适应他这一刻的指责。
他作出一切努力从他的敌人身上榨出钱来。然后他寄回,票子都撕成了碎片。这便是他多么蔑视他,他多么蔑视贪婪,以及他多么想直接击中这个敌人贪婪的心。
不朽也有它的高利贷者。
一个兜售人们遗言的女骗子。
古埃及最快乐的人的木乃伊。
在最近三四千年里为自己扬了名而如今要永远保守它的民族。
他对任何他获准改进的东西都印象深刻。
他既爱石头海岬也爱知识,由于在两者的峰巅之间开裂的深渊。
同一片风景年复一年的景像变成一种予人安慰的空虚,一个人对它不再有感觉,因此也不再害怕。
他不再对生活有任何欲望了,除非是一场前生。
他视植物为有局限而动物已过时。
他喜欢浏览观点。
研究计划集中于历史学家——以揭开照亮他们生命的最初的光明。
一场当代英语诗人的聚会,其中每个人都在谦逊方面占先。
他认为自己深沉,因为他只模仿那些除了几段零散片断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的作家。
思想失去其重量,倘若它变得平常的话,它应当将自己投在它的主题之上,仿佛从极高处落下。
每当他有一段时间没有阅读有关众神的事,他就会不安起来。
所有他曾经认识的人都请求他让人听见。
活着是可能的只因为有那么多东西可以知道。因为在它涌进我们头脑之后颇长一段时间,知识仍旧保留其平滑与温和,像倾在情感海洋上的油一般。但一旦知识与情感相混合,它便不再有任何用处,于是便必须有新的知识就倒在那波涛之上。
在他生命中的每一股精神思潮都要等待其时机,直到聚合为一个人,与他对抗并成为他的命运。
一个诗人是某个发明无人相信却也无人能忘记的人物的人。
某个从来无人见过两次的人。他怎么办到的?
她不能放弃任何东西:如果你把你的手交给她,就再也收不回来了。
一个世界,在其中人们喜欢死多少次都可以,但每一次只死有限的一段时间。
某人,在他身上每个人都认出一位不同的熟人。
他选择了一个耳聋的神,这样他便能按他喜欢的任何方式祈祷了。
在大大延长的一生中人们将能够用更多时间做一切事,只要如此延长的手段受传统分秒的传染不算太重。可能我们将不得不试行某种新的时间安排。
“作好准备存在为任何东西,在永远存在的迷狂之中。”
托马斯·布朗爵士
时间的皮摊在地上,内脏已被清出。现在他们要把它制革。
历史对一切都知道得更深,因为它什么也不知道。
我不想尚未至少梦想了每一种信仰就死去。
靠近危险的边缘他转头环顾。他已忽视了很多,但那一切仍在那里。他的眼光远远回溯,它就像一片鸣响的天空,温柔地覆盖起被漏掉的一切。
当人们非常快乐时,他们不能忍受任何陌生于他们的音乐。
意见有它们自己的左邻右舍,有些隔着最窄的小巷互相蔑视。
果戈里的遗言:“一架梯子,快,一架梯子!”
“世上除我之外并无新事,”蔑视一切的权力总和与实质。
上帝迅速收集了一些星星,以便将它们从我们手中救出。
雨使我高兴得仿佛我刚出生,顺利而毫无痛苦。
未来太喜欢自己了——但毫无用处。
那垂死的人把世界带走。去哪儿?
他老得不能再出生一次了。
他已经布了那么多道以至他什么也不再相信了。——人能肯定自己的信仰到什么程度而不危及它呢?要发现精确的联系。
一个世界,在其中所有人都是祖先,不是任何人的后裔。
聪明人快乐地悲悼。
你太聪明了,你必须失去更多。(对一位朋友的忠告。)
在一个梦里:来自下一世纪的一首诗。
一个人的故事,他被毁于一个词。
他已经在他最喜爱哲学家的范畴上把自己吊死了。
他的秘密向往:把善良的行为赋予古希腊人。
他生产了许多词语,他忘记它们,但别人则不。
读者,到处是读者,满世界都是,倾身于错误的书上,焦急,易于受欺,躬身,受毒害!
从不互相接触的思想。
一个国家,在其中耳朵被压住和熨平。
一个人的进化主要是由他长得超过的词语衡量的。
一个人应当强迫自己停止思考连续多年,这样他身体所有被拉在后面的部分便能赶上先驱了。
人们授予他们个人习惯的尊敬,希望一个人的习惯会与别人的相合,并由此创造出一种共同的消遣。
归根结底,你的敌人并不总是企图杀死你。只有对妄想狂的头脑而言才仿佛谋杀者每时每刻都准备着谋杀似的。
做他不想要做的已经那么久,终于他想要了:自我毁灭。
[1] Wilhelm Herschel(1792-1871),英国天文学家。
[2] Heinrich (Wilhelm) von Kleist (1777.10.18-1811.11.21),19世纪德国剧作家。法国与德国的现实主义、表现主义、民族主义和存在主义运动的诗人均将他奉为楷模。
陈东飚 FrankCDB
twitter / facebook / telegram / WordPress / Matters / 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