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顶替案发生在三四百年前会怎样?明代科场舞弊考
作者:zxx
编者按:以苟晶案为代表的山东高考顶替案已延烧逾一周,社会各界群情激愤,网民纷纷要求山东省有关部门给个说法,严惩徇私舞弊者,为以苟晶为代表的受害者讨回公道,山东省及济宁市有关部门亦表示要严查到底。自古以来,国家考试都承担着社会运行重要轴心的职责,它是普通民众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主要方式,也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由此,我们不妨以史为鉴,看看在三四百年前的明代,有关部门如何维护科举考试的尊严,严惩科场舞弊人员。
“学者如禾如稻,不学者如蒿如草。”
——(宋)赵恒 《劝学谕》
社会运行之根本权力并非在于上,而是来源于下。自下而上的对于规律的认可与维护让社会实现了自动的再生产。而规律则是一种普遍的共识性话语和行为,它“通过把人的社会活动场景‘固定化’,创造性地促发日常生活的惯例,使人的实践意识固定在特定的客体性场景之中”①,通过自下的认可拥护让上层统治者以体制共识来体现自己的意志。这样的过程产生了一种双轨制的权力运作方式,即:
(1)通过国家机器介入现实让权力进行直接的碰撞来展示如何运作;
(2)通过引导让个人追求自觉步入轨迹中来获得话语的主导权。
“个体的身份是由一组社会事实或社会事件构成的。”②在以上的双轨制中,(1)的直接展示让(2)有了先天的话语优势,而对(2)的认可也让(1)有了运作空间。在来自直观的可见强力和难以察觉的教化双重作用下,一个新的身份——“书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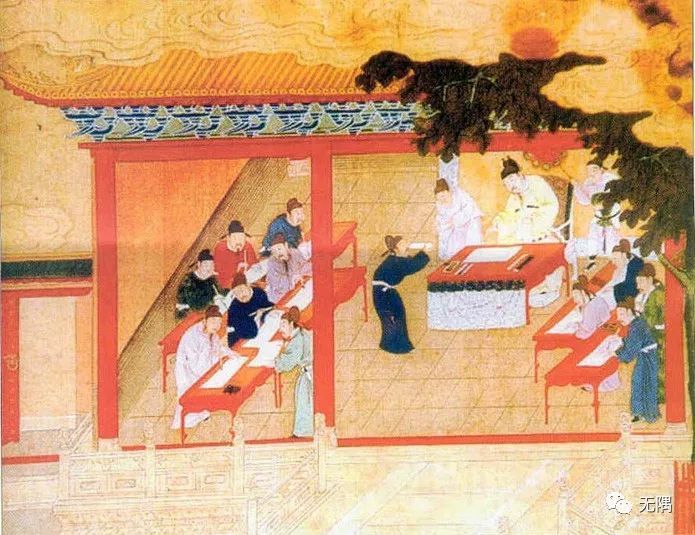
这一身份的出现让个体有了延伸的属性,“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就是最直接的展示: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提升是可以直观感受获取的,“考试——地位——差异”的三元结构像一个车轮,而这个车轮能够碾过每一个人心灵的根本就在于“教化”。“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③若非名门之后,企图通过考试晋升更是难上加难。

“县考难,府考难,院考尤难,四十二年才入泮;乡试易,会试易,殿试尤易,一十五月已登瀛。”④
一、明代科举的基本制度安排
考试的第一关叫“童试”,童试包括县,府,院试三场,县试等于混个脸熟,府试最难,甚至有“府关”之称⑤,只等三场全部通过才可以成为“生员”。各地教育资源的不平衡让童试成为了真正的修罗场,稍有钱财可请私师或者进入好私塾学习,从书具到侍童一应具全,而家境贫寒者则是在每日劳作完后才可以学习,学习条件和资源更是寒酸匮乏。个人家境,当地教育风气和政策,社会态度和人际交往全部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⑥,再加上期待和压力,也难怪梁启超感慨道:
“当其应童子试也,县试数场,经月始毕。又逾月而试之府,府试数场,经月始毕。又逾月事,一年去其半矣,既以半年人力,废以就试,一经黜落,则穷愁感叹,不能读书,而颓然以自放者,又复数月。感叹即已,而县试又至矣,试不一试,年不一年,即幸而入学,而诸生得解之难,其情形犹是也……”⑦
成为生员之后,考生即获得了一张门票,也迎来了三年一开科的“乡试”⑧。除了乡试之外,其所面对的还包括岁试、月考、季考、观风试和科试等一系列复杂考试。这些考试的内容各不相同,例如岁试和月课还考察德行⑨,而最痛苦的是岁试。岁试考两次,分六等,四等之内按排名赏赐,四等和四等之后依次惩罚,肉体上要遭受鞭打,地位也会随之下降,最次一等直接黜革。而科试则是拿到乡试资格的门票。笔者认为,最难搞的是观风试,这玩意儿是“敦劝古学,尝以策题试十府士以观风尚”⑩,也即考察当地风土人情,从当地各类文体文章中选一门测试考生的对当地风俗的了解。观风试考完就发榜,无赏无罚,但考好了也只等于在考官面前混个脸熟。如此复杂严苛的考试流程,也难怪有言道:
“取一线书香,几同断梗,未免触目心伤耳。” ⑪
至此,科考之路算是刚刚上路了。接下来是会试,会试考法跟乡试大抵相同,但从考官的变化就可以看出重视程度的不同。在乡试阶段,“考试官皆访明经公正之士,于儒官、儒士内选用。官出币帛,先期敦聘。主文考试二员,文币各二表里。在内应天府请,在外各布政司请” ⑫,可见乡试是由各省出钱聘请有才学的儒生来考⑬。但会试可不一样,会试从一开始就由礼部主持,用翰林学士考⑭,永乐二年后有专门的左春坊司经局官⑮,可见官方对会试的重视程度。
殿试是最有趣的一个环节,其纪律如下:
先进行举人廷试。纳卷之日,弥封官以会试首列数卷,潜送内阁,以备一甲之选,或内阁密规状头仪貌及生平有声者。阅卷官出自东阁,归宿私第是岁礼部尚书席书疏其弊,乞弥封官不得与送卷,读卷官退朝直宿礼部。诏日“可着为令”。⑯
殿试在3月15日开考⑰,殿试直接由内阁出题,皇帝赐题,考一整天,考完后,受卷官把试卷给弥封官,弥封官弥封完给掌卷官,掌卷官给读卷官,读卷官评三甲。第二天,锦衣卫发榜,皇帝到奉天殿鸿胪寺,令官唱名,宣唱由阁门承接,转传于阶下,卫士六七人皆齐声传名高呼,其仪式俗称“临轩唱名”或“传胪”。唱名时,文武百官具穿朝服侍班,礼部官员捧“黄榜”打鼓奏乐走出宫廷外张挂,之后由应天府官员用伞盖仪送状元返其住所。第二天,赐状元朝服冠带并设宴于会同馆。宴毕,赴鸿胪寺仪礼,而后状元率众进士上表谢皇恩。接下来,众进士到孔庙行释菜礼,最后由国子监刻石题进士名单以资纪念⑱,而状元则受最高待遇,会“以黄纻丝金书状元,立竿以扬之”。⑲
考试带来直观收益,收益塑造直观察觉,察觉形成阶级和身份,阶级和身份促使人通过考试来你追我赶,而追赶又必须通过考试。纵向的社会阶层,从出身到努力,从教育到仕途,都投入到这台考试机器之中⑳。“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 ㉑,教育(学校),科举(考试)和仕途(官场)成为了一个三位一体,学校开始充当国家礼仪的一部分㉒,也就是“礼教”;而基于礼教基础之上的科举和仕途成为了可增值的文化资本,这种文化资本通过特定机制自上而下至个人之中形成身份,而个人身份则向上认可形成阶级和权力,自此形成了“个体——科举——仕途”的体制化网络,在网络之中由不同个体形成了“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㉓
“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油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 ‘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即之鸿,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如此情况,当局者痛笑欲死,而自旁观者视之,其可笑孰甚焉!”
——蒲松龄著 朱其铠主编 《全本新著聊斋志异》卷九 《王子安》 第1279页
二、明代科场舞弊的惩罚制度
既然考试如此重要,那么别有用心者肯定不在少数,尤其是在制度并不优越的古代,就经常出现很多诸如冒替㉔,代试㉕等诸多不正能量的事儿。对此,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第一条针对冒籍的发令始自开元十九年㉖,唐玄宗下令“诸州贡举,皆于本贯籍分信明者,然以例,不得于所附贯,便求深送。如有此色,所由州、县即便催科,不得递相容许” ㉗。明代对冒籍更为重视,主要是因为“人才之生其地者多寡不同,故解额因之而异” ㉘。正如如今的我国,地区教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导致了名额不平均,故而很多人为了名额铤而走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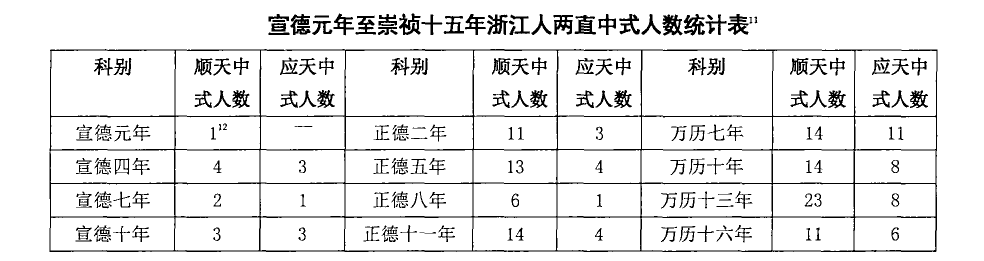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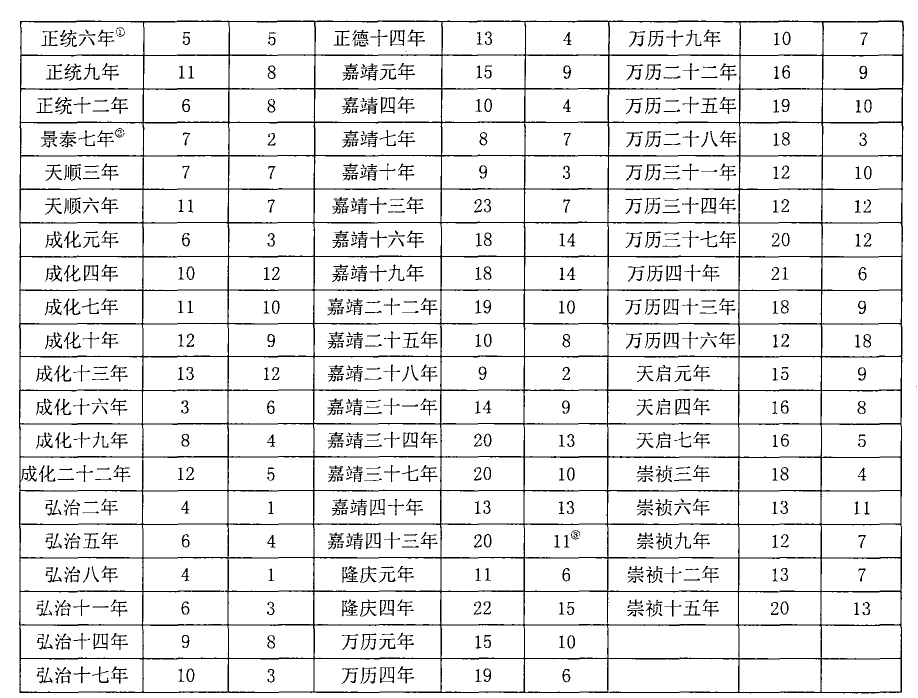
一旦被发现,立即除籍处分,例如嘉靖二十二年工部侍郎陆杰之子陆光祚和太仆寺卿毛渠之子毛延魁,鸿胪寺卿陈璋陈策等十三个人冒籍被劾奏,太医院官员子侄马銮被除籍㉙,对此,伍袁萃言道,“世之冒籍者何多也,则皆父兄之过也”㉚。对于冒籍现象的惩罚是非常严厉的,正统十四年刑部奏定若出现冒籍则“直隶发充两京国子监膳夫,各布政司发充邻县入学斋夫、膳夫,满日原籍为民” ㉛;嘉靖十六年朝廷重申各地生儒“不许诈冒乡贯,投充入学” ㉜;万历十三年,神宗下旨 “务要严查籍贯明白方准收取” ㉝。而对于相关人员,则要求“夫保者,甘与同罪;结者,要以终身” ㉞。对天下考生核查,则“仍谕天下巡按各核诸举子,复原籍为民及削籍者十余人” ㉟。
而在崇祯年间,扩大的党争也逐渐介入到冒籍事件中。姚希孟借武生俞世灏冒籍大做文章㊱,俞世灏被打断所有手指,保人高岱也被“斥革问徒” ㊲,此次惩罚仅次于万历年间的冯诗和章维宁冒籍案㊳。说到冯诗和章维宁,当时顺天府尹沉思孝见他们被打的半死又放在大街上快被冻死了,给了他们点衣服,就被“贬三秩视事” ㊴。
这样的惩罚到了清朝更加残酷,最大的一场戊午科顺天乡试案包庇考官柏葰,浦安,李鹤龄,罗鸿绎全部斩首,副考官朱凤标和同考官邹石麟因失察被革职㊵。
最残酷的惩罚莫过于对挟带这一类明目张胆的作弊行为所作的惩罚:
“近科丁未,浙人邵喻义者,故才士,第三场将所纂邸报中时事偭语,抄录批点,携入以供策科。偶与监军争语,谓其怀挟文字,邵不能平,至拳殴之,监军扭结登堂。时内监试御史为叶永盛、李时华二人。李素以酷名,意右监军,微訾邵之横。叶曰:“仆巡监两浙,会试此生拔为案首,其人奇才,今番必登进士高第,且所携亦奏疏中语,实非怀挟,宜命之卒试为便。”李以乙科起家,叶偶不记忆,遂触其盛怒,立命去衣,痛笞二十,枷之场前。虽屡次疏辨良苦,终无人敢为昭雪。”㊶
当然,其实对于权贵后代也是会有照顾的:
“正统元年丙辰,二甲进士辛瑾,为礼部左侍郎张敝之子,试时竟不引例回避,瑾亦至礼部右侍郎。正统是三年戊辰,二甲第二名曹鼎,为首揆文忠公鼐之嫡弟,文忠读卷不回避,又选为庶吉士。成化二十三年丁未,庶吉士万宏璧,为首揆少师安之孙,二甲进士倪阜,为礼部右侍郎岳之嫡弟,岳会试不回避,且为廷试提调;弘治十八年乙丑,第一甲二名谢丕又为迁之子,以出后其叔选,不书本生父文正公名,文正虽亦引嫌,竟充读卷官;嘉靖二年癸未,状元姚涞,为新任工部左侍郎姚镆子;二甲进士杨惇,为首揆少师杨文忠(廷和)次子,仍充读卷官;嘉靖十一年壬辰,三甲进士刘灿为副都天和之子。此后数科未之见。至嘉靖二十三年甲辰,而翟诸城当国,长子涌现论,以试中书舍人;次子汝孝,以国子生登第,为臣科王交等所劾,致父子削夺。嘉靖三十二年癸丑,二甲进士孙铤,为礼部左侍郎升之子,南宫试亦不回避,仍充廷试提调。”
——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卷十五《科场•现任大臣子弟登第》 第 397页
最恶劣的一种是偷换试卷:
“弘治十二年会试,大学士李东阳、礼部右侍郎程敏政为考试官,户科给事中华昶劾程敏政鬻题与举人唐寅、徐经,乃命东阳独阅文字。敏政谪官,寅、经皆斥谴。“
——张廷玉 《明史》卷七十《选举二》 第1703页
“举业虽小道,舍此无由进身,虽有其德,苟无其位,孔孟无设施之地矣”。㊷在科举为唯一的上升途径的社会里,选择冒籍或偷换的行为对其他考生是极其残忍的。当然,有人会说,只要努力就不会遭遇这样的事情,这明显是对既往社会的不了解。继续以明代举例,陈宝良考证,明末全国生员数为497031人,加上三氏学及宗学生员,大致为500000人,仅占人口的0.38%~0.46%㊸,张仲礼算出太平天国前任何一时期的文生员总数大致为526869人,武生员总数为212330人,共约74万㊹,而哪怕是最低微的小秀才也可以获得远超普通人的社会地位㊺。捐纳制度的出现让不平等更加分化㊻,大量考生长期滞留在基层,而如当下富裕阶层所拥有的出国等手段,明代有钱的考生也早已通过各种手段上升。如此年复一年基层的压力越来越大,上升也越来越难,所以文征明有言:“顾使白首青衫,羁穷奈倒,退无营业,进靡阶梯,老死牗下,志业两负,岂不诚可痛念哉!”㊼

“以为尔门户若是,而父兄若是,闻见丽泽若是,而弗能是,是不肖者。从而曰:‘是某氏子也。’可不惧哉!夫门第之盛,可惧如此,乃不若彼无所恃者之易于为贤,此之所负固重哉!”
——文征明 《文征明集》卷十八《相城沈氏保堂记》 第477页
世家子弟拥有先天的优势,再加上朝中有人的庇护,自下而上的资源眼界,本就比寒门学子要领先许多,若再出现冒籍顶替这种不正能量的事儿,很明显是对寒门学子赤裸裸的阶级压迫和剥削。
当然,这种不正能量的,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教育公平正义的现象,只会出现在古代封建社会和类似美国的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一定要警惕恨国公知和境外势力借机抹黑。(手动狗头保命)
参考资料:
①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 李康/李猛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8年第8页
②陆益龙 《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年 第430页
③《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 载汪受宽译注《孝经译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 第1页
④钟敏龙 《科场回忆录》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7年 第21页
⑤“凡岁、科入学六七十名,府录不过倍之,而学使之严者,尚有截去后段不收考之数,大概一登府录,入泮十有七、八……所以有府关之名。以为幸而得过此关,则文理稍顺,取青矜如拾草芥矣” 引:叶梦珠 《阅世编》卷四《宦迹一》 北京:中华书局 第101~102页
⑥何怀宏 《选举社会及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 第208页
⑦梁启超 《变法通议•论科举》 载《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一》 第26页
⑧若有缓考和停考也得补缺,例如嘉靖元年江西省壬午科就补缺190人,但除非是正德十四年乡试己卯科因为宁王之乱让武宗亲征没考,不然都得补缺。
⑨《兖州府志》记成华三年依据德行列一二三等。
⑩张绍南编 《孙渊如先生年谱》 载《干嘉名儒年谱》第10册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年 第59页
⑪张希杰 《练塘年谱》 载《山东文献集成》第二辑第32册 第805页
⑫王世贞 《弇山堂别集》卷八十一《科试考一》 北京:中华书局 1985年 第1544页
⑬至少在嘉靖七年四月之前是这样的,兵部左侍郎兼学士张璁于嘉靖六年在《慎科目》中提出“各省乡试主考,临期许令吏、礼二部查照旧例,访举翰林、科部属等官有学行者疏名上请,分命二员以为主考”(因为张璁和桂萼赢得了“大礼仪”所以有了实权),故明世宗于七年采取建议任命京官考(虽然五年后遭到过礼部侍郎夏言反对,但还是继续执行下去)。
⑭“会试主考官二员,临期具奏,于翰林官请用”;申时行 《大明会典》卷七十七《科举•会试》 第745页
⑮周应宾 《旧京词林志》卷四《校选人才》山东:齐鲁书社 1996年 第433页
⑯王世贞 《凤洲杂编》卷四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8年 第10页
⑰其实本来不是3月15日,成化八年才改的,据说是因为“以悼恭太子发引,改殿试于十五日”( 朱国祯 《涌幢小品》,卷一十五 北京 中华书局1959年 第263页)。
⑱黄明光 《明代科举制度研究》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 第37页
⑲王世贞 《瓤不瓤录》 上海文明书局 1915年 第8页
⑳Julie Diamond. Status and Power in Verbal Interaction Network. 1996.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9.
㉑张廷玉 《明史•卷二三一•列传一一九•顾宪成传》 北京:中华书局 1974年 6032页
㉒“惜乎乡饮酒之礼久废,人不知尊卑,党有序之学久废,人不识廉耻……是以筑为儒宫,修其祀事,请笾豆之古器,复牲币之旧仪。祭之者可以交神明,观之者可以知劝教。神明交则福至,劝教明则化行”;吴铮强 《均田制以来的军民整合》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年 第213页
㉓Pierre Bourdueu. The Forms of Capital. 1986. New York: Greedwood Press, 258
㉔“冒籍”就是冒用户籍考试,这是很常见的事儿,例如周永春的《丝纶录》卷三《礼》就曾言“各省多有冒籍无耻之人”;陈文在《明英宗实录》卷一一八“正统九年秋七月丙辰”记载“凡遇开科,多有诈冒乡贯报作生员”。
㉕代试很明显就是代考试了,不过这有两种请款个,一是知道题目后请人代写,二是直接代人去考(见廖亚菱在《科举考试舞弊、防弊及对现代考试的启示》第9页,但代试其实还涉及泄题这个情况,这也是十分严重的罪行)。
㉖“贡举之用乡贯,自明皇始也”;高承 《事物纪原》卷三《乡贯》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20册 第89页。
㉗王溥 《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缘举杂集》 北京:中华书局 1955年 第1384页
㉘涂山《明政统宗》卷二五 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2册 第690页下
㉙徐学谟 《世庙识余录》卷一八 续修四库全书第433册 第615页
㉚伍袁萃 《林居漫录•多集》卷五 续修四库全书第1172册 第265页
㉛徐学聚 《国朝典汇》卷一二九 第110页
㉜王圻 《续文献通考》卷六〇《学校考•风宪官提督》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86册 第141页
㉝周永春 《丝纶录》卷三《礼》 第633页
㉞沈鲤 《亦玉堂稿》卷三《学政条陈疏》第234页;这指的是“保结”制度,要求“始以里老邻右之甘结,谓居相近者知之必真;继以师生之互结,谓学同痒者信之必审;又继以司、府、州、县官吏之印结,谓干系重者勘之必严”( 沈鲤 《亦玉堂稿》卷三《学政条陈疏》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8册 第234页),分乡里保举(“里邻户首甘结一纸”;佚名 《八闽学政》 万历间刻本 第17页),学校保送(“赴部会试者,除监满拨历外,其余必由两监起文,方许会试”;叶向高 《明神宗实录》卷四三“万历三年十月丙戌” 第978页)和官员担保这三种(“专掌学校每季考校生员,品题优劣,以示激劝”;沈应文 《万历顺天府志》卷四《职掌》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08册 第175页)
㉟王世贞 《弇山堂别集》卷八四《科试考四》 第1594页
㊱武举也要担保,“各卫所保送各府,类送中府;上十卫并武学径保送中府”(王圻 《续文献通考》卷四七《选举考•武举乡试条格》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85册 第717页)
㊲汪楫 《崇祯长编》卷六二“崇祯五年八月庚午” 第3551页
㊳文秉 《烈皇小识》卷三 第64~65页;冯诗和章维宁因为胡正道冒籍案被“各枷号示众,发为民”( 王世贞 《弇山堂别集》卷八四《科试考四》 第1593~1594页),被沈德符称为“盖自来冒籍受法,未有此严峻其滥及者”( 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卷一四《京闱冒籍》 第374页)
㊴过庭训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四五《沉思孝》 续修四库全书第534册 第217页
㊵李国荣 《科场与舞弊—中国古代最大科场案透视》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7年 第 321~325页
㊶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卷十六《会试搜检》 第413页
㊷刘永澄 《刘练江先生集》卷二《举业》载《四浑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 1997年 集部第179册
㊸陈宝良 《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 第215~216页
㊹张仲礼《中国绅士》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年 第106页
㊺“吾少时乡居,见闾阎父老,阛闺小民同席聚饮,悉其谈笑,见一秀才至,则敛容息口,惟秀才容止是观,惟秀才之言语是听。即有狂态邪言,亦相与窃笑而不敢言短长。秀才摇摆于市,两巷人武部注目视之曰:‘此某斋长也,,人情之重士如此,畏其威力哉?以为彼读书知礼之人,我辈材粗鄙俗,为其所笑耳”;吕坤 《实政录》卷一《弟子职之二》 ;《吕坤全集》 北京:中华书局 2008年 第920页
㊻但平心而论,捐纳在当时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儿,《醒世姻缘传》第五十回里面有句话叫“援例纳监,最是做秀才的下场头;谁知这混帐秀才援例,却是出身的阶级”,在当时正经考上去依旧是正途,例如张笃庆就曾说“盖恐入监不中,则不如静候挨贡,犹不失正途也”( 张笃庆:《厚斋自着年谱》,载刘聿鑫:《冯惟敏、冯溥、李之芳、田雯、张城、郝懿行、王戴荣年谱》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年 第1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