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识形态:意底牢结与人的价值
本文写于三月,因对结尾不满意,一直拖着。此后数月因为特朗普的神操作,显得文中举例与情绪过于陈旧,但也拜他所赐,到了七月份谈论疫情仍然不算过时。本文立足于疫情下的意识形态之争,近来无事略加修改,特与诸君分享。
疫情蔓延以来,不少朋友问我为何不撰文分析。我一直关注进展,情绪由诧异、震惊、愤怒、乃至伤感,迟迟下不了笔。原因有二:一是各个渠道的信息过载,让我深感不同领域的知识壁垒之高,讯息难辨真伪;二是在全民的广泛讨论下,各种批判之声俱在,实不知自己能写出怎样有价值的观点。于是只私下和朋友们聊聊,听听他们的想法和消息。
聊得久了,隐约发现了一个诡异的现象:政治立场不同的人,面对同样一场疫情,其结论却截然相反。以疫情处理而言,有人认为是制度缺陷带来了疫情公告的拖延;有人却认为对疫情的管控,恰好体现出了集中力量的制度优势(后者随着如今欧美疫情的不可收拾而占据上风)。简而言之,这次疫情,实际上让左的更左,右的更右。

我在《如何不伪善地交流》中提过,理想的交流,应当存在对观点的自我修正机制,立场不同的人可以通过新的现象修正观点,或更深刻地理解彼此的差异,而非同温层抱团取暖。“左得更左,右得更右”无疑与之背道而驰。要理解并摆脱这一现象,就要从病毒背后的“疫识形态”入手。
3月初,一个文科博士群中有人贴出一张“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名单”,名列其中的王广发,正是1月初赴武汉调查新冠肺炎的专家组成员,因声称疫情“可防可控”而广为诟病。王广发在此后十天也感染了新冠病毒。群中直接有人称王广发为“垃圾”,死有余辜;但也有人表示王广发作为一线医生,而且曾经抗击SARS,如今因公染病,不该被视为垃圾,双方由此吵了起来。我忍不住留言:
如果要用道德指责这位医生,就得先区分他的误判是一个医学专业的问题,还是他个人的道德问题。结合现在的信息来看,应当是专业的认识问题,毕竟这个误判很普遍。何况,他在一线染病本身就排除了他“道德低下草菅人命”的可能性。那为何要对他采用道德审判。除非我们自己把医生神化了,认为医生全知全能犯了错就是道德有问题辜负大家的期望。这就和求不来雨去捣毁庙宇差不多了。要给医学人士容错率,犯错了可以追究程序上可能的责任,不要挥舞道德大棒;或者道德大棒至少挥向医生,毕竟他们只是处理具体的医学问题,无关道德。一线染病的医生都值得尊重,当然包括这位医生。
事后我想,自己潜水多年,却忍不住发表这么一番议论的原因恐怕是,把王广发斥为垃圾的人,已经无视了他也在一线染病的事实,他们字里行间“死有余辜”的心理,让我不寒而栗。人们对疫情失控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愤怒归根结底是因为疫情失控会使更多病人与医护人员染病乃至失去性命;如今王广发这样一位因为在一线而染病的“人”,摆在面前,我们却看不到他作为人的属性,而觉得他死不足惜,实则构成了一种矛盾的伪善。
这种矛盾,正是我想谈谈“意的牢结与人的价值”的原因所在。“意底牢结”是牟宗三对于意识形态(ideology)的翻译。牟先生译的是法文ideologie,以他的胶东口音念起来颇为神似。初看此翻译,有沉郁顿挫之感。意识形态正是一种使人“画地为牢的根深蒂固之观念”。大陆语境下的意识形态总是关乎政治,这很大程度上受到马克思的影响,创造此词的Destuttde Tracy,本意代指客观审视与分析观念的科学。不过即便撇除政治的阴影,意识形态所蕴含的概念与意识自身便会自我建构,从而形成层层的囚笼,即所谓“意底牢结”。

这次疫情如同一面镜子,将社会各个阶级、族群之间的理念之“牢结”显露无疑。如前所述,疫情激起了极大的社会动荡,但对于这些动荡的诠释,不同立场的人基于既有之“意识”,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读,并不断强化立场,陷入更深一层的“牢结”。例如疫情爆发伊始,便有多篇文章指出控管不力的原因和中国足球如出一辙——制度问题。但如今随着欧美疫情的爆发,另一批人似乎又拾起了之前士气不振的制度自信,认为欧美作业都抄不来,甚至认为世界需要感谢中国,引来台媒大做文章。
这两派看似针锋相对,实则都有“唯制度论”的味道。我始终反对唯制度论,因为它过于简化了现实问题的复杂性。我先读数学,再读历史;前者追求极致的抽象,后者强调现实的复杂。二者对于现实问题缺一不可。我们需要理论框架来梳理、认知世界,但理论绝不可能成为唯一的解释因子。唯制度论者,同质化(甚至无视)了体制中各个人的能动性。疫情在武汉爆发时,不少文章坚称另一种体制下不会存在隐瞒疫情的现象,显然和后来的发展相悖(唯制度论者的叙述,不会考虑到日本今年奥运、美国今年大选影响决策这些特殊因素)。那这是否说明另一种体制等而下之呢?也不是。
体制是社会的骨骼,固然兹事体大,但疾病往往是透过表皮感染,通过血管流动到各个器官。这些皮肉、血液、器官,都不是骨骼所能囊括的。制度或许是社会的骨骼,但社会的皮肉是一个个鲜活的人。可是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我们往往忘记了争论双方彼此个人的属性,而将之与种种标签等同:“五毛”、“美分”、“公知”、“砖家”。
生活中,我们已经习惯把各种话题转换为政治的、非政治的意识形态之争,各派的论述,在彼此的同温层上结下厚厚的蛛网。有的人习惯用阶级剥削来认知世界,有的人习惯用性别差异来认识世界,双方都预设着天然的朋友与敌人,以及朋友的朋友、敌人的敌人。陷于这样处境的人,其预设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他思维以及发声的基本概念,于是观察到的任何现象都不足以动摇其根本理念,也就是不能实证地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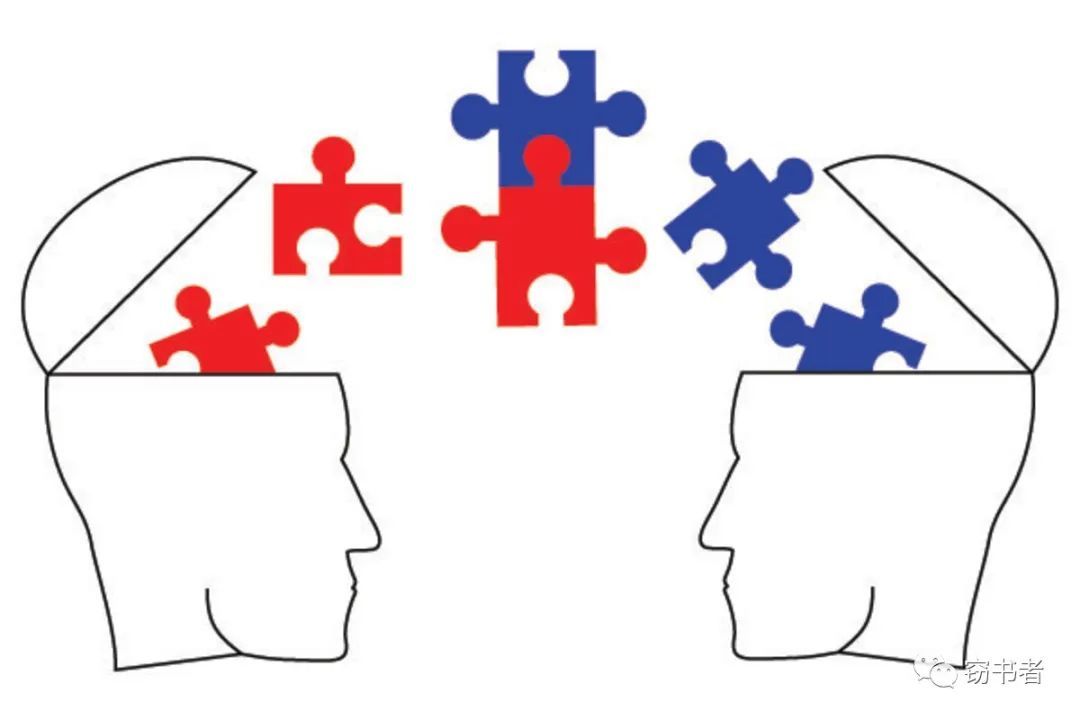
意识形态可以帮你确定朋友与敌人,但无助于抗疫。 因为病毒采取了无差别攻击——不论你疾病或健康、贫穷或富裕、美貌或失色、顺利或失意,都愿意侵入你、感染你、摧毁你。It does.
但是疫情本身,也启示我们摆脱意底牢结,重新审视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近两月来,爆发于美国的Black Life Matters有席卷全球之势。对于这一运动,反对者表示All Life Matters,何必要强调Black?示威者则称用All Life会模糊黑人遭受歧视的事实。我无意介入这类争辩,但不可否认,大部分人基于自己的成长环境、教育背景,不可避免地对不同社会群体有所偏见。如果说这世上真有什么发自内心秉承All Life Matters的物种,那与其说是人类,还不如说是新冠病毒。
因为病毒传播时,看到的不是个人的种族、阶级、抑或宗教信仰,只是人的生命本身。人的存在可以作为它们的宿主,这对病毒而言已经足够。从存在主义的角度,病毒看得比人透彻。人沉浸在意底牢结久了,反而容易把生命抽象化、数字化。在川普们看来,生命是选票,是养老金的缺口,是失业数字;在吃瓜党看来,生命可能是疫情奥运会的奖牌榜:早期中国照例一马当先,中期欧洲诸强迎头赶上,最后美国不意外地强势登顶;在加州的青年看来,死亡可能是病毒派对刺激的来源与意义所在;在自媒体眼中,一桩桩惨剧则化作无数的流量入口。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建构中,生命可以衡量、可以叠加,甚至可以产生复利,唯独失去其自身的血肉与尊严。而感受到生命分量的人却往往即将失去它,比如那位死前发帖懊悔自己参加病毒派对的大叔。
我的母亲是位医生,疫情严峻期间,看她工作时全副武装,让我切身感觉到对于疫情与死亡的恐惧,那是一种阅读新闻难以带来的临场感。后来疫情席卷美国,我从局外人转为被国内亲友关怀的对象,疫情对我的影响变得愈加清晰可感。有那么几天,在疫情的威胁前,我辗转难眠。想到的更多的是自己的亲人,这是我作为人的情感纽带。此时意识形态显得如此苍白。
存在先于本质。我们可以通过价值、理念、乃至意识形态帮助自己认知与理解世界,但不应困在意识形态的牢笼,连人的存在本身都忽略或虚无化。疫情终将过去,但疫情提醒着我们,死亡并非一场遥不可及的幻梦,它悬在我们头顶,暗示着我们首先是具有生命的存在,而非某种理念的奴隶。
这或许是这场疫识形态对我们最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