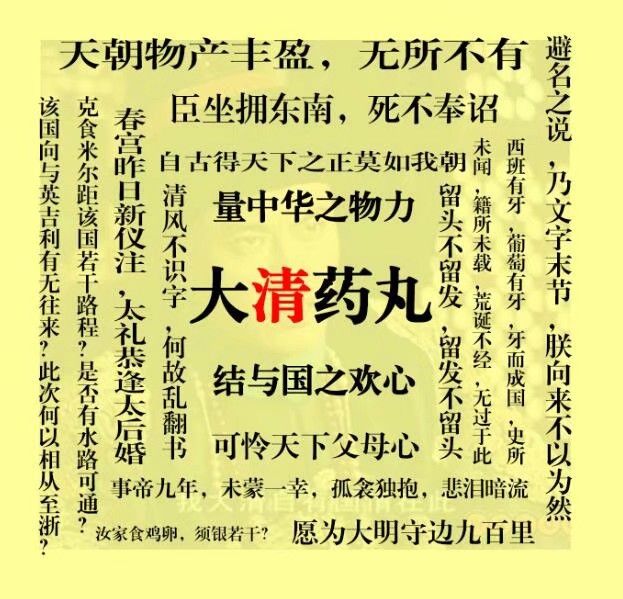『論國家的權力』
「利維坦的權力」這個名稱,對於我個人最喜歡的兩個政治哲學命題來說是一種引導,其一是休謨給出的,他在清乾隆十三年(1748 AD)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你是自願加入你的國家嗎?」 對於一個只會講本民族語言、不懂外語和外國文化的農民或者工人,我們能認為他們有自我選擇的餘地嗎? 休謨給出了回答,一個在睡夢中被人搬到航船上的人「你出生是自願的嗎?」,若要離開船則只能跳海淹死,或者打倒船主吧? 如果他選擇繼續留在船上並且不打倒船主,那說明他自願地同意了接受船主的奴役。
另一個命題是盧梭在清乾隆十九年(1754 AD)於『Second Discours』一書中提到的,他說:「統治階級虛構了一個社會契約,聲稱要用法律和刑罰來維護社會穩定、恢復社會秩序,但是這種‘詭計’,除了給統治階級更多的專權,給底層人士更多的高壓外,別無他用。」所有人都奔向鎖鏈,他們相信需要捨棄部分自由,來維護個人的更多自由。可是這更多的自由卻是按照階級劃分的。於是人們開始傾向於互相傾軋,「他奉承自己所憎恨的大人物与所蔑视的有钱人,他为了获得服侍他们的荣耀,不遗余力。他自傲地夸耀自己的卑鄙,以及他们的保护;他对受奴役感到光荣,在谈到那些没有资格来分享这一切的人时,反而透露出轻视的神情。」
表象是什麽?不可不察,須深究其根源。修昔底德有言:「城邦是承載一切的船;沒有它,城邦的公民什麽也不是。只有它平穩航行時,任何事務才會變得可能。」索福克勒斯在『Antigone』中借Kreon之口也說過類似的話。
在他們看來船是一件工具,它的良好運行是必需的;不然將會危及船員的生命。這是首要的基礎,在此之上,船員們來到船上,並不僅僅是為了平穩航行,他們還有其他的目的,船隻提供了到達目的的環境和手段。假使一個船員試圖脫離船隻,他就會受到其他船員的責難,會失去船隻的保護。後來,有人提出,這樣一來船隻就變成束縛牲口的韁繩,使人變得與動物無異。一開始Kreon就把船隻認定為善的化身,而對立的除了惡,再無其他,為什麽Antigone會站出來反對?因為她深知惡法的害處,同樣是有害於船隻的,儘管Kreon佔領了道德制高點,但很快讀者就會明白,誰才是觸犯神的人。
Kreon的意思很明確,即船隻是一切的根源,沒有船隻,你什麽也不是。
但注意,如果船隻本身是惡呢?那麼它會把你帶向何處?
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寫的不是船,而是船上的人,船本身是惡的化身,那麼船上的人最終決定將這艘船淨化,也是合情合理的行為,因為人的天性之一就是自保,出於自我拯救而做的事,不能稱之為惡,正是如此,世界上才存在正義與尊嚴。
Antigone為了自由及正義不惜以身犯險發聲,表明Antigone不接受Kreon強制施行的所謂「維護城邦」。同時Antigone樂見支持惡法的Kreon遭受正義的制裁,因為當法律不再保障公民權利,保持所謂的法治就只是打壓公民權利的工具。
到了柏拉圖的『理想國』或曰『王制』這種船隻隱喻變得更為精準了。
柏拉圖說:「假設有一艘隱形的船,船上的船長,身材高大,但耳聾眼花,航海技術也不太高明。船上的水手都吵著要接船長的舵,自己來駕船,水手們從沒學過航海技術,說不出來誰教過,或者學了多久。他們斷言航海技術是天生的,不能被教授,誰要是說可以教,他們就準備幹掉他。他們成天圍著船長,盡其所能地讓他把舵交出來;如果一派比另一派更接近掌舵,那麼他們的對手就會使用‘馬基雅維里之術’使這些人消失,然後用‘黃泥岡之酒’,或者‘呂後的秘法’把高貴的船長放翻,控制船隻,隨便取用船上的一切,把通往天國之旅變成了駛向馬里亞納海溝之行,你可以盡情享受這一切。事後,凡是曾經參與謀劃控制船長奪取舵並耗費大量‘查克拉’使用‘馬基雅維里之術’的人,他們都保持尊敬;給這些人冠以英雄的榮譽稱號,對於失敗者或者不站隊的中立者,他們就尊稱其為廢物。(488a-d)」
柏拉圖把統治比作航海,也就是掌舵國家。掌舵者,如果是一個只會一直加速的人,可以想象我們這些船員的命運將會如何。柏拉圖說,這將是一趟「地獄之行」。我們將直接面見哈迪斯。
小粉紅或歲靜詭辯說:「不談政治,在長城內會生活很好。」這是極大的錯誤,因為社會的普遍道德就是國家政治的延伸,現在利維坦出現的多類惡性事件,難道還不能說明是政治問題?比如說,杭州的殺妻拋尸糞池案,有的中國粉紅就拿來威脅自己的妻子,甚至還有妻子感謝丈夫的不殺之恩,諸如此類。富蘭克林有言:「一切都是政治的,因為一切都是道德的。」從根本上政治和生活就無法割裂,否則你如何解釋中國粉紅現在的道德狀態如此低下。政治是人為的而非天然的,從根本上影響了人的自然天性,人的天然道德是良好的,而一切不道德的根源就是政治,政治充滿了陰謀、血仇和兵刃,是一切罪惡的淵藪。亞里士多德說:「政治是為國家獲得最高道德為目的的科學,對最高道德的追求能使人成為一個更完備的醫者或船主。」無需贅言,各位心裡有數。
中國粉紅一談到如帝登煤山之類的事件,往往痛嘆,大臣無能,流賊窺器,卻從不把問題的矛頭對準那位執有神器的人,一提王朝覆滅,就是封建二字必然,他們從不反思,流賊和大臣被某人之前的所作所為逼迫無奈。一位朋友說:「你还记得历史教训,只是因为你没有享受那种掌握生死的快感。」對此我十分認同斯賓諾莎所言:「Each person’ s natural right therefore is determined not by sound reason but by desire and power.」
在抑壓委讓原理通行的世界裡 位於金字塔最底層的民眾的不滿已經沒有可委讓的地方,所以必然要向外爆發。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7月14日夜間,出現了這樣的對話。「這是一場叛亂嗎?」「不,陛下,這是革命。」未及開始,已然結束。這是後世法國史學家對這次事件的總結。舊日的利維坦土崩瓦解,非人格化的現代利維坦降臨人世。多少美麗的詞語謳歌這次事件,然而狂熱下的人群喪失了理性,回到了自然狀態。
盧梭說:「富人的霸佔,窮人的搶劫,各種無節制的熱情,使自然憐憫心偕同那微弱的正義之聲音一起窒息,並展現出人的吝嗇,野心與惡毒。在‘先佔為主’的權利與‘強者為主’的權力之間,一直不停的發生爭端。只要看到對方還不是處在最悲慘的環境之中,我方就必須用盡心機,迫使其走投無路。爭端的結果就是無止境的戰爭與謀殺。」
一般來說這時候的統治階層往往會站出來學習大禹,丸山真男說:「為了防止不滿的逆流,統治階層便自動出面煽動這一傾向。」
實際上船已經沉了,每個人都不可能平安到家。獻忠公車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對現實生活的不滿,而又無法上達天聽。Luis ⅩⅥ採取的是堵而非疏,結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