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在阅卷组:为何阅卷组长成了“小镇做题家”

上篇批驳浙江高考范文的文章言辞比较激烈,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对阅卷组长陈建新的品味感到失望,二是认为他这句话不够厚道,有排挤同僚之嫌:
第一位阅卷老师只给了39分,但后面两位老师都给了55分的高分,说明我们的阅卷老师还是能识别作文的好坏的。
这句话明褒暗贬,就差直说第一位老师不配阅卷。以陈建新数十年阅卷经验,不该如此沉不住气。此外,陈的表述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他与后两位观点相同,反对第一位;但若从满分与否的角度,他其实力排众议,否定了全部三位阅卷者。因为三人都认为此文不足以满分。满分和55乃至59分最大的区别是,前者要作为范文公开宣传。实际上陈建新也提到了,故意定为满分既为彰显阅卷组的鉴别能力,也为“展现浙江高三学生的作文水准”。
其实把堆砌辞藻当成深刻、缺乏文字的感知力,正是广受批判的“小镇做题家”的审美。问题在于,为何“小镇做题家”成了千万学子的主考,他又为何不惜把阅卷组的矛盾公之于众,力排众议推出这么一篇争议范文?本文将从科举与高考的比较分析出发,借由“场域”与“知识-权力”理论(毕竟上一篇我承诺要用学术概念说人话),分析为何高考主考出现了德不配位的现象。
我的导师周启荣老师致力于明清出版文化研究,代表作Publishing, Power,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前近代中国的文化、出版与权力)以晚明科举为核心,讨论主考、举子、以及制举用书编者(可以理解为卖教辅的)之间围绕着考场作文评判权的博弈。周师借用布尔迪厄的“场域”(field)一词,指出科举构成了一个中国特有的考试场域。那么什么是场域?
“场域”常见于社会学理论,如文学场域、政治场域等。对这个概念最常见的质疑是,场域和通常说的领域有什么区别?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视角的转换。当我们说领域时,强调的是领域中的行动者,如“电影领域的陈导李导”,这句话的主体是导演,电影只是他们工作的场所。但若要研究电影场域,那就不是研究电影人,而是针对一个抽象的电影圈子,研究它如何对具体的电影人施加影响,以及这个圈子自身的权力结构、流动性等特征。这是因为场域借鉴自物理学的电场(二者原文都是 field)。布尔迪厄认为场域能对其中的行动者造成宏观上的影响,但行动者本身仍然具有一定的能动性(agency);这对应了电场对微观上不规则运动的电子产生作用力,使其宏观上沿着电场方向产生电流。此外,电场作为客观物质,其自身是物理学的研究对象。因此社会理论家提到场域,研究的也是场域的主体性,而非作为舞台的场域。
了解这些后,我们先看晚明的科举如何形成一个场域。首先科举几乎垄断了天下学子阶级晋升的渠道,促使着不同家庭背景的士子“一心只读圣贤书”。这就是宏观层面的规训作用。其次在科举场域获得的功名,可以转换为其他场域的资本,比如举人租赋全免,农民会自愿将田产托付名下;又比如高中之后,编纂制举用书的书商会主动约稿。而主考也因为在科举场域的地位超然,积累并扩散着自己的政治影响。一方面,主考选拔的举子自动成为自己的门生,日后可引为官场的奥援;另一方面,主考也可如欧阳修一样借此整顿文风,把自己的文章理想辐射到整个士人阶层。也正因如此,对于科举文章优劣的评价权,在晚明成为不同势力的争夺对象。
明初,科举文风多为翰林把持。翰林由进士出身、文笔超卓者遴选而来,担任主考本无可厚非。但到了明中叶,涌现出前后七子,高举“复古”大旗,从翰林手中争夺评价文章优劣的权威。科举场域的权威,由翰林过渡到六部官员手中。万历以降,随着商业出版的兴起,层出不穷的制举用书逐渐取代了政府官员对于科举文章的影响力,应运而生的文学评论家又取代六部官员,成为了品评时文的权威——尽管他们大多数人自己都没考上。
科举场域与商业出版场域在考卷评判权上的展开了剧烈竞争。其中最典型的体现是艾南英。他屡试不第,便投身商业出版,一跃成为天下闻名的制举大家。虽然社会地位与收入已不逊于科场的佼佼者,但他不忘初心,屡败屡战。科场失败者与出版界大佬的矛盾身份,最终激化出了颇为讽刺的一幕,艾南英从考场失意归来时,南京官员往往出城数里相迎。须知以科举场域的地位而言,艾南英不过是一介落榜考生,南京贵为陪都,官员多半进士出身。后者对前者出城相迎,体现了旧的科举场域所孕育的权力已被新兴的商业出版所压制。场域的意义就在于此,艾南英未必比那些南京官员更会舞文弄墨,厉害的不是他这个个体,而是他背后的整个商业出版这个主体。既然天下考生已经习惯从商业出版物学习与阅读时文,并反过来借此品评主考的判卷是否公允,那在野的文学评论家自然就压倒当朝的学院派。游戏规则变了,就不是一两个个体所能扭转的了。
到了高考,游戏规则又变了。最大的改变体现在它与政治权力脱钩,失去了对政治精英的吸引力。其左右学术风气的功能又被学术圈所剥离。高考不过是针对青少年的一次智力排序。语文只是排序所需科目中的一门,作文又不过是其中一项。考生既不指望靠篇作文一跃龙门,主考也不必以匡济文风为己任。高考至多是一个缺乏独立性的副场域(semi-field)。如今把高考、司考、公考等一系列考试整合起来,或许更接近科举,但由于不同考试去中心化的倾向,无法统合成一个独立的考试场域。写作从“天下公器”被还原成了一门具体的考试技术。学界泰斗不当主考,莫言们也不愿插手,主考的担子就落到了主管语言教学、中学素质教育的陈建新们手中。换言之,高考场域的权力失衡造就了如今主考尴尬的定位。
看看陈建新在浙大主页公布的论文,与文学创作可谓南辕北辙:

那么学界泰斗和莫言们在干嘛呢?他们在学术场域和文学场域积累文化资本,这两个场域中的资本可以互相流动,比如莫言可以受邀去大学授课,名牌大学教授若投身文学创作至少在营销上也有爆点。两个场域都不怎么和高考圈子玩,但他们本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翰林。
不过,虽然高考作文因脱离了政治与学术场域导致“翰林们”不愿屈尊俯就,但正因如此,在高考作文的副场域内又存在监管真空。古代出于避嫌,罕有主考参与制举出版。今天阅卷组长不仅堂而皇之冠名教辅,如果陈建新和考生约定好以艰涩的字眼串通,如何杜绝?就《树上的生活》来说,陈要是秘而不宣,外人从何得知?
虽然一方面,高考与政治权力脱钩导致主考没什么官场前途;但另一方面,正因为学界与政界无意过问,主考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又成了土皇帝。要是古代,要是状元文章闹出这么大的争议,翰林与六部官员怕不是人人参上一本。倒不是古人对文字更有操守,而是大家知道,扳倒了当朝主考无论是声望还是政治资源都有利可图。如今监督主考无利可图,主考也就无从约束,无怪乎陈建新能够阅卷几十年而不倒。(发稿前,看到北大和复旦教授发文驳斥这篇作文,算是有个别翰林站出来了,但仍无法形成合力)。阿克顿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虽然德不配位不必然意味着腐败,但主考的判卷权缺乏监管却是事实。
鉴于科举场域的政治权力分给了技术官僚,学术选拔能力则分给了高校系统,陈建新们既不能指望凭借阅卷工作提拔门生成为日后官场的助力,又不能指望靠阅卷发表论文在学术场域积累资本,只能另谋出路。这个出路就是向商业出版场域“投诚”。
于是我们看到古今对比最刺眼的一幕:晚明的士人投身商业出版主要是为了解决屡试不第的经济窘境,甚至在商业出版暴得大名后仍然汲汲于考场功名;到了21世纪,我们的主考大人(虽然不比古时位高言重,但压制同僚、指鹿为马也绰绰有余了)居然主动投身商业出版,用考官的身份圈考生的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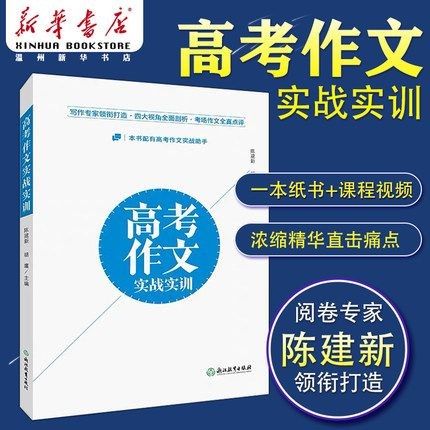
但是历史研究讲究“理解之同情”。我们若要探究现象背后结构性的原因,就要把道德审判放一边,避免归因于私德。重点不是“应然问题”:陈建新应不应该一边当主考一边卖教材;而是“实然问题”:他实际上是怎么卖的,卖教材这个行为如何影响了他的言论与决策。
这里我用福柯的权力-知识(power-knowledge)来讨论主考投身商业出版的现象。福柯认为,权力不是一种所有物(possession),而内嵌于话语之中。知识作为一种话语,本身便具有权力,这种权力又往往会延展出新的知识。(不过福柯的knowledge更接近于抽象的认知形式,我在这里取狭义的knowledge,即所知之物)在科举场域,“权力-知识”最好的例子就是四书。四书作为儒家经典,是一种文本知识。但一旦被确立为科举的指定读物,就附着上了与科举场域相关的政治权力。正是这种权力的魔性才让百年来无数士子癫狂,成为范进式的人物。另一方面,既然四书具有如此的权力,自然会出现商业出版的四书评注等参考书,试图从科场分一杯羹。这些形形色色的四书评注,就是四书内嵌的权力所催生的新知识。
从政治权力的角度,高考虽然是低配版科考,但依然吻合“权力-知识”的特质。《黄冈密卷》、《三年高考》、《灿烂在六月》便是权力衍生出的新知识;而王后雄、葛军、陈建新等人虽然在学界声名不彰,但在本省考生心中如雷贯耳,这便是内嵌于知识之中的权力发挥的影响。
权力-知识背后的权威,天然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四书对应的权威是孔子,因而曲阜孔氏千年不倒。此外,权威还要与场域吻合才有意义。例如,《道德经》虽然是道家权威,但无法形成科举场域的权力-知识。而陈建新之所以要力排众议,把争议卷定为范文,并把阅卷组的冲突广而告之,其用意就在于塑造向受众传播自己在高考场域的权威。
有网友发现,《生活在树上》引用的素材与陈建新的教辅多有重叠之处。虽然有买过这套书的人吐槽其质量不怎么样,但这还是以传统的知识观(审美、文法)来衡量。从权力-知识的角度,无所谓传统的知识观,权力一经确立,就能生产“有用”的知识(例如你照着他写就能拿高分的话)。那他嘲弄同僚也就说得通了,可能是有意输出自己在阅卷组能够拍板的形象,可能是无意体现了权力形塑的个人意志。
或许有人会说,我这也未免太捕风捉影,点评个作文非得和自己卖的教辅扯上关系吗。会这么想,是没有以浙江考生的角色自处。倘若我不幸成为2021年浙江考生,而经此一役陈老师依然稳坐钓鱼台的话,别看我对陈老师的中文颇有微词,这本《高考作文实战实训》我一定买爆。毕竟高考的判卷权在他又不在我,这就是权力-知识的魔力。
自古以来,浙江学子素有文声,明清便不得不以政策压制,避免浙江挤压他省学子的空间。所以浙江主考写出这番点评,让我惊愕之余难免感叹德不配位。不过一点接受了这个设定,倒也变得合理起来。就像前述分析的,政治权力的脱钩,使得学术界与文学界的领军者无意于涉身于高考阅卷,而他们本对应了这个时代翰林的角色。那么阅卷重任自然落到了专事中学教育的陈维新们身上,阅卷工作既不能积累政治资本,也不能与在学界引发学术探讨。经年累月,阅卷者成了这门技术的专家,自然磨炼出了小镇做题家的风范。而缺乏政治资本的做题家,不得不求助于商业出版,一是加深了应试色彩、二是直接催生了借由争议性范文树立权威的此次事件。
这样梳理一遍,倒合理了许多。只不过这些合理之处,最终导致了把文辞不通的文章拔高到“满分范文”这样荒诞的一幕。就如韦伯所说,工具理性的源头是非理性的。这一切的“合理”,追根溯源,莫不是权力与生意的计较,至于文章的价值理性,恐怕早就被扔到一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