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过再多的故事,不如懂得一个原理,或为什么中国人依然不会讲理?
几个月前,我在一个群里说过一句话:“听过再多的‘故事’,不如懂得一个原理”,懂了的都说好。现在有了些闲,也想分享给读友们。
当时,这句话(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金句的味道呢),虽是即兴之言,却也是长期以来的心得。所以,在对它进行阐释之前,请有一点耐心(柏拉图说“耐心是一切聪明才智的基础”哦),容我说说这个“金句”所对应的我一直在感受和反思着的时代语境。
1.
差不多与我说这句话的同一时间,一家自我宣称“新闻专业主义”的“媒体”的一个“记者”发明了一个词儿,“故事会人格”。
缘起是,这位“记者”发了一篇报道——信源只是当事中年男的书面辩白和部分聊天记录,并没有接触和采访到当事未成年女孩;报道的内容一边倒地倾向于中年男,且夹杂着诸多明显不合常理的细节。对于一个足够复杂和微妙的事件来说,这显然是极为“不体面”,又相当“反专业主义”的。
不明真相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自然会引发了众怒。但有意思的是,这位“记者”竟然在朋友圈里反咬一口,指控当事女孩是“故事会人格”。我们可以推断,这个“记者”在朋友圈的表现,显然是一种巴普洛夫式的反应性行为,而这往往会是当事人的自我投射,或心理倒影,其图形就像是一只自我指涉的咬尾蛇。通常所说的“恶人先告状”和“倒打一耙”,就属于此类症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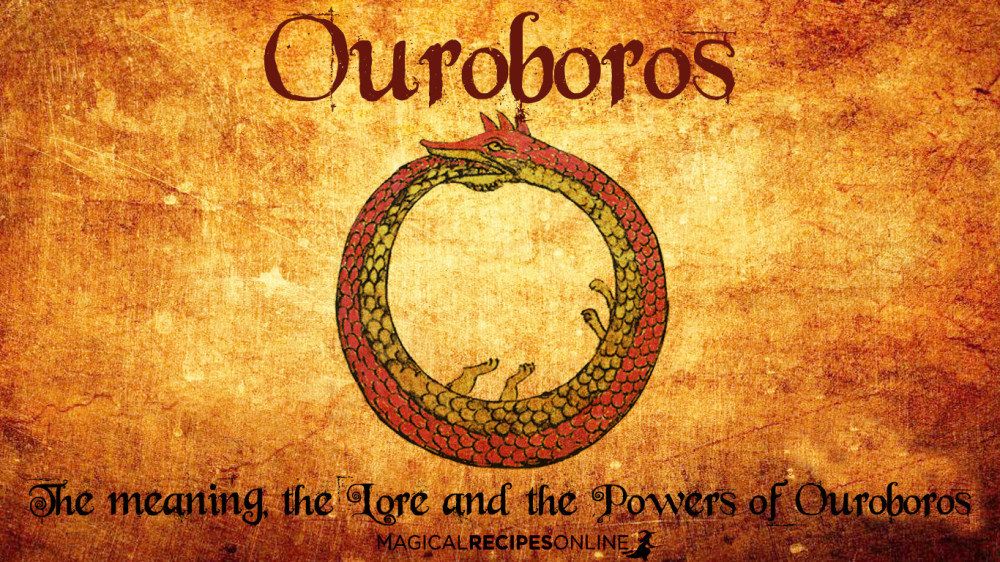
那么,这就是一个内涵(没有“段子”)丰富的病例,值得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心理学和精神分析以及人类学等领域的专业(没有“主义”)研究者好好研究一下(当然,对你我这样的非专业的一般群众来说,自然是免不得反胃和恶心的)。但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记者”倒是做出了自己潜在的学术贡献——以“把自己作为方法”和“道成肉身”(The word became flesh)的反身方式表征出了一种泛媒体-故事化时代的人类学症候。
这种“故事会人格”,绝不是个例,而是时代症候之一种。我们知道,如今国内的诸圈和诸自媒体,热衷于讲故事,编故事,卖故事,擅于以制造“简单粗暴”和“对立化”的叙事来引爆流量和套利,而且,这已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PUA众生的“浪”潮,“风”尚,话术,越来越多的人也跟着内卷了进来,乘风破浪,带节奏,偏风向,拉仇恨,把事故“故事”化,把虚构“非虚构”化,把启蒙“咪蒙”化……
竖子,不止是成了“名”,也成了“精”,并称了“霸”,白骨精吊打起了孙悟空,但最终也无非只是“是非成败转头空”——陷入佛系虚无主义和神经官能症,可怜的是那张“不再被要”的业已丧失了孩提时代曾经令人赏心悦目和产生催产素的“笑能”的紧张、扭曲和抽搐的面部肌肉群集结成的“脸”。
2.
由于说到了“泛媒体-故事化”,那就不得不再加上一个背景。十几年前,我还是一名记者时(是啊,我曾经也是一名记者呢),就不喜欢——不,是很反感——一些记者把新闻媒体喜闻乐报的诸种悲惨的事故轻佻地说成是“故事”的腔调,尤其是厌恶那种津津乐道于如何“新闻专业主义”地操作更能吸引读者的眼球和流量的做派。我们姑且把他们称为“故事”派和“专业主义”派吧,也就是媒体圈儿中自以为是的精英主义一枝。
媒体圈儿中另一支,也就是以“调查”派或“深度”派而著称的草根主义,说实话,在近距离接触之后,我也深度不以为然。凡是自诩为“调查”的,或“深度”的,自身却是最禁不起调查的,也是最没深度的,这些年来就从来没有把一件事情真正搞清楚过。但我对他们还是会有基本的理解和同情的,除了几个跳来跳去的自以为是和自我加冕的蠢货会让人不由自主地厌恶以外。
两边儿我都不想站,我当时的新闻理念是,“放大光明比揭露黑暗更重要”,因为,在“黑屋子”里揭黑,在“粪坑”里掏粪,是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价值和前途的,即便是那些被记者们津津乐道的舆论监督的成功案例,哪一个不是一阵风过后便死灰复燃,一切照旧;而且,这必定是一条不容于当局的越走越窄的死路。这是我在2005年左右的看法。后来是什么情况,大家都看到了,无需再赘言了。
如今,说起这些,并不是想体现一下自己的“先见之明”或智力优越感(正因为顾虑到这一点,此前我对于这个圈儿一言未发),因为我对成为“先知”一点兴趣也没有,自小到大也没有什么“好胜心”,我所着迷和念兹在兹的一直是“致力于成为解决问题的人”,既然是被抛进了一个问题重重的世界,自身也遭遇了诸多困厄,那么,任何一个自尊心未泯的人都不可能不如此选择。当时,我所能想到的方法和策略,就是推进一种不同于所谓的“调查性报道”类型的“解释性报道”(我当时用居里夫人的“元素”与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来类比这两种报道的差异),旨在促进国人之理解力的提升、思维方式的改变和观念范式的转型之类(厘清和构建中国的观念和思维的“元素周期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改造和替换掉人们脑子里的那口“深井”。
不被理解、遭遇挫折是常态,后来,我终于有机会在所供职的一家新创报纸中推动开辟了“时代议题”栏目,但遗憾的是,在几经波折做出来一番声色后,最终还是被一位热衷于“揭黑”的蠢出了天际线的主编给砍掉了——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蠢不到,自以为是热血,其实是狗血。即便是在十年后的今天再看,严肃认真而有策略(孙子曰:以迂为直)地致力于提供国人之理解力的内容依然是系统性短缺的,相反,如前面所说的,利用国人之理解力缺陷而套利的内容和“故事会人格”却是大行其道,肆无忌惮,恬不知耻。
3.
“听过再多的故事,不如懂得一个原理”,想必会有人会由这句话而联想到那句“听过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然后六神无主地认为,学一堆“原理”(道理)有毛用。其实,那只可能是因为:一)你听过的只是一些假道理、伪道理或“旧”道理(吃错了药,或过了有效期),在一个缺乏理性思维的文化和现实中,要是不如此的话,那才是有点不可思议的;二)你只是“听过”但远远没有“懂得”且能“运用”:1)正如没有炼丹炉的淬炼也就不会有火眼金睛,原理的“洞察力”(insight)和“理解力”(understanding)不可能是那么“易得”和“易懂”的,是不是;2)光“道听途说”和“纸上得来”也是远远不行的,还得撸起袖子加油“练”,不是有流行“刻意练习”的说法嘛,是不是。
同时,应该还会有人联想到一个曾经很火的词儿,“第一性原理思维”,众所周知,它对译自马斯克所推崇的“first principle thinking”。但是,我实在搞不懂的是,那个“性”是怎么一点逻辑思维也没有地冒出来的呢,难道是荷尔蒙、力比多或多巴胺在作祟?
事实上,这不仅是对其字面含义的误译,也是对其哲学含义的误解,稍微懂一点哲学史的人对此都能一目了然。于古希腊哲学而言,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它所指的无非是一种“回到事物自身”(being qua being)的哲学思维,循着原理的证明链条而上溯和还原到作为逻辑起点的“第一原理”而已,实际上也就是那种不可证明但是自明(self-evident)的“公理”或“公设”的意思,欧几里得几何学体系则是这种思维的集大成和典范。《利维坦》的作者霍布斯,就是“几何学方法”的推崇者和实践者,通过提出政治哲学的“第一原理”或者说“公理”——“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原理而成为了现代政治哲学之父。
4.
说到这里,想必心思缜密的读者,还想进一步细究一下“道理”与“原理”两个概念的区别或联系。我的观点是,“道理”与“(第一)原理”,讲究的是“物皆同然”或“人皆同然”的普遍性,因此可以说就是一回事儿,从“第一原理”的角度反切来理解“道理”,我们也就更能容易明白这一点,不是随随便便什么话就足以称得上是“道理”的,万万不能因为“伪道理”横行,就把“道理”本身也不当回事儿了而“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掉”。
古希腊哲人区分了“意见”(opinion)与“知识”(knowledge),后者所指并非是我们中国人通常所理解的那种实践性、经验性和操作性的“技术”,而是一种形式性的、逻辑性的和普遍性的东西,在柏拉图的两个世界区分中,前者属于流变的(becoming)、不确定性的因而也是低贱的“可见世界”,后者属于不变的(being)、确定性的因而也是高贵的“可知世界”。在这个意义上的“知识”,其实就是“原理”,就是“道理”(自明的“第一原理”,这隐含了主体-客体的同一性或意识-对象的同一性,类似于中国人所说的“天人合一”)。如今都21世纪了,竟然还会有写手把“知识”与“道理”对立起来,这叫人说什么是好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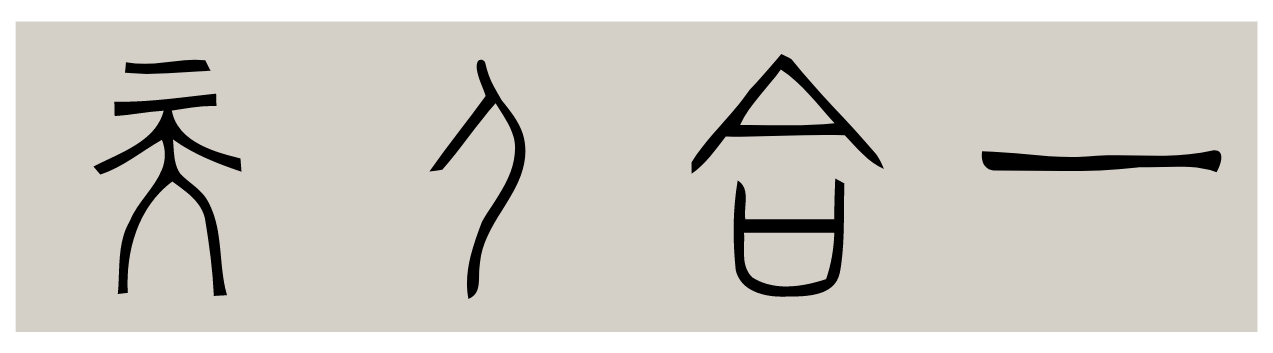
其实,中国的传统思想中,也存在类似的区分,只是要晚得多。例如,清代的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就区分了“意见”与“理”,“(孟子云)心之所同然者,谓理也”,“一人以为然,天下万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之谓同然”,“则未至于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见,非理也”,但是,“人莫患乎蔽而自智,任其意见,执之为理义”。这也是为什么说宋儒理学以来是在“以理杀人”(“以意见为理,自宋以来莫敢致斥者”)。
戴震的“意见”与“理”区分与古希腊哲人的“意见”与“知识”区分之所指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缺陷只是没能做到像亚里士多德那样为“理”立法,建立一套系统的形式逻辑和论证方法(公理化方法),当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Elements)已经由利玛窦和徐光启(1562-1633)部分地译介入中国上百年,但由于备受冷落,加之没有如今的信息通达,估计戴震(1724-1777)是没有读过的。
遗憾的是,中国人至今依然没有学会如何讲“理”,没什么理性能力,惯用的套路是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来搪塞自己的理短或无知,根本就不知道也不会用公理化方法和逻辑来达到“同理”与“同然”(自然),也就是说,每个人依然被困为“意见的奴隶”。所以,哪有什么知识分子啊,充其量只有“意见分子”,或“偏见分子”,例如许知远同学,问题的焦点不在于“偏见”或“成见”并自我辩护,而是如何从“偏见”或“成见”抵达普遍性的“知识”,这才是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的天职所在。
既然缺乏理性和知识的传统,那么,最终以谁的意见为准,以谁为尊呢?历史和现实中的事实一再表明,是以权势大者的意见为准,以最大权势者为尊,这是一种“势即理”历史和文化,讲“势”不讲“理”(名义是“理”实则是“意见”),“讲政治”不讲“逻辑”(日本人把logic翻译为“论理学”),玩“阴谋”而不是尊“理性”,在这样的历史和文化的惯性下,“泛故事化”和“为权势者编故事”的“故事会人格”和人格分裂症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以至于太多人说出来的话,常常是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笑料迭起,造不出芯片搞不了创新,这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即便是“灵魂的助产士”苏格拉底穿越到今朝,他对那些已经是“不孕不育的灵魂”恐怕也是无能为力的。
5.
戴震说:“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孟子称‘孔子之谓集大成’曰:“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由此亦可见,”理“、”条理“或”道理“可不是那么易得的。易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但“易简”却并不易得)
要说清汉语中“理”字的义理和来龙去脉,这至少需要厚厚的一本书来写,但也可以一言以蔽之,既我们中国人始终未能给“理”赋予一种直观、易懂和确定的形式。所以,这一点还必须借助“他山之石”来“攻玉”(《说文解字》云:理,治玉也)。我们知道,数学是西方人的理性思维的母体(Matrix)、“典型”(archetype)和骨架。那么,我们就不妨通过毕达哥拉斯定理为例,来理解“理”——“条理”、“原理”和“道理”。
众所周知,毕达哥拉斯定理的数学形式是a²+b²=c²,我们中国人叫作“勾股定理”,但尤其是商高定理版本的“勾三股四弦五”(3²+4²=5²),只能算是作为一种一般形式(the general)的毕氏定理的一种特例情形(the particular)。但对于更高阶、更一般的余弦定理来说,毕氏定理则又成了一种低阶的特例情形,即当A=90°时,cosA=0,余弦定理的形式c²=a²+b²-2ab·cosA,也就转换成了毕达哥拉斯定理的形式a²+b²=c²。当然,这是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才成立的,在这个体系中,毕达哥拉斯定理又是通过10条最基本的自明的公设和公理(预设了主体-客体、意识与对象的同一性和统一性,于中国人的说法而言,即是“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道”的层次)而一步一步推演出来而得到证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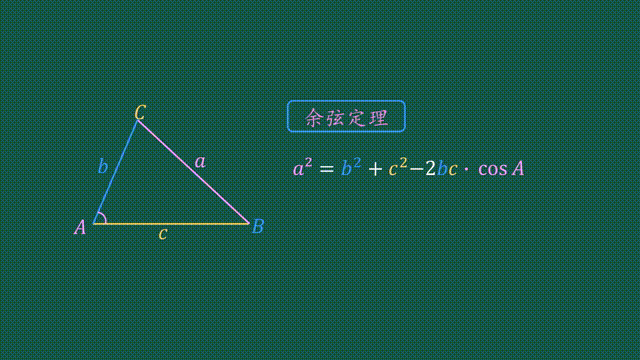
我们不难想象,这种高阶、抽象、一般与低阶、具体、特例的关系,就像是原理与故事的关系,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与居里夫人的“元素”的关系,项链的金线与珍珠的关系,或者房屋与砖瓦的关系(柏拉图曾把哲学知识与技术知识的关系比喻为建筑师和泥瓦匠的关系),也像是哲学中经典的“一”与“多”的关系。我正是在这样的低阶与高阶的意义上来说“听过再多的‘故事’,不如懂得一个原理”的。
至此,我们可以说,一个“原理”(理)之所以称得上是原理(理),是因为它刻画了依赖于某个主体性框架(例如,欧氏几何就是一种主体性框架,而非欧几何则又是另一种主体性框架)的对象体系内部各要素、各变量间稳定的关系结构,换句话说,也就是“变化中的不变性”,或“变量中的不变量”。正是这种结构不变性起着整体的规定、约束和组织作用,使其表现出一种如交响乐团的演奏般的“一体性”、“协同性”和“旋律性”。
那些抓住了某些领域中的“(第一)原理”并灵活运用“第一原理”进行思维的人,心智中也便有了“精神的锚点”、“思想的金线”和如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般的“心灵的眼睛”(Nous,eye of mind),可以“看得见”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例如,超越“权-钱-性”的“尊严、创造和爱”),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人生的持续性投入和连续性积累,也可以一眼洞穿那些假冒伪劣,妖魔鬼怪,魑魅魍魉,从而免于内卷进那些机会主义的短视和陷阱,也就不会最终落得个“故事会人格”和人格分裂症的后果了。所以,你说“听过再多故事,不如懂得一个原理”,可不可以成为一个金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