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博尔赫斯感到失望和痛苦的时候
在博尔赫斯诞辰121周年的今天,我们想要推介他的作品《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巴勒莫》。这篇不长的散文收录在随笔集《埃瓦里斯托·卡列戈》当中。

当提起博尔赫斯,首先会想起“迷宫、镜子、无限与永恒的时间、往复难解的命运”……对于大多数读者——也包括我们——,《埃瓦里斯托·卡列戈》这本集子并不是最初开始了解他的那一本。这本书有关的是一个“旧时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民族性或者地方性的写作并不是为这位阿根廷文学家赢得世界性声誉的主要原因。如果对他的短篇稍做一些列举——《无礼的掌礼官上野介》是日本的故事,《德意志安魂曲》是德国的,《小径分叉的花园》来自中国的文化,《另一个人》的背景架设在美国,《蓝虎》在印度的丛林中……至于另有许多虚构,读者无法在字里行间提取出具体地点的提示,它们似乎有一种神话式的通用感——故事诚然是有关于人类的寓言,但它们并不放在地球上某个真实的地名上,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些寓言超越了某单个民族或者文化的限制,而指向了生与死、时间与空间、命运与巧合,成为了“所有人类”的事情。
不过理解博尔赫斯的地方性或许与理解他的去地方性同样重要。是的,他是一个世界性的写作者,但我们不能议论他为一个没有故土的作者。1899年,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巴勒莫,他在这一片土地上所望见的沉默的黄昏与月亮,祖母带他去巴勒莫动物园时凝望的老虎与玫瑰,停留在皮肤上的那种持久的荒败郊区的气质,骑马来往的高乔人跋扈斗狠的性情,以一种或许消隐的方式溶解在此后创作许许多多(虚构和非虚构的)作品里面。
……当时的巴勒莫只是祖国背后一些荒凉的湿地。最直接的办法是采用电影手法展示一系列静止的画面:一帮葡萄园的骡子,脾气倔的蒙着眼罩;宽广的死水上漂浮着几片柳树叶;一个孤鬼游魂似的人颤巍巍地踩着高跷涉过湍急的流水;辽阔的田野毫无动静;赶往北方畜栏的牛群践踏出来的蹄印;一个农民(拂晓时分)下了累垮的马,砍断它粗壮的脖子;消失在空中的烟。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巴勒莫》
上面这些文字用一些场景的快速剪辑和拼贴提供了知觉的触点,很快也很成功地描摹出了一幅城镇的整体意象。虽然不免突兀,但是博尔赫斯对于故土的白描式追思让我联想起了鲁迅的写作。
鲁迅把《社戏》放在小说集《呐喊》的最末尾一篇。在它之前,《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故乡》这些更为“典型鲁迅”的作品展现了他手术刀一般的尖刻、嘲弄、愤怒和叹息。但是在这些冷峻的笔调之后,《社戏》却表现出一种似乎很不一样的平静与温和。这时候,作者一切向外的疾声呼喊,最后收束在向内的、对童年一段简单平白的回忆当中,那是一种非技法的、个人的怀想和爱意。可能正是因为这种编排顺序,《社戏》才达到了如此强大的情感推动力。因为它足够个人,所以无比平和的叙事就会带以深邃的抒情效果。
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在阅读了大量博尔赫斯更负盛名的作品之后,达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巴勒莫》时会有一种异样的触动。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巴勒莫》显现了一个裸露与真切的博尔赫斯,这在很多其他文本当中似乎并不常见。博尔赫斯并不是一个经常抒发个人化情感的作者。他即便有情感的表露,也是针对一种更广阔和永恒的对象,譬如对于文学和诗歌本身,或者对于“色彩”、“黑夜”和“死亡”这样抽象的事物。他的故事与寓言没有强烈的倾向,没有道德的判断——没有赞美和批判——博尔赫斯似乎只是把自己放在叙事的幕后,对“谜一般的时间”中涌动的事物做一些不失客观的描述而已。许多诗歌当中的抒情,他也是借他人、历史人物或者其他作者之口表达出来。
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巴勒莫》中,他在此处告诉我们:
我把记忆中的这些往事写下来时,忽然无缘无故地想起《乡思》里那句诗:“此时此地,英格兰给了我帮助。”勃朗宁写诗时想的是海上的自我牺牲和纳尔逊阵亡的旗舰——我翻译时把他祖国的名字也译了,因为对于勃朗宁,他立刻想到的是英格兰的名字——对我却是孤独的夜晚,在无穷无尽的街区着迷似的散步。布宜诺斯艾利斯十分深沉,我失望或痛苦时,一走在它的街道上,不是产生虚幻的感觉,便是听到庭院深处传来的吉他声,或者同生活有了接触,这时我总能得到意想不到的安慰。“此时此地,英格兰给了我帮助”,此时此地,布宜诺斯艾利斯给了我帮助。那就是我决定写下这第一章的诸多原因之一。
The city has a depth, and never once, in disappointment or grief, did I abandon myself to its streets without receiving unsought consolation either from a sense of unreality or from a guitar played in thedepths of a patio or from the touch of other people’s lives. “ ‘Here and here did England help me” ’—here and here did Buenos Aires come to my aid.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巴勒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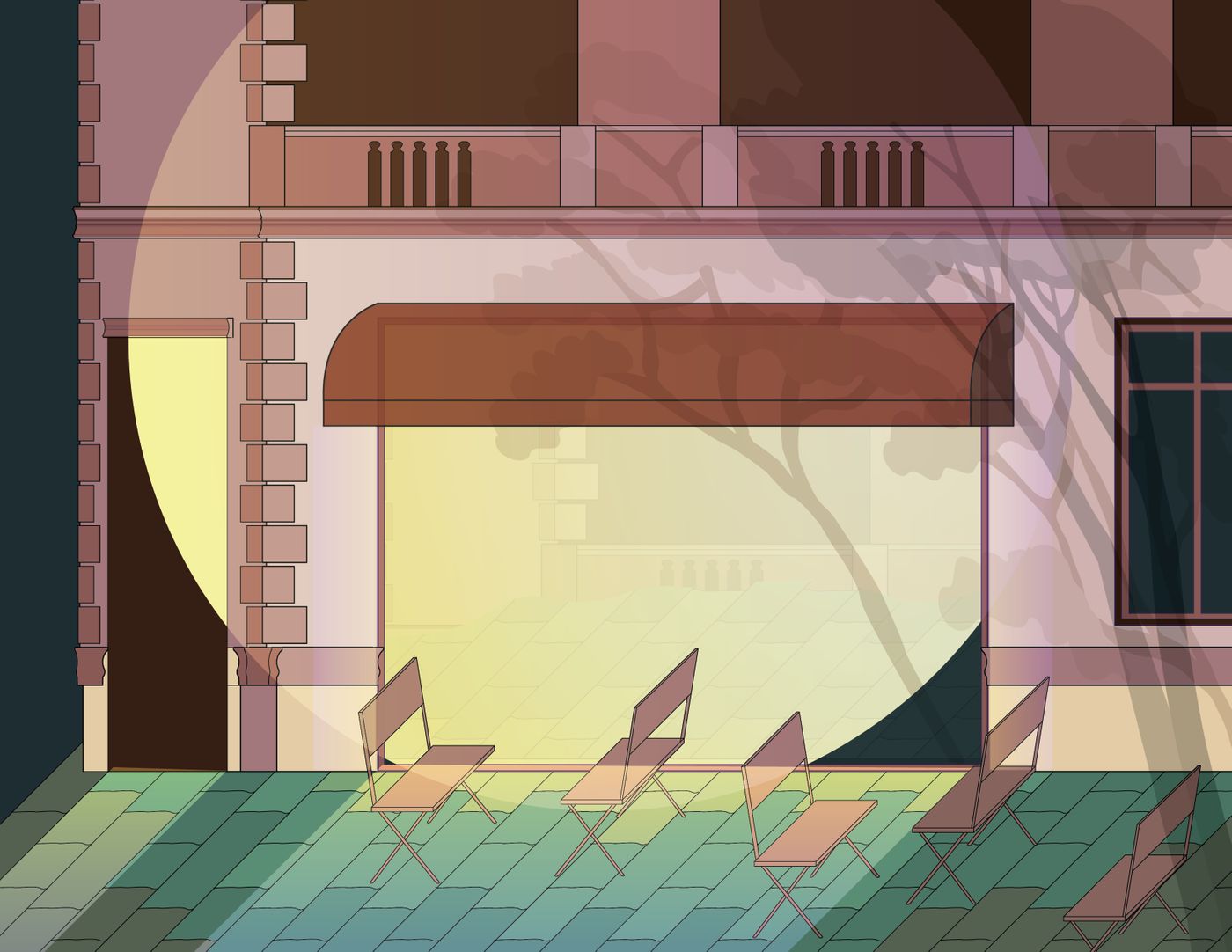
一个在文学的形而上和虚构中居住的人,当他感受到了失望和痛苦,一个实实在在的故乡能够提供深长的慰藉——给予一种“帮助”。在这一篇散文中,作为他人的博尔赫斯变成了私人的博尔赫斯。
对于这个阿根廷人,布宜诺斯艾利斯拥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夜晚巴勒莫宽阔的街道、街角像月亮一样明亮的商店、阳台栏杆后传出的吉他声、动物园的老虎、午后雪茄店玫瑰色的烟雾、夏天的傍晚坐在树下的人群。这些记忆中模糊的空间感受和影像与神秘的故事和寓言交织在一起创造了无数意向,也一直陪伴着他,带给他安慰。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这样一座城市,它记忆和幻想的成分多于此刻的现实。这个城市不仅在我们孤独、迷惑、伤感的时刻,以童年记忆的形态给我们安慰,也同样会变幻出现在我们的梦和想象中,为我们的生活创造独特的诗意。
关注微信公众号沙丘研究所获得一手更新
本文原文链接:当博尔赫斯感到失望和痛苦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