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的边界与民族的发明——《民族的重建》读书笔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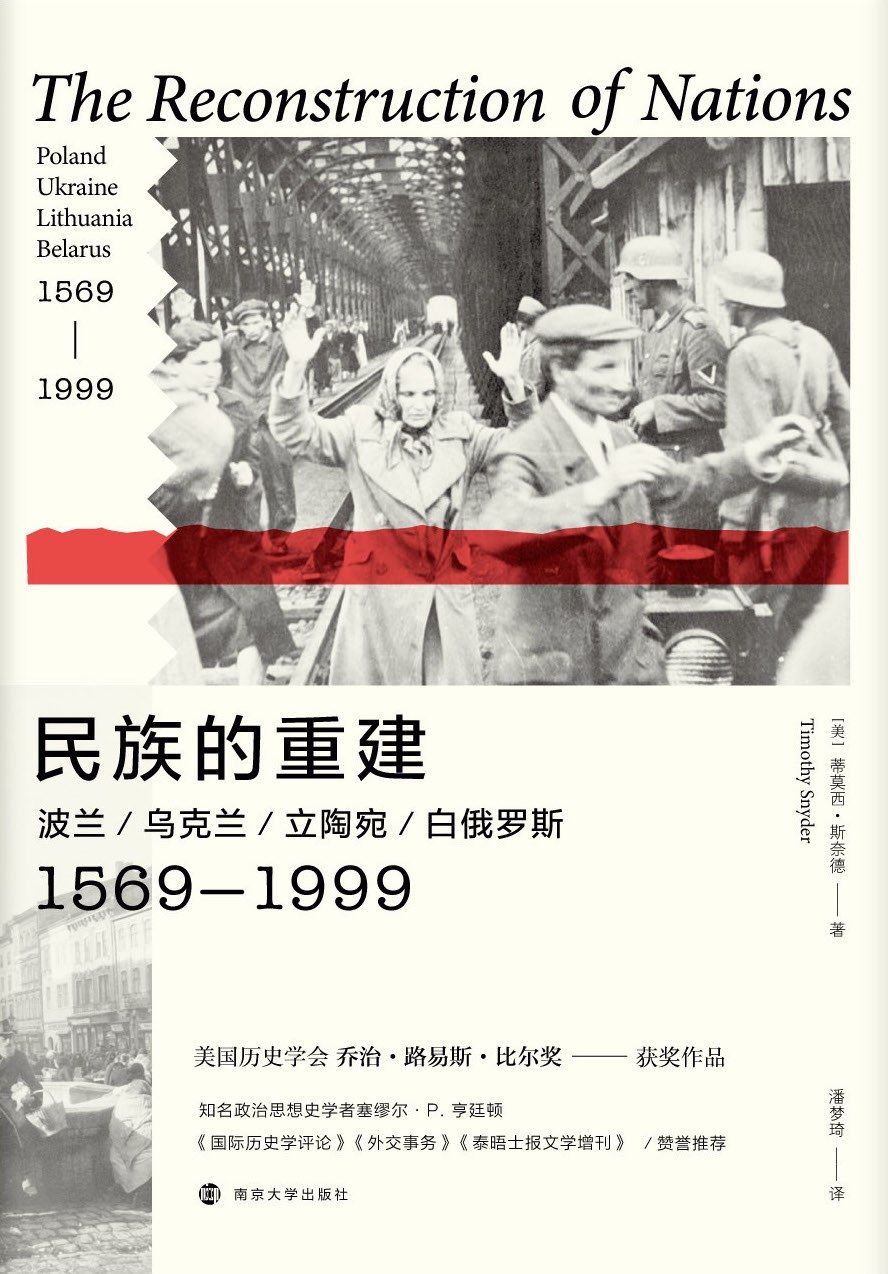
一
通书看下来,觉得书名绝对有误,与其说是《民族的重建》,不如说是《民族的发明》更为妥当。本书作者,蒂莫西·斯奈德,在书中讲的是波兰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传承,指出,今日东欧这些斯拉夫民族,究其实质,都是中世纪波兰——立陶宛王国分裂出来的碎片。
基辅罗斯原来是幅员广阔的东欧强国,后来国家分裂割据,分为若干公国。十三世纪初,蒙古入侵,原有各公国或灭或降,基辅罗斯灭亡。数十年后,乘着罗斯人的虚弱,波兰-立陶宛国家(1568年两国合并)也从西方入侵,逐次吞并了绝大部分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土地。至此,罗斯的东西分裂之势就造就了。在西,是波兰——立陶宛贵族共和国,以文明西来的姿态呈现于世。在东,则是专制的俄罗斯帝国。
这一波兰——立陶宛联邦,同卡斯蒂亚与阿拉贡,或者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联合并无不同,都是情势所需(波兰人想要同哈布斯堡君主拉开距离,立陶宛贵族对西方文明有所倾慕,而东部罗斯人视之为保护性力量),在相当时间内是欧洲边陲的最庞大的一个斯拉夫人共同体(俄罗斯在当时还不被算入欧洲之内),是若干不同宗教、族群的共同家园。
书中有许多细节可以佐证这一共同体的存在——比如,现代波兰的国父约瑟夫·克莱门斯·毕苏斯基,父母其实都是立陶宛的贵族(鉴于立陶宛贵族波兰化的程度非常之深,其实与波兰贵族也无甚差别)。其毕业事业旨在复兴波兰-立陶宛联邦,为其理想的失败痛苦万分;又比如现代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纽斯,虽然在十六世纪之前确实是立陶宛古都,但是到了十九世纪的时候,在这座城市里面讲立陶宛语的人口只有1%到2%(对这一大片土地上的人来说,波兰语是一种高雅语言,是知识分子与贵族的语言,立陶宛语则是一种乡村语言),犹太人倒是占到了该城总人口的40%。无独有偶,直到二十世纪早期,现代乌克兰的重要城市利沃夫中的波兰人口比例也要超过52%,更有75.4%的利沃夫居民声称自己的母语是波兰语;再比如说,在1648年到1657年间曾经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哥萨克起义(这一起义被认为是对波兰王国的极大打击,有大片乌克兰领土从王国中分离开来),起义的哥萨克领袖赫梅尔尼茨基是乌克兰的地方贵族,与波兰宫廷关系甚深。哥萨克的酋长们用波兰货币,使用波兰语作为行政语言,甚至打仗的时候也用波兰语发号施令。当赫梅尔尼茨基决定成为俄罗斯帝国的属国之时,他是读不懂俄语的,只能请人将俄语信件先翻译成拉丁文才能加以阅读;蒂莫西·斯奈德还讲了一个例子,描述的是二战中及二战后波兰人与乌克兰人的相互仇杀。有一次波兰人组织了一支假的乌克兰游击队,以引蛇出洞,结果因为实在是太逼真,导致被波兰军队误击(其伪装如此之好,以至于在场的真乌克兰游击队士兵也无法分辨出这支部队到底是不是他们的人)。在另外一个事件中,一支真的乌克兰游击队被波兰军队包围,他们用波兰语高声唱起波兰革命歌曲,反而被认为是自己人,遂被放虎归山。如此以上种种,都能显示出这些现代民族之间交互交错的亲缘关系。
二
看这本书的时候,无时无刻不让我联想起弗里德里克·巴斯的“族群边界论”。这个可能需要解释一下:
在过去,人们一般认为族群有一些客观实在的基础,但是到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这种客观实在论就受到了多方的批评。比如霍洛维茨(Horowitz)在其名著《冲突中的族群》(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中就指其不可靠,他指出,人们用来识别不同的人群的线索多种多样,“是一个从可见到不可见的连续的集合”,从明显的生理特征(如肤色、面貌、发色、身高到体格)、行为特征到语言文化、经济生活。而选择哪一个线索或线索的组合,似乎是任意的。
以血缘论?卢旺达的胡图人和图西人有着共同的祖先,在语言、体格和文化上都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们在古代可能有着经济生活方面的差别(一个务农,一个游牧)。在中国,汉族和回族之间几乎也没有血缘差距,它们的区分主要是宗教上的(中国的基督教徒却并不被看成是一个独特的族群)。
以语言论?王明珂先生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中以羌人为例,指出说羌语的不一定都是羌族,有些藏族也说羌语。而且羌族间并没有一个彼此能沟通的羌语。从民族服饰上、宗教信仰上及其他文化特征上,羌族都像是汉族与藏族之间的过渡型,难以划定一个固定的族群界限。
以文化论?外人几乎不能在白俄罗斯人与俄罗斯人之间做区分,他们的文化习俗极为接近。比方说在加拿大、美国、奥地利、乌克兰和中亚都有白俄罗斯人存在,但通常被被归为俄罗斯人(而无人质疑)。在印度的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安得拉人(Andhras)和特伦甘纳人(Telanganas)的主要区别在于,安得拉人的脖子上常会围上围巾,特伦甘纳人就不会这样做;特伦甘纳人的语言中有很多乌尔都语词汇,安得拉人的语言中少些;特伦甘纳人的食物比安得拉人更接近穆斯林食物;特伦甘纳人喜欢饮茶,而安得拉人则偏好咖啡。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或”字把上述这些线索/标准总括起来,声称只要满足上面一种或几种就行。但是,为什么在此处以甲线索形成族群,在彼处又以乙线索形成族群呢,中间的选择机制是什么?
而且,人们发现,用于划分族群的线索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常有武断之嫌,“语言、体质、文化在人群间常有同有异:相似到哪个程度就是一个族群,相异到哪个程度就不是一个族群?事实上并没有一个学术上的客观标准。”王明珂指道:“文化特征在人群中的分布,经常呈许多部分重叠但又不尽相同的范畴。以个别文化特征而言,它们的分布大多呈连续的过渡性变化,族群边界似乎是任意从中画下的一道线。因此,以客观文化特征界定一个族群,有着实际上的困难。”
其三,人类学家埃德蒙•R•利奇(E.R.Leach)在二十世纪中期对缅甸高地的观察中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本地的克钦人实际上讲着好几种不一样的语言,社会结构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形态之间来回摆动,这个族群的存在,似乎完全是由其与临近的掸人的冲突与交流来界定的。但是,“这些说不同语言、穿不同服饰、拜不同神灵,有着如此等等之不同的人,并不被看作是完全超越社会认可界限的异乡人”。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有共同的祖先与血缘,是一个群体。这个案例告诉我们,至少某些族群的塑造似乎是主观选择的结果,而非客观的界定。
为了解决上述三个困难,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1969年在其主编的论文集《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提出了著名的“族群边界论”。在这个论文集中,人类学者与社会学者们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见解:那就是,“族群”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存在于与其他族群的互动关系中。对此,巴斯说道,过去我们总认为人类的文化差异是不连续的,也就是说,“既存在本质上分享共同文化的民族集合体,又存在着把每种这样的独立文化与所有其他文化截然分开的相互关联的差异。”人们过去相信,种族差异、文化差异、社会隔离和语言障碍在各人群之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与其说各人群像一个个孤岛彼此隔离存在,倒不如说各人群像大陆板块一样彼此碰撞、渗透。在这些大陆板块上存在无数细小的裂缝,人们完全可以任意选定这条裂缝或那条裂缝作为一块大陆的边界。
巴斯认为,族群是一个自我归类过程的结果,归类的客观依据是有的,但却是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说,假如同时有两种类别/要素(A或者B)可以区分一个群体,该群体视情况选择认同A或者B,其群体的扩大、缩小与伸缩并无定制,要看这个群体与另外一个群体的竞争与交流情况而定。在有些场合下,该群体会重点强调某个(或某些)类别/要素,以便与其竞争的群体区隔开来(王明珂认为,在此区分过程中,这个群体借助创造某种集体记忆来追溯共同的祖先、血缘与历史,以此来模拟类亲缘团体,从而产生了族群)。
王明珂总结道:“族群是由它本身组成分子认定的范畴,造成族群最主要的是它的‘边界’,而非包括语言、文化、血统等在内的‘内涵’;一个族群的边界,不一定指的是地理的边界,而主要指‘社会边界’。在生态性的资源竞争中,一个人群强调特定的文化特征,来限定我群的‘边界’以排除他人。”当然,王明珂也指出,“将族群当作人群主观认同之结群,并不表示体质与文化特征就毫无意义了。它们不是客观划分族群的判断标准,但的确是人们主观上用来划分人群的工具……即使在体质上毫无差别的人群间,如果主观上的族群界限存在,则体质上的差异甚至可以被创造出来。人们经常以刺青、拔牙、拉大耳垂来改变身体本身,或者以衣服、饰物来作为身体的延伸。以此,一群人扩大本族与他族“体质外貌”上的差别,从而强化族群边界。”
在我看来,族群边界论是一种解释力很强的学说,它指出族群是主动构建的产物,但这种构建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还是有客观基础的。这点同社会科学家们对集体认同/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的研究是相当一致的。学者们认为,集体认同/身份的产生有几个基本条件:一是产生了某种社会分类概念/方式,并且为人们所接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重大事件所推动的。这是主观的一面;二是这种分类方式同人们的生活体验所兼容,人们可以从自己既有的社会模式中观察并体验到该分类方式的合理性。而这种既有的社会模式可以说是一种客观存在(尽管未必是唯一的客观存在)。族群的形成与维持其实也是这样子,客观条件指出族群可被观察的内涵,主观论选择则具体描绘族群边界。
美国政治学家霍洛维茨(Donald L. Horowitz)1985年在其名著《冲突中的族群》(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一书中也接受了“族群是一种根据先天给定条件下的动态建构”这一观点。霍洛维茨指出,一些群体在某一种环境下可能会分为两个族群而且彼此敌视,而在新的具有更大异质性的环境中又可能会被认定为一个族群。比如印度的马德拉斯邦(Madras),有泰米尔人(Tamil)和泰卢固人(Telugu),泰卢固人被看成是一个单独的族群。后来1956年印度通过“国家重组法”,规定各邦的界限按照语言界限重新组织起来,于是该邦的泰卢固人获得了自己的邦。在一个大家都是泰卢固人的邦里,泰卢固的族群认同就没那么重要了,很快就被种族、地域和宗教划分的子群体取代。相应的,族群间的文化边界也会涨潮退潮,有时它们会强调文化的共同部分,有时则会强调差异部分。
综上,从族群边界论的眼光看来,族群并不是一个自然存在,而是一个社会存在。它有自然的基础,但出于人的建构。学者们可以从这个道理中推导出很多东西,比如,族群接触的增多不一定会带来族群之间的融合,如果它们各自居于不同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态位的话,倒是很可能会促进异己族群意识的产生与发展。又比如,有的时候族群冲突不是因为族群边界的存在而发生的,相反,族群边界正是因为预计到了冲突才确立起来的(族群文化有的时候也是后于族群而出现的)。
三
话回到这本书,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用“族群边界论”来理解蒂莫西·斯奈德在书中的的描述,再方便不过了——波兰/立陶宛王国这块“大陆”,因着时势的变化,内里的诸人群逐渐沿某条边界分化/发明(强调差异性而非共同性)而成诸现代民族。
波兰——立陶宛王国的兴起自然并非幸致,其分裂其实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初这个东斯拉夫共同体之所以形成,除了波兰武力强横之外,更是因为这个天主教斯拉夫王国背靠西欧,无论是政制、技术还是社会都有文明引介之功,无论是立陶宛,还是乌克兰的贵族都被此高阶文化所吸引,在十六、十七世纪迅速的波兰化。可以预想,如果该王国能够挺过十八世纪的地缘政治冲击,没有发生俄、奥、普“三家分晋”(1772-1795年对波兰的三次瓜分),那么该王国完全可能以波兰为核心进行统一的国族构建,一如法兰西与英吉利。
但是也正由于波兰文化的高阶姿态,使得波兰语人群与其他人群之间的关系有点“内殖民主义”的味道,此种姿态尤其显现在波兰人与乌克兰人之间(立陶宛人与波兰人之间的关系要更为平等)。乌克兰的下层贵族与农民往往要受到波兰贵族与地主的支配(中上层贵族则波兰化了)。蒂莫西·斯奈德写道,1569年之后,一些波兰家族在乌克兰获得了大量的土地,他们带来了大量的波兰士兵以及犹太人助手,大量乌克兰农民由此陷入赤贫之中,时人的抱怨是“(乌克兰人)被视作低人一等的存在,成为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奴隶或侍女……”。自1648年兴起的哥萨克叛乱,就可以看成是拥有军事武装的乌克兰底层贵族与农民对自己缺乏政治权利(由此而带来的经济剥夺)所表达的不满。赫梅尔尼茨基之所以率领哥萨克起义,最初的缘由就是因为一位波兰官员窃取了他的地产、霸占了他的爱人、谋杀了他的儿子,而他本人向波兰宫廷申诉未果。他之所以能获得大批人手,也是因为波兰贵族对土地的侵占导致有大量农民逃向边境成为哥萨克。
波兰地主与乌克兰农民的分野在沙俄时代也一直延续下来(尽管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们的文化隔阂日渐减少),沙俄政府本来完全可以利用这种社会隔阂来加强对乌克兰人的吸纳,但是沙俄政府在1830年、1863年两次波兰起义之后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将乌克兰民族主义也视为要打击的对象(尽管乌克兰人在两次起义中都是配合帝国政府的)。1863年沙俄政府颁布瓦廖夫法令,禁止乌克兰语作品的出版。1876年,这一禁令又被埃姆斯法令所强化,使用乌克兰语的公共演讲、戏剧和歌曲表演都被禁止,教师被撤职,报纸也被关闭。乌克兰民族主义在这种刻意打击下反而成长起来。
一战之后,新生的波兰再度将部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纳入版图之中。独立的波兰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格外关注,乌克兰认同自然显得颇为刺眼。在1924年,波兰颁布了格拉布斯基法,让乌克兰语学校成为双语学校。波兰人不但无意解决乌克兰的土地问题,反而通过迁入人口、加强行政管制,使自己显得格外的“殖民主义”。与此同时,乌克兰人在合法政治中也被边缘化。尽管有三分之一的波兰公民是少数民族,“但是没有任何少数民族代表在波兰政府中担任过部长(连地区和地方长官都没有)。几乎没有重要政治家把乌克兰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民族渴望当回事儿,更鲜有人试图通过向乌克兰精英提供比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更有吸引力的选择,来邀请他们成为同道者。”于是本地的乌克兰人开始慢慢将本地的波兰人同外来的波兰人视为一体,进行反击。
二战作为一场全面战争,彻底撕裂了本地社群,通常的社会控制因素不复存在,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在外来因素的怂恿下开始相互仇杀与种族清洗,在战后更进行了人口交换。乌克兰民族从此发明成功,再无转圜余地。斯奈德由是叹道:“是民族主义导致了种族清洗,还是种族清洗给不同人群贴上了民族标签?”他的意见,多半是后者。
以上只是斯奈德所讲述的四例之一,但通过以上的描述,我们足以发现,至少在东欧,民族的产生是多种复杂力量组合而成,受限于一时一地的社会政治运动、结构与走向。从此历史教训来看,今人不妨放开对民族是由文化定义的执迷,文化的统一是果不是因,切记。
注:本文已发表于《经济观察报》书评栏目,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