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格雷伯:想象一个没有狗屁工作的世界
译者:邢麟舟
原文链接:https://www.dissentmagazine.org/online_articles/booked-david-graeber-bullshit-jobs
译者按:2020年9月3日,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公共知识分子,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猝然长逝,年仅59岁。格雷伯是当代最著名、最具公共影响力的人类学家之一,研究兴趣遍及经济人类学、官僚主义与劳工运动,著有学术、公共领域影响力俱佳的畅销书《狗屁工作论(Bullshit Jobs: A Theory)》《债:第一个五千年(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并在著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担任组织工作。
作为一名(非典型)人类学学子,译者的博士研究计划深受格雷伯教授对价值理论和工作理论的学术探讨的影响与启发,亦喜爱、钦佩其诚恳而尖锐的文风与新奇的思考角度。在此,译者谨以此译文介绍格雷伯教授近年关于工作与劳动的畅销书《狗屁工作论》,悼念格雷伯教授。
Rest in Power, David Graeber.

引言
根据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的估计,我们的社会中几乎一半的工作是毫无意义的。那么这些工作是如何存在的,而这对于劳工活动家又意味着什么?
你的工作是否毫无意义?你是否觉得即使你的工作消失了事情也照样行得通?你是否觉得如果你的工作从未存在,社会甚至会变得更好?
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请你放心,你不是一个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人类学教授,《狗屁工作论》的作者大卫-格雷伯说,近半的劳动者认为自己的日常工作是毫无意义的。
根据格雷伯的说法,几十年来自由市场政策在使得许多人的生活与工作更加艰难的同时,也创造了一大批经理、电话销售员、保险公司官僚、律师和游说者,这些人薪水高昂,所做的工作却毫无用处。为了知晓这么多毫无意义的工作是如何产生的,而这对劳工活动家又意味着什么,劳工记者克里斯-布鲁克斯(Chris Brooks, CB)采访了大卫-格雷伯(DG)。
访谈
CB:你在书中区分了狗屁工作和屎一样的工作(shit jobs),可以简单谈谈吗?
DG:其实很简单。屎一样的工作就是不好的工作,你不想要的工作,比如艰苦繁重,工资低下,无人认可,毫无尊严,不受尊重……的工作。问题在于,大部分屎一样的工作并不是狗屁工作,因为前者并不像后者那样毫无意义或者完全不重要,它们实际上通常涉及真正需要完成的工作:把人们送到某些地方,建造某些事物,照料他人,收拾清洁……狗屁工作往往有很好的薪水,很好的福利,在其中你往往被当作真正完成了需要完成的任务的重要人物对待——但实际上,你知道你并非如此。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两个概念是正好相反的。
CB:你认为这些狗屁工作中多少可以被消灭?这对社会又有什么影响?
DG:我想……几乎是所有吧。从事狗屁工作的人背地里也认为,如果自己的工作(甚至有时是整个行业)都消失,也没什么大不了——或许它们消失后世界会变得更好,比如电话销售、游说者或一些公司法律师事务所。这还不是全部:想想那些为了支持狗屎工作而真正在做事的人们,比如清洁办公室写字楼的人,做安保或除虫工作的人,应付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而努力的人所造成的心理与社会创伤的人,这些工作都可以消失。我们可以轻易地把我们所做工作的一半都消灭掉,而这可能会对许多事情产生巨大的正面影响,比如艺术、文化,乃至气候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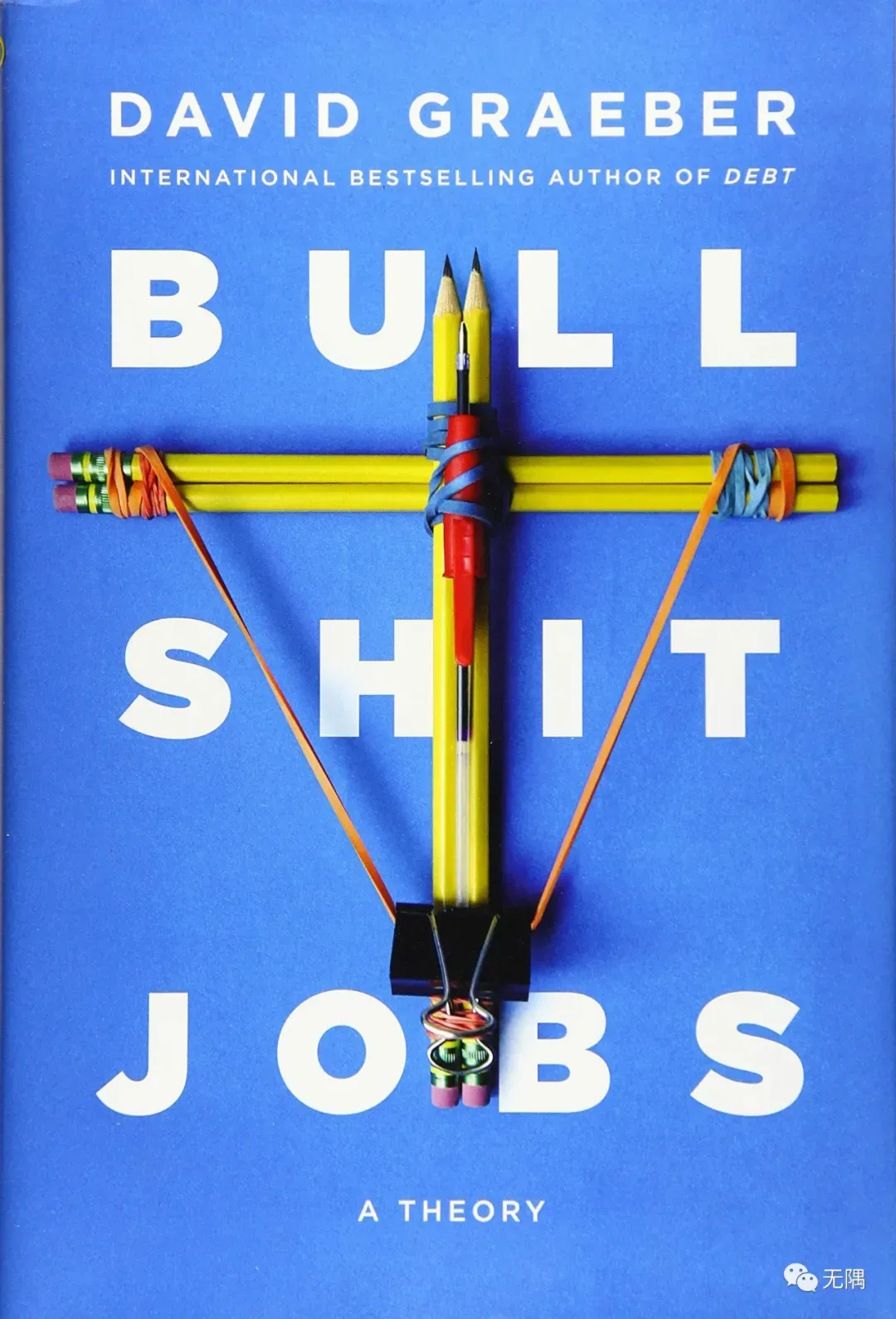
CB:你把狗屁工作的兴起与生产力与薪酬的不匹配连在一起,这一点令我很感兴趣。可以谈谈这个过程在过去几十年中是如何发展的吗?
SG:老实说我不确定这个现象是什么时候兴起的。这里的关键问题与其说是关于经济意义上的生产力,还不如说是关于社会效益。如果一个人从事清洁、护理、烹饪或驾驶工作,你能明确地知晓他们正在进行这些工作以及这些工作为何重要。但如果是品牌经理或财务咨询师,你就完全不清楚这些了。有些工作的有用性及其回报总是呈现某种反比关系,尽管有些例外如医生或飞行员,但总体来说的确是这样。
现在发生的这一切更多是由于无用而又相对高薪的工作岗位的大量增加,而不是因为某种模式上的变化。我们错误地把这个现象归因于服务业经济的兴起,但实际上大部分真正的服务性工作是有用而低薪的,比如服务员,网约车司机,理发师等等,而这些工作的数目完全没有变化。真正增加的是文书、行政和管理类的工作,这些工作的比例似乎在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增加了两倍。这些才是毫无意义的工作。
CB:金-穆迪(Kim Moody)认为,生产力的提高和薪水的低下更多与管理技术的增加有关,比如简约零库存生产以及对劳工的监视技术,而不是和自动化有关。如果这是真的,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公司创造更多的狗屁工作来管理和监视工人,而工人的工作则更加像屎一样。你怎么看?
DG:如果你说的是亚马逊,UPS或沃尔玛,那的确如此。我觉得导致工作节奏加快的监督性工作并不真正是狗屁工作,因为他们至少在做一些事,哪怕这些事不是什么好事。在制造业中,机器人的确在许多行业导致了生产力的巨大提升和工人的大量裁员——尽管留下的一小部分总体上较之前有所提高。然而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同时也存在着在老板(有钱人)和真正的工人之间加塞误用的管理者的倾向,这些人的监督并不能让任何事情加速,而只会拖慢事情的节奏。在关怀性的行业,如教育,健康,社会工作等等中,就更是如此了。在这些行业中,无意义行政工作的增加和真正工作的不断狗屁化——强迫护士、医生、教师和教授整天填写没完没了的表格——导致了生产力的大大下降。
这也是统计数据所显示的——工业生产力和利润在飞涨,但在健康和教育这些行业中生产力在下降。所以,这些服务的价格在上涨,而企业却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挤压劳动者的工资来维持利润。这解释了为什么在世界各地教师、护士甚至医生和教授都在进行罢工。

CB:你的另一个论点是,现代企业的结构相比与市场资本主义的理想型,更接近封建主义。这该如何理解呢?
DG:大学时期,我的老师教我说,资本主义意味着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比如工厂,并雇佣工人进行生产,然后卖掉产品。资本家没法给工人足够高的薪水,因为这样他们就无法获得利润,但他们又必须至少能让工人的薪水足够购买工厂的产品。而相比之下,封建主义意味着你通过收租来获取利润,让人变成负债者,不断压榨他们。
如今,大部分公司的利润并不是从制造或销售产品而来,而是从“金融”而来——这是“从他人的负债而来”的一种委婉的说法,包括收租和收取利息。这正符合许多人秉持的封建主义的经典定义:基于政治关系的直接压榨。这也意味着政府的角色非常不同:在古典资本主义中,政府只保护你的财产,又或许会监管你的劳动力以免他们的生活太过艰难;但是在金融资本主义中,你是直接通过法律体系榨取利润,所以政府规章制度是绝对的关键。一般地,你需要政府的背书,才能通过他人的负债来压榨他们。
CB: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市场狂热者们的主张,也即资本主义不会或不可能会产生狗屁工作,是错误的。
DG:正是如此。可笑的是,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倾向于基于这个原因攻击我,这是因为他们一般还秉持着当下的资本主义与1860年代的资本主义等同的概念——在1860年代,许多小型的、在制造和销售商品方面竞争的公司构成了资本主义。如果你是说个体经营的餐厅,那这的确是成立的,我也同意这种餐厅一般不会雇佣他们不需要的工人。但如果你是说主宰当下经济的大公司的话,它们的运营遵循着完全不同的逻辑。如果利润是通过收取行政费用、收租或创造负债来榨取的,如果国家深入地参与者剩余价值的榨取,那么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差异将逐渐消失。为了榨取利益而获取的政治上的忠诚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商品。
CB:狗屁工作的兴起也有政治上的根源。在你的书中,你引用了奥巴马总统的一句特别惊人的话。你能否谈谈这个引用,以及它对于狗屁工作的政治支持意味着什么?
DG:我主张,狗屁工作持续存在的一个原因是它们为许多有权势的人在政治上提供了方便。当然,很多人因此将我指控为患有妄想症阴谋论者——尽管我认为我实际上写作的是一部反阴谋论(即为什么有权势的人不走到一起,试着解决当下的情况?)。那一则对奥巴马的引用正是这一点的确凿证据。他大致说道:
“每个人都说基于单一付款人的医保会远更高效。当然,它可能会高效,但我们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因为重复和低效而在各种相互竞争的私人医疗机构工作。如果我们保证了高效,这些人该怎么办呢?”
所以,他承认了自由市场可能会更低效,至少在医疗行业是这样,而这种低效正是他想要的——因为这种低效使狗屁工作得以持续存在。
你从未听过政客们以这种方式谈论蓝领工作,比如“这个领域是市场规则消灭、工人工资被挤压最严重的行业,如果蓝领工人受到了损失,他们怎么办呢?”例如,奥巴马似乎就并不对在经济危机和纾困后因裁员和工资大幅削减受苦的汽车工人有同样的忧虑。所以在他们眼里,有些工作比其它工作更重要。在奥巴马的案例中,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非常清楚的:正如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k)最近所说,民主党在1980年代作出了一个战略决策,即放弃工人阶级,而把专业群体和管理人员阶级作为他们的核心支持者。现在,狗屁工作的从业者已经是他们的基本盘了。
CB:在你的书中,你强调,不仅是民主党在制度上助推了狗屁工作,工会也是如此。能否介绍一下工会是怎么做的,而这对于工会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DG:人们过去常常讨论滥雇,也即坚持雇佣不必要的工人的行为。当然,任何官僚机构都倾向于拥有一定数量的狗屁工作岗位。但我的重点在于对作为一种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方案的“更多”工作的持续性需求。增加就业这种要求是你一旦提出,就没人能拒绝的,因为你并没想着不劳而获,而你只是要求被允许通过工作丰衣足食。就连马丁-路德-金著名的向华盛顿进军运动都被标榜为一场关于“工作与自由”的运动——因为如果你想要有工会的支持,就一定要要求更多的工作。
从六十年代开始,一支激进主义思想开始把工会看作滥雇问题的一部分,但我觉得我们应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工会一度为更少的工作和更短的工时摇旗呐喊,但现在却从根本上接受了消费资本主义所植根的清教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妥协,接受了工作应该是一种苦难(所以好人就是能吃苦的人),工作的目标是物质丰盈,而想要消费就必须吃苦的信条?

CB:你在书中花了很大篇幅来探讨传统概念上的“工人阶级”工作是多么错误。具体来说,你主张工人阶级工作往往更接近与通常和女性联系在一起的工作,而不是男性在工厂的工作。这意味着公共交通工人的工作和教师的照料工作比和建筑工的工作更加接近。这和狗屁工作有什么关系?
DG:我们往往认为工作的基本部分是制造事物——每一个行业都被其“生产力”所定义,哪怕房地产也是如此!然而实际上,我们用脚后跟想一下就知道,大部分工作什么也制造不出来。这些工作是关于清洁与润色,照看与挂怀,帮助、抚养与修理。你一下子就可以制造一个杯子出来,但你要清洗它上千次。这也是大部分工人阶级工作的本质——保姆、鞋匠、园丁、打扫烟囱的、性工作者、清洁工、洗碗工等等总比工厂工人多。是的,甚至是公共交通工人,在这个售票机都已经自动化了的时代,也仍然很多,他们需要处理孩童走失,乘客不适,劝退醉酒者等等的工作。
然而,我们的价值理论只关心“生产力”,并把这个事实排除在外了。我认为,重新思考工作的价值是十分重要的,而随着自动化使得照料性劳动越来越重要,这种重新思考也会变得更加重要,尤其是因为照料性劳动是我们不愿自动化的。我们可不想让机器人来劝退醉酒者或安抚走失的孩童。我们需要在我们真正希望人类来从事的劳动中看到价值。

CB:你的狗屁工作理论对于劳工活动家有什么价值?你说你很难想象一个反对狗屁工作的运动是什么样的,但你能否为工会和活动家们开始解决这个问题给出一些简单的想法?
DG: 我喜欢探讨“照料阶级”的反抗。工人阶级一直是“照料阶级”,不仅因为他们承担了几乎所有的照料性劳动,更是因为他们因此比富人更关心他人(顺便,这是心理学研究的成果)。你越富有,就越不能理解别人的感受。所以试着把工作想象为一种照料的物质延伸,而不是把它当成一种价值或目的本身,是一个好的开始。
但这是一个长期过程。在更短期的意义上,我们需要想清楚如何反抗专业-管理阶级,由此反抗狗屁化。在七月份,新西兰的护士们进行了罢工活动,他们的一个主要诉求是他们的实际工资一直在减少,但另外一个诉求却是他们在填表上花费了太多时间,以至于无法照顾病人。这些填表的工作在许多护士的工作中占据了超过一半的时间精力。
这两个问题是相互联系的,因为所有本该用于持续提高其工资的钱都被挪用到雇佣新的毫无用处的行政人员身上了,而后者又为他们增加了更多狗屁工作以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然而,这些行政管理人员往往也是被同样的党派,甚至是同样的工会代表的。我们如何制定出一个实践计划来对抗这些现象?我认为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战略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