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楊小娜
原文於2016.8.23刊登
作者/ 丘琦欣 Brian Hioe
翻譯/ William Tsai
今年5月6日,《破土》編輯丘琦欣透過Skype訪問了楊小娜。楊小娜最近出版了敘述台灣白色恐怖與威權統治的小說《綠島》。她目前任教於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的創意寫作課程。
丘琦欣(以下簡稱丘):我想問的第一個問題是,可能還有人沒聽過你,你能不能簡單介紹一下你自己,以及你的出身背景?
楊小娜(以下簡稱楊):當然。我在加州長大,父母親是在台灣相識的。我的母親來自台灣,父親是美國人,但他的母親是德國人,他其實出生在德國。我在北加州長大,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讀大學本科,然後在加大戴維斯分校攻讀創意寫作碩士。我也寫了一本關於沙加緬度三角洲華人社群的書,那是我的第一本作品《水鬼》。如今我寫成了第二本書,是關於台灣的。
丘:能不能談談是甚麼樣的歷程促成了《綠島》的寫作?近年來以台灣為題材的英文小說並不多見,那麼,是因為甚麼促使你探討台灣史這個主題?
圖片:Anna Wu Photography
楊:我在大學畢業的時候,打算搬到台灣和我的親戚同住一年。在我出發時,我的寫作指導教授跟我說:「你會帶著一本書回來。」我那時從字面上理解,以為他的意思是我在台灣會寫很多東西,最後出成一本書。但結果並非如此。
後來發生的事情是,我在行程結束前參觀二二八紀念館,讀了葛超智的《被出賣的台灣》。我太震驚了,因為我對這些事一無所知,那是1999年,因此我覺得人們對這些事並沒有太多討論。
所以這個故事是從我的無知與驚詫產生的,我想:「哇,為什麼人們都不知道有這件事!人們應該知道的。要是人們知道這個故事的話,對台灣的想法或許會改變很多。」我想,我理解台灣及其境遇的旅程是由此開始的,我一開始去台灣的時候真的不瞭解她的歷史,只知道最基本的資料。多年以後我總算明白,教授說的帶著一本小說回來是甚麼意思──我在心中種下了種籽,即使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領會。
丘:你會不會覺得,在某種程度上,引領你走上這段旅程的也有對認同的探索?
楊:對,我會這麼說。我從大學時代開始對自己的混合認同思考得更多,原先我對這件事一直有著自覺,但那只是我個人的認同,除此之外我並不多想甚麼。然後我上了大學,那是1990年代的柏克萊,談的全是認同政治,於是我加入了Hapa Issues Forum這個亞裔混血學生社團。經過這些討論,我開始對自己的認同、也對台灣思考得更多,可能因而促使我前往台灣。
丘:那麼,我覺得你從二二八屠殺開始寫起這件事情很有趣。你剛剛提到這本書寫作的開端,是你參觀了二二八紀念館。《綠島》從二二八屠殺開始,一直寫到SARS危機。我認為這非常獨特,因為這個時間斷限並沒有太多英文作品寫過。
比方說,人們很容易忘記台灣曾經有過美軍基地,或是黨外運動有這麼大一部份都在台灣之外,以美國為重心,這是其中幾個例子。是因為甚麼讓你在設定上聚焦於這段時期?
楊:關於這點,我確實是因為參訪了紀念館而想要從二二八屠殺開始寫,同時也因為我覺得那是一個軸心點。根據我所做的訪談,那場屠殺也是他們開始對自身認同產生不同想法的起點,因為那時他們才剛脫離日本殖民統治,過去被皇民化教育灌輸了日本意識,但心裡明白自己不是日本人;然後國民黨來了,他們覺得:「好吧,中國人來了,或許我們是中國人。」接著卻又體會到:「不對,我們也不是中國人。那我們一定是台灣人,對不對?」
 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圖片:維基共享資源
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圖片:維基共享資源
我覺得二二八真的讓這一點明確起來,因此想要以它作為開端。我想,其中大部分應該是從我做過的訪談裡得知的,尤其是我曾經訪談過的那一代台裔美國人,因此黨外運動當然也是他們的重要經驗和話題。再者,我也覺得以這段時期作為小說設定同樣令我著迷。
丘:那就說得通了。你是怎麼研究這段經歷的?你剛才提過訪談,訪問台裔美國人和那些經歷過二二八的人。
楊:我和一些仍然健在,還記得二二八的人談過。我也和一些二二八受難者的家屬談過,還有一些也許從父母口中聽過二二八,但年紀太小記不清楚,後來成為海外留學生又遭遇過其他事情的人。
丘:那麼,你會把《綠島》的目標讀者群設定在哪些人?它是為了美國人、台灣人,還是台裔美國人而寫的?比方說,我注意到《綠島》最後有一個附錄,列出延伸閱讀書目。
楊:這個嘛,我想我試著寫給兩群讀者看。其中一群讀者是台灣人和台裔美國人,還記得威權統治時期的一代。我希望這本書對他們來說是真切的。我希望他們讀了之後覺得:「哇,她怎麼有辦法想像得到我們的遭遇?」
我也得到了一些像這樣的回應,太令人驚奇了。有一位女性寫信給我,差不多是這麼說:「你今年幾歲?在哪裡長大?你怎麼知道我的人生是這樣?」(笑)這樣的回應實在太棒了。我希望它聽來、想來都是真切的。
而在另一方面,我想要構思一個故事,讓完全不認識台灣的人讀了會說:「嘩,我真沒想到。我甚至不知道台灣是甚麼。但我現在知道了關於台灣的這一切,還想知道更多。」我努力想要同時兼顧這兩端。
丘:那麼,在這層意義上,我們是否也可以談談這部小說和亞裔美國文學的關聯?以及和離散經驗的關聯?我的意思是,你的故事主角又一次是個出生台灣、移居美國的人。我們稍早談了一些認同問題,以及面向不同目標讀者的差異。這樣的話,你在當代亞裔美國文學中會怎麼定位《綠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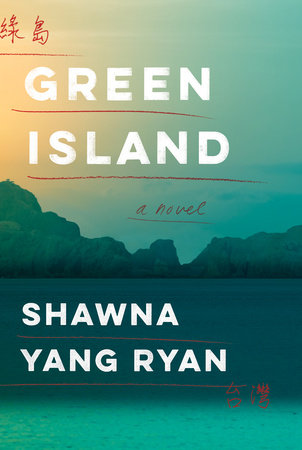 《綠島》書封
《綠島》書封
楊:這問題不容易回答。我也教亞裔美國文學課程。我開始寫作的時候,或者說,我讀大學的時候,亞裔美國文學指的是湯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譚恩美,或者還有李昌來的作品。到了我現在教課的時候,已經有這麼多作品了。我感覺它無邊無際。
比方說,我開了一門亞裔美國都市文學課程,因此我們讀林景南(Ed Lin)的偵探小說系列,也讀林韜的《台北》。有這麼多作品產生了。現在還有科幻小說及其他不同文類,我認為這非常好。
那麼,我的書可以放在其中哪個位置?或許有些老派?因為它是歷史小說,而且更直接觸及認同問題。我認為有些新近的文學作品,故事情節和認同關聯不大,主角恰好是亞裔美國人。這些課題如今是更被隱沒的。
我也認為我的書是不一樣的,因為它不僅是女性主義的家庭小說,也是政治驚悚故事,我試著結合不同文類。當然,正如你在你的書評裡提到的,它也是個關於台灣的故事。它和台灣人比較相關,和台裔美國人關係不大,對吧?我其實沒有提到太多主角女兒的事,她們是在美國出生的。
我也看見自己試著以書寫抵抗鋪天蓋地的中國敘事。像是:甚麼叫做華人離散?人們或許是在這個過程中落腳於台灣的,但我也想要給予他們一個自己的地位,不被含括在那個泡影裡。我目前一直試著透過學術會議做這件事,試著籌辦會議,以不同方式思考台灣。最近我主辦了一個討論島嶼地帶的會議,將台灣納入其中,而不是讓台灣成為中華世界的某種附屬品。
丘:接下來我想問的是在台灣引發的回應。華文媒體對於《綠島》有很多報導,尤其是關於《紐約時報》的書評。能不能談談在美國、台灣兩地,從我們先前提到的像是美國人、台灣人、台裔美國人之類的不同群體產生的回應?
楊:那篇書評一出刊,我就看到Reddit上關於專訪的討論串裡,有人在上面說了這樣的話:「哦,不過又是個想當譚恩美的,被洗白了的亞洲女人。」他們連書都沒讀過,不是嗎?有這樣的回應。幸好,有些人跳下去為我說話。那真把我惹火了,實在令人不悅。
我想,這是預期心理可能會產生的結果。讀者看到封面、看到我的名字,又看到書的大小和「一部宏大的家族史詩」這句介紹。但我要把話說在前頭:我認為譚恩美奠定的基礎十分重要,她寫下的作品也真的很重要,但這是一道陰影,籠罩在每一個亞裔美國女作者頭上,因此我覺得人們看到我的書也以為是那樣。
 《紐約時報》對《綠島》的報導
《紐約時報》對《綠島》的報導
他們讀過之後又說:「太黑暗了。」或是,「太壓抑了。」「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但實情是,我已經收斂了黑暗的部分。我會覺得:「哦,這還不夠黑暗。」本來是要更慘的。像是刑求的場面,我的編輯就跟我說:「你要輕描淡寫一些。」敘事者受到的摧殘更重,因此我把她軟化了。
但人們還是說:「這是我讀過最黑暗的一本書。」這也就是回應了。美國讀者則是說:「我以為蔣介石是好人。我以為他是我們的朋友。這本書把學校教我的事全都推翻了。」我也聽過很多這種回應。
丘:真有趣。
楊:人們常常來找我,跟我說這些,像是「我完全不知道發生過這種事。」然後台裔美國人,特別是出席朗讀會的時候,很多人都想在讀者提問時間分享自己的故事和經驗。我想,這本書為他們開啟了一個談論自身經歷的契機,這實在太美妙了。
他們說想要把這本書送給孩子,讓孩子們了解他們的遭遇。至於台灣人的回應則是支持鼓勵。剛剛有人傳給我一篇文章,小說《複眼人》的作者吳明益在文中提及這本書,並且談到說出這些故事是多麼重要。真令人興奮。
所以整體上,我覺得回應是相當正向的。就像你說過的,這個主題並沒有太多人寫過,正因如此我才要寫。告訴人們這個故事,讓人們說話三句不離台灣。
丘:我的最後一個問題是,你想對台灣讀者和全世界讀者說些甚麼,做為結語?
楊:這本書很黑暗,但我認為,它終究還是傳遞了希望的訊息,讓人們知道改變是可能的。書中的人物受困在時代之中,受困於戒嚴法令之下,他們看不見隧道盡頭的光,但終究是走出了隧道。他們走到了歷史轉變的那一刻,因此我認為,這終究還是一本懷抱著希望的書。我想,這就是我要傳遞的訊息:就算是在改變看起來不可能發生的時候,還是有可能改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