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譜的閱讀與閱讀的系譜 | 尼采伴我思 | 電子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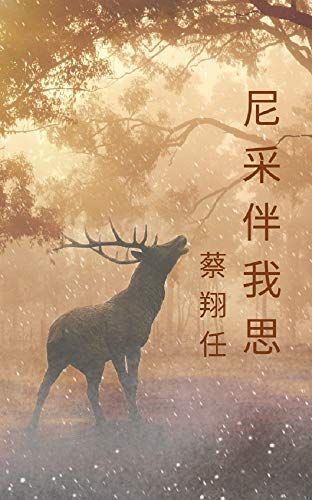
註:這幾篇文章不是我的作品。是我幫朋友編輯、出版電子書後,做為行銷讓人試閱的文章。
<系譜的閱讀與閱讀的系譜>
作者:蔡翔任
是我錯得離譜嗎?當我認為在此發現了好的閱讀所採取的那種貴族習慣之遺風。(je me
trompe absolument en prétendant découvrir ici la trace des habitudes
aristocratiques prises dans les bonnes lectures.)—波特萊爾〈德拉克瓦的作品與生平〉
(一)
讓我用一種很漫不經心的方式,先從今天閱讀的兩本書—《顏氏家訓》與《葉隱聞書》—談起。這兩本作品都是學在家門的代表。既稱家學,必有強烈的自我意識,尤其是顏之推三次被俘而易主,必然把頑強的生存意志灌注在家訓中。然而,顏之推表現出來的還是一種儒家式的平易跟親切:「夫聖賢之書,教人誠孝,慎言檢迹,立身揚名,亦已備矣。魏、晉已來,所著諸子,理重事複,遞相模效,猶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吾今所以復
爲此者,非敢軌物範世也,業以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序致第一〉)。意思是,家訓跟聖賢的政教之道相比,實乃卑之無甚高論,不足為外人道。
相反地,山本常朝把家臣之學提升到很崇高的地位,就算不是至高無上,也是自成一格、不能用聖教或其他任何智慧體系的尺度來衡量:
「無論釋迦、孔子,還是楠公、信玄公,他們誰都不是龍造寺鍋島家的家臣,不曾以家臣的身分侍奉過我藩,所以不能說他們適合我藩當家的家風吧!……如果是當家臣的家臣,就不該傾心於他國的學問,而應該專注於本藩的國學傳統。在此基礎上,稍為涉獵其他學問流派作為遣懷,倒也無妨;但是如果要潛心鑽研,那麼與我藩的歷史和傳統不相稱的學問,就應該絲毫不為所動」(〈前言〉)。
這話講得何等驕傲啊!我們看到,山本並沒有把世間所有的學問都放在一個普遍的基準去看,不同身分有不同的基準。所以,不但公卿、武家各有各的標準,而且武家中的幕府大將軍、大名、大名之下的家臣,其衡量學問的尺度都各自不同。因此,就山本自己的身分—家臣的家臣—觀之,最高的生命的學問就是家臣類型的武士道。那是甚麼東西?
那是把禪宗的漸/頓之辯證吸收到武士訓練的一種隨時可以覺悟「死狂」的瞬間之道:
「緊要關頭不是突如其來的,是由許多『眼前的眼前』堆疊起來,都是眼前要做的。平時就要開動腦筋,仔細搜索眼前的一切可能,以應付那緊要的瞬間。疏忽了一瞬又一瞬,既然每一瞬都可能死去,那就要牢牢把握死。武士於每天早晨醒後所想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該怎麼死,彼時死還是此時死,想著身著盛裝的死姿,就能拋棄對生的執迷」(卷二˙第43節)又「平日的訓練終於發揮了作用,眼前一閃而過的瞬間,真正的男人已完成了武勇的表現」(卷二˙第44節)。
那種死狂,就是道本身,它頗類似巴塔耶所謂的無條件、無保留、不可使用的、不可被道德與理性所中介的純粹耗費,那就是赤裸裸的存在本身:
「比正義更高者為道,發現『是』很困難,若能做到,就是最高智慧的擁有者。從『是』的角度觀察,『義』便不夠充分飽滿了」(卷一˙第42節)。「奉公武家所要達到的目標,應於一開始就有所覺悟:要麼做浪人,要麼準備切腹」(卷一˙第87節)。
由此標準衡量,山本認為赤穗47浪士(電影我只看過基努李維和柴崎幸那個版本)的報仇,雖然都已抱著切腹的決心,還是不純粹的,他們混雜了兵學算計的心機而汙濁了武士道的純粹行動。這標準之高令人震驚,這就是為人家臣的最高美德。
(二)
對此尼采想必不會感到震驚。對他而言,人類最早的那一批美德,都是修羅式的:
「最多樣的經歷教會了他們,所有那些依然存活下來、並總是得勝的神祇和人們,是首先要感謝哪些特性才得以至此。他們稱這些特性為美德,就單單把這些美德培養壯大。他們很強硬地這麼做,甚至願意強硬;每一種貴族道德(aristokratische Moral)都是不留情面的(unduldsam),在對青年的教育上、在管束女人上、在婚姻禮俗上、在長幼關係、刑法等方面。他們把不留情面本身放入美德之列,掛在『正義』(Gerechtigkeit)名下」。—《善惡之彼岸》第262節
在尼采看來,人類是越來越普遍的、純粹的、齊一的。一開始,其實沒有所謂的人類,有的只是來來往往的各路人馬,帶著自己的美德而交會、摩擦、衝突、合作、混同或相互迴避。在1880年代,尼采為什麼甘冒不韙地使用種族、人種、血緣、類型、世系、身世、出身、雜種、混種這類的字眼,並開口閉口等級秩序(Rangordnung)、貴族、高貴這類不合時宜的封建觀念?
其實,尼采的種族觀念,一方面可以是一般意義的種族(希臘人、猶太人、德國人……),一方面又大過於此。先不論後者,即便是前者的意義,今日的我們顯然已經對於種族歧視太過神經質了,乃至於,如Allan Bloom所說的,對民族特徵的敏感已經消失。對我而言,那就是一種「戒禁取」,是矯枉過正的邪見。它對一些種族特徵(外貌、習慣、動作、生活方式等)只是視而不見罷了,就像印度人看到有人大小便就直接從將它視覺中消除,但那事物本身還是在那裡。但這種戒禁取更令我擔心的是導致對各民族、各國家的歷史興趣缺缺,或許這容我有機會再聊聊。至於種族的另外一種意義,我覺得尼采所指稱的涵蓋甚廣,有點類似但又超過古典思想所說的血氣或意氣(thumos),那可以是體制、文化、道德、宗教、教派、藝術等等。在尼采那裡,種族的這兩個意義多半無法分辨得那麼清楚,所以它是一種概括的、直觀的、靈活的哲學把握,雖然可以被其他學科所挪用(比方韋伯對Ressentiment有保留地採納,見《世界諸宗教之經濟倫理˙導論》),但卻無法被科學所取消或取代。我會說,那正就是一種閱讀方式。
舉例來說,《舊約˙創世紀》不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家系(Geschlecht)故事?然而,它也是一部民族史、一則犯罪紀錄、一份精神檔案、一種人格類型的最殊勝刻劃。有甚麼理由能禁止我們把它跟《葉隱聞書》還有《顏世家訓》放在一起對照閱讀呢?我最近越來越懷疑,會不會今日的讀者有個最不自知的理解前提:國家?也就是說,我們不知不覺是用國家—這個已經變得太理所當然乃至貧乏的東西—去圈限了我們理解事物(特別是過去的事物)的先決條件。這裡的國家,我是指保障著法治、人權跟平等主義的國家。所以對應於此,我們無意間都是以「國民」或「公民」的身分—同樣貧乏的道德—去閱讀的,這會讓我們對過去不忍卒睹,並無法認同像是《堂˙吉軻德》中騎士動不動就賞僕人耳光那種殘忍的樂趣(尼采卻說當時的讀者是心安理得被此逗樂,見《道德的系譜》第二章6節),故索性不再看過去。 尼采提出系譜,不僅是要我們去看出系譜,還要讓我們看出自身所屬的來歷。閱讀—在此等同於任何的理解活動—本身就有不同的系譜。波特萊爾對此同樣敏感,他在德拉克瓦那裡讀出了一種貴族式的閱讀習慣,而在《惡之華》〈告讀者〉,他不是更恣意妄為地把我們這些讀者歸為「偽善者」之族類?而我們對此不應更不陌生嗎?我是指,有此一說,《水滸傳》是強人說給強人聽的。
電子書可在這些地方購買:
Amazon Kindle Store:https://www.amazon.com/dp/B07WP5D8QZ
Pubu:https://www.pubu.com.tw/ebook/202879

另外,蔡翔任的詩集【日光綿羊】可在此購買:https://reurl.cc/Q3Yle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