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7日,和Kent的最後一天
2016年10月22日,我在奧斯陸第一次見到Kent。那時,我以為那就是我和Kent的最後一天。
我登錄了遺棄許久的豆瓣,幾乎顫抖著把我的經歷寫下來,沒想到因此與久違的豆友重逢,他因護照遺失,去不了Kent在斯德哥爾摩的終場演出,於是將票轉賣給我。
這場意外之旅,是我最寶貴的記憶之一。三天兩夜的行程裡,我只拍了幾張照片,害怕相機代替我的眼睛去記憶這一切,因而無法專心感受那場一生一次的旅程。我用盡全力將畫面刻在腦子裡,如今一切仍歷歷在目。
這篇文章寫於2016年12月20日,首發在豆瓣,截至今天將近四年。我一直覺得,文字比照片能更好記錄過往,所以這些年過去了,哪怕文章裡有錯誤,也沒有再碰過一回。
很驚奇的是,近四年過去了,我還時不時會收到「點贊」的提醒。不禁一想,或許,我的記錄比我想像得要有意義。或許,是時候好好修訂一下文章,增添一些照片和影片,讓它更有聲色一點。
原文章我不想碰,那是彼時的寶貴記憶。不如,就重新發表一篇吧。
以下便修訂版的《12月17日,和Kent的最後一天》。
三萬多人,帶著不同的故事,來到這相同的場地,參加這場盛大的告別演出,掌聲、尖叫、哭泣後,又各自回到各自的幸與不幸裡去。想到這畫面,心裡空蕩蕩的,被Kent生生拿走了一塊。
(一)
這是我第一次來到瑞典。第一次,一個人,去完全陌生的國家。第一次,住12人集體宿舍式青年旅社。第一次,一個人,去看演出。
這一次我有備而來。來之前的一個半月,我學了好些瑞典語,聽歌幾乎只聽Kent,我記下了演出曲目的順序,我買了折疊凳和雨衣,我查好了去了青旅的路線⋯⋯
我住在Skanstulls Hostel,飛機之後坐機場快線到T-centralen,然後坐綠色地鐵(17、18、19號)到Skanstull,從右邊出來,走過兩個紅綠燈就到了。
大街上一眼就看到了藥店,apoteket這個詞我記得,心裡暗自得意。進去買了退燒和祛痰藥,發現瑞典人也並不是人人都說流利的英語。
來到青旅再次驗證了這一點。已近晚上八點,前台要下班了,用蹩腳的英語跟我解釋了一通各種事宜,期間我們手舞足蹈著筆劃,好不容易都弄明白。
12人的房間,大家都是旅客,卻沒有我想像中那樣歡快聊天,大家都只是呆在各自的角落,互不關心。
晚飯時,就近去了中餐館,要了一碗15個餃子,85瑞典克朗(約8.5歐元),比我想像中要便宜。
餐館裡,只有一群老人在大聲聊天,一個中年男人在默默吃飯喝酒。老闆和老闆娘在隔屋里普通話和四川話夾雜著聊天:有一天,一個老婦在這裡偷了兩隻碗,抓到了還不承認,摸著她的袋子問她裡面是什麼,她才羞紅了臉。結賬時,一位蓬頭垢面、牙齒已掉光的老婦口齒不清地要了一瓶酒,坐到角落裡獨自喝。老闆們看著她,說她是常客,也是可憐。
北歐漫長的夜晚能把孤獨無限放大。
(二)

「17 december 2016, tillsammans på väg till kents sista konsert.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七日,一起去Kent的最終演唱會。這是粉絲自發為Kent舉行的最後遊行,發了黑白小紙旗,上面有這樣的話。
斯德哥爾摩第一晚過後,我起得還算早。問了青旅前台去Tele2 Arena的路線:坐Hagsätra方向的綠色地鐵,在Globen下,就兩個站,Tele2 Arena是個龐然大物,我一眼就會發現它的。

十點左右到達那裡時,幾乎一路無人,龐大的建築物讓孤身一人的我有點害怕。我圍著鳥巢似的演出場地轉了一圈,猶豫著要不要和那零星幾個年輕人一起挨凍。
斯德哥爾摩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冷,地上結了冰,如果不刮風還是可以忍受的。但是我膽小又害羞,鼓不起勇氣和陌生人搭訕,怕他們和我「hej」後就只顧用我聽不懂的瑞典語聊天,不願意用英語費勁了解我這樣一個亞洲人⋯⋯ 我總是想最差的結果。
我躲進了附近的麥當勞裡,一直到中午。

還是決定去參加遊行,雖然,那可能意味著佔不到前排位置了。
我這樣安慰自己:奧斯陸我已經站過前排,演出精彩絕倫,我已經沒有遺憾了。而為Kent遊行,這會是最後一次,不能錯過。
不到一點半,我就到了Medborgarplatsen,廣場上在放Kent的歌,已經有很多人提早到了。

拿了一面黑白旗,我尋找著搭訕的對象。可終究還是膽怯,我不知道說些什麼。在人群裡穿梭時,和一個亞洲面孔含笑點頭,因為她疑似韓國人,我還是沒能說上一句話。我說什麼好呢。
後來偷聽到模糊的中文——台灣口音——我想起Firth那個台灣迷妹,心想或許是她。於是,我問他們是不是台灣人。他們說是。我問女生:妳不會就是Firth吧?她說不,Firth一會兒會來。
不過,我最終還是沒有看到她來(我在演出結束後,終於見到了Firth)。這對台灣人也去到了人群中。
我依然是一個人,這注定是場一個人觀看的演出。

人群中,有人化著「 Då som nu för alltid 」影片裡打鼓女生那樣妝容,其他人大多一身全黑——因為這是給Kent送葬的遊行。
下午2點,化著類似妝容的打鼓隊出場了,一陣既莊嚴又激動人心的鼓聲後,人群跟著警車、鼓隊、旗幟向Tele2 Arena走去。
我就走在舉旗人之後,身後有幾個男生時不時高吼「喔噢哦-喔噢」——「 Då som nu för alltid」影片裡的調子。那短短兩三分鐘的影片,集合了過往唱片所有重要的元素,宣告了Kent的解散,宣告了我的心碎。
大家跟著唱起來,我們試圖創造影片裡的場景。
鼓聲有時停了下來,應該是打累了,可馬上男生們又會帶頭起調,鼓聲繼續響起。有時相反,人群的歌聲淡了下來,鼓聲反而越打越響,似乎在給人群鼓勁兒。

走了三四十分鐘,也許更久,終於到達場地門前,大家鼓掌叫好。
組織這次遊行的其中一個粉絲激動地流下淚,我見了也好想哭,想去給他一個擁抱。
(關於這次遊行的詳情,可以參見Facebook上該活動頁面,活動名叫「Hyllningsparad till kents sista konsert」,討論里許多人發了照片和視頻。據警察粗略統計有5000人參加了遊行。)
這時天色已晚,即使只是下午三點多。我從餐館裡買了壽司當晚餐出來,天色便已全黑。風刮得更大了,有點後悔打包外吃。在寒風胡亂快速塞了幾口,只求趕緊吃完,好把手放進溫暖的口袋。
吃完後就去排隊了。一直到17點,第一波安檢開始。
欄杆打開那一剎,大家高呼,然後快速地向大門口跑。安檢人員攔住跑步的人,讓他們慢一點,其中就包括我。
在大門口,又等了漫長的三十分鐘,像做了三十分鐘的瑞典語聽力理解,因為我邊上的一個男生一直用極快的語速和朋友聊天。那時,我覺得瑞典語真的挺好聽,它的語調和法語好不一樣,是完全不同的好聽。
大門開後,我有些迷失方向。場館巨大,昏暗的藍色燈光下,我根本搞不清哪裡是舞台,慌亂地跟著人群走,沒想到他們是去廁所!我更慌了,跑起來,再次被保安攔住,他用英語跟我說:slow down !
等我到達舞台時,場館中央已站滿、坐滿了人,但靠邊還有前排位置。猶豫好久,我還是選擇了靠邊。至少累了還有欄杆可以靠,說不定演出結束能和成員握手呢!懷著這樣的想法,我安心坐到地上。

19點30分,大屏幕上出現了倒計時。還剩7分47秒時,大家歡呼起來,我抓拍到了那一秒,興奮不已,左邊的女生因此和我相視而笑。
還剩兩分鐘,人群歡呼。還剩一分鐘,人群再次歡呼。還剩十秒,人群開始倒數:tio,nio,åtta,sju,sex,fem,fyra,tre,två,ett,noll!!!
(三)
因為不是第一次參加最終巡演,又仔仔細細研究過網上其他人錄製的完整視頻,這最後的演出對於我更像是去朝聖,少了一些驚喜但仍然激動。當大屏幕上打著鼓的姑娘出現時,我還是感動得想哭。

不知是不是因為我有備而來,因此有了錯覺,我感覺開場以及中場間隙都加快了很多,打鼓姑娘的臉幾秒就變了,而在奧斯陸,我感覺有幾分鐘之長。之後的第一次和第二次返場,我感覺還沒來得及吹哨,樂隊就重新上來了。
演出的完整曲目順序如下:
- Intro (打鼓那段)
- Gigi(只有女聲合唱)
- 999
- Stoppa mig juni (lilla ego)
- Romeo återvänder ensam
- VinterNoll2
- Var är vi nu?
- Hjärta
- Andromeda
- Egoist
- Vi är för alltid
- Inna allting tar slut
- Den vänstra stranden
- La Belle Époque
- Ingenting
- Kärleken väntar
- Vinter17(這是新歌,之前沒有以任何形式發布)
- Jag ser dig
- Musik Non Stop
- Socker(之後是非常短暫的中場閒聊)
- Utan dina andetag
- Sverige
- 747
- December(之後是第一次退場)
- Förlåtelsen
- Dom Andra
- Mannen i den vita hatten (16 år senare)(之後是第二次退場)
- Den sista sången
有幾首是我沒有料到會演唱的:
「 VinterNoll2 」,怎麼會唱這首B-side呢?我想應該是為新歌「 Vinter17 」做鋪墊,其實我並不確定這就是歌名,只是網上大家都這麼說,演出時Jocke沒有做任何的解釋⋯⋯
「 December 」,也沒想到唱了這首B-side,或許因為演出正值十二月⋯⋯
我曾經一度妄想,期望在現場聽到我最喜歡的B-side作品「M」,可惜再也沒有機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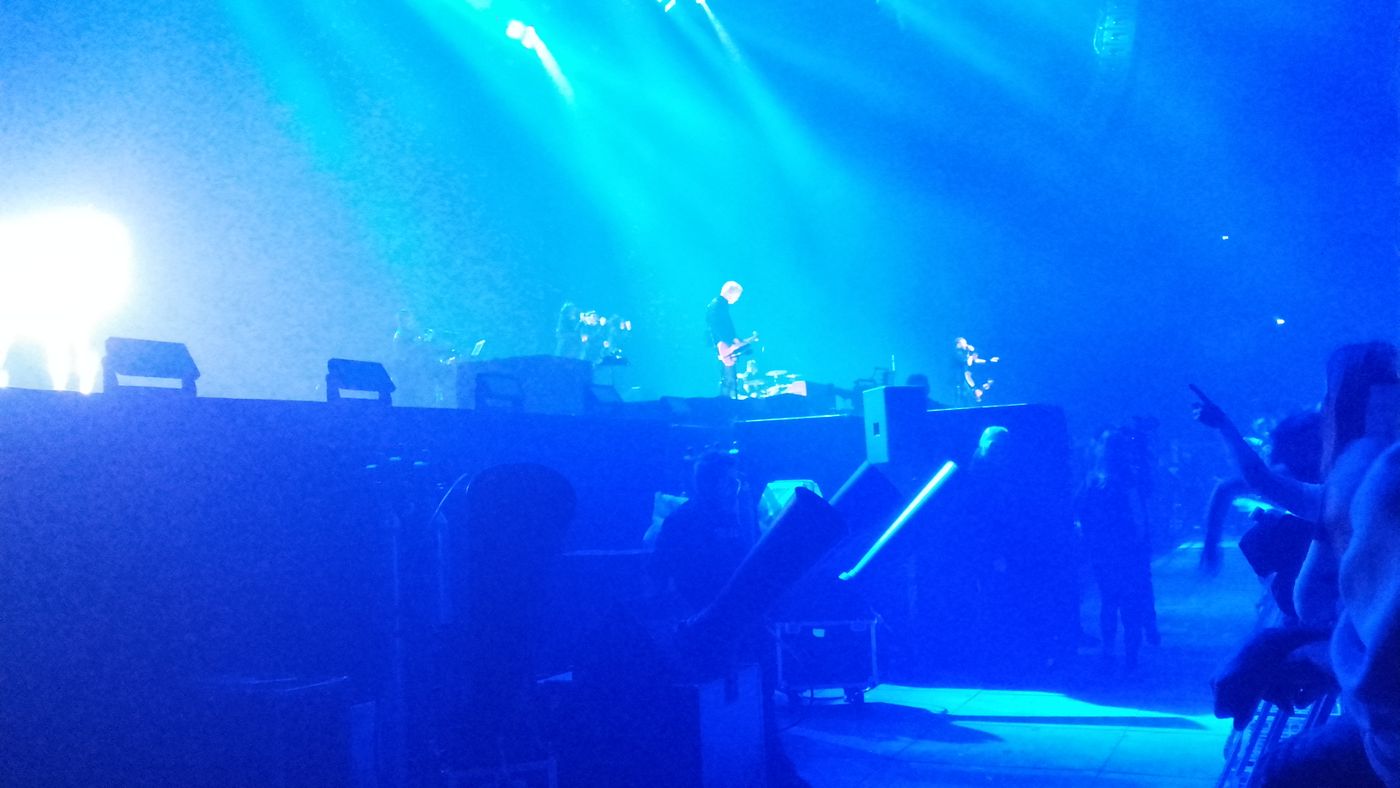
每一首歌都是一場大合唱,我身邊的姑娘們都能跟著唱。可是她們都好冷靜,除了用力揮舞手,偶爾扭動舞姿,從來不會激動地跳起來。
雖然,我清楚知道Kent不是一支能讓你想pogo的樂隊,但是,聽到「Egoist 」難道不會讓你們想用力蹦躂嗎?我雖然羞澀,但一到「 vi ska leva leva livet… 」,整個人都忍不住了,就算只有我一個人,也必須蹦躂,必須用力甩頭!
我的左邊是一位個頭很高的女生,比我高出一個頭。當然這在瑞典太常見,我隨時被淹沒在人群裡。她從不知道哪一首開始就一直哭,一直哭,哭到妝全部花掉,到「 Dom andra 」時她已經泣不成聲,後來讓工作人員給抬了出去,在一邊坐著休息。
我的右邊是一位帶著眼鏡的女生,她比我還矮,真的不太常見。她和我一樣不愛拍照,不愛錄像。她總是帶著微笑,讓人心裡感到無比欣慰的微笑,跟著唱時時而會閉上眼睛,感覺整個人都沉浸其中。
整場裡,我不停哭了又笑,笑了又哭。有一次她看見我在哭,撫了撫我的臂膀,對我微微一笑,就這一個眼神讓我無法忘記她,這是我在斯德哥爾摩感受到的第一縷溫暖。演出時,即使她有朋友就在她身邊,她也會時不時望向我,和我相視一笑,真的好感動。
接近尾聲時,我想應該是「Dom andra 」時,或者「MIDVH(16AS) 」時,我已記不太清,她也難過得似乎在流淚。她看了我一眼,我摟著她的肩緊緊擁抱了她一下。而她,在演出結束後,給她的朋友一個擁抱,然後給了我一個擁抱,一句話也沒說,離開了現場⋯⋯我連名字都沒有來得及問。
可我永遠都會記得妳,那個在如此寒冷的斯德哥爾摩的冬天給我溫暖的姑娘,妳讓Kent的演出對於我更加有意義。

演出之前,官方極力宣傳一款為演出專門設計的APP,除去裡面的拍照功能,其實就是一款燈光軟件,巡演最後三場裡在「Sverige 」和「 Dom andra 」兩首歌時使用。
「Sverige」時,就是一個手電筒。幾乎所有人在黑暗中舉起「手電筒」,那場面實在太美,像點點星光。
而在「Dom andra」,就是一個一閃一閃的手電筒。看到身後的觀眾群變成閃閃的星星,真的很讓人感動。這似乎是在呼應「Den sista sången 」裡那句英文:The stars are up. One fell down and flew away. 而這款應用就叫作「Den sista sången」。
「Socker」之後的演出間隙也格外短,比起在奧斯陸Jocke劈裡啪啦嘮叨了十多二十分鐘,這次簡直短得不可思議。
Jocke指著Sami說:Sami。指著Markus說:Markus。指著Martin說:Martin。他用英文說:「You guys, I love you. 」似乎在表達強烈的愛意上,全世界非英語國家人民都有共識:用自己的語言說我愛你難說出口,得用英文說。
他一度強忍情緒,看向身後。要知道,如果控制不住,哭了,那接下來的演唱會變得多麼困難。觀眾們瘋狂為他鼓掌,尖叫,跺腳——狠狠跺腳,現場一片嘩啦啦的腳步聲。最後他什麼都沒說,便突然起了音樂,開始了「Utan dina andetag 」。
這是Jocke在舞台上最後一次介紹樂隊成員了,這真的是最後一次了⋯⋯
「 Den sista sången 」,最後一曲,真的就是最後一曲,Kent拋棄了我們,而我們還傻傻站在原地,不敢相信這個事實。
沒有玫瑰嗎?沒有。
沒有握手合影嗎?沒有。
沒有最後最後最後的輓歌嗎?沒有。
什麼都沒有。
Adjö, Kent.
反應過來時,大家抱頭痛哭。我沒有人可以依靠,我的眼淚流到臉頰上,流到心裡,流到一片空蕩蕩的心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