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文藝》之回顧,及我們的初衷
我們創刊已經六年,時光如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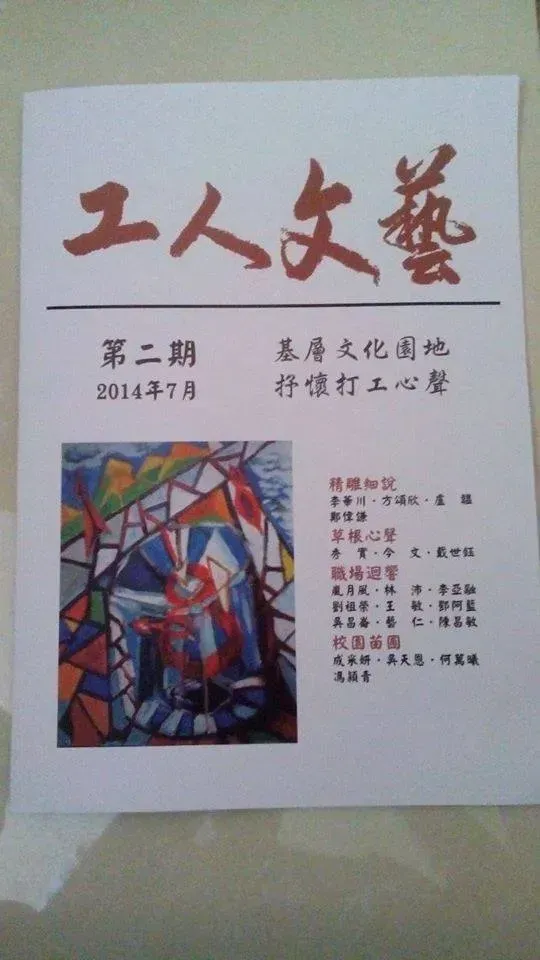
流通率不足,吸引力不足夠,本土的作家不夠多,來稿題材多元性有限,或是很多未盡完善之者。望將來的日子,我們承擔更多,乃令我刊日趨完善。星馬,印尼,美國乃至內地的朋友,都表示我們是華人社會中少有的,聚焦於基屠及工人的文藝雜誌。他們找不到一個文學平台可以為日出之段的辛勞,有喘口氣的空間。
立足本土固然是我們的要旨,但是自工人文學獎,或工人文學的概念從我城播種,四海朋友旨當此為盛事。畢竟,本土只是一個很有限的概念,而工人,普羅的仰息,是共同的經驗,豈可以以國土邊界來劃分 ?
人類的勞動,是普世的,生活的痛苦,是普世的,普羅的操勞質感,是普世的。立足本土,是為了在我們的土地,用艱辛的生活中得到的同理心,把四海的工友,連繫在一起。
文學是具生命力的東西,有人教訓過我,作家是不可以抽離勞苦而得到作品,這樣抽離的作品,只是用最美的詞句,堆砌一個大而無當的垃圾。
雷蒙卡佛不是因為到他人的醫療所做清潔,看見自己及他人生活存在的困窘,才有作品中那妙極的終結。赫拉巴爾不是放棄汰學博士可以為他帶來的成就,在不同的崗位,車間打工,他如何可以把人命運無奈及荒謬,像公案一樣拍醒內心沉睡的我們?
齊格菲藍茨寫的,不是他痛苦逃亡的後對歷史,對自己及他人的重新思考嗎。
回顧當初欲創立《工人文藝》時,我們所希望的,是除了提攜一下香港本土總是被忽略的筆耕者之外,再者是讓文學創作及欣賞的動機帶到基層街坊工友身上。我們在推動本土作家投稿,令他們成為作者群的方面,現時來說是略有起色。在街坊工友推行的過程之中,卻總遇上困難。問題並不是因為學歷上的問題,也不是他們對於文學有既定成見。而是大眾都有的問題,對閱讀文本的動機興致缺缺,及大家都把焦點放在更具即時反應的媒介,即智慧型手機身上。文學對比起信息,變得累贅而且難有共鳴。
三年多以來,我們的投稿人士的主體,多是來自青年學生,或是已經有一定寫作經驗的作者,偶爾,有內地的產業工人願意與我們分享他們的故事,為我們這些早已脫離了工業產業經濟的人明白那種日復一日擰扎的境況,而我們面臨的另一個困難是,我們很少會收到屬於香港人的職場新聞,而且本土作家都喜投詩作,除詩之外,我們希冀他們可以投稿不同的文體,散文及小說難寫得好,然而好還是好是次要,重要的是曾經都嘗試過勾勒都市的生命與命運,在在寫作中成為互為主體,具同理心的人,生活感就可以在人性的洞察之中,被發現。
工人有的是他們的質感及生命的重。工人的文字,是用來築夢的,那為何我們可以做上面那美麗的夢,不能釋懷的夢,是因為有太多人在冷風中的卷城,用雙手犧牲自己的夢。我們或許欠一份感謝,但是人的尊嚴竟可以被剝奪,竟然被無理由的咒罵?
這是我們投入活著的夢之前,所經驗的生命的重嗎? 夜,太長了。
工人文學,作為一種概念,乃如初生牛犢,它不停被眾工友,作者,勞動者去塑造,去雕琢著。普羅民眾勞動中的肌肉,這一份生活質感,把它們都躍在紙上,如同一件琢磨的石膏像,盼待成形。但又不像石膏,他是活著的。
既然是活著,你就一點一點的消亡,如果是有一些真的永遠活著的東西,那就是已經永遠逝去的東西,不斷的勞動,卻又被不停的忘卻,時空抹去了他們的痕跡。這矛盾辨證的邏輯,才是我們為什麼存在的原因。
一時的勇氣,虔誠,熱情,感觸頃刻逝去,你們會稱這就是活著,然而消亡是我們因為看事物的日常,習慣了,理所當然了,以為永恆都存在著,這是真正的消亡,因為你忘記了你的消亡。
工人沒有祖國,文學也有四處飄泊的命運,經驗在不同面孔皺紋中訴說。訴說因為操勞永不止息,而不會停止。因此,琢磨不休止。我們在一場寧靜而漫長的戰爭。為了大眾了解為他們服務的工人,清潔的,加工的,守候我們家園的,跟車的,紮鐵的,我們在此,有機會聆聽他們的聲音,閒聊,鐘愛的東西,生命中的詩意,工傷,危險的處境,不合理的待遇,時不時有著無私的精神,默不作聲想把事件做好,有時微笑,有時操勞,更多的是擔心,更多的是期盼,絕大多數在等待希望。
讓我們寫下去,是我們希冀的機會,不會就此消亡的證明。
在此,我需要感謝每個投稿予我們雜誌的人,你們都使我們成長,而且為我們帶來了雜誌如何走下去的思考。
支持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