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的意义:写于二十九岁之前
这个标题有种年终总结的味道,毕竟二十九是个质数,似无纪念之必要。但我倒没有生日前回顾的习惯,只是忽然想起大二时,写了一篇《写于十九岁之前》,不觉已是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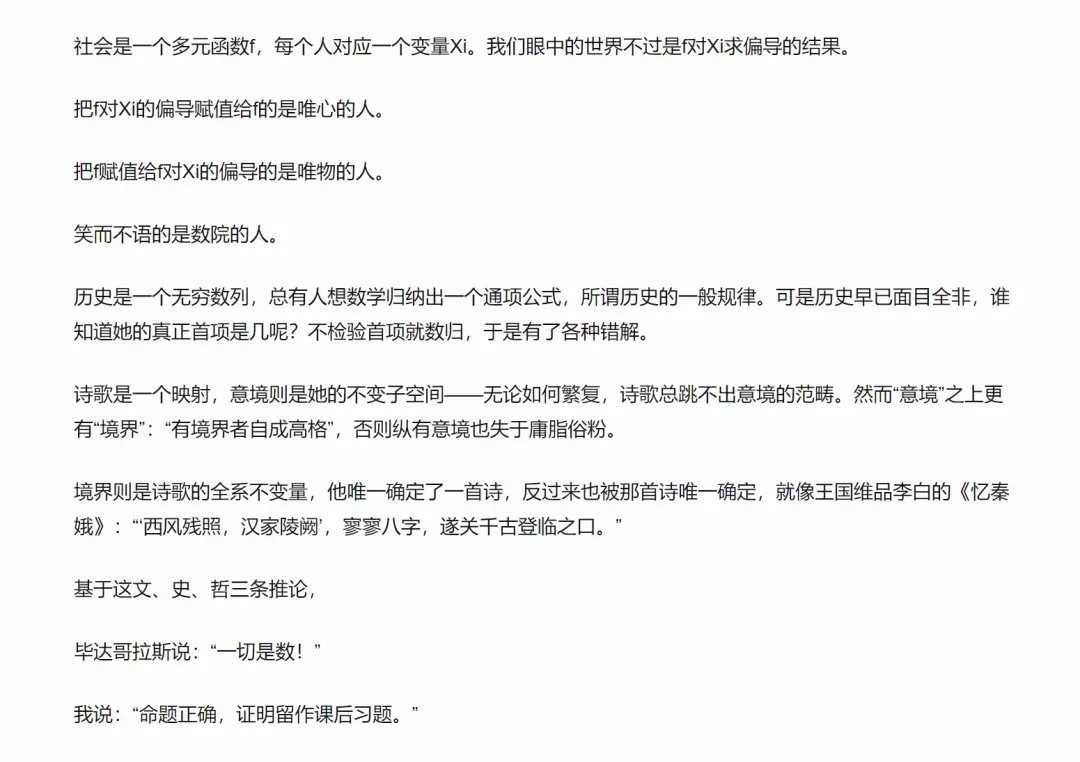
重读那篇随笔,有种莫名的抗拒。好像阅读一个陌生的十九岁少年,读得越多越觉得与自己的割裂,还不如在记忆中留下一个影影绰绰的印象。不过今天不写,下个十年又不知是何种心境。想到此处,又好像自己只是十进制的傀儡,想纪念的不是自己,倒是“十年”这个概念本身。那么二十九岁前,就谈谈“纪念”的意义与消解吧。
二十九岁是个尴尬的时间点,它的存在似乎只为了给三十岁提供一个倒计时。拜孔子一句“三十而立”所赐,三十岁成了一大心理关卡。明代人用笑话来消解这种压力,戏称孔子三十岁才站立地起来,又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可见他二十九岁时还做官不得。这固然是句玩笑,不过三十岁似乎确实有种压力,让人不得不做出些什么,似乎时针走过某一时刻,便要验收人生的成绩单。
这个压力,用博弈论的术语,源自一种公共知识(common knowledge)。本来人们对不同年龄各有自己的判断,但孔子那句“三十而立”仿佛一次全国广播,使所有人共享了三十岁的这一内涵。你可以不认同这句话,但至少知道它,并且你知道他也知道,他知道你也知道他知道……这些无穷层的嵌套即构成了公共知识。具体表现在,三十岁之后,即便旁人不说,心中也总觉得他们对自己有种而立之年的预期。这种预期就像一个无形的手,扼住了每一个曾经在二十岁肆无忌惮地喊着“奔三”的青年的喉咙,让他们到了二十八九却对“奔三”讳莫如深。
也正因如此,我们纪念三十岁,以及每一个作为共识的时间点。害怕过了某个节点事情会发生质变,就像股市的跌破整数关卡往往会引起恐慌性抛售一样。并不是整数本身有什么魔力,而是我们相信别人相信整数关卡的意义,于是被裹挟着前进。具体到年龄上,就是奔三的人不必然认同三十而立,但相信旁人会认同,于是这种共识性的认知内化成了奔三者自身的压力。
但这种心理关卡未必不能消解。美国有位数学家在科普概率论时故作神秘地说:“我今天刚换手机号,太幸运了,拿到了千亿分之一概率的号码。”观众一片惊叹,结果发现只是一个“普通”的11位数,纷纷吐槽。数学家“委屈”地表示:它确实是一千亿个数字中独一无二的一个呀。他暗示的是,每个数字在平均分布下都一样“平凡”,它们随机出现的概率是一样的,让他们显得不平凡地只是人的期望。比如人们把三位数中的666、888、001当成特殊数字,其他统一归为“普通”的行列,那前者的概率确实就变小了,因为后者的基数变大了。不过现实生活要复杂得多,因为人们有88888特殊的“共识”,于是一连串8的车牌号就具有了象征资本。如果在路上看到这样的车牌,预测其车主大有来头自然是合理的。这是因为外界的期望重塑了原本平凡的概率。
认识到这些,我尝试重构纪念的意义,就从生日开始。每个生日,追根溯源,代表了自出生以来,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你说这一圈有什么深刻的隐喻?倒也未必。作为对比,地球自转一周便是一天,但人们除了在婴儿百天举行庆祝外,似乎并不庆祝千天、万天纪念。从十进制的角度,千天、万天似乎比二十年、三十年更优美一点,人们为何不留心纪念?恐怕没什么高大上的原因,只是技术手段所限:在没有电子设备、历法又不完备的年代,计算一万天实在过于繁琐。
几年前,我发现手机软件可以一键计算出生以来的天数,立刻兴奋地查了下我出生一万天的日子,刚好是去年的愚人节。心中莫名有些欣慰,好像这么一个深刻的日子与愚人节的解构性相得益彰。我相信,从数字的角度,一万天生日就是这辈子最重要的节日。因为以日计算,比以年计算更符合“生日”的本意,而一千天已无印象,十万天又不可能。即便是两万天那时候,也离退休不远,怕是唯恐老之将至,失去了庆祝的心情。于是到了愚人节那天,我特意邀请了几个朋友桌游,算是庆祝了一把,也帮他们算好了一万天的日子,顺便鼓吹我的这套理论。
后来有个朋友说他把我庆祝一万天的事告诉了他的朋友,他们觉得这人还挺有意思。他是好意,但我却矫情起来,倍感失落。因为“挺有意思”的前提是另类,而我期待的反应是“有道理啊,我也要纪念一下。”这种失落不仅源于这套“一万天”如何重要的理论推销不出去,只能自娱自乐;更在于让我意识到,纪念的本质是共识,不是十进制或其他学理上的必然逻辑。可个体想挑战社会积习的共识,又几乎没有可能。
人毕竟是种社会性的动物,节日的氛围不在于某种超然于人的客观原因,而在于众人的参与感,甚至只是一种关于参与的共识。以前不明白诗人为何会望着月亮,寄托那么多思念。当自己涌上类似的情绪时,才意识到虽然他孤身一人,但他想象在目力所及之外,也有同样的人正遥望着同一片月,由此便并不孤独。一个符号的意义,在于我们相信。而相信的基础,在于共识。我们不能改变时间节点,犹如不能改变月亮的轨道;但却能在固定的时间中建构自己的意义,犹如在阴晴圆缺的月相中寄托自己的情绪。
18年世界杯决赛前,我写过这么一段话,关于如何建构世界杯的意义:
今天厚着脸皮买了一堆小时候的零食,就和02年那个夏天一样。一直觉得对足球无感的朋友也不妨看看世界杯决赛。这无关足球,只是为未来留下一个记忆节点。时间从来不是均匀流淌的,去年的事情可以宛如昨日;数月前的记忆也可能像公元前一样陌生。四年之后,未来的喜怒哀乐想必又会把如今的回忆冲击地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今日所珍重的,四年后是否变得无谓;今日所执拗的,四年后是否早已妥协?记忆就是这样变得散乱与割裂。不过至少在电视机前的九十分钟里,四年前、八年前、十二年前的模样纷至沓来,仿佛一切都又没怎么变。时空的交错与弥合,这就是世界杯决赛的终极奥义。
现在读来,我们在一些节点留下回忆,就像记忆的相片。小时候叛逆,父母越要给我拍照我越抗拒,现在颇以为憾。不过所幸我还有写作的习惯,文字也是我的照片。只不过它们零零散散不像照片与时间的联系那么规整。《十九岁之前》与《二十九岁之前》,或许可以当成两部相册的封面。
写到这里,忽然想到《万历十五年》。它的英文标题是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美国史学界强调研究的重要性(significance),论文答辩委员会问的最多的就是选题的significance何在?黄仁宇偏偏要从没有significance的一年中嗅出一个时代的风气,多少有点抗议的味道。
人生走到二十九岁,似乎也是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我也终于明白,纪念的意义执拗不来,每个节点自有它的意义。不过选择在不甚起眼的第二十九年写下这些,而不是留待三十岁发表宏论,也算是一点小小的抗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