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青春的輓歌:黃耀明《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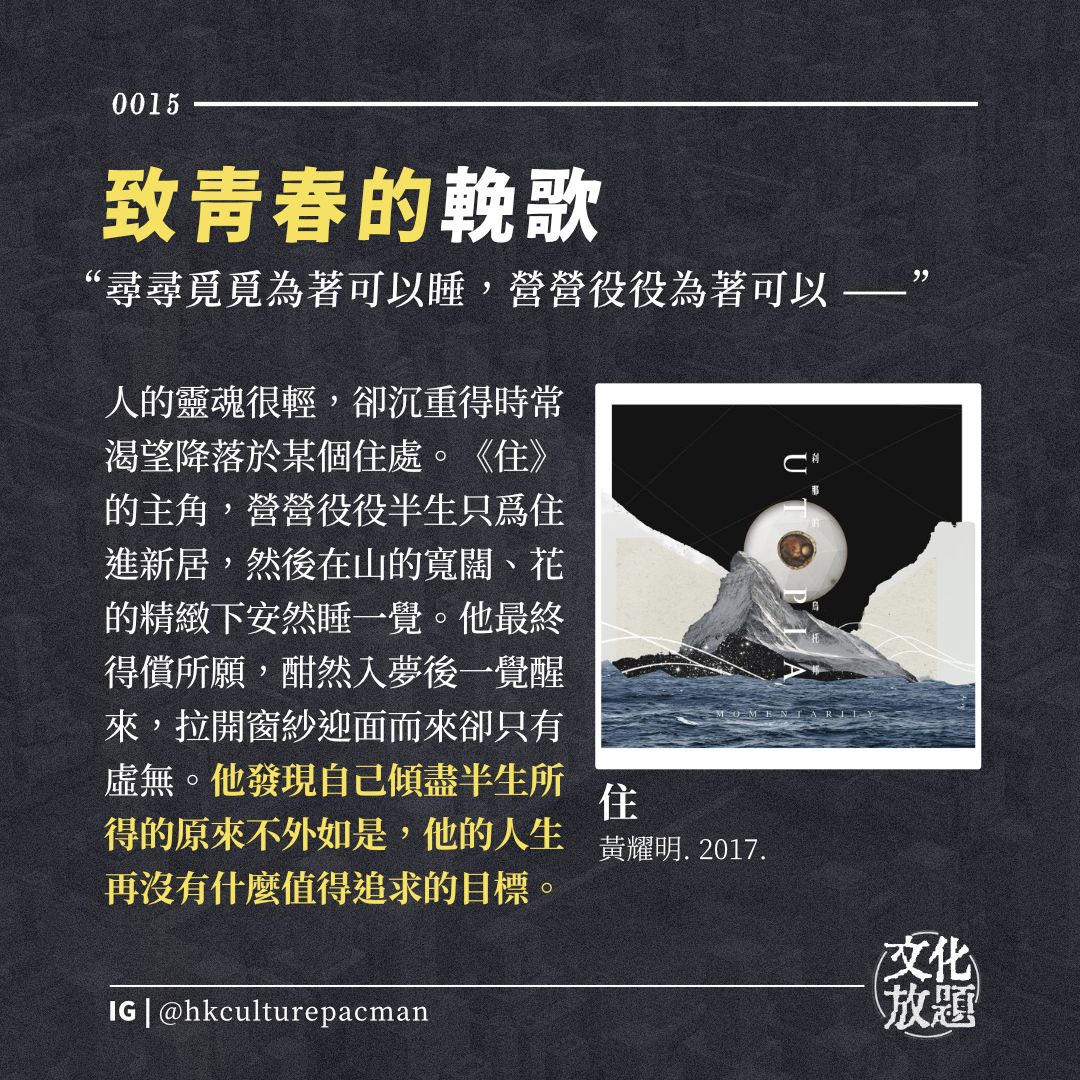
匆匆忙忙、忙忙碌碌,彷彿是每個香港人的宿命。以前搭地鐵上班,我看着車內的人無不睡眼惺忪、目無表情,左手握着扶手、右手握着電話,然後沉睡於某個不容別人侵佔的小世界中。直至車門一開,一眾昏睡著的靈魂卻立時集體甦醒,魚貫的湧出車廂,爭先恐後向着扶手電梯擠擠擁擁,你推而我不讓 —— 有時不禁會想,他們日夜奔波,究竟是為了追趕什麼?
《剎那的烏托邦》的文案寫着:「時代催人老, 生活逼人啞。」其中《住》這首歌,正正就是描繪着一個中年人瞬間蒼老的一刻。他人生的最大渴望是找到一個安身之處,他營營役役半生之後,某天總算得償所願,終於搬入了夢寐以求的新居。圓夢一刻,他放下千般重擔,跳入大牀酣然入夢。
然而夢醒之後,他拉開窗紗,卻發現渴望已久的快樂竟然就此變消失無蹤,取而代之竟然只有一片可怕的虛無。因為他發現到,自己傾盡半生追求一個安樂窩,此刻他卻竟然最記掛自己的故居;他以為自己終於找到了一個安身之處,此刻卻發現自己比起以前竟然更加迷失;他明明終於完了半生的夢,此刻卻發現自己的人生已經再沒有任何目標。
住
曲:馮穎琪
詞:周耀輝
編:謝國維
監:謝國維 / 馮穎琪
青春的死
這首歌關乎存在之虛無、青春之死亡,難免沉重。我甚至清晰記得初聽此曲時那種椎心泣血的震撼,因為我在頃刻間突然發現 —— 他勞碌一生最終搬入的新居,很可能是一個墳墓。
我喜歡住在哪裡?卻湊巧遇著風吹。
幾張被單翻過已十歲,
幾雙筷子面前幾多思緒。
我到底住在哪裡?正滿足或是唏噓?
幾杯美酒飲過已爛醉,
幾幅照片換來幾多根據。
日後在過去,紅塵漫漫在身軀。
不想刮花木門,不想染污白牆。
但我靈魂開始粉碎。
日後在過去,茫茫大地在身軀。
街中究竟是誰?廳中究竟是誰?
但我靈魂開始粉碎。
他翻過的幾張被單,是不是蓋掩着他那翻了又翻的黃土?他面前叫他思緒混亂的幾雙筷子,是不是祭祀用的紅筷?他飲到爛醉的美酒,是不是拜祭他的白酒?他賴以證明自己存在的照片,是不是他墓碑上的遺照?他不想刮花的木門,是不是他所身處木棺材的門?他不想染污的白牆,是不是他所身處石墳墓的牆?他茫茫大地、漫漫紅塵在身軀,是不是他已被埋葬?他的日後在過去,是不是他已經喪失未來?他模模糊糊搞不清身邊的人、他的靈魂開始粉碎,是不是他已經不在人世,是不是他已被火化?
其實是不是我想多了?但我始終覺得,歌中每個意象彷彿亦陽亦陰,此刻主角猶如薛定諤的貓,到底是生是死無人知曉。可是我又細想,其實他究竟是生是死又有何分別呢。他的存在豈非是同樣的虛無,同樣的迷失?
尋尋覓覓為著可以睡,
營營役役為著可以 ——
在花的精緻躺下,在山的寬闊坐下,
在新居醒了,窗紗開了,偏偏想到故居。
工作佔據了他人生的全部時間,卻沒有為他帶來絲毫的快樂。歌詞點出了他生命的荒謬之處:他營營役役原來只為一覺安睡,尋尋覓覓原來只爲一處安身 —— 結果他的肉體千辛萬苦終於搬入大屋,靈魂卻是前所未有的迷失。
用最大氣力,在最終有一堆 ——
隨鮮花一札散下,來高山一處放下。
歌詞形容,他的人生是「用最大氣力,在最終有一堆」。可是,究竟他最終擁有了一堆什麼?是成就?是物質?是快樂?是一福?原來統統都不是。
所謂一堆,原來是隨着一扎鮮花、放於高山一處的一堆骨灰。
原來他無緣無顧就死了 —— 如今這個六神無主的靈魂,走到奈何橋的半途,用盡他最後的一口氣,向着在第四道牆外,依然活着並且正旁觀着他悲涼一生的每個生命發問:
從此安居哪裡?你在哪裡?
青春的生
人的靈魂很輕,卻沉重得時常渴望降落於某個住處。不少人順從着社會引導,選擇住進名利與財富 —— 叔本華卻說受慾望擺佈的人生,猶如一個在痛苦和無聊間遊走的鐘擺:慾望滿足,人便快樂。可是短暫的快樂消散過後,迎來便是更大的無聊。偏偏人卻會慢慢習慣快樂,因而若要克服更大的無聊,便需要滿足更大的慾望。結果,痛苦永無止盡,快樂卻是越來越難得到。
亦有人選擇住進夢想,縱然偶遇迷失,他們卻從與命運的摔角中找到抗命的樂趣;亦有人選擇住進親情、友情、愛情,縱然偶遇傷害,他們卻通過同行彼此完滿了對方的生命;亦有人選擇住進他崇尚的價值,縱然偶遇迫害,他們卻不屈的澄明了人性的高貴和美麗。
相對主角的悲涼,一個清清楚楚知道自己心之所向的人實在何其幸福。縱然他們披星戴月而連夜奔波,偶爾自覺人微言輕而力不從心 ── 但只要他們在某刻,偶然見證到自己為身邊的人、身處的世界,帶來些微影響與改變,便會持之以恆的生出一股盲勁繼續堅持,即使身處勞碌,依然能夠不斷發掘出快樂和意義。
只可惜我尚未有幸成為這種人,不過有時看着這些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人,不禁便會想傾力成全他們的志趣、發掘他們的價值 —— 因為他們的存在彷彿為我述説着原來快樂人生是可得之物,並且有力的證明着:原來生命尚存各種可能,原來青春尚存各種或許。
或許一天我亦能躋身他們之中,或許突然天降橫禍我便命喪黃泉。但在死神的大貨車逾越時空輾過自己之前,我們大概可以相信自己還有時間、還有青春,還能任性的探索,還能天真的寄望,還能固執的相信:在真正死去之前,我們或許至少能夠經歷過一次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