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的碎片:王嘉儀《微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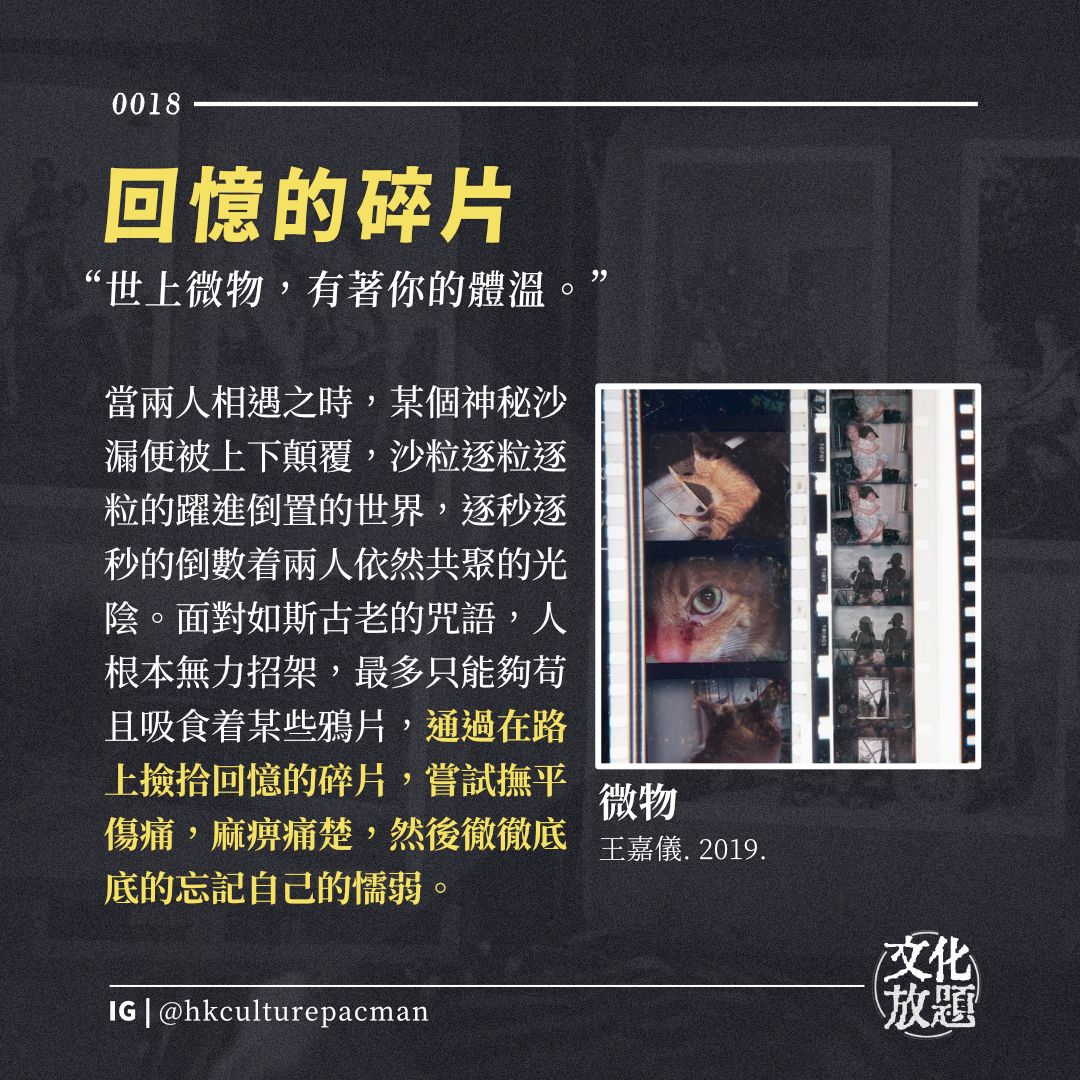
越過烽火,穿過迷霧,可惜浮城終究還是生不了根。縱然身邊的人如何裝作若無其事,其實總會意會到對方其實亦在暗中盤算着借來的時間,到底還剩多少。也許是害怕再沒有機會,想鼓起勇氣把説話吐出,一陣苦澀卻殘留在喉嚨之中:這會否就是你和我的最後一次説話?話畢之後,你會否就此消失,從此下落不明?
近來慢慢發現,原來一切曾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人和事,都能夠在傾刻間化為無有,只遺下一些細細碎碎、無從辨認的痕跡。走在街上,看到某個被抹去的塗鴉、某個被棄於路旁的啤酒罐、某塊缺失了的磚塊,有時會生出一股似乎永遠無法滿足的好奇:究竟此物背後那消聲匿跡的主人,此刻身在何方?生活過得安好嗎?
大概是萬惡的潛意識之故,最近莫名奇妙想起了 SOPHY 的《微物》—— 儘管接近兩年都未曾想起過這首歌。縱然歌曲以離別為題,但是從文字到聲音的每個細節盡都極其温柔,沒有大灑狗血、刻意煽情,或許是因為離別的愁緒,就是一種淡然而柔弱,卻又痛之入骨的悲愴。
微物
曲:王嘉儀
詞:王樂儀
編:hirsk / Soni Cheng @ gdjyb
監:王嘉儀 / hirsk
回憶的確據
髮上,冰冷滲入,
當天的身影,已是不可能。
你種下,花開閉合,
手中卻是,偏執不變的掌紋。
這種寧靜的愁緒,始於三千煩惱絲忽然闖進的冰冷 —— 那是一個突然閃現腦海的可怕念頭:那個熟悉而温暖的身影,是否永遠不能再能被我親眼見到?縱然對方曾經在自己手上種過什麼美好的花,可是花開過後,是否就迎來了它永久閉合的時刻?
若然所有的果實能夠就此突然腐爛,散失以後,還能夠憑着什麼證據證明它的確曾經出現過?我伸手想要抓住什麼痕跡,想要證明兩人的時間線有過片刻的交集,結果打開掌心卻是空無一物,只見自己偏執不變的掌紋。
原來,微温消散過後,遺留下的虛無竟能冰冷如此。
望著,望著沙漏。
時間,拒絕解咒。
這個想法極其悲觀,卻又極其誠實:人兜兜轉轉終究都只會歸於孤獨。當兩人相遇之時,某個神秘沙漏便被上下顛倒,然後萬有的引力誘使着沙粒逐粒逐粒的躍進倒置的世界,逐秒逐秒的倒數着兩人依然共聚的光陰。
或許是起初的熱情隨年月淡化,或許是兩人因為步伐不一而失散,或許其實根本毫無緣由 —— 段段親情、段段愛情、段段友情,種種沒有事先張揚的離別、種種曖昧不明的死法,無不源自那偏執地擺動着的秒針,滴答滴答的施出咒語,執意要把兩人各自推向時間之河的兩端,註定漸行漸遠,從此永不相遇、互不相干。
忘掉萬物,拋掉宇宙。
想找你,留給我的鈕扣。
面對如斯古老的咒語,人根本無力招架,最多只能夠苟且吸食着某些鴉片,通過在路上撿拾回憶的碎片,嘗試撫平傷痛,麻痹痛楚,然後徹徹底底的忘記自己的懦弱。
可是回憶卻是比鴉片的一縷煙更不實在,不然人們就不用時刻都要把腦海中曾經鮮明的想法和情感,封印於某些外物之上:一張合照、一隻戒指、一封書信 ⋯⋯ 然後期望能夠在沙漏窮盡之後,從抽屜之中發掘出這些鋪滿了灰塵的微物,如像叮噹的時光機般,強行的把逝者的屍體從虛無的黑洞之中,拉進這個依然保存着體溫的世界。
可是主角卻是連些微的鴉片也找不到。宇宙無疑是佈滿萬物,可是依附其上的不過是他者的回憶,對他根本意義全無。弱水三千,他只想尋回一個鈕釦 —— 偏偏這件在全宇宙絕無僅有的微物,此刻竟如逝者般同樣消失無蹤。
微微哭泣,尋找聲音,
可證實傷口,與你都相近。
微微呼吸,為可偷生,
想記住肌膚,有過那親密。
編曲者 hirsk 和 Soni 刻意在歌中放入了很多瑣碎到無從辨認的聲音。誰知道那些斷斷續續的女聲,實則是否誰的聲音?誰知道那些恍如鐵皮震動的聲音,是如實的錄音,還是來自其它不相干的聲音,通過改變頻率、改變音波所加工而成?聲音輕浮的飄於空氣,雖然透過錄音能被捕捉,可是透過取樣又能被扭曲 —— 聲音本來的面貌,是只有取樣者才知曉的秘密。
回憶豈非同樣如此?收集微物、收集聲音,不過都只是嘗試把虛浮之物變成實在之物。若然我們足夠誠實的話,總得承認雖然它們的底藴源自真實,可是始終難免失真。通過記憶,痛苦的過去竟然化淡了,愉快的經歷竟然隨住年月變得更刻骨銘心了 —— 所謂回憶,不過是一場幻覺而已。虛與實間的種種玄妙、種種奧秘,是只有回憶者才知曉的秘密。
世上微物,有著你的體溫。
你用一切接近,風之間一顆悸動的灰塵。
我慶幸翻開秘密,找到你在一生刻過的指紋。
原來回憶如此虛浮,它的力量存於心而非存於物 —— 細想這豈不是個喜訊?畢竟如果兩件微物曾經相遇過,總不可能不在對方身上留下半點痕跡。原來只要用心發掘,總不難發現到本相不過為空的萬物,其實無不承載着逝者的餘温。既然如此,何苦要執着於要尋回某個鈕釦?
主角再次打開掌心,竟然發現到逝者偷偷刻在自己手上的指紋。他看着微風間一顆悸動着的灰塵,他猝然察覺到逝者的身影 —— 縱然它微小得無力抵擋命運,縱然它輕巧得只要微風一吹便會永恆的失散 —— 但至少在這凝注了的瞬間,它的存在是真實的,因為它正訴説着逝者的故事,畫滿了依然未被抹去的塗鴉。
想到離別,大概還是很可怕吧。但自相矛盾的我又想:若沒有這不斷縈繞着的恐懼,人又豈會洞察到人之相識其實何其偶然難得?若非知其難得,人又豈會想沿途取樣回憶的碎片,從微物之中發掘出意義,創造出各種永恆的美好和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