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衡与决策:来自LSE哲学系的三项抗疫政策研究
LSE哲学系自Sir Karl Popper创系以来便以对科学和社会议题的密切关注闻名,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多名哲学家积极参与相关研究和讨论。本文介绍三篇已经发表的文章。
第一篇最近发表在Nature Medicine上,在整体上研究了抗疫和未来类似的公卫紧急决策需要遵从的原则,由来自英国、美国和欧洲的7位公卫专家、经济学家、法学家和哲学家联合撰写,其中Dr. Liam Kofi Bridgt和Prof. Alex Voorhoeve来自LSE哲学。
第二篇讨论在“生命VS生计”也就是说“救人还是救经济“的权衡中如何决策的问题,由6名英、美、欧顶级高校的经济学家、法学家、公共政策专家和哲学家联合撰写,其中Prof. RIchard Bradley和Prof. Alex Voorhoeve来自LSE哲学。
第三篇研究由Dr Jonathan Birch完成,依据英国政府紧急状况科学顾问小组SAGE (the Scientific Advisory Group for Emergencies) 公开的大量会议记录和内部文献检讨“按照合理的最坏情况着手”这一指导思想在英国防疫决策中带来的巨大代价。 【1】应对新冠肺炎的艰难权衡:为什么决策应当公开而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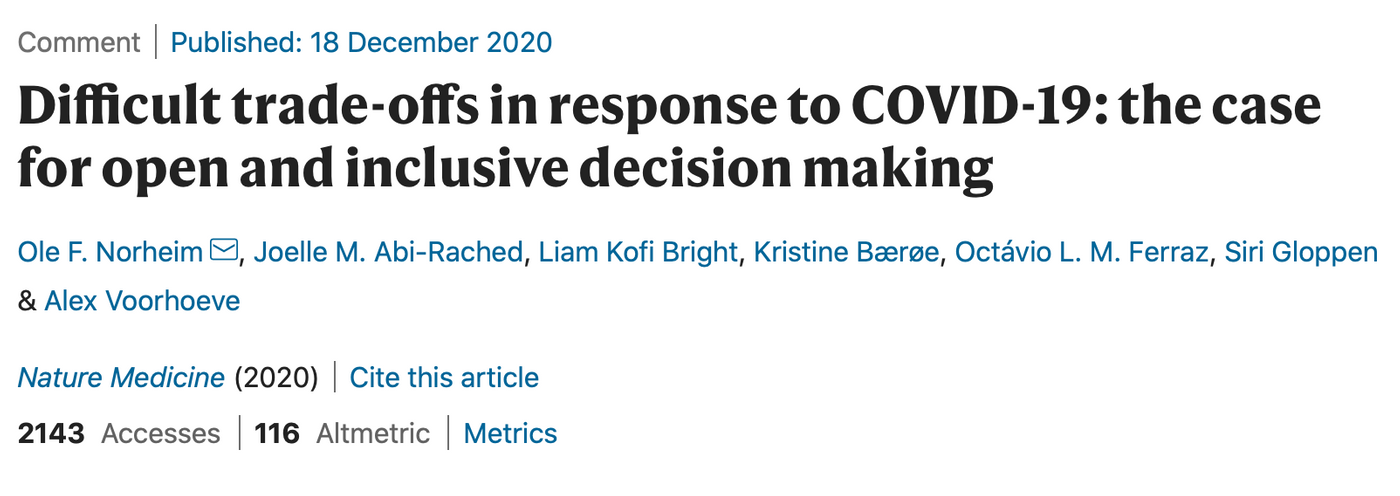
研究者指出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中各国政府不得不迅速作出很多艰难的抉择。公众的健康、物质利益和人民的自由在这些决策中都会遭到重大影响,然而相关决策过程却甚少有这些利益攸关方参与。研究者认为政府有道德、法律和实践上的理由推进更加开放和有多方积极参与的决策机制。这样的决策机制可以提高决策质量,提升决策的合法性和人民的信任程度,更好地满足法治和人权方面的要求,并且让老百姓更愿意坚持贯彻政府的决定。
政府在面对新冠疫情时的需要通盘考虑很多因素:疾病和死亡、自由、短期经济状况、长期经济发展、社会服务水平、就业因素、人际交往关系、心理健康状况、教育问题、贫困问题、以及非直接因为患病导致的整体寿命和生命质量变化。尽管果断而严格的封锁措施可能大大减少直接的健康损失,但是实际情况是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庞大的人口由于疫情的负面经济后果返贫。能够执行什么样的政策很大程度上也受限于对防疫疲惫到来和社会不安定因素爆发的担忧,至于很多已经非常脆弱甚至在战乱中的地区更是各有各的困难。
即便成熟有能力的政府,也必须衡量其采取行动的速度、严厉程度和管控的范围,考虑当地公共卫生能力、收入水平、社会不平等问题、年龄结构和公众的态度与观念。在应对这样非常复杂的问题时,许多政府不约而同地动用了紧急权力采取措施限制本国的民主政治,但是这样的做法反而削弱了对政府和科学权威的信任,而这种信任恰恰是确保百姓遵守防疫负责的决定性因素。
面对这样的挑战,研究者提出各国需要的恰恰是在决策面上更加开放和包容,并且给出了以下理由:
1)政治平等和人权
开放包容的决策过程能够满足法律尤其是人权法和政府可问责性原则的要求,能够真正将涉及众人利益的决策建立在事实证据、对每个人的平等关切、众人公认的理由、和民主制度中众人平等参与的理念之上,并且可以避免决策中对特定群体利益的忽略。
2)审查和交流
开放性和多方参与有助于让决策建立在更加广泛而准确的证据基础之上,对证据和不确定性的公开的批判性审查有助于改善决策质量,而就决策过程中的各种理据和存疑问题与人民公开交流有助于压制假消息、凝聚共识并建立信心。
3)信任和坚持
开放的、有公众参与的决策过程有助于建立公众对政府决策的信任,此种信任可以让相关政策的贯彻落实更加有效,而政策的有效性反过来会促进公众对政策决策者的信任,形成良性循环。
研究者格外强调了可问责性的重要性,认为在开放的防疫决策过程中,所有利益攸关方都应当可以对决定提出质疑,这些质疑连同新的证据应当遵循某种机制得到有效反馈和考虑,所有参与方面在决策过程中的互动和提供的信息都应当被完整记录,此外在防疫过程中的政府开支必须确保完全公开透明。
关于决策过程中专家团队的作用,研究者认为,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专家在探讨疫情相关的政策和不确定性时,其考虑难免是涉及价值判断而不仅是关于科学事实的,而在科学交流中应当明确澄清哪些问题涉及什么样的价值判断。科学家们同样应当尊重一般大众的反馈和体验,促进科学家与大众的双向交流。此外,参与决策的专家团体应当广泛包括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而不仅仅是医学家、公卫专家与经济学家。
评价:这篇文章的观点我大体赞成,但是它没能回答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1)广泛参与和决策效率之间的trade-off如何解决,或者有没有两全的办法?2)社会中已经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撕裂和disinformation会不会被纳入决策过程从而反倒降低决策质量?3)为什么似乎在应对疫情的时候可以主张这样做但是似乎同样的逻辑不适用于比如说应对核威胁时候的国家安全战略?
【2】生命VS生计:评析防疫政策

研究者指出在应对新冠疫情的政
策决定中很大部分纠结点在于“救人”还是“救经济”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相关领域最常用的衡量方法是考虑“统计生命价值” Value of a Statistical Life (VSL),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可以接受每年少挣$10,000来换取每年死亡的风险下降0.1%,那么这个人的VSL是$10,000,000,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考虑1000人的一个社区,让这些人平等地承担$10,000,000的经济损失来减少1个死亡案例是合理的。
研究者认为这样的基础对于防疫政策和普遍公卫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是不可取的,因为一个人的VSL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财富和收入水平,这意味着富裕的人会得到大得多的照顾。(注解:考虑马云会为降低自己0.1%的死亡风险付出多少钱,一个月薪三千的打工人会愿意付出多少,如果国家就此估价每个人的生命并且据称作出权衡显然是不公平的。)简单将富人和穷人平均起来同样会忽视很严重的问题,因为通常而言越年轻的人死亡带来的损失越大,已经年纪很大的人的死亡损失相对较小。因此似乎相比于死亡人数及其价值,关注统计寿命年度的价值Value of a Statistical Life Year (VSLY)似乎更加合理。具体的做法是将VSL的平均值除以某组人剩余的预期寿命综合再按照某个人剩余的预期寿命来分配,确定某一年龄组中某个人剩余寿命的价值。
但是即便如此简单平均也会产生问题,比如某一防疫政策将导致某个年收入总共也没有很高的穷人损失$10000,而此人的死亡风险相应降低0.1%(注解:事实上从整个人口来说,每个人因为新冠肺炎死亡的风险是很低的,几乎不可能达到0.1%,但是对于相当大部分人来说损失$10000对他们生计的影响很难承受),这个人很可能合理地认为,不值得为减少那点风险损失这么多的收入。此时,政策施加在穷人身上的经济负担因为富人更乐于承担经济损失减少死亡风险而被提升了。这并不正义。
一种更可取的方式是衡量社会福祉,直接关注每个个体的生活质量,认为生活质量由健康和财富决定,而这两者是紧密相关的。这种方法将每个人的福祉平等地进行考虑,由此不会偏向富人。政策对不同人群的福祉影响是不一样的,一种防疫政策有可能有利于保护退休人群但是给正在找工作的年轻人带来巨大损失。但是整体而言,有必要优先考虑那些生活质量已经相对不佳的人,给他们更多的关切。
研究者进一步借助几个模型讨论了VSL分析、VSLY分析和Wellbeing分析在抑制政策和控制政策下的呈现的不同结果。其结论为低收入人群往往因为防疫政策对于生命VS生计的权衡而面临不成比例的经济负担,而社会福祉分析比成本收益分析能更好地将不平等因素纳入考虑。结论是,在没有社会再分配的情况下,越早开始抑制或管控措施对于中上收入群体越有利而对于低收入群体相对不利,而越早开始抑制病毒传播越好这一情况只有在社会再分配体系可以有效缓解低收入群体经济压力的情况下才成立。
评价:这篇文章发表较早。事后复盘,我的个人观点是这项研究严重忽视了由于持续大量死人带来的心理印象对于精神健康和人们经济行为的影响,显而易见,并不是只有政府的干预措施会带来经济上的负面后果,人们担忧和恐惧的后果同样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后果,英国和疫情防控上面更加放任的瑞典在人口和经济上同时损失非常惨烈的表现就是证明。
【3】极端情况下的科学与政策:从英国对COVID-19的最初反应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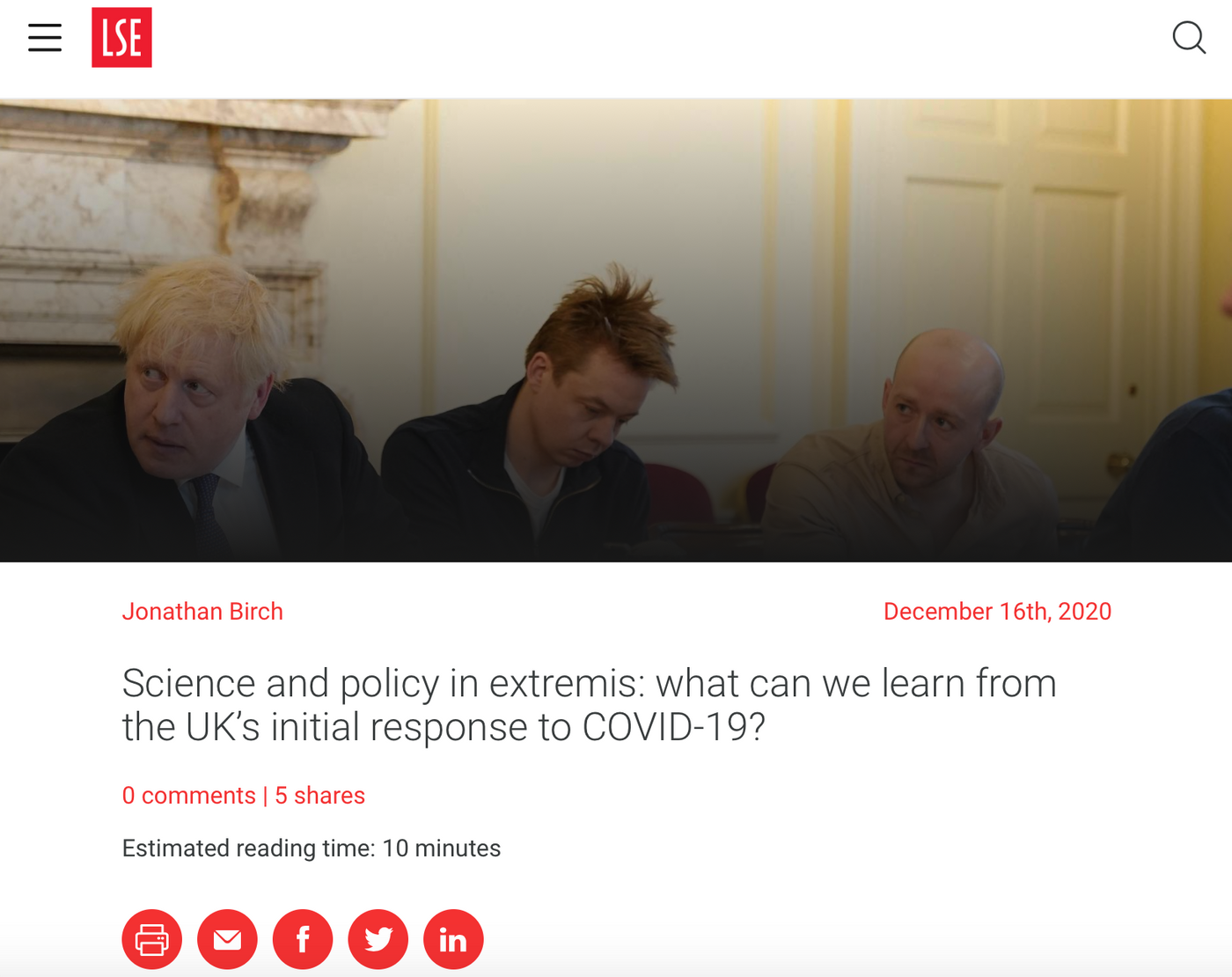
Birch在他的一项未刊发的研究中讨论了英国防疫决策过程中科学家与政治家互动的很多方面,而在已经发表的一部分中,他着重讨论了所谓的“合理的最坏可能情景” “reasonable worst-case scenario” (RWCS)这一思考方式对于英国SAGE的影响及其后果。
Birch指出,英国政府实际上非常早就开始筹备处理疫情,成立了顶尖专家构成的SAGE为政府提出建议。但是在三月份政府刻意按兵不动之后尤其是在所谓“集体免疫”概念进入公共视野之后,SAGE一下子沦为舆论和政治操作的风暴眼。实际上一系列令人感觉迷惑不解的操作包括所谓“集体免疫”都可以在RWCS中找到来由。
RWSC表达了这样一种思路:尽管我不知道究竟会发生多么糟糕的情况,但是如果我按照最差的情况来进行准备,那么不论最终来临的是什么情况,我都已经准备好了。这种“底线思维”乍一听上去非常合理,实则有很大的问题。
Birch表明,实际上SAGE和受其影响的英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并不是“太放松了”而是太悲观了。3月6日SAGE提出的一个最坏状况情景假设了80%的人口在9周内感染,其中50%出现症状,死亡率为1%,结果是3个月内造成52万人死亡,而在这个阶段,SAGE已经默认了将不会有有效的疗法或者疫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集体免疫”从一开始就不是主动追求的结果,而是在最坏可能的情况下不得不最终发生的一件事。此外,SAGE还假设一旦开始干预措施比如社交隔离,人们执行该措施的最长时间不会超过13周,并且假设只有50%的人口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实际上这两项假设至少在第一次英国封锁期间还是比较切合实际的。但是SAGE却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估计偏向于乐观,比如将R0估计为2.4,这在当时的各种估计中算是去了较低的值。
那么SAGE的RWCS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一思路实际上直接导致了英国政府在三月初选择按兵不动。因为政府预估到在未来五六七月份可能发生大量的死亡,而防疫干预政策只能持续一小段时间大概三个月,那么最合理的选择当然是延迟进入lockdown时间,把最有力的政策留到曲线最高的地方去用,避免防疫政策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得不到人民的配合。同样,因为对于死亡人数做出来最悲观的预期,英国政府决策的重点从一开始就不是如何严防死守减少死亡,而是有限保护NHS的医疗能力,给最差的情况流出余地,因此三令五申地要求疑似病例和轻症患者在家自己隔离,避免发生医疗挤兑,留出增建医院和扩张床位数的时间差。这就解释了除了被广泛误会的“herd immunity”以外同样非常著名的两个来自首相发布会的短语“flatten the curve”和“stay at home, protect the NHS”。同样是在一种RWSC的考虑中,SAGE在早春就提醒英国政府需要考虑第一波疫情过去之后秋冬季节会来the more deadly second wave的可能,并且认为第二波的到来几乎不可能阻止。这意味着通盘考虑下在一开始就进行最大程度的积极压制即使能够成功也不一定合理。
Birch评论到,SAGE采取RWCS的选择在两个方面的严重问题导致英国付出了严重的代价:
1)SAGE在相当大程度上对于情况作出了过分悲观的估计的同时,在一些严重的问题上做了过分乐观的估计。比如SAGE将没有干预措施的情况下的R0估计为2.4,但是事后复盘推算英国春季封锁前尽管已经引入了各种缓解和抑制措施,R依然在2.4以上。如果一种RWCS是真正合理的,它必须在所有方面都足够悲观(global pessimistic scenario),尽管假设所有方面都沦入最差的情况并不十分切合实际,但是每一项假设都代表着一种严重的可能性。
2)更微妙的问题在于,为最坏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不意味着就同时也为相对不那么坏的情况作好了准备。在为最坏的情况作出准备的时候,会不得不放弃很多其他的东西,而在情况没有那么坏的时候,这种就会导致延误或者遗漏,带来严重的后果。比如如果英国在一开始就果断采取最大程度的控制措施,尽管确实有在最坏情况下崩溃的危险,但是综合考虑种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其长期影响大概率会远远好于现在的状况。
Birch由此提出三个建议:第一,如果一定要使用RWCS,那么这种估计必须是全面悲观的,而不能是选择性悲观的。第二,尽管RWCS很可能有助于指导日常生活,但是并不适用于主导政府的战略选择。有时候放松某些假设以适应更可能出现的情况的估计更有益。实际上,正是帝国理工学院3月16日的一篇论证了无限期维持积极管控措施直至获得疫苗为止的论文改变了英国的战略选择。第三,科学顾问团队有必要在给出建议的同时突出强调每一项建议又可能带来的严重遗憾,比如说选择RWCS情况给出的建议会带来在更多可能性下造成巨大损失,以此帮助政治家作出思虑周全而非自以为非常科学的决定。
评价:Jonathan做的这个研究非常好,但是在RWCS(假设足够global)的不适用性和precautionary principle在公共决策中的适用性之间如何衔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