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打工人的2020大盘点

文|后厨刘师傅
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在这一年经历了疫情、洪水等多番磨难。上千万农民工成为受冲击最严重的的阶层起起伏伏,处于中产的白领阶层也未能幸免,他们经历了降薪、冻薪甚至被解雇,有些人不得不下沉成为体力劳动者。2020对于“打工人”来说,是艰辛且痛苦的。
新冠和洪水:灾难中首当其冲的工人
2020的前半年,中国工厂遭受了大起大落,从疫情期间的复产复工难,到年中洪水侵袭丶国际疫情反弹丶国际订单减少。为应对经营困难,裁员降低成本非常普遍,受到最严重影响的就是中国的农民工阶层。
春节过后,上千万农民工和服务人员返程后发现,受到疫情影响,餐馆丶旅馆和许多出口工厂几乎没有招工。有些工厂老板在放无薪假丶取消加班等策略用完后选择裁员,令不少工人难以维持生计。虽然其后国内疫情受到控制,但是由于新冠病毒在国际间蔓延开来,令不少工厂因为盈利丶订单的不确定性而趋向减少招工丶增加劳动强度,工人生计没有获得丝毫改善。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遍布全世界,虽然中国的国外订单急剧减少,然而大量口罩厂的窜起吸纳了不少闲散工人进入。但超强的体力劳动和安全培训的缺乏,令工人疲惫不堪、危险丛生。“新工号51”,便报道了“比亚迪”的口罩工厂中,一名工友的手被口罩制作机碾碎。据称,车间已经三个月无休,口罩车间从3月开始连续生产,直到6月中才有了一天休息。他们每天从早8点工作到晚8点,在这当中就有三名工友猝死。其后因为口罩行业竞争加剧,导致口罩价格利润降低,一些基础不稳固的工厂开始出现商品囤积和拖欠工资的情况。这些行业的波动最终还是转嫁到了工人身上。
今年夏季,中国南方多地发生洪水灾害,农业和制造业繁盛的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受灾极其严重。毫不意外,在洪水中遭受冲击最大的仍然是中国的低收入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群体。网上广传很多视频都能看到,农民辛苦数十载,用微薄收入在家乡建造的小楼一瞬间被洪水冲走,全部家当化为泡影。经济损失外,刚刚从新冠疫情冲击中舒缓过来的工人们,又要再次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业,急急返乡冲上抗洪前线。而各地的女性劳动者则要在洪水之后,冒着危险清理积水堵塞丶处理垃圾和疾病问题。
扶贫中的打工人:返乡还是再外出
那么来自贫困地区打工者们的家乡又如何呢?自2013年习近平到湖南十八洞村考察时提出精准扶贫的指示后,短短几年的时间,一场自上而下、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精准扶贫运动在全国迅速铺开,中国官方年底宣布,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这消息在主流媒体上引起了一阵狂欢,在这“人类减贫奇迹”的断言下,现有政策的持续性以及扶贫政策的结构性困境却少有提及。

《多数派》曾经写过关于因为扶贫政策返乡再离乡的农民工大亿的故事。
83年生人的大亿来自贵州铜仁,外出打工已有18年“家中资产却从没超过四位数”。2017年,在A厂重复熨烫、打包、钻图制作、查货、剪线、钉扣工作六年的他决定借着扶贫项目回乡。可是他回家后却发现并非那么美好:一没关系二没创业经验的他难以拿到政府项目资助,不得已只能加入现有的合作社。旅游合作社有着村内干部的势力盘踞,大亿只能打零工一样参与到农民表演队中;而油茶合作社则是由浙江老板引进的项目,大亿做的不过是原料供应者,利润归老板,风险却由他自己承担。最后,合作社连当初承诺的补贴也没有兑现。不得已,大亿再次回到A厂,他存折里的钱,“都还固执地保持在8000多元”。
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教授认为,精准扶贫总体上仍延续80年代以来中国扶贫工作依靠“开发推动减贫”的一贯做法。然而在国家主导的扶贫资源的分配层面,对像大亿一样千千万万的普通贫困户而言,想要凭借一己之力获得扶贫资源和项目,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些资源和项目往往被当地的政治或经济精英所攫取。如此一来,本就身处农村社会底层的贫困户,在扶贫资源的信息获取、项目参与、利益分享等多个方面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外。
其次,当产业扶贫是以牺牲贫困者(小农或城市贫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为前提的市场化手段进行时,永久脱贫是不可能的。对那些被转化为城市工业和服务业劳动力的贫困户来说,虽然在绝对收入上超过了国家设定的贫困线,但实际收入却仅仅能维持当下家庭生活的基本开销和自身劳动力的再生产,几乎没有机会和能力在这一代和下一代实现生活条件的实质性改善和阶层的跃升。
外卖员与快递员的挣扎
工人们仍然需要在城市中寻找新机会。当下接纳低学历、低技能的工人的工作不多,除了普工,他们还能选择的不过是外卖员、快递员等职业。这些工作的相似之处是,都难以获得晋升空间。即便如此,很多打了十多年工的人仍跃跃欲试,在前些年快递业“神话”的渲染之下“搞点钱买电动车跑外卖,自由些,进厂太压抑”。
然而《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却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由资本操控的平台算法,早已经将外卖员牢牢锁死在了被资本家剥削的生产链条之中,时间、路线和薪资都是不自由的。在巨大的罚款压力之下,骑手们不得不逆行闯红灯、超速驾驶、事故频发却没有保障。

而快递员的状况同样令人堪忧。今年双十一消费狂欢中破纪录的成交额背后,几大快递平台不断恶性竞争,派件量不断上涨、派送费却越降越低。平台对快递员的不合理罚款层出不穷,派送网点欠薪跑路时有发生。据中国劳工通讯不完全统计,本年度快递行业的抗议事件至少30多起。《多数派》写过快递员小南不仅不能“多劳多得”,反而遇到了“越干越没钱”的生存困境,在深圳做快递员的小南,被快递公司拖欠工资数个月,更被站点罚款。更难的是,他在申请劳动仲裁的时候举步维艰。收集证据、当下的经济压力、漫长的维权路搞得他焦头烂额。
另一边,蹿升的菜鸟驿站也在蚕食快递员的派件收入,每件派件费从过去的一块多已经降到了几毛钱。而更大的问题是快递员无法完成上门送货,导致客户和快递员的矛盾升级。快递业的价格战仍然在燃烧,导致廉价的商品和服务层出不穷。当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正当措施往往会被描述成对快递员的不道德行为,快递企业却小心翼翼躲在了快递员的背后编织着美好的消费神话。快递业的最后一公里,变得越来越难行。
零散工:共享员工与特殊工时
受疫情影响,许多打工者原先的工作受到了冲击,打零工成为他们在疫情期间的收入来源。一份就业门槛相对较低、进出灵活自主的工作成了不少人维持生计的权宜之计。有健身教练去送外卖、被减薪的白领开起网约车、而工厂工人转去送快递。然而打零工这种新就业形态,打破了雇主与劳动者的传统用工关系,对目前已有的劳动、用工、就业、培训、社保等政策和体制机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服务体系提出了巨大挑战。“零工经济”在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的同时,剥夺了一些雇员的职业安全感,由于很多人在“打零工”时签订的并不是正式劳动合同,不利于自身权利的保护。
而今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人社部“共享员工”文件和深圳“特殊工时制度”对未来工人权利所造成的影响。人社部9月发布《关于做好共享用工指导和服务的通知》文件,对疫情期间多跨行业多企业间采取的“共享用工”模式进行了法律上的认可和实践上的背书。所谓“共享用工”,是指企业间的员工调配。其中制造业、服务业等低技能的一线劳动者在其中有更多的参与,这些岗位工作性质比较简单,经短暂培训能够快速上岗,是企业眼中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共享”的工种。但是共享制度在其中涉及保险、福利等一系列复杂的劳资关系,“与劳动者协商”的共享模式在实践中几乎等于将工人抛弃在了保护之外,一旦发生纠纷,劳动者必然会被置于相对弱势的一方。
继共享用工新策之后,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改革试点方案出炉,方案表示,“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允许探索适应新技术、新业所需要特殊工时管理制度”。一时之间,关于996将合法了,007还会远吗?的讨论甚嚣尘上。因为采用综合工时后工人加班费和收入大量缩水,休息休假权严重受侵犯,连续工作24小时或数天亦是合法。基层劳动者将面临过劳伤害和收入锐减的双重危机。
“特殊工时制度”的实质是要为日趋普遍化的“零工经济”开道,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实验田、先锋地”,原本就是各大“996福报”公司的集中地,“特殊工时制度”将原本在这些公司已经广泛采用的“不(9)定(9)时(6)工作制度”进一步推广到其他行业,使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在实际上成为“零工”,让资本可以予取予求,用完即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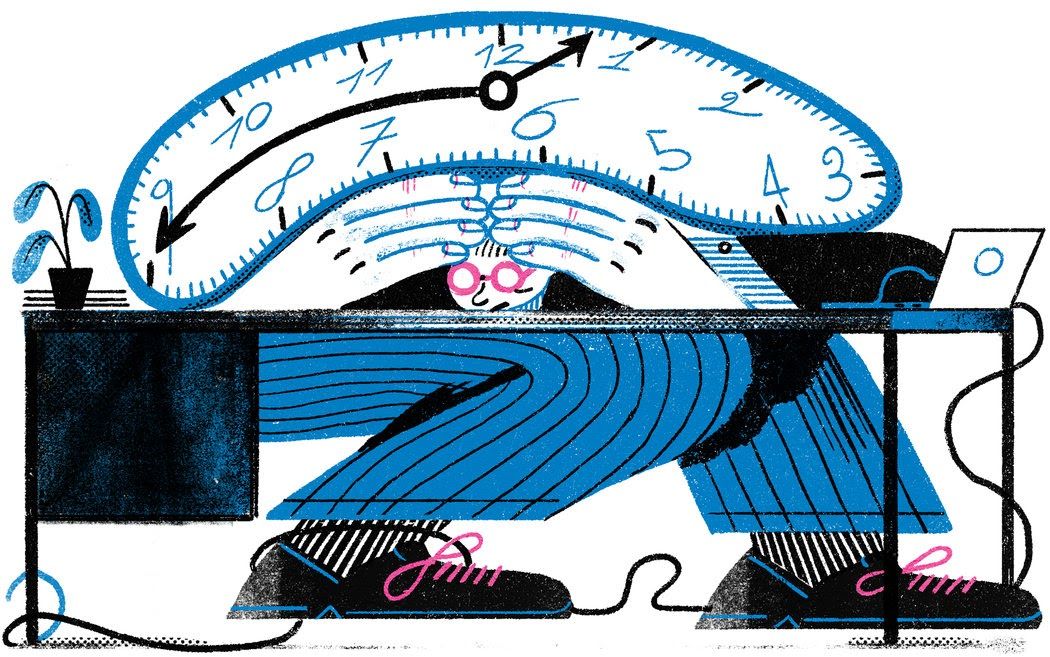
从社畜到打工人: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合流
属于劳动者的网络热词每隔些日子便会生发出不少,例如程序员之类脑力工作者自我矮化的“搬砖”,从日本舶来的“社畜”则广泛用在公司白领的话语之中,而今年“打工人”这个朴实无华词汇则成为了不分脑力体力全体劳动者共同的自我代称,这种称呼的合流在今年显得意味深长。
比特币开始兴盛之时,“挖矿”“搬砖”这些词汇经常被程序员和炒币者使用,前者是以计算机消耗电能的方式获得比特币、后者则是通过比特币价差获利。随着参与者变多,相应利润也越变越少。这两个词汇就被脑力劳动者逐渐演变成在电脑前花费时间精力的代名词。而社畜则源自于日文汉字中的“会社”和“家畜”的简称,简言之就是“公司的牲畜”,指的是一些为公司放弃自我生活的劳动者,多用于日本公司员工的自嘲。对于沉浸在996生活中的中国白领,社畜这个词用起来也没有丝毫的违和感。
而打工人的兴起,是将过去打工仔、打工妹这些有着些许工作不安定、工种相对低端的头衔被抹平约化为了“打工人”。相较其他,打工人三个字不分性别、地域、年龄,最重要的是不分工种和阶层的使用,曾经那些白领或者脑力劳动者已经抛弃用自嘲来做最后的挣扎,在这个词的使用上已经和体力劳动者没有了分别,大部分人都开始意识到自己不过是给老板干活的“打工人”而已。一场疫情揭示了无数老板们自私的嘴脸,也剥夺了白领脑力劳动者最后的尊严,正如前面提及的,有健身教练去送外卖、白领去做网约车。《2020年白领生活调研报告》显示,疫情期间,白领们经历资缩水问题最为普遍,占比达37.34%,还有30.68%的受访白领在疫情中遭受裁员。值得注意的是,年龄越长的白领,在疫情中遭裁员的占比也越高,近4成70后受访者表示自己的职位和薪金已被公司“优化”。

而这种“优化”玩的最好的,就是华为。早在几年前该公司就开始有系统大规模的辞退35岁以上员工。今年10月,广东高院驳回了前华为员工曾梦状告华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等的申请。40岁的曾梦曾在2012年入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2018年5月,华为公司以曾梦旷工三日为由将他解聘。
而此案的另一个争议焦点为,法院判定曾梦手写的《成为奋斗者承诺书》有效。这份臭名昭著的《承诺书》,作为前面提及“特殊工时”的先行者,主要内容是:承诺人为获得分享公司长期发展收益的机会,愿意长期艰苦奋斗,努力工作。承诺人承诺自愿成为奋斗者,自愿放弃在公司工作期间的带薪年休假及带薪年休假工资。即使离职,无权也不会要求公司支付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然而正是这样一个违反法定基准和侵犯劳动者合法权利的协议,竟被堂而皇之的被法院接纳了。
事实上,近年很多网络公司将996视为不成文规定或者天经地义,对员工的压榨甚至到了荒谬境地。前两月亦爆出多家互联网企业疑似监察或压榨员工去厕所的时间。其中,有报道指快手在一个厕格门口安装了一个计时器。通过这个计时器,厕格外的人不但可以知道内里有没有人,甚至还能够知道里面的人已进去多久。有人降薪失业;有人被迫无偿加班;困于户口、住房、教育、医疗,在压榨和剥削之下,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中正在逐渐消融。无论是白领还是蓝领,最终不过都是劳动力的不同分型,本质上都是不掌握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所谓“打工人”的成为便是相同阶层劳动者意识觉醒的第一步。另外,随着大学毕业生失业浪潮的到来,脑力无产者和体力无产者或将出现合流的趋势,而其后的阶级抗争也必然出现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