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预言 互联网会让我们集体失忆吗? | 历史 | 半岛电视台

互联网的发明真得帮助人类获得知识和智慧吗?哲学家马特·布卢明克通过 2400 年前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的辩证法,阐述了互联网对记忆力和注意力的影响。
托特说,“您看,国王啊……知识将使埃及人更聪明,更能记住。我发现了智慧和记忆的秘密。”国王回答说:“哦,托特,无与伦比的艺术大师:有一个人被赋予了发明艺术的能力,还有另一个人会判断这种艺术给使用它的人带来的伤害或利益。现在,作为文字的发明者,我看到您出于偏见而将其归因于它的真正后果,这项发明最终会落在那些记忆力差的人身上,因为当他们依赖文字时,他们将停止锻炼他们的记忆力。”
柏拉图的《斐德罗篇》,由赫尔米·马塔尔埃米尔博士翻译
令人惊讶的是,一句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名言与我们当代社会面临的问题仍然如此相关,在这句引自柏拉图的《斐德罗篇》的引文中,苏格拉底利用古埃及神明、文字发明者托特和塔穆斯国王之间的想象对话,向斐德罗展示了苏格拉底认为写作的危险及其对人类智慧令人不安的影响,托特认为,通过发明字母,他找到了一种保存埃及人记忆的方法,并且通过这样做,他为埃及人民提供了超越自然可能性极限的智慧。
但塔穆斯认为,托特发明的革命性书写技术根本不会给埃及人带来智慧,埃及人没有获得新的记忆能力,而是将他们的记忆委托给外部系统,从而失去了拥有内部记忆的自然能力,而内部记忆是知识的基石,随着知识越来越多地存储在外部符号中,他们的记忆力和智慧将会退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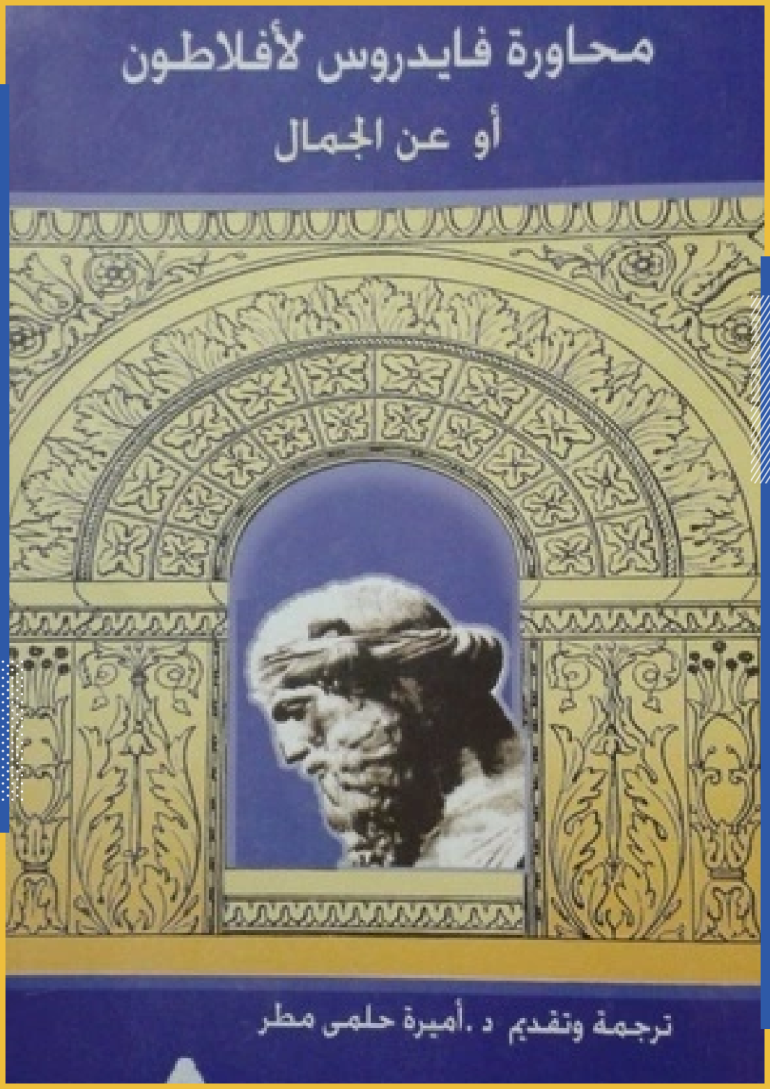 柏拉图的《斐德罗篇》一书(社交网站)
柏拉图的《斐德罗篇》一书(社交网站)我们从2400 年前跳跃到现在,假设托特的发明不是文字,而是互联网,文章开头的那句话居然还适用于这种情况,着实令人惊讶。根据苏格拉底的说法,互联网是人类历史上集体失忆症的最大载体,因为互联网的内存容量是无限的,在书籍增加记忆存储容量的同时,我们发现依靠现代技术,尤其是互联网作为存储记忆的巨大外部银行,让我们越来越失忆。
现代哲学家都意识到这一点,对记忆和大脑感兴趣的哲学家查尔默斯写道,“一个月前我买了一部 iPhone,它已经接管了大脑的一些中心功能,当我在 iPhone 上存储电话号码和地址时,iPhone 取代了我的一部分记忆,我过去常常让我的大脑记忆疲倦。”斯蒂格勒还在他的著作《对政治经济学的新批评》(2009 年)中写道,技术“将记忆传递给机器,以至于我们不再知道身边人的电话号码。”我们现代的智能手机是可以成为我们工作记忆过程一部分的外部对象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注意力和记忆力
是什么决定了我们记得什么和忘记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看看一位毕生致力于研究记忆专家的作品,这个人就是埃里克·坎德尔,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精神病学家和神经学家,坎德尔认为,注意力是形成清晰记忆的关键,通过关联想法来存储和保留这些记忆是一个需要高度专注的过程,换句话说,可以通过智力或情感的投票率或注意力来获得记忆。
在他的《追寻记忆的痕迹》(2006 年)一书中,坎德尔写道,记忆是牢牢记住,“必须对传入的信息进行深入分析,这是通过关注信息并以系统和有意义的方式将其与牢牢扎根于记忆中的知识联系起来的方式来实现的”,而当我们不注意一个想法或经验时,神经元会在几秒钟内失去兴奋状态,记忆就会从脑海中逃逸,留下轻微的痕迹。
 我们的大脑通过分配记忆任务和降低注意力的能力来适应遗忘,使其在记忆过程中失去效能
我们的大脑通过分配记忆任务和降低注意力的能力来适应遗忘,使其在记忆过程中失去效能近年来,注意力已成为西方社会的一个紧迫问题,因为自 1990 年代初互联网诞生以来,我们持续关注的能力已经减弱,我们每次上网时都会遇到大量信息,不仅会给我们的工作记忆带来负担,还会让我们的额叶难以专注于一项特定任务。所以,坎德尔说,形成记忆的正确过程不是从起源开始的。
我们中有多少人发现,越来越难以专注于需要长时间专注的任务,例如读书或观看长电影?每当我们使用互联网时,我们的大脑就会习惯于分心,并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和效率处理信息,甚至没有注意到它。即使在写这篇文章时,我也注意到,不打开页面查看 Facebook 或电子邮件是多么困难,并发现集中注意力而不被我正在查看网页上的外部链接分心是多么困难。
我们的大脑通过分配记忆任务和降低注意力的能力来适应遗忘,使其在记忆过程中失去效能,所以我们陷入了一个无限循环:在我们的生物记忆中存储信息越困难,由于互联网的使用,我们就越需要依赖外部记忆库。
毒药
那么,苏格拉底说得对吗?我们越来越依赖外部技术是否意味着,人类注定会陷入注意力不集中和社交痴呆的未来?看起来可能是这样,但还有另一种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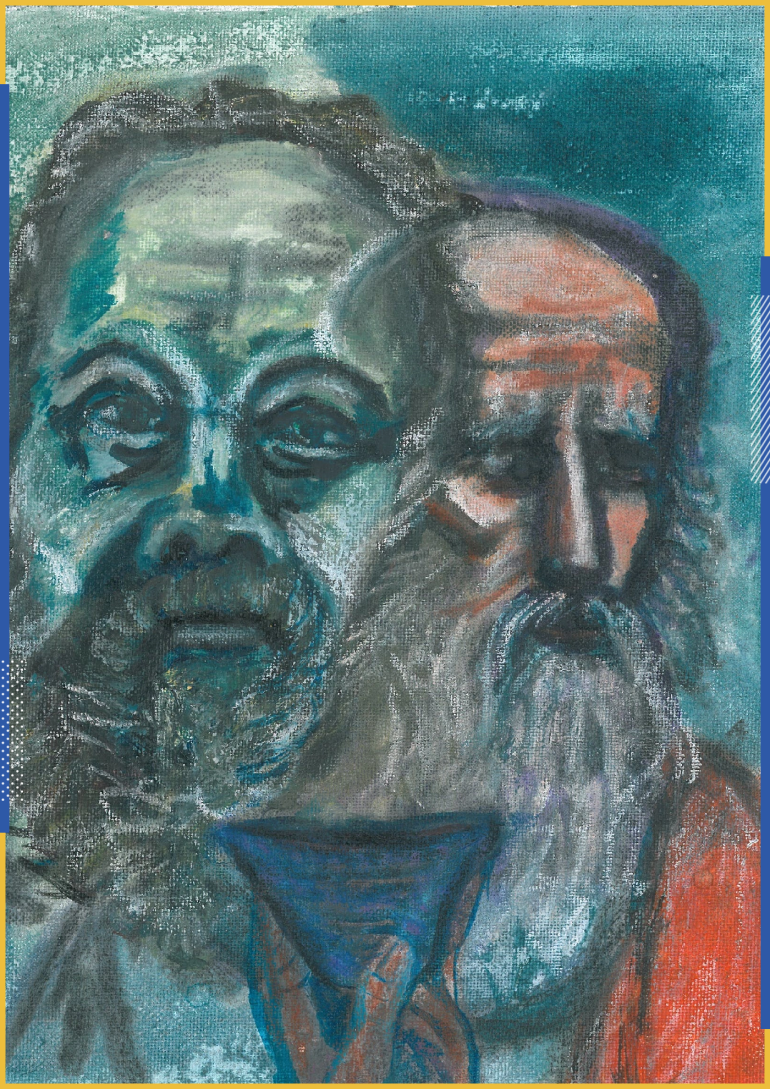 根据坎德尔的说法,重点应该放在深度思考上,以恢复注意力并扭转互联网造成的理解扁平化(社交网站)
根据坎德尔的说法,重点应该放在深度思考上,以恢复注意力并扭转互联网造成的理解扁平化(社交网站)在《斐德罗篇》中,托特将书写的发明描述为“pharmako”,这个词有两个含义,解毒剂和毒药。因此,在《斐德罗篇》之后,哲学家们以这种双重方式看待技术——人类制造和使用的东西,这意味着技术具有药理学性质,可以这么说,现代技术可以,而且也应该,被理解为具有治疗和毒性两种特性。
但是,在浮华的知识和随机信息的世界中,提高注意力的最有效方法是什么?根据坎德尔的说法,专注于深度思考以重新获得注意力,必须扭转互联网造成的理解扁平化,我们必须对此予以重视。
关注
有趣的是,注意力(attention)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attendere),可以表示心智的锻炼,这意味着同时处理一件事。当我们说医生“关心”病人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词是如何保留其双重含义的。因此,如果形成记忆的关键是注意力,那么我们就应该真正关心我们的大脑在做什么。此外,伯纳德·斯蒂格勒 (Bernard Stigler) 解释说,当你将一个人描述为 (attentionné),即用法语表示专心时,你是在表达他们对他人的考虑和尊重。
“这意味着文明,虽然我们通常认为注意力是一种专注的心理能力,但它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注意力既是心理的,也是社会的,两者密不可分。”简而言之,要细心就是要善解人意。不仅如此,忽视他人的观点会失去感受他人感受的能力,从而失去“关心”和关心他人或周围社区的能力。

基于此,注意力问题不应被视为纯粹以神经为中心而仅依赖于大脑,我们的记忆超越了生物的界限,延伸到了文化。正如唐纳德·赫布用他的永恒名言所说:“共同刺激的细胞彼此连接在一起。”因此,纽带可以由文化情境形成和瓦解,正是这种形成的神经元能力将使我们免于重新获得注意力和记忆力的斗争。
如果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我们学会在互联网浏览习惯与促进阅读或写作所需的深度集中的方法之间取得平衡,那么,我们就可以改变我们的思想结构,以利用在外部记忆中发现的巨大好处。
知识遗产
在柏拉图的对话中,我们发现苏格拉底拒绝书写,因为通过书写表达思想存在各种固有的危险,但应该指出的是,如果没有这次审查,就不可能对这些危险发出警告。苏格拉底是一位演说家,而柏拉图是一位作家,苏格拉底的遗产通过其后人的书写流传至今。事实上,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柏拉图,都不能以强有力的理由谴责书写的做法,可以说,柏拉图是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即使是苏格拉底没有写过任何东西,但他的思想却被数百万人仔细阅读,苏格拉底通过柏拉图的对话提出的辩证法的本质,是基于以文字为基础的希腊文化遗产。
阅读长篇文章,尤其是阅读书籍所必需的持续深度关注,可以看作是重视我们大脑和思想的方式,但要掌握这一点,首先需要了解如何关注整个社会。(然后从各种意义上来说,关注我们的文化发展方式。)这就是我们致力于找回在互联网时代开始消退的能力。互联网仍然是最近的发明,我们仍在学习适应它,但有必要了解它的双重“药理学”性质,旨在个人和集体层面基于知识做出理性决策,以处理未来的技术问题。
最后,我要引用一位作家在 2005 年的演讲,他比大多数同行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些问题,伟大的大卫·福斯特·华莱士 (David Foster Wallace) 说:“学会思考……这意味着学会对自己的思考方式和想法进行一些控制,这意味着要有足够的意识和洞察力来选择要关注的内容,以及选择如何从经验中构建意义……真正重要的自由,需要注意力、意识、纪律、努力和真正关注他人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