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審視自由主義——歷史上的意識形態鐘擺?
新審視自由主義——歷史上的意識形態鐘擺?
徐曦白
公共和政治領域中的重要概念無不具有爭議性,但在過去幾十年中,恐怕沒有哪個概念比「自由主義」更容易引發誤會和爭論。在中文語境中,這個問題格外嚴重。自由主義常常被當作自私自利、無組織無紀律的代名詞;有時也被用來籠統地形容一切反對中國「社會主義」體制的主張。一些人將其等同於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或者美國霸權,另一些人則用它指代在經濟和文化議題上立場偏左的歐美「自由派」,譏諷他們是「白左」、「聖母」。
這種概念混亂,甚至是刻意的曲解和污名化,使很多公共討論淪爲雞同鴨講。自由主義到底是怎樣的學説,它從何而來,經歷了何種歷史變遷,產生了哪些内部流派?這正是羅森布拉特(Helena Rosenblatt)的新作《自由主義被遺忘的歷史》(The Lost History of Liberalism)旨在梳理和澄清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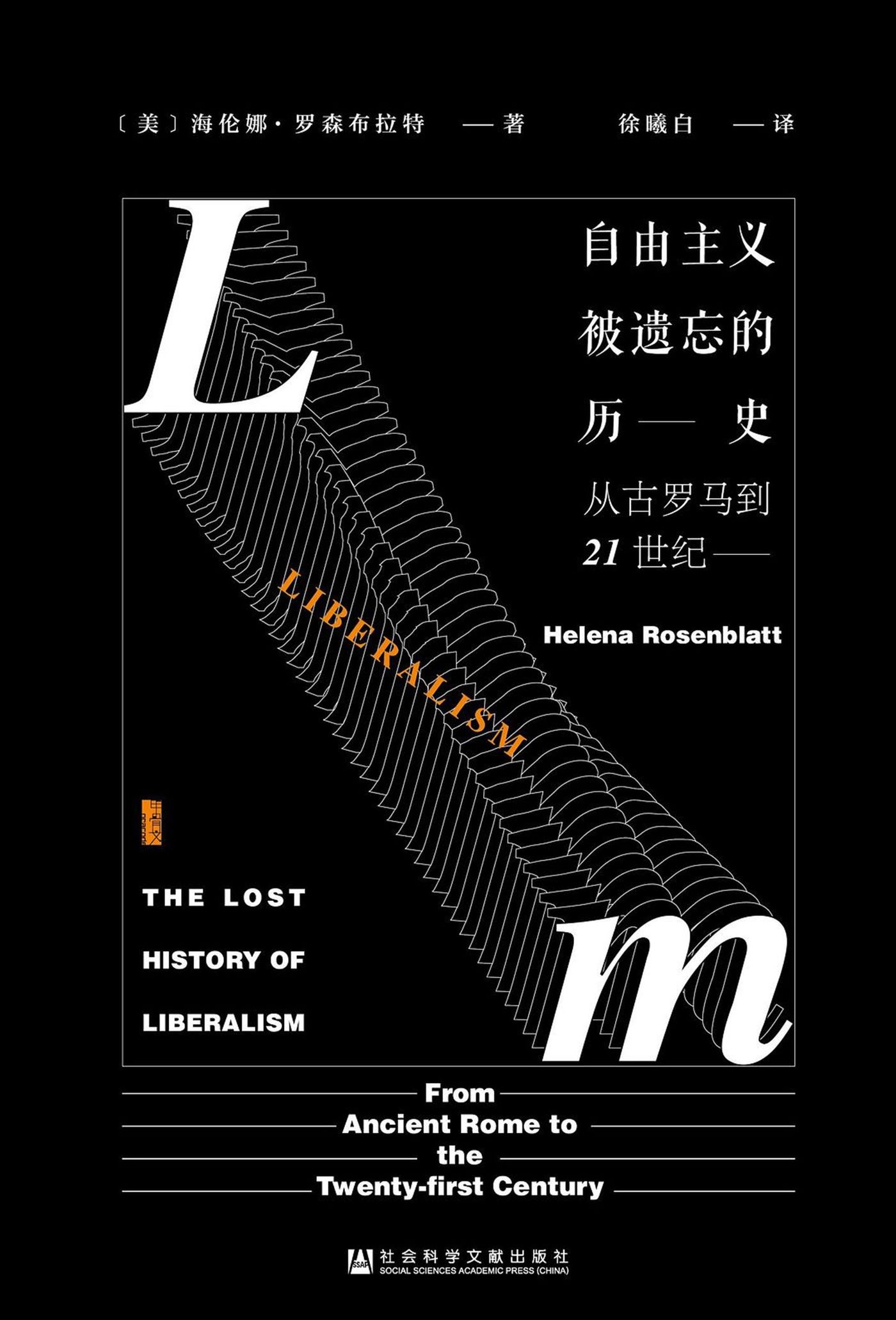
《自由主義被遺忘的歷史:從古羅馬到21世紀》
作者:海倫娜·羅森布拉特
譯者:徐曦白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年10月
她指出,在過去幾百年中,「自由」强調的是高尚、慷慨的公民美德,是社群的共同利益和人與人之間的聯繫,這與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毫不相干。歷次法國大革命在推動這種注重道德的現代自由主義的發展中發揮了核心作用,德國則在19世紀下半葉强化了這一點。然而,這段歷史隨著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逐漸被人遺忘。自由主義被塑造成一種主要致力於保護個人權利和利益的學説,與美國的全球霸權緊密聯繫在一起。人們在面對當下的思想危機時,需要撥開歷史迷霧,回到自由主義的傳統中去找尋、理解和闡發那些被遺忘的核心價值。
「自由」概念的演變
爲此,作者把我們帶回到2,000年前的古羅馬時代,講述了自由(liberal)一詞如何脫胎於拉丁文的liber(慷慨)和liberalis(生而自由的身份)。在那時,自由意味著具有公民身份,不是奴隸,也不屈從於他人的專斷意志。同時,自由的公民需要踐行慷慨、互助的行爲方式,而不是只考慮自己的需求和享樂。自由的對立面恰恰就是自私。這種貴族式的自由理念隨著歷史演進發生著細微變化:基督教的出現為它增添了仁愛、慈善的内容,宗教改革和啓蒙運動擴大了它的内涵,除了人身自由,還需要自由的情操和理念,自由人應當消除偏見,變得更開明,更紳士。到了18世紀,宗教寬容逐漸成為「自由」的核心價值之一,儘管這種寬容僅限於基督教内部。
現代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誕生於18世紀末風起雲湧的革命時代。作爲反抗和鬥爭的學説,自由主義的含義在很大程度上取決它在歷史時刻中經歷的具體鬥爭。在美國,民衆的自由和權利不再是英國君主可以隨意收回的賞賜,而是所有人與生俱來不可被剝奪的。自由而慷慨的民衆自行立法組建政府,政府的權威完全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
在法國,鬥爭的對象則是代表封建主義和專制主義的舊制度(ancien régime)以及和它勾結的天主教會。在革命者眼中,法國的自由原則是保衛共和體制,保衛人民主權,防止反革命復辟,推進法治、憲政、代議制政府和政教分離,並保護各種權利,特別是新聞自由和宗教自由。不過,對美德的討論從未缺席。貢斯當(Benjamin Constant)就指出,天主教會使法國人迷信、軟弱、麻木,要把人們從這種枷鎖中解放出來,才能恢復慷慨、大方、寬容的自然狀態。尋找一種新的、開明的自由宗教,並通過建立公立學校體系對民衆進行道德教化,這成爲貫穿法國近代史的主題之一。除了與天主教的長期鬥爭,在19世紀的歷次法國革命中,自由主義還遭遇了各式勁敵,無論是1848年的「社會主義」,還是拿破侖三世以人民之名所行的專制(也稱「凱撒主義」)。在這些鬥爭中,自由主義不斷壯大,其含義也逐漸顯現出多樣性。
實際上,自由主義從來也不是一個統一的學説。自由主義者對當時的所有重大問題都存在根本分歧。比如,應當支持暴動還是應當在現有體制内進行改良?如何應對貧困和工人福利等社會問題?是否應當給予更多的人投票權?如何看待奴隸制?女性權益的邊界在哪裏?她們是否也應該獲得投票權?自由主義理念能否和殖民主義或者帝國主義相容?
在經濟領域中,人們往往認爲19世紀是古典自由主義的全盛時期,其核心主張是自由放任、自由貿易和市場經濟,反對一切形式的政府干預。然而,那時並不存在古典自由主義,雖然也有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這樣的極端自由放任主義者,但大部分自由派並不把自由放任視爲教條,也不推崇財產權或者追求自利。
相反,很多人明確提出政府有權力監管各個行業,也有義務保護工人利益。托克維爾(Alexis Tocqueville)認爲在私人的慈善之外還需要公共慈善。斯密(Adam Smith)和密爾(John Stuart Mill)對政府干預都有過正面評價。晚年的密爾甚至認爲貧窮與工人的所謂「道德缺陷」無關,而與社會制度的總體失敗關係重大,因而需要更多的社會變革,留下了遺作《社會主義論章》。
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融合與分離
然而這些文字似乎被很多人遺忘了。這就引出一個問題:自由主義的歷史往往是後人根據當時的意識形態需要,人爲建構出來的。比如「古典自由主義」,就是把幾位差異頗大的思想家組合在一起,忽略他們對慷慨、美德和政府干預的論述,只突出他們對個人自由和自利的論述。這樣做的目的當然是爲了針對19世紀末開始流行的,融入了不少社會主義理念的「新型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
羅森布拉特指出,這種新型自由主義最早可以在拿破侖三世那裏尋到端倪。正是他的獨裁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改善工人生活的社會改革和大規模的公共事業計劃。後來的普魯士政府也進行了類似改革,為工人提供强制醫療、工傷、退休和殘障保險。19世紀70年代,德國的經濟歷史學派興起,主張國家有義務致力於公共福利,後者不但不是不可避免之惡,還是國家的最高使命之一。這自然引來了自由放任主義者的批評,他們把德國的自由主義貶低為可憎的國家主義,强調公共慈善只會助長工人的懶惰。法國經濟學家紀德則反駁說,自由放任主義者提倡的是毫不關心公共利益、不道德的自私,也許應該在他們的自由主義名號前加上「古典」二字,以表明他們活在過去,不願意面對新的現實。
德國的思想很快在英國生根發芽。英國的自由派開始主張政府對貧困問題進行干預,不僅應當賦予人們自由,還應該賦予人們實現自由的條件,而不是一味允許資本家無限度地剝削弱勢的工人。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出現了深度融合。霍布豪斯(Leonard Hobhouse)就斷言,真正的社會主義旨在完成,而不是破壞自由主義的理念。連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也説,自由派不必擔心社會主義標籤,因爲只有這種新型的、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自由主義才能使社會發展更加平等。自由黨的事業就是要幫助那些被丟下的人。
在當時的美國,自由主義仍是一個相對冷門的政治術語。直到20世紀初,進步知識分子才開始向美國讀者譯介自由主義。他們當中很多人曾在德國留學,引進的自然也是在德國和英國流行的「新型自由主義」。這個傳統後來逐漸成爲了美國的主流,最終在羅斯福的新政自由主義中發揚光大,以至於不再需要「新型」二字作爲修飾語。正如杜威(John Dewey)所説,自由主義存在「兩大流派」,一種是為大工業、銀行業和商業服務,致力於自由放任,另一種則是更加人道主義的,接受政府干預和社會方面的立法。美國的自由主義與自由放任或者個人主義毫無關係,而是代表了「慷慨和寬容,特別是精神和品格方面的慷慨和寬容」,其目的就是在政府的幫助下促進平等,打擊財閥統治。
一戰的爆發强化了英美同盟。德國成了敵對國,學者們開始避談德國的政治和經濟學說。德國對自由主義的貢獻逐漸被遺忘,順帶著連法國的貢獻也被弱化了。自由、民主幾乎成了西方文明的代名詞,隨著美國國力的增强,美國似乎成了這些理念理所當然的繼承者和捍衛者。二戰進一步抹殺了德國在自由主義發展史中的地位。德國成了「極權主義」和「非自由主義」的總源頭,而歐洲也被視爲自由主義運動徹底失敗的地方。
1944年,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發表了著名的《通向奴役之路》,明確反對政府干預。他警告說,英美的社會自由主義如不加以制止,必將重蹈德國的命運,導致極權主義的復興。柏林(Isaiah Berlin)則在《兩種自由概念》中區分了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他認爲保護個人自由,使個人免於政府的强制或侵犯的消極自由才是符合自由主義原則的。强調能夠「去做」的積極自由許諾的是某種「集體的自我指導」和「自我實現」,這通常與極權主義或者烏托邦式的社會工程相關,最終反而會以自由之名剝奪個人自由。
正是在這樣的批評中,原本有機相容的自由主義被切割成了兩個涇渭分明,甚至相互敵對的傳統。一種是保護個人權力和消極自由的英美自由主義傳統,另一種是强調平等、干預,旨在實現積極自由的法德自由主義傳統;後者成了暴力、混亂和極權主義的代名詞,就連羅斯福的新政主義,也被貼上了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的標籤。正是在這種冷戰的學術氛圍中,美國的自由主義者開始轉而强調個人權利,不再談論平等、干預或者改革,試圖以此撇清身上的極權主義標籤,但在這個過程中,自由主義幾百年來對慷慨和美德的追求,以及法德自由主義在國家建設方面所做的努力都被一筆勾銷了。
自由主義的左右鐘擺
作爲高舉法德自由主義傳統的矯枉之作,《自由主義被遺忘的歷史》還原了法德兩國在自由主義發展史中起到的重要作用,這對於只了解英美傳統的讀者來説,無疑具有醍醐灌頂的意義。但對不了解自由主義歷史的讀者而言,搭配偏重英美傳統的作品對比閲讀,可能會產生更好的效果。限於篇幅,作者對德國的描述明顯比法國更簡略,一些重要的德國自由主義思想家,例如康德、歌德和洪堡竟都沒有出場,不免令人遺憾。
該書的最主要問題在於當代自由主義部分。美國的「自由派」可能很難接受作者的觀點,認同自由主義已經淪爲主要致力於個人權利的學說。他們會反駁說,那只是大衆化和庸俗化的理解,或是自由主義的某些批評者加諸的錯誤指控。在當今美國的語境中,「自由主義」指的恰恰就是反對自由放任、支持政府干預和收入再分配的主張,或者說就是「大政府」的主張。這正符合杜威描述的那一支强調慷慨、公德、共同利益,反對財閥統治的自由主義。2016年和2020年桑德斯參選總統帶來的關注熱潮就是明證。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等青年政治家也已接過衣鉢。更重要的是,即使這一傳統在美國稍有衰微,在它的故鄉法國和德國,以社會民主主義爲代表,旨在保護個人自由的同時,兼顧社會平等、公正的自由主義傳統仍然佔據著意識形態上的主導地位。
此外,雖然書的副標題是「從古羅馬到二十一世紀」,但作者只寫到二十世紀中葉,並未提及二十世紀末「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興起和本世紀初以來自由主義面臨的危機與挑戰。如果將這部分補齊,讀者就會發現,「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個人自由與民主的關係、宗教與世俗化的衝突、自由放任vs政府干預、種族主義、帝國主義、社會主義這些自由主義者幾個世紀以來激烈爭論的議題,在今天依然是我們無法迴避的問題。
歷史有如鐘擺一般,在19世紀末,擺向了以政府干預和再分配來修正自由放任主義的「新型自由主義」。這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歐美工人階級的境遇,避免了馬克思預言的那種暴力革命,並一直延續到羅斯福新政和歐洲福利國家的誕生。到了20世紀70年代,哈耶克的傳人們重新發明出「新自由主義」以對抗政府干預。歷史又開始向回擺,削減公共福利、減少市場監管,放開資本流動成爲主流意識形態,而這也造成了嚴重的分配不平等,直接引發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和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其惡果今天仍在不斷浮現。哈維(David Harvey)認爲,新自由主義是全球化背景下自由主義被金融資本主義吞噬的產物,正因如此,自由主義爲人們帶來自由、平等和繁榮的許諾無法得到實現。
從這個角度來看,羅森布拉特為當代自由主義開出的藥方——僅僅重回自由主義的傳統思想資源,找尋關於慷慨和美德的理論——恐怕不足以應對當下的各種結構性問題。我們可能需要更大膽,更激進的想法,需要奪回「新」字,發明一套「新新新自由主義」。這套新新新自由主義需要堅守核心的自由價值,比如公民權利、憲政、法治和對政府權力的約束,抗拒威權主義和民粹主義對民主的侵蝕;它需要保持對普世和平等的追求,能夠强力制約全球資本主義,並以必要的手段在全球範圍内消除經濟,文化和社會心理上的不平等,創造平等的機會;它不能僅限於某種道德相對主義,而是應當如書中所説,注重社群和公共利益,並給人們帶來必要的歸屬感。
羅森布拉特向讀者展示了自由主義的多面性。它不是單一自洽的學説,而是龐雜到有些混亂的思想拼盤,或如施克萊(Judith Schlar)所講,是由 「不同傳統構成的傳統」(tradition of traditions)。這當中既有個人主義、自由放任,也有平等主義、改良主義和普世主義。它們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可能達成妥協或者平衡,但在更多的情況下,自由主義内部的分歧和爭議甚至超過了自由主義與其他競爭理論的分歧和爭議。自由主義的歷史就是秉持自由信念的人們不斷試圖推翻過去的壓迫和枷鎖,尋找在自由的條件下和睦相處之道,應對每個時代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挑戰的歷史。羅森布拉特這部跨越數百年、內容無比豐富的政治實踐史也將爲我們應對時代挑戰提供無價的理論寶藏。
注:本文2021年1月16日首發于端傳媒,獲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