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谁在伤害底层?就“不稳定无产阶级”概念谈学术及其政治

【编按】此文就“不稳定无产阶级”概念谈学术及其背后的政治,编辑部认为本文从某个侧面回应了近期学界关于“底层研究正无形地伤害底层”的讨论。《隐形的伤害——“底层研究”与民粹性学术》一文认为,“很多‘底层’学术研究……在学理上制造了极端二元论,通过学术话语不断制造和强化了社会的‘断裂’”。我们需要指出,不管是996猝死的社畜,为讨薪自焚的快递员,或是在爆炸中被埋于矿洞的矿工和因尘肺窒息而死的工人,资本之恶即使是再高明的学术研究也不过是描绘其机制,而不足以在“学理上”造就这样的对立。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改革和劳动关系转型带来的究竟是“不同群体社会功能的互补和依赖”,还是基于阶级位置和利益的“对立”,对于这一问题的判断和立场,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伦理和政治的问题。假装中立地宣称“整体”、“互补”或是“自愈”不过是掩耳盗铃。
文|马岚
劳工研究、底层研究中的学术概念从来不可能是中立客观的、描述性的,而必然携带着特定的政治内涵。比如,马克思和韦伯在“阶级”概念上的著名分野并不只是由于两人看到了“客观”阶级问题的不同侧面,而更是反映了不同的政治方案和未来想象。本文以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 提出的“不稳定无产阶级(precariat)” 概念为例,剖析学术概念背后的政治意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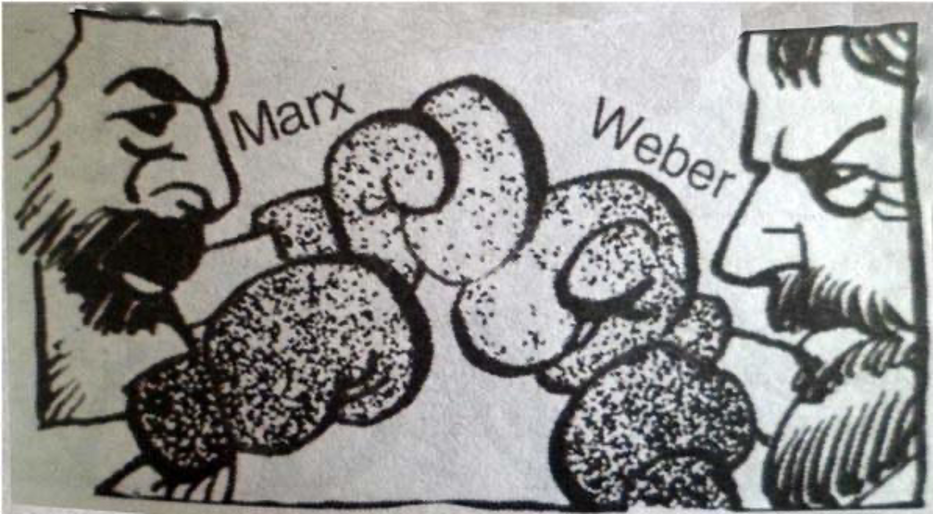
什么是“不稳定无产阶级”
“不稳定无产阶级”的概念最近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中国,逐渐取代了“非正规劳动”。斯坦丁指出,“不稳定”(precarious)一词的原意是“以祈祷的方式乞求(to beg by prayer)”,这意味着,不稳定无产者首先是一个“恳求者”,他们需要依靠他人回应自己的需求,需要他人的帮助方能过活。斯坦丁将不稳定无产阶级视为形成中的社会阶级,他认为,“非正规劳动”不足以描述当下工人面对的困境,而不稳定无产阶级这一概念则更准确地描绘了在不稳定就业的情况下,工人在阶级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他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斯坦丁所描绘的不稳定无产阶级涵盖了兼职人员、非正式工或临时工、季节性工人、自雇者、派遣工、学生工、实习工、志愿者,以及很多其他与雇主存在非正式雇佣关系的人。如此,不稳定无产者可以是高技能的知识工人或创意工人,也可以是低技能的工人,因为界定他们阶级身份的是他们的就业状况,是他们非正规(informal)或不常规(irregular)的工作方式。在这种韦伯式的阶级概念中,职业技能构成了阶级分化的基础,就不稳定无产者而言,最终决定了他们与其他阶级相区别的阶级身份就是在就业市场上缺乏保障,以及只能通过短期的、非正式的方式来参与就业的境况。
“不稳定无产阶级”的概念是相对于“无产阶级”(proletariat)而提出的。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推动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政府放松对资本的管制,强调通过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flexibility)”使企业得以提高效率、适应国际竞争。在资本得以在全球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工人却是相对固定的,这就带来了劳-资关系的重组,工会的力量被不断削弱,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黄金年代(20世纪60年代)通过抗争得来的稳定就业和社会福利被不断侵蚀。斯坦丁和其他这一概念的使用者认为,相对于20世纪的产业工人,不稳定无产者只能部分地参与劳动、时刻面对就业不足的风险,并且为了获得工作的机会和维持基本的生计,他们往往需要不断地寻找新工作机会,同时不得不承担大量的“无酬劳动”。与稳定就业的产业工人相比较,不稳定无产者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缺乏就业保障,没有稳定的雇佣关系,没有获得社会保障的渠道,同时缺乏完整的公民权利,由此引发出来,也难以就自己的“劳动者”身份建立归属感和集体认同,失却了传统“工人阶级”的地位、荣耀感和团结。在斯坦丁那里,不稳定无产者面对更多的,是分裂和脆弱,他们“缺乏清晰的阶级意识”,“内部充满着激烈的斗争”。

“不稳定无产阶级”在中国
在中国,“不稳定无产阶级”的概念尤其多地被用来分析数量巨大的农民工,他们受困于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城市中的“次等公民”,由于没有城市户口,他们被剥夺了在城市接受教育、医疗、养老等等基础的社会权利,到2017年底,农民工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的比例仅22%,参加失业保险的比例则为17%。在工会参与方面,2019年,13.4%的进城农民工加入了工会组织,然而,在利益受损的时候,进城农民工却很少通过工会寻求解决方法。同时,农民工也面对极其不稳定的就业环境:即使在《劳动合同法》出台之后,2016年,农民工与雇主和单位签订劳动的合同比例仅为35.1%,甚至低于2009年的42.8%(2016年以后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都没有公布这项数据),而因各种原因被拖欠工资的情况却很普遍。
李静君透过“不稳定无产阶级”的学术棱镜来考察中国农民工。她认为,在中国“有两个制度性因素使不稳定持续存在”:政府在劳动法的修订和执行上,机会主义的政治取态(如选择性地执行、对工人组织化的打压等);将农民与土地分离的土地改革(如土地流转、合村并居等)。在这样的学术棱镜之下,李静君一方面看到失地农民、新生代的农民工意识到自己处于社会底层的位置,面对“威权体制下的雇佣关系不稳定”,另一方面又强调在威权体制之下,劳资纠纷只能是暂时的,因为国家机器会不断纳入并消除这些纠纷,而相对应的,不稳定带来的分裂则使得工人中间不可能积极地形成阶级团结,工人的要求只会越来越多地转向养老金、住房、生计等再生产性的议题,而对生产领域的问题不再有反抗意识。
今年8月,新冠疫情之下,《探索与争鸣》杂志的讨论会上,众多学者针对零工经济、平台工人的讨论亦重提了“不稳定无产阶级”的概念。平台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平台工人,包括平台上的外卖工人、网约车司机、家政工人、作者等等,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而对于这些工人工作困境的描绘和现有法律框架的分析都引向不稳定、制度保护缺失、分散化(分裂)的结论。
诚然,我们不应否认,“不稳定无产阶级”的概念被用于分析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发展之下工人阶级的困境有其合理之处,然而,这一概念的运用亦存在更大的问题。譬如,在这一概念框架之下,无论是李静君、亦或是分析零工经济之下平台工人的学者们,都很难看到工人团结的可能和反抗行动,“不稳定无产阶级”在强调困境的同时,否定了工人的能动性和现实存在的阶级行动。而事实上,零散化、不稳定的雇佣方式虽然打散了原本集中稳定的工作方式,给团结带来了客观的困难,但它同时也加深了对工人的剥削,而剥削的深重必然也带来更强烈的反抗:2018年塔吊司机的罢工行动如此,今年双十一前后的快递工人罢工亦是一例。

我们认为,“不稳定无产阶级”概念的问题在于对“阶级”的错误认识,而这背后,则是相关学者没有充分意识到学术背后的政治意涵,很多自认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政治性缺乏认识。
“不稳定无产阶级”、“阶级”与政治
盖伊·斯坦丁关于“不稳定无产阶级”的论述在学界已经饱受批评。
芒克(Munck)指出,它假定了“一个只存在于神话中的、稳定而且有完整的社会和政治权利的工人阶级”,并以不具备这种“工人阶级”的这种权利和稳定的雇佣关系来定义“不稳定无产者”。不少历史学家指出(比如彼得·莱恩博、尼格拉斯·弗吕克曼等),作为“工人阶级”的“理想型”的工薪劳动者(wage labour),在历史上便不是“工人阶级”的主流,数量更多的反而是“非正式”的工人,战船上的兵工,矿场上、农场上的奴工,困于家庭的家政工。将资本主义黄金年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里具有相对稳定的就业和福利保障的产业工人作为“工人阶级”的模板,不能不说是一个怀旧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劳工理论模型。
赖特(Wright)和布拉加(Braga)的批评更加犀利。他们认为,不稳定无产者不应该从工人阶级中被区分出来,无论他们的劳动力是用何种特殊的形式被购买的(全职雇佣、兼职雇佣、自雇亦或是平台劳动),作为领工资的劳动者,他们拥有一些共同的利益。苏熠慧和姚建华指出,“由于‘不稳定无产者’在物质基础上和传统工人阶级并无根本性的差异……它最多算是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下无产阶级中失权的那部分群体”。赖特认为,斯坦丁“过多地强调了分裂,而不是团结,而这种团结在事实上是可以存在的,也是应当被向往的”。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和潘毅进一步指出,诚然就业状况的复杂性和工人在劳动力市场所处位置的分化确实影响到阶级的团结,但这只可能是延长阶级形成的过程,而不会完全阻止这一过程。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斯坦丁那里,阶级不是由生产方式和所有制来界定的,而是由“就业状态”来界定的,这就意味着,工人可以通过签订不同的雇佣合同来改变他们的阶级位置。然而,这种做法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雇佣合同的条款设置常常是人力资源管理的策略。比如,很多工人最初是通过中介机构受雇的派遣工人,然后,经过雇主一段时间的考察再赚到正规的或者是连续性的就业岗位上(换句话说,获得相对“稳定”的雇佣关系),事实上,全世界的大雇主们都在使用这种“从临时工到长期工”的挑选机制,这种“稳定”或者是“不稳定”的雇佣关系更多地是一种管理策略,而不是阶级策略,工人合同的改变不应该被解读为“阶级过渡”。

那么,阶级如何被界定?
史密斯和潘毅反对这种韦伯式的阶级划分标准, 强调应当回归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要回到阶级构成要素的基本问题。达伦多夫(Dahrendorf)认为,对马克思来说,阶级可以理解为由三个基本成分构成的有机概念:首先,一个阶级通常被理解为“客观”因素,在资本积累和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它与生产资料有着共同的关系,同时又与其他阶级相对立;其次,阶级意味着其成员必然会对他们的共同利益有类似的看法——这通常被称为阶级意识;最后,各阶级随着生产领域内冲突的进展而展开组织化的进程,随着资本主义的成熟,社会对抗日益深化,并且,工人阶级围绕着工资的斗争变成了围绕着控制政治权力的斗争,即阶级斗争。从这样的理解出发,阶级是一个关系性的概念。
在这样的视角下,我们看到改革开放引入市场机制、外资的涌入、私人资本的重生,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这些都构成了阶级关系重建的物质基础。不管是国企下岗工人,或者是身份“暧昧”的农民工,或者是没有获得合法雇佣关系认定的平台工人, 他们劳动合同的形式、工作环境的变动以及他们对于自身身份的讲述并不改变他们作为工资劳动者(wage labour)的性质,亦不会改变他们所处的生产关系——这就是阶级的物质性。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二元结构、不稳定、零散化、机器换人等等越来越困难的境地之下,工人对于自身阶级位置的醒觉,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抗争行动。不管是以法律诉讼的形式,或者是静坐、罢工,乃至自杀等行为,不管是在工作场所的行动,或者是在法庭上、街道上或者是其他的空间里,在剥削越来越深重的情况下,工人的行动只会越来越激烈,越来越频繁,所谓“威权体制下的雇佣关系不稳定化(authoritarian precarization)”并不能够阻止工人的意识觉醒和抗争。

结语
关于学术的所谓“价值中立”,早被证明不过是一厢情愿。学术亦是政治的,学术概念背后的政治意涵需要我们保持时刻的警觉。自认关心底层的研究者带着什么样的学术棱镜进入到田野,必然影响他们如何选择性地看到或者看不到某些现象,选择性的强调或者忽略种种现象的某些侧面,这也是学术的政治。于是,要应对“不稳定无产阶级”的困境,盖伊·斯坦丁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这个看似激进的解决方案事实上维持了不稳定无产者“以祈祷的方式乞求”的状态,只是“乞求”的对象从老板、亲朋戚友变成国家;而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之下,数量越来越广大的不稳定无产者的劳动境况并不会改变,所有制的基础不变,分配方式的改变就不可能“稳定”,“全民基本收入”这样的施舍便不可靠。可靠的只能是无产者自身的团结力量,而这样的团结在剥削越来越深重的情况下就必然会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坚定。
参考阅读
苏熠慧、姚建华:“不稳定无产者”是“新危险阶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