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子里的人 | 社会学半吊子看社会阶层


最开始也是因为很偶然的原因,匆匆忙忙地加入了「炉子里的人」这个栏目。一直到大概一个月前的晚上接起文轩的电话先互相熟悉,尝试聊聊选题的意向,这篇稿子才算是真正开始。文轩的语速很快,语调也很明快,我们从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社会学学科设置聊起,聊到了犯罪学、性研究、自身丁克的抉择、高三到大学的经历、文学小说、宠物、室友、家庭氛围、自己的社交经历和性格等等,洋洋洒洒三四个小时。临结束前也还没有能确定一个合适的方向,怎样才能把我们的个人经历转换成大家都能有共鸣的内容,带来一些引申的思考,这些都压在心头上,好像变成了某种责任。
大约过了一周,我们打算跟吴丹一起聊一下,加入她的视角或许能够帮我们聚焦话题。凑巧的是,吴丹的欧洲留学生活背景、文轩的香港留学背景还有我在广州上学和生活囊括了极大的地域空间和一定时间长度的生活经验,给我们的讨论增加了不少真实的素材。可能是文轩聊到城市里的流浪者,我说到前段时间看到的一篇牛津大学学生的文章,吴丹提到大学里的生活区隔的时候,讨论方向豁然开朗,不如这篇稿子就谈「阶层」吧。谈「阶层」好难,我们几个大学生又能对社会有怎样深刻的感悟呢?聊阶层恐怕也只能从有限的间接的生活经验入手泛泛而谈,是否太过单薄,又能为读者提供怎样的思路呢?再者,「阶层」本是个和不平等深刻相关的宏大学术命题,内嵌于中外社会发展的政治历史格局之中,抛开结构和理论只谈结果和经验,又是否太过片面?总之,依我所见,处处皆限制。
我想了很久,不能因为我们自认的不足放弃发声的自由和意愿。作为大学生,面对「阶层」,我们的故事是什么?我们如何讲述自己的经历?面对其所带来的对生活的种种震荡,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所以,重要的不仅是内容,更是内容里面尝试传达的某种复杂的和难以言说的情绪和态度,希望大家在其中也能看到某个阶段拧巴、无奈、又带点理想主义和乐观精神的自己。
——陈可沂

首先,想问一下两位最开始为什么会选择社会学这个学科?作为社会学学生的自我观感是怎样的?
可沂 | 好像没有怎么纠结过学校和学科的选择,高考结束后度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暑假。高一的时候班主任曾经邀请两位前辈来我们班宣讲,其中一个学姐说她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念书,系里会有各种各样田野实习的机会,比如可以上岛研究黑猩猩,毕业了还能去各种地方给大公司做市场和文化研究的工作。这一下子就吸引了我,能旅游还能工作,研究人类和社会也不赖嘛,就记在了心里。两年之后填志愿,成绩也还可以,自然而然就来读书了。
文轩 | 我选择社会学也没有想太多,纯粹出于兴趣。虽然有时也会担心就业问题,但更多是一种“船到桥头自然直”的盲目乐观。我们港城大的学系安排比较特别,入校的时候是都在“社会及行为科学”一个department里,大二会分流成三个专业,心理学、社会学及犯罪学、社会工作,我现在就是在社会学及犯罪学。但正因为心理学这个分流的存在,其实我认识的不少系友都是冲着心理学来的,所以跟我一样真正想学社会学的其实很少。实际上,心理学名额比较紧张,不少进了社会学及犯罪学的同学都在考虑转专业,你能看出来社会学在我们这儿是什么地位了。(笑)
可沂 | 确实,社会学的地位有点尴尬。但其实我有关注另外一些东西,比如在中大社会学系一共有65个人,前几周我听了一个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的升学分享讲座,数据显示我们院出国深造的比例在去年达到了48%。也就是说,将近一半的社会学学生都有条件出国留学,我很惊讶,也相信这个数字在全校来看是比较高的。抛弃其他条件,从经济方面也可以看出我们学院学生的家境都是非常不错的。我初中念的是广州非常好的一所公办高中的民办学校,又去到了这所高中念书,身边的同学形形色色。我可以感觉到,选择社会学的学生并不算是社会顶层,或许是因为选择其他学科,经济金融啊、法律啊、医学啊、顶尖技术类型的,或是为了维护社会制度带给他们父辈的红利,或是为了在向上流动过程中争取到一席之地。相反,社会学系的学生家庭优渥,但并不像所谓的“精英家庭”那样对子辈有严格的要求和规划好的路线,相对来说尊重子辈的选择,也有相应的条件支撑我们的理想化成分。这一点,我这周和我舍友聊职业规划的时候我们都挺赞同的。
文轩 | 我也有同感。我有时候去逛豆瓣的一个小组,叫做“985废物引进计划”,里面聚集着很多身在985、211名校但是感到各方面不如身边的同学、对未来非常迷茫的大学生。我看到过一个帖子,楼主是人大的社会学学生,他是一个从偏远地区考到北京的文科状元。他发现自己的英语和高数比同学差很多,经常不及格,但他社会学专业课成绩很好。我想大家应该会给他一些提升英语和数学的建议,结果发现评论区清一色的让他转专业到计算机或者金融。可这两个专业明明对数学要求更高呀。哑然失笑之后,我其实也能理解他们的想法,因为楼主的家境一般,他通过高考来到北京,正在经历所谓的阶级跃迁。就像可沂讲到的,社会学学生一般都家庭比较优渥,或者说大多数来自中产家庭。因为社会学确实不是一个赚钱的学科。我们的教授在分享三个分流专业的职业前景的时候,心理学自然有一大堆,社会工作也有不少,到了社会学及犯罪学只有一句话:这个专业并不是指向某个职业的培训,而是培养人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所以可能对于很多社会学学生来说,“毕业即失业”不仅是一种自嘲,更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也导致社会学学生可能往往是一群关心社会、希望能针对社会问题做出一些改变、带着些许理想主义的人,但这种理想主义是需要一定经济基础的。另外,社会学的学历成本也会比理工科等高一些。像香港本地的学生并不倾向去读很高的学历,很多理工科学生本科毕业就会踏入工作岗位,但社会学基本上都会读研。

可沂 | 可能我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社会学是学什么的?还有,以后能干什么工作呀?被问多了,也就习惯了,可能我在就业这方面还没有太过浓烈的焦虑感和被边缘的恐惧吧。
文轩 | 对,而且我觉得社会学没有那么高的市场效益并不意味着它是无用的。相反,社会学的调查研究能帮助揭示和解决社会问题,而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社会上很多的偏见、污名化都是不成立的。比如贫困问题,政府一般都会为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提供补助,很多人觉得补助花费太高,要求个人为贫困负责。但实际上贫困是一个制度性问题,因为贫困往往意味着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缺乏,个人其实很难仅仅通过努力实现阶级跃迁。当然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几位教授对性工作者的研究,在香港一位四十岁的性工作者月收入可以达到十万港币,而且事实上很多性工作者是自愿做这个工作,也不会觉得不体面。这些更准确的信息能更好地帮助决策者分析问题、制定政策。
可沂 | 确实,我真的会碰到别人问我你专业对口的工作是什么,然后回答不上来。大一的时候我上社会学概论的课程,教授跟我们说“或许很多年之后你们都忘记了社会学的知识,忘记学过了什么,但是社会学带给你们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式会留存在你们身上。”对于这个性工作者的话题,可以关注一下国内潘绥铭教授和黄盈盈教授做的研究。文轩提到的性工作者的话题,主流文化也许认为是肮脏的、不合法的、黑暗的,但是在社会学的研究中,许多学者主张将性工作者这个群体从社会边缘拉回,重新审视性工作者的身体和动机,企图从女性主义的角度重新进行解读。相关研究里面有很多珍贵的一手资料给我们展现了这个行业更为丰富的图景。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说,性工作是否合法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它不仅仅关乎性、经济,还关乎于家庭、城市规划、疾病控制,它是可以作为一个产业来分析的。
文轩 | 是的。你刚刚讲到“社会学带来的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式”,我真的会感觉到自己的思维方式跟以前不一样了。就像米尔斯(Mills)所讲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很多看似个人化的境遇其实都离不开大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比如一个人贫困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贫困作为一种现象和市场经济是永远分不开的;哪怕是一个学生成绩的好坏,都和其家庭出身、教育制度等等有很大联系。其次就是一种比较经验主义、现实主义的态度,很多知识分子喜欢泛泛而谈,虽然也能给出很多见解,但其实在社会学研究中只能算作假说。因为他们看到的数据不够多,他的结论可能不是概括性的;或者他未必对当事人有深入的访谈,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假设和臆想。社会学研究的结论必须要有定量数据和定性数据的双重支撑。这使得我总是提醒自己,对不了解的事情不要妄作评判。

在自己的受教育经历和社会经历中,感受到的阶级/阶层是怎样的?
可沂 | 这个肯定是有的。这里面带给我的生活感受也很复杂,最直观的就是身边发生的所谓“有钱”的同学、“特权阶层”意识不到他们所享有的优势而无意伤害到他人。实际生活中可能出现的语言区隔、生活方式区隔等等都能体现。但我始终认为,区分所谓阶级和阶层的不同,并不在于衣食住行,也并不是说这个人喜欢什么、爱好什么就能决定其所处的社会位置。结合我自己的生活经历,我记忆最深刻的一点是“站得高,望得远”,他们往往能对人生经历和规划有着超越年龄的把握,对社会现象和社会制度的运行有着更加清楚的认知。之前我在我们系教授的公众号里看到一篇文章,是他一位在牛津大学读研究生的学生记录的如何在牛津大学这个“田野”里看见他者,看见自己。文章提到由于牛津是贵族学府,里面的学生社交时会有意无意用介绍自己家庭背景和财产的方式跟你打交道,令作者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困境。一段时间过去后,作者问他一个相熟的同学说我怎么才能融入你们的社交圈子,那个英国同学跟他说:“不要跟现在这样讲话(英语)。”
文轩 | 是的,虽然阶级跟一个人的视野和能力不可能是完全正比的关系,但确实感觉到一些家庭条件特别好的同学站到了更高的平台,更有可能看的长远。相反,就像我之前讲到的“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以及所谓的“小镇做题家”,其实你真的很难责怪他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们的家庭出身、所在的城市、应试的教育制度限制了他们的眼界和应试以外的能力。他们或许是功利的,但阶级跃迁是有风险的,所以常常会采取一种保险的心态。我的一位叔叔,他初中的时候成绩很好,但是他父母坚决不让他上高中,而去上中专。因为他们是农村户口,有了中专学历就可以“农转非”——农村户口转非农村户口。虽然他当时成绩优异,但他父母就是担心他上了高中考不上大学,就没办法转城市户口。这就是一种保险心态,尽管他明明很有可能考得上大学,但他们经受不起考不上的代价。
至于社会的底层阶级,我觉得在大城市里是越来越隐性了。我印象里十来年前的上海,经常能看到商业广场、路边、地铁有乞讨者或者卖艺者。但因为影响市容,这些底层的人慢慢地“消失”了。我高中的时候,地铁里乞讨的人就已经很少了,偶尔会有在车厢里乞讨的,但现在真的完全看不到了。至于街边乞讨,有时能看到唱歌卖艺的,但真正意义上的流浪汉我已经不太能看到了。曾经有一位流浪汉,搭了一个小棚子在我们家小区门口,住了可能有十几年了,平时会帮我们修修自行车什么的。三四年前开始看到有城管模样的人时不时来找他,直到大概两年前,他的棚子被拆了,我再也没见过他。上海是一个大城市,但繁华不属于他们。我们身在一二线城市的人可能会觉得没有他们城市更“文明”了,但我们看不见不意味着他们会活得更好啊,我们只是把他们赶走了而已。一个城市要靠一种不文明的方式变得文明,这是常常令我感到悲哀的一点。
吴丹 | 问大家这个问题,其实是因为我在中国时关于“阶层”的观感其实并不多,从身边人的观察来看感觉这个问题多少是和所从事职业和受教育程度有关。自然,来自东南沿海的自己和身边许多人是有享受到一定的社会资源的。温州的社群感觉其实是相对封闭的,可能社会联系就是那么固定,而人情世故在阶级资源中也扮演一定角色。
在大学则是另外一种体验,和可沂提到的牛津“田野”的环境其实蛮像。巴政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学府,虽然学校有拓宽招生途径以招收更多来自教育弱势地区的学生(法国本土、海外属地等),但在以英语授课为主的项目,学生群体和背景其实相对单一:中产、国际化履历,语言优势,精英出身也屡见不鲜。在法国,有许多高中都是公认的未来名校学子的培养基地,而在学校的bubble里许多人都有着类似的来路,各有各的圈子。这段时间我校因开学周新冠感染人数登上了媒体报道,而在讽刺漫画中我们都是“衬衫西裤,香槟在手,面容高傲、正在参加晚宴的白人男性”(大概是法国民众对巴政学生的刻板印象吧)
我是我小班课上唯一的非白人,同学里甚至有一位出身法国名流,社会学课则是我最会和大家“吵架”的时候,因为确实我们的生活经历、体验都是与成长环境和自身阶级背景息息相关,会有时觉得大家“不知民间疾苦”,也同时会思考并尝试定义自己的身份。尽管有“政治正确”和强调包容、多元的环境,但大多数人会很难理解我在校园外的日常和心理体验(而我也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不理解和距离感)。同时学校给到学生群体的非教学资源和支持并不多,在应对困难或是寻找机会(实习、工作等)的时候会感受到更多的阻力。和在牛剑上学的朋友讨论这个问题时会有很多共鸣,也会发现我们有在避免和一些“over-privileged people”过多接触(当然,身处不同的圈子/阶层里本来就会有距离),因为其中会有许多和“阶级”相关的冲击和不理解,让自己会很困惑吧。有时会被校长甚至身边人的“精英论调”打击到,但是我想自己已经是因为拥有一定的资本才来到这里,也希望在这个平台进行资本重组,而外面的世界和社会还有更多我无法切身体会的生活观感。
至于阶层问题,如何看待自己所处的阶层?这让你与周围生活的联系何在?
可沂 | 阶层这个问题在中国大陆按我自己的感觉来说是一个比较隐晦、比较微妙的话题,大家都知道、大家都能感受到,但很难光明正大地提出来,我们都是无产阶级(笑)。在衡量阶级的三个标准: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中单独拿任何一个出来比较都是片面的。和我们生活联系最紧密的或许是文化资本的积累,我们通过高考进入大学,进入更好的大学,继续深造,每一步都是文化和社会资本的积累。那其实反过来讲,每年出现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盛况和“小镇做题家”等现象的出现是不是在警醒我们对于文化资本的追求和积累如此执着代表了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积累之路的无望呢?据我所了解到,像是在德国或者欧洲大部分学生对于进入一个好大学没有这么强大的执念,许多人都选择留在家乡就近上学。在中国语境下仿佛形成了一个有前后因果顺序的逻辑,先进入好大学才有好未来,反正我觉得怪怪的。
文轩 | 国内的阶级划分可能确实不如国外那么复杂。国外有的家族企业、贵族身份可以延续好几代,但我们阶级的区分很大程度上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的,因为毛泽东时代的一系列运动把旧的阶级几乎完全摧毁了,有学者甚至认为1949-1994的中国是一个“扁平社会”。因此国外的阶级可能也与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相关,或者享有一些经济以外的认同,比如宗教信仰、贵族精神等等。但我们的阶级观可能更多关乎消费。我记得《中产中国》有一篇文章讲到,中国公众对中产阶级的认知被媒体、流行文化和消费文化塑造,消费是区分中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决定性标准。加上人口基数和城乡发展不均的问题,中产阶级在国内语境中也通常指中上阶级甚至上层阶级,而不是字面上的中等收入的普通家庭。至于对文化资本的过分追求,其实更多跟就业市场相关吧。我们这一代对学历的追求普遍比父母辈高,一方面当然是教育水平提高了,另一方面可能是所谓的“文凭通货膨胀”或者“文凭凯恩斯主义”,因为就业市场容纳不了那么多年轻人,只能让我们多读会书咯(笑)。
可沂 | 文轩提到“消费是区分中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决定性标准”这一点我是不太赞同的。某个阶层的群体对应某一种生活风格与方式或许有规律可循,但反过来说用某一种风格对应阶层是无法解释的。首先是因为城市生活已经被消费文化和消费欲望裹挟,过剩的生产力制造出了足够多的商品供我们选择。广告、媒体和品牌塑造出一个充满幻想的浪漫世界,到了七夕就要口红礼盒,到了圣诞节要限量包包,最喜欢的品牌出了联名,哪里又新开了一家米其林……所有人对生活的美好期望都被这些商品符号所激发,渴望拥有这些代表着优越、舒适和精致的商品,看似这些商品对所有人都开放,而不是只供给贵族。然而“消费民主”在激发消费和享受欲望的同时,忽视了这只会给原本就消费不起的阶层和跳一跳才能够承受的阶层带来相当大的负担和冲击,经济上的、心理上的。表面上看,大家只要有能力这些商品都available,实际上刷爆信用卡和只用一顿饭钱去购买同一件商品是有差距的。我想表达的是,批判消费社会所体现的的衣食住行来替代阶层的区隔是不够恰切的,不能够通过批判符号的方式来掩盖真正的阶层问题。
吴丹 | 我在国外生活的体验实际比较复杂。身处移民社群,肯定有体会到阶级差距以及阶级弱势,而在本地人社群(尤其是奥地利等社会福利较高的国家),感受到的更多是阶层而非阶级。一位老师和我解释,在这里阶层之间的矛盾并不如阶级矛盾那么尖锐,教育和社会福利使得阶层向上流动的成本更低,而按比例选举的议会使得各个阶层的声音都可以得到反馈、互相协商,避免重新洗牌式的revolution。我身处经济政治资本弱的移民阶层,有感受到许多阻力,同时也会为在这里长大的弟弟妹妹担心——他们的生长条件和我在国内所能接触到的资源相距甚远;而在异国社会,从零开始建立社会联系、融入(integration)也是一个挑战。
而在疫情的风暴里,我所经历、看到的恰恰证明了在社会学课上学习的理论:各方面资本占有量少的较脆弱阶级受到的打击更大。海外华侨许多都是服务业从事者,疫情的冲击让许多家庭直接失去收入,而许多父母没有较多接触新媒体资源,孩子在网课教育中也有很大的影响。信息的获取和接收又是另一个点——数字时代的“信息鸿沟”其实产生了信息层面的阶级之分。之前在澎湃有关“信息鸿沟”的报道里读到一句“知识改变命运,前提是能接触到知识”,我想,这可能会加深所谓阶级的固化,也是数字时代显明的社会不平等体现;再比如说“假新闻”和低质量信息的大肆流动,身边总有人对一些阴谋论、煽动性话语深信不疑,而无论中外,在信息取得的过程和习惯中也体现着阶层差异吧。两位也有提到布迪厄。
当然我谈的都是自己所见所闻的一些零散现象,我也希望可以能更系统深入地审视我的经历。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阶级问题呢?
文轩 | 我觉得想要明白应该怎么看待阶级问题,首先要知道什么观点是错误的。上个世纪初以来,面对激烈的劳资冲突和悬殊的贫富差距,共产主义者进行了“消灭阶级”的实践尝试,但都以失败告终。时至今日,“以阶级斗争为纲”已经被摒弃,虽然阶级问题依然存在,但是简单地进行二元对立、区分敌我、妖魔化社会精英显然只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和压迫。个人认为至少目前,只要市场体系还在,阶级或者说经济实力的差距就必然还会存在。但与其笼统地把所有问题归结于万恶的资本主义,不如脚踏实地接受阶级的客观存在,解决些实际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把阶级视为pure evil、以为消灭阶级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观点是不可取的。
另一种就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思潮,这几乎是上一种观点的反面。当时为应对滞胀型危机,撒切尔政府、里根政府放松了市场监管,削减社会福利(welfare),实行工作福利(workfare)。与经济政策相对应的是社会思潮,人们提倡形式上的“机会均等原则”,要求个人为自己的贫富负责。也就是说,人们不再视社会分层为结构性问题,而是个人问题。这种观点对于已经占据一定社会资源的人来说是非常诱人的,因为他们不再被认为是压迫者,相反是凭借努力实现“美国梦”的成功者。所以他们也没有理由纳太多税去帮助那些穷人,因为穷人是自己不努力才会穷。
这种观点也很容易反驳。一是个人能力不意味着一定能获得更多财富。《我在底层的生活》中,美国专栏作家芭芭拉伪装成了一个没有学历、急需工作糊口的离婚白人妇女,在三个城市的底层各工作了一个月。她尽量寻找薪水最高的低技能工作支撑自己的生活,然而无论她如何努力,身兼两份工作,仍不足以支付房租。她的个人能力和工作积极性显然没有因为伪装而降低。这证明了一个社会精英进入底层同样难以维持生活。二是道德随机性的存在。这个观点罗尔斯阐释的很清楚,当人处于“无知之幕”之后,你并不知道自己会出身在哪。但显然出身于中产阶级比出身底层更容易获得成功,而这种出身是随机性的,因此不能归于个人德性。不仅是出身阶级,时代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今天的富人需要感谢时代,因为这个时代有好的基础建设,有广阔的市场,有对法治的追求——如果出身于部落时代,你的经商头脑、法律头脑都将一无是处,强壮的人才能活得更好。这是因为各个时代所赞许的德性不同,这同样是具有随机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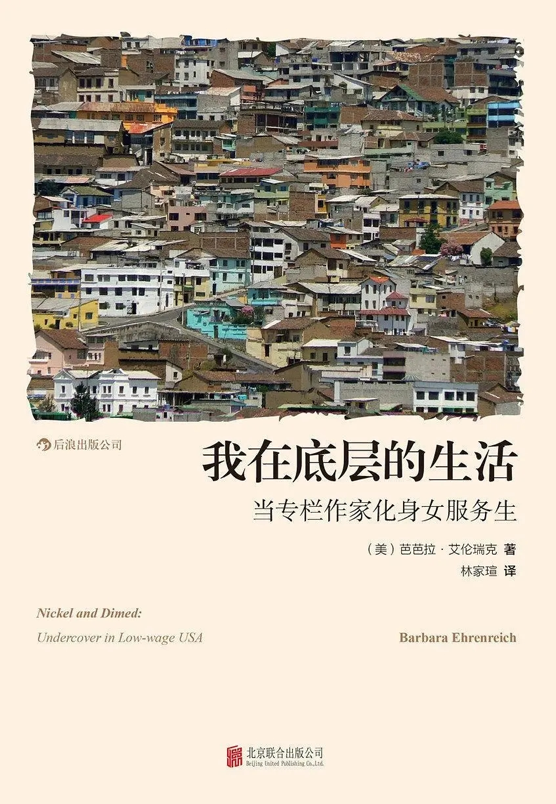
可沂 | 文轩把社会的宏观背景聊得很清楚了,那对于个体来说能做的只有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不断积累自身的文化、经济和社会资本来寻求更符合自己理想生活的社会位置。如何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取舍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了解到身边的朋友们都在为了各种限制而苦恼,有金钱、有父母的限制、有身体因素……但也在为了自己的计划而努力着,在实习、在打工、在创作、在各地体验……抉择面前,不论阶层高低人人平等。怎么样能在面对各种困难面前展演主观能动性,也就是你拿出了怎样的策略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多少是人性光辉的小小体现。
文轩 | 顺着可沂讲到的个人层面,关于怎么面对阶级问题,我觉得还有几点我们可以做的吧。一是要有意识。我指的不是作为身份政治的阶级意识,而是要意识到社会分层的客观存在,否则很可能会产生“何不食肉糜”之类的荒诞想法。二是要对身处底层的人抱有同理心,不要轻易苛责他们懒惰或者无能。就像《了不起的盖茨比》里所讲的,“每当你想批评别人的时候,要记住,这世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你拥有的那些优势。”三是,有机会的话亲身去感受。上学期我特地去了香港的贫民区深水埗,里面其实没有我先前想象的那么破败,但真的和其他地方格格不入。破旧的楼房,脏兮兮的下水道,异味从楼房之间传出。我看见几名流浪汉坐在花圃旁的长椅上睡觉,一个不知为何而笑的中年妇女,看上去有些疯癫,赤着脚走来走去。当时心里真挺五味杂陈的。当然,我的看法依然离不开我身在中产阶级的局限。如果有机会去做类似的社会考察,大概会有不一样的感触吧。(笑)



文 | 李文轩 陈可沂 吴丹
图 | 李文轩 网络
微信编辑 | 张一楠
matters编辑 | 蔡佳月
围炉 (ID:weilu_flame)

文中图片未经同意,请勿用作其他用途
欢迎您在文章下方评论,与围炉团队和其他读者交流讨论
欲了解围炉、阅读更多文章,请关注本公众号并在公众号页面点击相应菜单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