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不同但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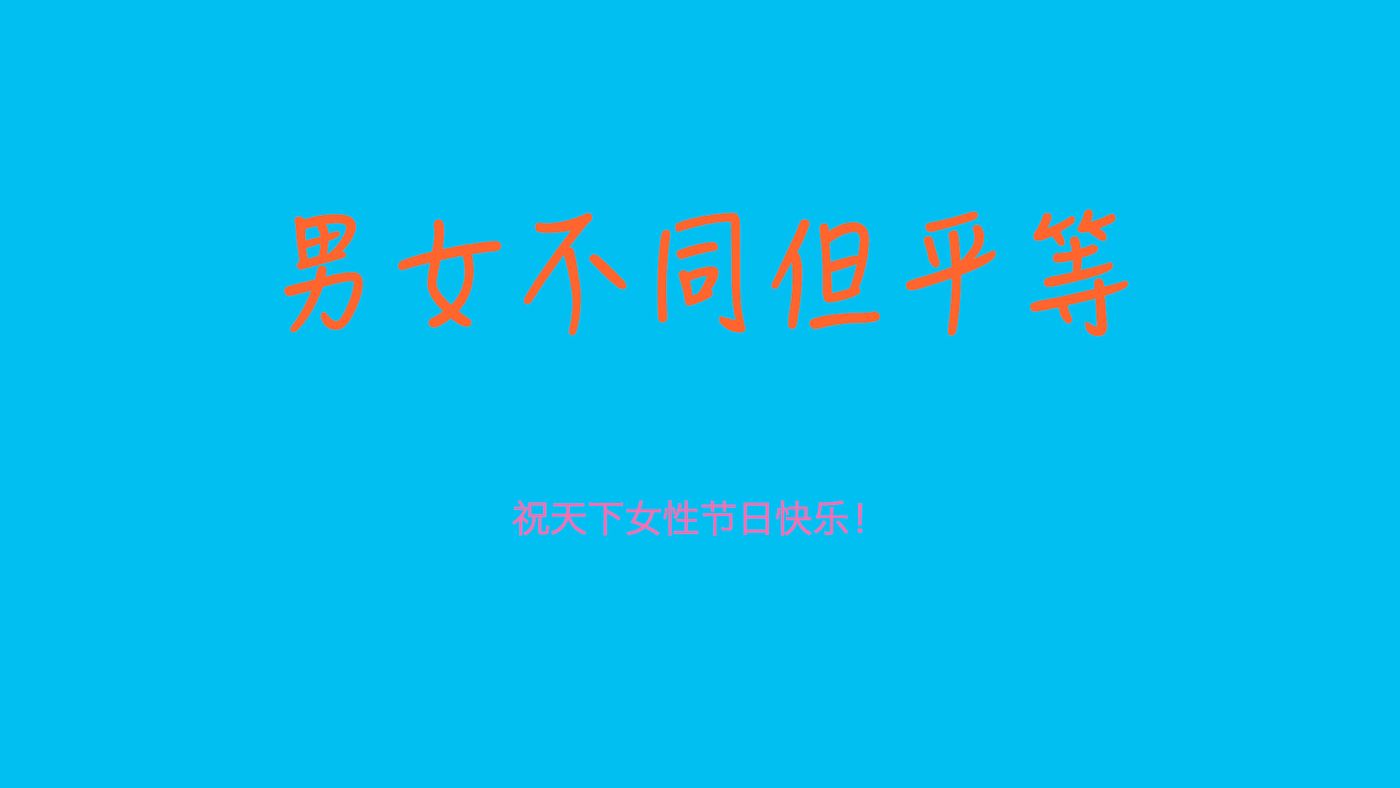
言语是一种矢量,携带着能量、大小和方向,可以成事,也可以败事,可以激励人,也可以伤害人,甚至是杀人,但凡有一定生活阅历的人,都不难明白这个道理,俗谚有讲“祸从口出”,福柯亦言“话语即权力”,在这个意义上而言,话术即箭术,方向性和准确性是核心标准。在圣经中,sin(罪)的意思即是“射不中标记”或“射不中目标”,在古英语中是箭术术语。
在日本的箭术中,最显著的一个特征是,箭术的修习即是心智的修习,是射手与自身的战斗,是不瞄准自己地瞄准了自己,不击中自己地击中了自己,射手同时成为了瞄准者与目标,射击者与箭靶;箭术不仅仅是为了要击中目标,而是为了使心智接触到最终极的真实,如日本弓圣阿波研造曾说过的,“弓术(箭术)并非技术。当你射穿自己的内心时,就能达到佛陀的境地”。
尽管这样的境界对多数人来说,可能是不可企及的境界,但显然,话术要求同样的修习过程和终极目标。我们知道,即便是绝世的箭术大师,也不可能永远百发百中,言者的困境同样是如此,这一方面内在地要求或请求一种善意原则,即听者在一定限度内基于善意的宽容和指正,否则,人与人之间便不可能达成有意义的交流和共识,另一方面,也要求言者成为自己的听者,以便能够随时能发现自己言语中的疏漏或偏差并进行自我修正和自我超越,这可能即是古汉字“聖”字中有“耳”与“口”的内涵,“说”离不开“听”就像“呼”离不开“吸”一样。
但不幸的是,我们的言语已经是过于年久失“修”了,粗鄙和败坏已成寻常之事,同时,我们也已经丧失了基本的敏感和善意。不管是网上中的舆论,还是日常生活中的交流,言者常常语不达意,听者往往自己“加戏”,认知和交流成本高到深度沟通和相互认同变得不可能,经常是狼烟四起,一地鸡毛,话语场几乎完全变成了争夺话语权的权力场,“泛道德化”成了终极的大杀器,而这恰恰正是智性贫困或者说心智赤字的症候。曾经发生的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的“出口成祸”便是一个典型例子,结果只是像几乎所有的中国事情一样“不了了之”。
在2018年的学习力大会上,俞敏洪在演讲中对“衡量的评价的方向决定了教育的方向”这一论点进行阐释时,引入了一个三段论做类比说明,即以女人找男人的标准(决定男人的行为)作为大前提,再加上“中国女生挑选男人的标准(只要他赚钱,不管良心好不好)”小前提,得出推论:“现在中国是因为女性的堕落导致整个国家的堕落”。此言一出,如离弦之箭,立即在网上引起广泛的“反射”和抨击,其中代表性的话语策略,即是两性平等话语,例如,女演员张雨绮在个人微博上发文称,“我只能说,北大的教育和新东方的成功都没能帮你理解女性的价值,没让你能理解什么是平等的两性关系,甚至没帮你搞明白什么是平等”。
俞敏洪首先是在微博上进行了回应和致歉,表示自己“由于没有表达好,引起了广大网友的误解”,想表达的意思是“一个国家的女性的水平,就代表了国家的水平。女性素质高,母亲素质高,就能够教育出高素质的孩子。男性也被女性的价值观所引导,女性如果追求知性生活,男性一定会变得更智慧;女性如果眼里只有钱,男性就会拼命去挣钱,忽视了精神的修炼。女性强则男人强,则国家强”,但这并没有使得如潮的抨击停下来,最终不得不登门到全国妇联向女同胞道歉,在公开道歉信中写道:“(论坛上的言论)反映了我性别观念上的问题,对女性不够尊重”,并承诺“加强对两性平等思想的学习”。
如果我们细加考察的话,就会发现这个过程的荒诞性。俞敏洪的言论,就像一个未经训练的箭手射出的箭,绝非无可指摘。例如,存在以繁驭简谬误,即以两性关系和国家状况的范畴来类比和解释教育的评价和方向的关系,显然,前者比后者更为复杂且敏感,俞敏洪所说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实际上一点都不“简单”,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不造成误表或误解才怪。同时,俞敏洪说自己是在“举例子”,却插入了一个存在争议的三段论,描述的大前提和小前提都存在偏差。
但是,公允地讲,俞敏洪的错误属于事实认知范畴的错误,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但并非是出在两性平等的价值理念,甚至可以说,俞敏洪在提出立论的大前提时,恰恰是预设了女性价值的重要性,舆论却以属于价值理念范畴的“不尊重女性价值”之类的话语来进行回应,揪住“女性的堕落导致整个国家的堕落”这段话不放,而不是深究立论的基础和事实本身,于是封锁了本来可以就此深化关于两性的关系、角色和价值之类深刻问题的认知契机。这种两性话语的泛道德化,可以说,同样也体现了言语和心智的未经修习症候。
我们知道,两性平等话语,或者说性别平等话语,如今是全球性的政治议题,是西方长久的女权主义运动结出的硕果,“两性平等”是其核心诉求,在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中争取到的是选举权,在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中争取的目标则是平等就业权、生育权(堕胎权)、平等教育权和性自由权。从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的观念史来看,两性平等观念基本上是以男性为参照的,批判的目标一开始是父权制,之后又转为男权制,批判的理论根基是性别建构论,也就是说,两性关系是一种统治关系,女性的性别特征是被男权社会建构的。
近些年来,就像自由主义话语一样,舶来的女权主义话语是中国舆论话语光谱中不可小觑的一部分,但同样也舶来了其固有的缺陷。例如,俞敏洪的话语与女权主义的性别建构论实际上共享了同一种逻辑,只不过是把被建构的对象转换成了男性,对他来说,女性成了真正的主宰者,女人的性选择和择偶标准决定着男人的行为导向。
这种性别建构论话语模式洞见(insight)到了女性之气质的“社会性”和“建构性”,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和现实基础,其中的那种将这种逻辑发展到极端即反本质主义而消弭了女性之气质的“自然性”与“本体性”,这显然会强化女权主义话语的战斗性和“简单粗暴”的一面,因而也隐藏着“屠龙少年终将成为恶龙”的危险,正如现实中我们看到的虽然占比很小但影响力却不容小觑的极端“女拳”形象。那么,致力于“两性平等”的性别建构论却陷入了一种尴尬局面,既消解了女性的主体性根基,又消解了男性的主体性根基,最终的结果是两性的同化与异化,然后是“天下男女尽入资本彀中”。
更为合理也更有解释力的假设应该是,“人”应该被视为“自然性”与“社会性”的辩证法或双人舞。基于此合理假设,我们应该以“男女不同但平等”为原则重建性别话语,变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斗争或博弈的话语模式为一种以互爱为中心的对话与共舞的话语模式,雅一点说即“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俗一点说即“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任何一方不自由,另一方也无解放。事实上,只有“不同”才可能真正“平等”,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相同者必定会为同一个生态位挣个高下甚至死活——“你不存在,对我很重要”,哪里最是“千人一面”,哪里必定最是不平等。“不平等”是病,但“(敢于)不同”才是药。
那么,不管女性,还是男性,真正的参照对象应该是自身,自我认同的根基应该是自身,有意义的目标应该是基于“个性原则”而不是“(东施效颦和山寨式的)集体原则”,即基于自身的独特性并通过自我超越而使自己走向“自己比自己更好”的“卓越”(arete)而不是“自己比别人更好”的“优越”(superior),后者只会最终导致所有人的内卷化、利维坦化与囚徒困境。
这样的立足点和话语会像箭术那样是一种和自身的战斗,那么,男性与女性不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一种“和自身战斗”的给养,需要相互为伴,换位思考,终生修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