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Justice Centre:生而为人的平等尊严 | 围炉 · HK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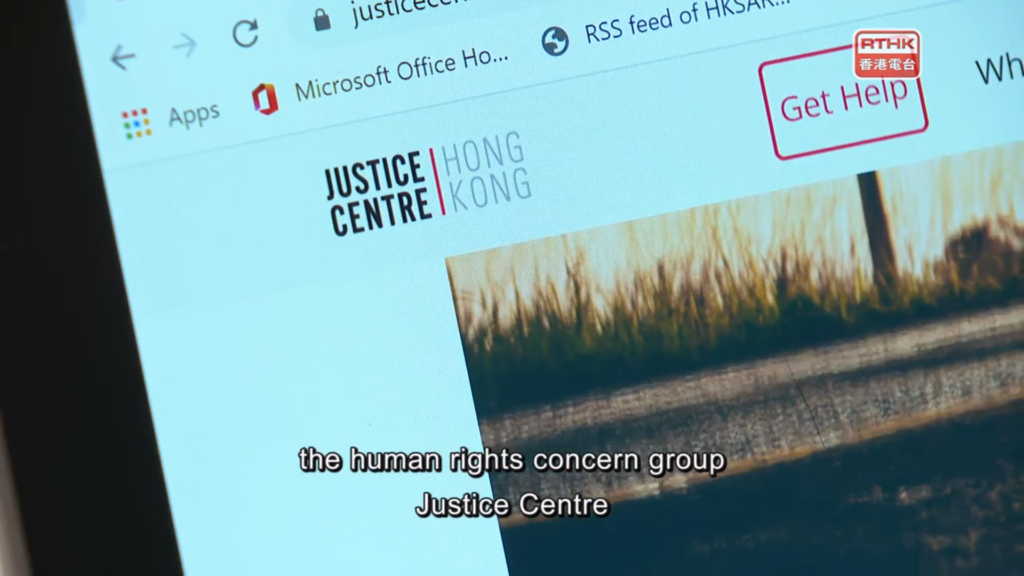

相较于难民(Refugee),寻求庇护者(Asylum Seeker)这个名字对大众而言似乎更为少见和陌生,可这才是我们平日里通称的“来港难民”的真正学名。他们因为原居国的战火,剥削,迫害等种种原因逃至香港,却又因为种种政策的缺失在这里成了被噤声的隐形群体。在多年无声的挣扎,叫喊,乃至绝望之中,终于有一群人顺着火光,找到了他们。
本次对话我们邀请到了香港非政府组织Justice Centre的宣传及通讯部主任(Advocacy and Communications Officer) Preston Cheung。在与他的对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香港难民援助NGO 的工作脉络,分享他们曾经亲眼目睹的难民故事,同时也进一步探讨香港现行制度下的难民问题。

P = Preston
C = Cynthia
C | 我们知道Justice Centre是一所很成熟的,致力于向难民提供法律方面服务的NGO,光是2020年就为285位助者提供了服务,当中包括48宗申请上诉和13宗难民工作申请。可以请你再为我们多介绍一些机构背景和历史吗?

P | Justice Centre是一所立足于香港的非营利性人权组织,主要致力于为香港最弱势人群的权利提供保护。机构创办于2007年,原名为Hong Kong Refugee Advice Centre。正如其名,机构本来只为来港的寻求庇护者提供法律相关的意见和服务。可在2014年,我们逐渐发现除了法律之外,寻求庇护者们仍有许多别的层面的需求,其中就包括心理支援及政策研究。
我们认为对于寻求庇护者的心理支援是十分必要的。在接触庇护者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了解他们的过去和所遭受的创伤。可在陈述的过程中,他们可能会因为要不断回忆起这些惨痛经历,而产生创伤性后遗症等心理疾病。所以自14年起,我们机构也开始着力于提供心理支援方面的配套服务。同时,我们也在14年开始进行政策研究。 比如书面记录一些寻求庇护者的案例,并将从案例中获得的观察变成客观的循证知识(Evidenced-based knowledge),从而协助政府更好地议定寻求庇护者的相关政策。
我们其实很强调一点,就是希望能够确保令弱势群体,哪怕最孤立的社群,也能获得平等诉诸法律的权利。这点其实并非如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就举来港寻求庇护者的例子。他们大多来自东南亚或是非洲国家,出于语言障碍,国家法律制度不同等因素,这些庇护寻求者来到香港后连基本沟通都成问题。他们之中的很多人生病不知道如何看医生,遇到问题更不知道应该求助哪个政府部门,而这些都对他们平等诉诸法律的权利造成了很大影响。因此,Justice Centre选择成全港第一,也是唯一一家提供上述全套支援服务的非政府组织。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中,就是希望可以确保这些群体在香港,也能够获得与他人平等的,诉诸法律的机会。
C | 除了寻求庇护者之外,Justice Centre还会帮助哪些目标群体呢?帮助寻求庇护者的具体工作又是些什么呢?
P | Justice Centre提供的直接服务就是刚才提到的法律和心理援助,主要针对的还是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但很多时候,难民,寻求庇护者,乃至别的弱势群体身份,其实是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并存的。在政策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很多寻求庇护者,可能是因为人口贩卖,强迫劳动,或是强迫迁移等迫害而逃至香港。换言之,我们的客户可以是一个强迫劳动工作者,也可以同时是一个寻求庇护者,而这种多重身份的案例往往也会更加复杂。

至于帮助寻求庇护者的工作方面,我现在是在Justice Centre当任传讯主任,少有机会进行案例研究,但在有媒体访问的时候,我也会和案例分析工作者们以及寻求庇护者有沟通和接触。2016年时我在联合国难民署香港办事处做过保护组实习,主要从事难民资格审核(Refugee Status Determinations),所以会多一些机会进行案例研究方面的工作。
在联合国难民署的难民审核工作中,其中比较特别的一项叫做原居国资料研究 (COI: Country of Origin)。这项调查有助于我们在审核过程中客观分析寻求庇护者对于痛苦经历的陈述。由于寻求庇护者在陈述过往的经历时,往往是以主观角度出发,但实际上的难民审核,除了需要难民在主观上感受到被迫害之外,也有一定的客观理据加以支持。包括在寻求庇护者陈述的时间段内,当地的治安状况如何?有没有国际NGO或其他权威报告证明当时确实有针对某个族群发生的迫害问题?我觉得这份工作其实就好像堆积木一样,要我们一条一块去拼凑在当时当地是否客观存在这种迫害可能。这点其实和法律层面的证明标准(Standard of Proof)是很相似的。在刑法里,我们的标准是“毫无疑问”(Beyond Reasonable Doubt),在民法里,我们的标准则是“几率的衡量” (Balance of Possibility)。可在寻求庇护的申请上,我们所要求的证明标准其实是更低于民法的。也就是只要证明存在较高几率的迫害便已经足够。至于举证责任,则是由官方和申请者分摊。可同时也需要考虑实际情况。比方说,如果寻求庇护者真的无法提供某些证件或文书,我们不能视作对方是不配合或是没有证明。这方面的法律知识比较专业,而在香港有相关知识的律师其实并不多。因此,在有需要时,我们机构也会提供相关的法律训练给合作的律师行及律师。
C | 那么语言方面呢?由于许多来港的寻求庇护者其实并非英文母语者,你们在提供服务时如何解决语言障碍的问题呢?
P | 这点其实不难。因为我们会请翻译(笑)。而且我们的翻译其实在服务的最开始就会介入。我们和受助者的关系其实就像律师和当事人的关系。一开始我们会商议服务内容和可能需要公开的信息,然后签订协议。但为了确保对方真的能够清楚明白协议内容,我们会选择哪怕只是服务的初步阶段也使用翻译。
C | 接下来想聊一些关于来港庇护寻求者的问题,可不可先为我们介绍一下香港现行的庇护寻求审核机制呢?
P | 香港现行的审核机制名为统一审核机制(Unified Screening Mechanism),由2014年3月开始实施。机制下的申请统称为免遣返声请(Non-refoulement Claims)。免遣返声请,指的是不会将申请者遣返至一个可能使其遭受迫害,酷刑,或其他非人道待遇的第三国。联合国酷刑公约在92年开始适用于香港,故而从92年至13年,香港政府只进行酷刑声请。但经过司法复核的成功挑战后,终审法院宣判酷刑声请的原理如下:如果当事人被遣返至原居国,并会在那里遭受酷刑,那么香港政府就不能够将之遣返。这也被称为免遣返原则 (Non-refoulement)。免遣返原则同时也是国际港的机制下是不存在的,而这其实和政府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有关。
至于来港庇护者的数量,其实并没有明显减少。其实可以想见,寻求庇护者在走难前是不会进行太多目的地的资料调查的。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到机场搭乘最近时间,并且不需要签证也能乘机降落的目的地,而香港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地。因此,机制本身并没有显著减少来港庇护者数量。
C | 正如我们刚刚提到的,整个免遣返保护的申请过程有可能长达十年。可在这十年中,寻求庇护者是无法在香港享有工作权的,很多时候只能依靠津贴和NGO 援助过活。您对这一点又是怎么看的呢?
P | 这在我们看来,这其实也是政府在政策方面所设的一个关卡。香港政府不能够允许难民工作,因为一旦允许,可能就会在某程度上助长经济移民借免遣返声请来港,造成难民潮。但在设计政策的过程中,政府也需要考虑寻求庇护者如何在港维持基本生活。这些寻求庇护者在香港无亲无故,也无法工作,只能被迫依赖于慈善或者政府津贴。我们认为政府的思路是,不能够给难民提供太好的人道援助,导致更多难民来港,但同时也不能太差导致他们穷困致死,因为这样也会违反人权法。于是,政府选择向寻求庇护者发放津贴。现行津贴政策为:大人每月1500房屋津贴,1200元超市电子消费劵以及300元水电杂费。而津贴发放的工作则是由社会福利署外判给了一家名为国际社会服务社(ISSHK)的NGO。到这里我们要问了,如果一个单亲家庭,孩子每月有750住房津贴,一家人加起来也只有2250元的住房费用时,在香港能够租到什么样的单位呢?所以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寻求庇护者,靠政府津贴连劏房(是可见于香港的一种特殊住宅、出租房形式,即是业主將一个普通住宅单位分成成不少於两个较细小的独立单位,作出售或出租之用;通常每个小单位均设有厨房)都住不起,只能住在改装的鸡栏和猪栏里。

访问的最后,Preston和我提到了政府制定政策和法律义务两者间的不同。他认为,后者只是一个政府制定政策时的考量的最低限度(Bare Minimum)。我们的政府在难民政策上虽然做出了最低限度的努力,却忽视了当只做最低限度时的努力时,会衍生出什么样的社会问题。
“Equal dignity as human beings,就算申请的过程中,我们又怎么可以去逼迫他们live less than a human呢”
生而为人的平等尊严,哪怕是这群流离失所的异乡人,也总有人愿意挺身捍卫。

文 | Cynthia
图 | 来自justice centre
微信编辑 | 吴雨洋
matters编辑 | 蔡佳月
审核 | 橙慕涛
围炉 (ID:weilu_flame)

文中图片未经同意,请勿用作其他用途
欢迎您在文章下方评论,与围炉团队和其他读者交流讨论
欲了解围炉、阅读更多文章,请关注本公众号并在公众号页面点击相应菜单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