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誌】序言:非公民的批判視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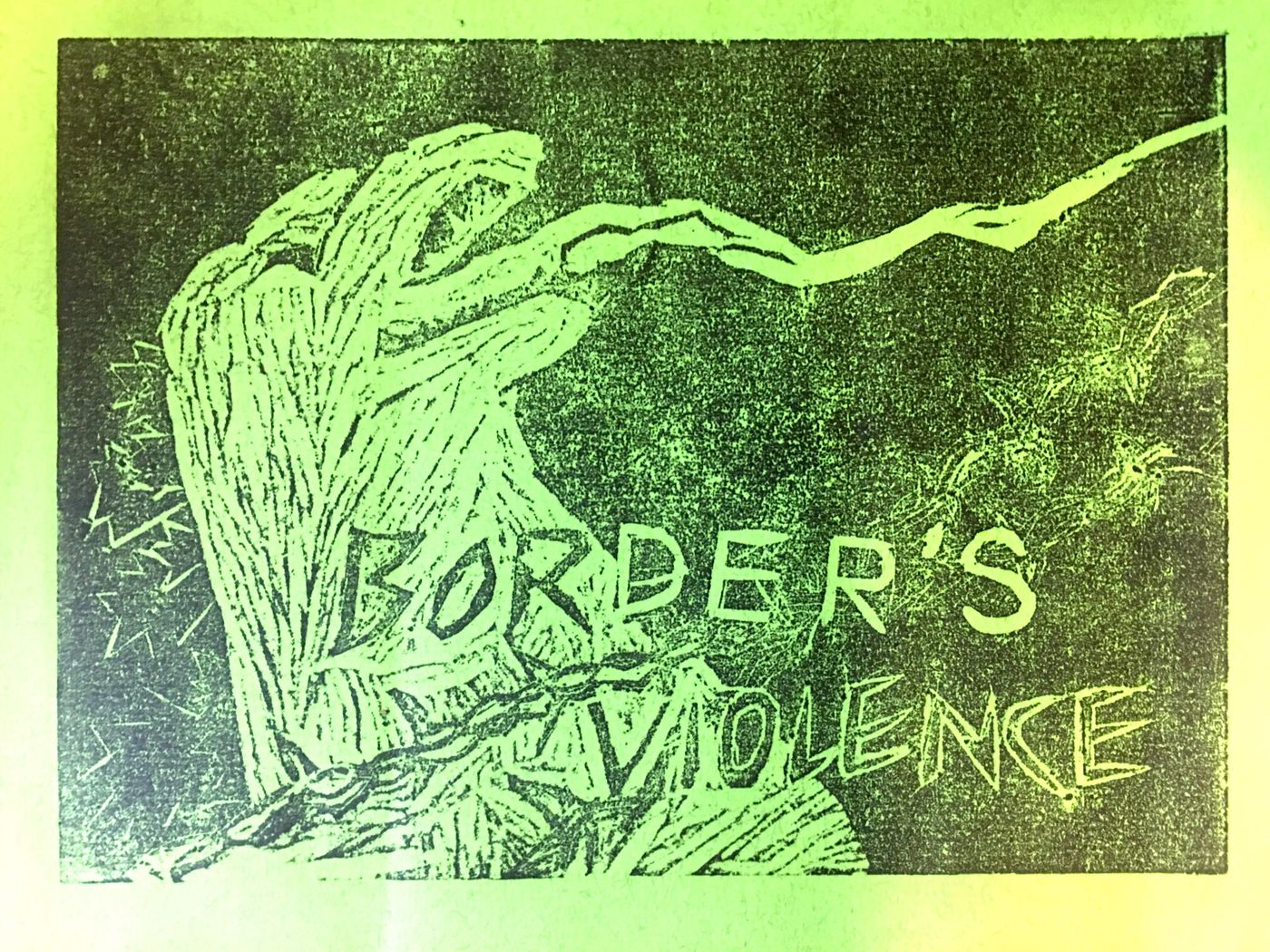
一、為什麼有境外生?
縱使自跨越國家或區域疆界的遷移存在,便有跨越這些疆界去學習的學生,我們今天看到的在台灣學校體制內的、具有不小數目的境外生,是在很晚近的政治、經濟與文化脈絡下始出現的。1995年,全台共有8,000餘名境外生;2009年,境外生已增至39,533,其中學位生20,676人;2018年,境外生總數更增至126,997人,其中學位生61,970人。境外生人數在近二十年的快速增長,有著頗為清晰的動因。
隨著新自由主義下政府從市場「撤出」及財政緊縮等,高等教育的市場化在世界範圍內發生。在同樣的浪潮下,加上台灣本土的政治和文化變革趨勢,九○年代初政府開始放寬教育管制,逐漸將教育推向市場化和私有化──政府教育經費縮減、大學偏向於市場與經營邏輯、著重於具經濟效益的實用學科和產學結合。然而與此同時,台灣自八○年代末浮現少子化的社會徵狀,各級校院將面臨教育市場內需不足。國民中小學學生從2004學年度開始大幅減少,2010學年度學生僅為151萬餘人,預計2026年將減少到94萬人。在國中小之後,高職與大專院校──尤其是在市場化進程中暴增至2006年的一百六十餘所公私立大學──也將面臨大範圍的減班、關校與教職員工失業。因此,台灣高教招生勢必向外發展。
新自由主義在全球化階段的重大影響是,為方便資本為在全球範圍內尋找最佳投資環境,各國需要開放邊界以提供資本、勞動力和資源。WTO(世界貿易組織)於1995年成立,為了在全球化浪潮中不掉隊並爭取競爭優勢,台灣經過幾年的努力於2002年加入WTO。一方面,為因應WTO的服務業貿易總協定內參與國須開放教育服務類商業貿易的條款;另一方面,為在全球高教產業內獲取利益和競爭力佈局,台灣才開始積極推動高教的全球化與國際化──提升國際教師與國際學生的數目、課程國際化、研究的國際競爭力、大學國際排名,並著眼高教產業的全球佈局。從2002年修訂的《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2008年推動「萬馬奔騰計畫」,到2011年推動「高等教育輸出:擴大招收境外學生行動計畫」,都致力於廣招境外生。尤其是因應九○年代的「南向政策」,2002年教育部提出「教育南向政策」、2008年行政院提出強化「陽光南方政策」,特別著重於東南亞學生;並循著戰後的「僑教政策」,亦特別著重於港澳僑生──於1997年擬定《積極拓展僑教領域開創僑教新境界擴大招收海外華裔子弟來台升學方案》。
也就是說,在高教市場化、少子化帶來的內需不足與加入新自由主義協定及競爭的共造下,台灣高教體制內的境外生達到一定規模,只是近二十年內的事情。2008年,政府針對「陸生來台就讀學」籌組跨部會專案小組,開始推進招收陸生的政策討論和立法,便是上述進程的進一步延展。2016年「新南向政策」提出後,台灣因著政治、經濟與文化的佈局考量,再度開始廣招東南亞學生並積極在東協十國、南亞六國開設境外專班,在為產學結合服務和台資企業海外人力資源佈局之餘,亦賺取超高額學費。
二、國家治理下的非公民:全球化與國家疆界的張力
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期,國家所力求的開放與資本、商品、人口的跨境流動,勢必跟民族國家同樣竭力維繫的主權與疆界產生張力,因為國家主權與疆界是民族國家產生與存有的合法性之所在。於是,平衡全球化下的開放與國家疆界間的張力,是現今國家治理的重要關切。
邊界並非只是地理上的,而是存在於所有進行著區分與排除之處。民族國家的社會內部本就存在著各式邊界,這些邊界正是認同/差異的生產者。社會中不同階序的權力之間透過塑造體制的、話語的或空間的邊界,區分「我們」與「他們」,從而維繫各自的權力。在叢生的邊界之下,一部分人佔據了高階的、集中的權力位置,另一部分人則不可能跟前者一樣自由及平等地實踐權力、分配資源。當然,所謂高位階的、集中的權力不僅是個人,更是跨國資本主義、代議制等橫行於社會間的權力單位。也就是說,邊界即對社會空間進行控制與隔離的威權機制。
新自由主義世界裡的跨境人口流動,並非均質的,而是有著跨國資本主義掌控下的流動方向與階序。譬如,資本流向更高的受益的環境,資源流向更高一級的生產位置,商品流向更廣闊的市場,人口流向更高勞動報酬(及更符合其他現代性欲望)的地方……全球自由市場之下,不同階層的人在跨境流動時,有著不同的軌跡,在不同的軌跡上移動時要面對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壁壘。而那些跨境而來的底層勞動力,往往會成為本地社會中底層之下的底層,甚至隱形的人口(比如無國籍居民、難民、失聯移工)。他們之所以不被看見,並非只是因為他們的文化相異、收入較低,更是因為本地社會內部本來就存在的邊界機制的運作──必須持續區分各式高位階的「我們」與低位階的「他們」,才能維繫高位階的權力。譬如,外來的底層人口是被持續地穩固在不具公民身分的位置,才能使他們更加不受法律保護的,也更加隱形的、更適合被本地資本剝削的勞動力。
在國際和區域政治經濟格局中較高位的國家,是人口移入的方向。越來越頻繁的人口的移入,也改變著國家對公民身分、公民權利、人權、國境管理等的判斷和實作。縱使國家在新自由主義下有體制性的後撤,但仍然是社會內高權力位階的行動者。一方面,國家為提升競爭力、為解決本地勞動力和商品市場困境,要開放人口移入;另一方面,民族國家想像共同體的合法性關鍵地來自國家疆界和種族劃分的穩固。而邊界機制的存在使得這些國家得以以此作為篩選的工具,再生產著國際的階級差異。於是,國家給移入人口設置的遷移壁壘首要地便是國家疆界的邊境管理政策:有些人要經歷重重審查才能跨過疆界,有些人甚至被拒之門外。在本地的移民政策中,國家只給少數移民以公民身分,大多數移民成為非公民。民族國家透過移民條款、家庭團聚條款、庇護法與國籍資格條款等政策,為移民設下種種壁壘,限制其公民身分。而公民身分直接關乎人權、社會權與政治權等權利獲取。沒有公民身分的移民,不僅無法平等地獲取社會福利等人權保障,也因無法進入主導著本地政治的代議制度而無法平等地參與政策演進。
並且,在民族國家發展歷程中,公民意識已經成為共同體想像的、實作劃分與排除的意識形態。人權被收攏進「公民權」範疇,在具公民身分的人群與不具公民身分的人群之間的疆界,除了決定了公民權的擁有與否,更衍生出叢生的族群、階級與意識形態矛盾。透過國家安全的修辭、族群劃分的修辭、移民社區的規畫等政策的、話語的、空間的建制,國家執行著本地社會內部對移民的暴力。本地公民亦透過族群的、意識形態的、階級的邊界,執行著公民/非公民劃分與排除。
三、非公民之間:資本家、外籍勞工、外籍配偶與境外生
當危機出現時,國家的治理對人民而言是否「有效」,首要地便呈現在邊境管理的模式與效用,據此國家才得以維繫國家的安全和共同體的合法性。比如,在戰爭或恐怖主義出現時,國家能否有效地甄別危險的人並阻絕其入國;在社會經濟困頓和社會福利危機出現時,國家能否有效地阻絕更多移民搶奪社會資源。在COVID-19出現時,我們可以看到各國政府都在短時間內封閉國境。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國家對不同類型的流動做出非常不同的處理,資本和商品仍然暢通無阻,人的移入則有著非常嚴格限縮的規定。台灣政府在疫情出現後便規定,有居留身分者仍可入境(除本國人與陸籍配偶所生子女及港澳籍境外生),但本國公民與外籍人士在隔離等防疫要求上有不同規定。在邊境管理稍微放鬆時,首先被開放入境的是持商務簽證的旅客和外籍移工,其後很久才是無居留證的境外生。這些危機政策中,交纏的即是國家對不同類型遷移者的需求與設定的差異。不僅是國家對不同遷移者的設想,實則更是新自由主義世界對這些遷移和遷移者的塑造,這些不同遷移者在本地社會的設想/功能/角色也在跟本地社會的意識形態相互建構。但總體而言,這些在世界人/物移動中處於低位階的遷移者,往往是本地社會的非公民(外籍配偶在取得本地公民身分前也要經歷一段非公民/準公民歷程),不僅無法獲取種種人權保障,亦被國家當作難以規訓者甚至危機管理的對象來治理。
新自由主義壟斷結構下的資本、原材料與商品向來可以自由通行,資本周邊的商務旅客向來也受到優待,這些是國家要在新自由主義世界存續和競爭的命脈,其他類型的遷移者則是在這些命脈的支配下遷移的。具體到台灣,對國家而言,外籍勞工沿著往區域格局下高位階方向的軌跡移動,他們是解決本地勞動力市場供應不足的主要生產者。然而,《勞基法》不適用於他們,他們亦處於台灣種族、階級的種種邊界下被排除的社會空間中。在台灣的外籍配偶絕大多數為來自東南亞和中國大陸的女性,也是沿著往區域格局下政治、經濟與文化現代性位階較高方向的軌跡移動,他們對國家而言首先是解決本地底層男性的生育、性、家務勞動與情感勞動困境的再生產勞動者,同時也是補充本地人力市場的生產勞動者。然而,他們在承擔家庭再生產勞動的同時,他們的社會福利位置被捆綁於異性戀親屬制依附的戶籍制度之下,亦因為母國文化與物質條件與台灣不同,而常常被視作文化上、道德上的異類。
其實,在台灣的境外生大多來自東南亞和中國大陸,跟外籍配偶處於相似的遷移構造,他們的首要考量不必然是在台灣或許會有怎樣的收入,而是基於在東亞-東南亞區域中,對台灣有著更多的現代性想像。這種在新自由主義形塑下的現代性想像,成為他們遷移的欲望與驅力。對國家而言,境外生則與外籍勞工、外籍配偶截然不同。台灣設想中的境外生在本地不是重要的生產者或再生產者,而是高教產業和商品市場的消費者,主要功能是提升高教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以及作為潛在的未來勞動者在本地或台資企業所在地的人力資源,但也因此並非在當下那麼地不可或缺。
這些遷移者的處境同時關涉到後冷戰的兩岸關係、台灣與東南亞及中國大陸與東南亞的區域關係。除新自由主義構造外,台灣自二戰後在國際間的主權問題,使得台灣對陸籍、港澳籍、其他國籍遷移者的政策受不同法律管束。同時,加上台灣政府與民眾間的反共防諜的文化邏輯,才得以解釋為何涉及陸籍配偶的婚姻、居留議題,以及涉及陸生的健保、返台議題,往往在政府決策和公眾輿論中被當作攸關國家生計、台灣存續的爭議議題。兩岸間的各種流動,實際上塑造著不同遷移者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差異。流動於兩岸的台商被視為「愛台灣」的、對台灣社會極具貢獻的人,並且可以在台灣社會的政治、經濟領域具決策影響力。流動於兩岸的陸籍配偶和陸生,則因為這樣的流動,而被台灣社會視為對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和台灣意識形態的威脅。在台灣,個別國籍(如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國家)的配偶在入境和獲得居留權時接受的審查比其他國籍配偶要繁複、困難得多,陸籍配偶獲得台灣身分證的年限比其他國籍配偶都要長。國民黨政府為開放陸生來台啟動修法時,來自政府內外的爭議多圍繞陸生會否是共諜,也只有開放陸生時民眾才關切作為境外生的陸生是否會搶奪本地學生資源。原本就是納入其他國籍居民的《全民健保法》,要納入陸生時,卻引發誰有資格是「全民」的爭議。
四、面對非公民
在新自由主義壟斷結構下,因為跨境流動的軌跡與壁壘,產生出越來越多的非公民。在各國內部,人權被收束和化約為公民權,公民與非公民的邊界對非公民執行著權利、政治、經濟與文化的排除。在COVID-19爆發後,台灣政府先禁止了陸生、港澳籍及無居留證的其他國籍境外生返台就學,後規定可入境的境外生一律得在防疫旅館進行檢疫;在後續邊境管制逐漸放鬆時,先是開放無居留權卻「有用」的商務旅客、外籍勞工等入境,後開放被認定為「中低風險」國家境外生返台,最後才是陸生。在整個境外生返台進程中,台灣社會的不同行動者──國家、政客、資本家和本國公民──對境外生的排拒,以不同方式顯現了新自由主義構造下對生產與再生產的調動,及對非公民的治理方式。
國家第一時間禁止陸籍、港澳籍境外生入境,自然有當時疫情爆發地域的因素,但依國籍而非旅遊史或接觸史甄別入境者風險並非科學,亦包含了台灣邊境管理的種族主義和冷戰邏輯。國家率先開放作為命脈的在資本周邊的商務旅客,後續開放本地必須的勞動力──外籍勞工,並優先安排他們入住防疫旅館和集中檢疫所。對於國家而言並非必須的境外生,被拖延到資本與勞動力之後,且境外生入住防疫旅館時的訂房困難與經濟負擔,不被國家理睬。實際上,境外生不只是台灣高教產業的消費者和提升國際競爭力的助力,也是實際的、較隱身的勞動者──不論是在大學內的研究工作、助理工作、在大學外的打工,還是在高教產業的產學合作名義下被迫進行的「假唸書,真打工」;並且,他們也是未來的本地勞動者,及台商企業在大陸及東南亞的人力資源,是台灣提升全球人力資料佈局競爭力的資源。但是,在疫情這一危機時刻,國家要穩固共同體的合法性,其首要任務便是及時且有效的邊境管理,運用「國家安全」、「國民健康」的修辭操弄社群的邊界,以維繫國家安全存續。
我們看到兩黨政客也在境外生(尤其是陸生)返台事件中紛紛表態。因為作為非公民的境外生在掌控本地政治的代議制中沒有位置,依靠選票存續的政客要麼為高教資本、台商資本代言──支持境外生返台,以維持本地高教產業,並為台資提供潛在勞動力;要麼為民族主義代言──反對境外「危機」入境,以保護本國人安全為優先;要麼為現代性意識形態代言──支持港生返台並反對陸生返台,以維繫台灣在東亞區域內的反共及民主意識形態的合法性。正如他們在過去十年間的開放陸生來台就學和陸生納入健保的爭議間的表態一樣。
本地高教產業的資本家或資本周邊人,自始便支持儘早讓各國境外生返台就學。這首先是有從表面便看得到的要賺境外生學費的原因,境外生的學費是本地學生的1.5至2倍。更因為台灣高教產業在市場化方向上、在少子化困境中,必需境外生才能生存下去,以及進而提升在新自由主義結構下的國際競爭力。
疫情期間的台灣民眾(本國公民)幾乎一面倒地反對境外生返台,與境外生相關的網路空間充斥著「不要來台灣傳播病毒」、「不爽不要來」、「滾回去」、「有種去中國維權」等等仇恨言論,以及「本國人優先」的話語。在危機時刻,本地社會內部的階級、族群等邊界似乎被暫時地超越了。壟罩人們的是本國人/外國人、公民/非公民、民主的/威權的劃分,據此塑造出穩定的「社會安全」與共同體想像。同時,戰後台灣社會的「恐懼政治」至今仍起著操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總有著不可預期的暴力──不論是戰爭還是「亡國」,中國大陸/大陸人的「入侵」可以隨時激發個體的恐懼。尤其是當面臨近幾年的兩岸緊張、同時面臨一場由大陸爆發的疫情,「亡國」的恐懼與個人的「死亡」連結起來,恐懼政治成功地調動起對大陸人/陸生/陸配的絕對排拒。
事實上,不論是政客、高教資本還是本國公民的反應,不外乎都是基於國家在新自由主義之下對生產、再生產的調動,以及危機下的治理。在此進程中,不論哪一方對境外生作為非公民的指認,都凸顯著台灣的公民與非公民在入境、居留、社會福利等權利上,以及種族、階級上的區分。然而,本國公民以為憑藉排拒非公民,就能因為「公民身分」而應被優先賦予「公民權」,實則是一個虛幻的泡沫。「公民」身分並不像本地公民想像得那樣可以保障自己的安全與健康;相反,國家之下的「公民」身分不過是國家調動生產與治理的修辭術,讓本地公民加固共同體想像,依此維繫危機下的穩定。
其實,越是在危機時刻,公民身分就越是不穩定,邊界的效應越是凸顯出來。在本地社會叢生的邊界之下,危機之下各式人權、社會權與政治權愈發無法超越本地的階級、族群、性別的劃分,並不存在本地公民間真正平等的公民權──譬如他們在面對疫情下的行業與個體經濟補助、高價防疫旅館、對異議聲音的壓制、衛生資訊流通等面向時都處在不同的位置上。也就是說,公民身分本就是流動的,即便在日常,某些法律上的台灣公民會隨時成為性別上的非公民、族群上的非公民或經濟上的非公民……
因此,境外生權益小組以「非公民」來看待境外生(以及外籍勞工、外籍配偶、無國籍人士)在台灣社會中,因為公民/非公民的劃分而在政治上、權利上、意識形態與文化上被排除的處境。縱使我們的行動大多直接訴求境外生的相關權利,我們並非限縮於為非公民爭取到「公民權利」的權利論述與運動。我們的論述立足於對於非公民處境的呈現、對於公民/非公民差別待遇與社會疆界的批判,我們期待構築「共同生活在台灣的社會成員」的基進視野,為台灣社會運動補足非公民的視野,亦是期待自身可以成為邊界叢生的社會中讓邊界兩側的人們得以相互遭遇、相互對話的仲介者、翻譯者。
撰文 Kuo Jia
本文為境外生權益小組的小誌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