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了,为什么我们亟需一场人性大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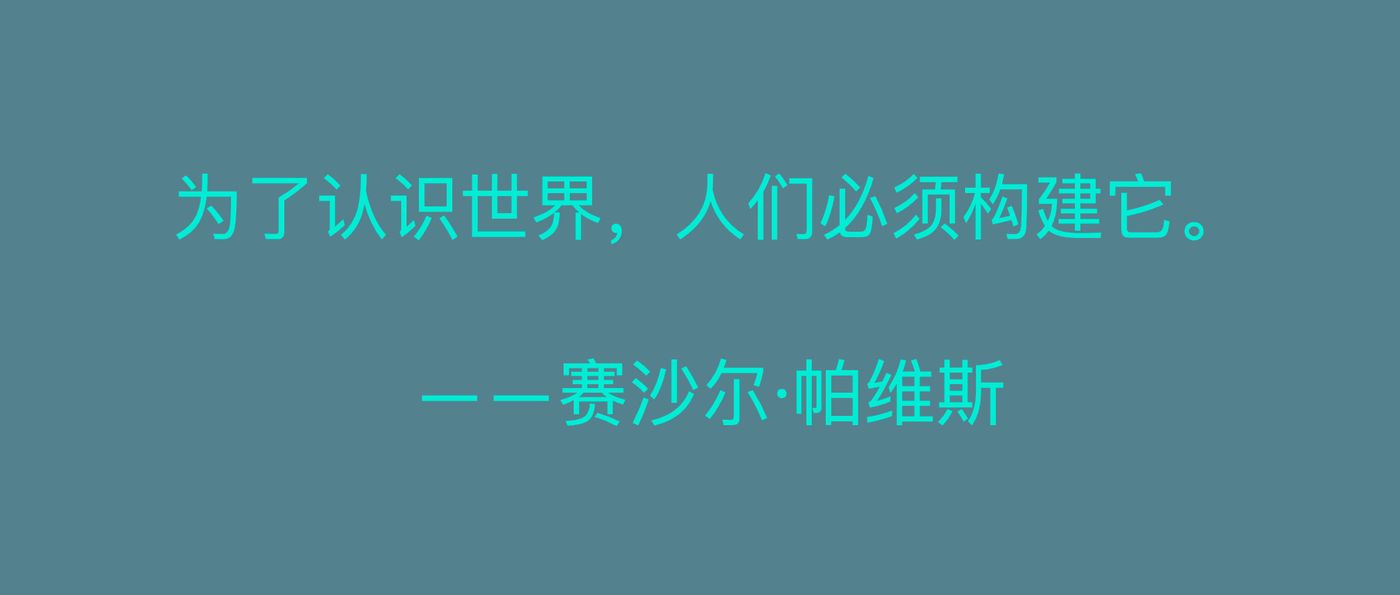
儿子嚷着要爸爸陪着玩儿,
正忙着的爸爸拿出一张世界地图,
撕成碎片交给5岁的儿子后说,
你把这张地图拼起来,我就陪你玩儿
儿子一会儿就拼好了。父亲很纳闷儿,
问儿子怎么这么快就拼好了,
儿子说:“很简单啊,
这张世界地图的背面是一个人像,
人对了,世界就对了。
十年结晶,中西合璧,值得深读
(全文15828字)
1、“在人生的中途,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黑暗森林之中,正道已失”(但丁),如今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正深陷于前所未有的系统性危机之中,我们所称谓的“人类文明”又到了一个历史性的黄昏时刻,过去那些一直在如“幽灵”或“影子”般潜在地起深层作用的历史性构造、结构性矛盾与文化性创伤(Trauma),现在日益变得显在化、现实化和症状化了,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并不是动因,而只是显影剂、加速器和分水岭,但这将成为人类远未走出的人对人之殖民的“中世纪”之大复辟,还是会成为已告全面瓦解的自我吞噬的“现代性”(Modernity)之再起航,完全取决于我们这一届人类自身如何思想、决定与行动,我们有什么样的作为或不作为,就会有什么样的命运与未来。
2、因为,不管这个世界如何变迁,未来如何到来,人类始终是思想、决定与行动的主体(Subject)。假如消除了“人”(自我)来谈论存在、世界和未来,那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会陷入逻辑上如“说谎者悖论”一样的自指悖论(self-referential paradox),严格来说,应该叫“自否悖论”或“自反悖论”,因为,单纯从形式的角度,自指并不必然导致悖论,自指且自否才会导致悖论。
2.1、笛卡尔从普遍怀疑出发而提出的“我思故我在”,即是避免自否悖论的经典例子之一:我“怀疑”(否定)我自身的存在性会导致自相矛盾(悖论),而这反过来则可以成为我的存在性的一种逻辑证明(反证法),从这个逻辑过程,我们也可以明白:“我思”只是“我存在”之从证明论而言的“理由”(reason)而并非是从本体论或存在论而言的“原因”(cause)。其实,从常识我们也可以确信:“(我)存在”(existing)显然比“(我)思”(thinking)更初始、更基本,正如婴儿在能够“我思”(自我意识和理性)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理性并不是先天具足的,而是后天生成的,或“生不成”(创伤)的,例如,“狼孩”的故事,“自闭症”儿童,或成年的“巨婴”,这就像是种子未必总能长成树、开出花、结成果直至“成熟”一样,只有在相应的条件具足的时候,它才能“自由”生长,开花结果。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恰恰是整个现代启蒙运动的盲点。康德说,“敢于认识”,“大胆运用你的理性”,“从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却并未认识到其中的作为“中世纪后遗症”的创伤问题及其主体性匮乏综合症。那么,康德的这句口号就像是鼓动身体和心智还停留在中世纪的“被启蒙者”大胆地运用自己所匮乏的东西(理性)。如今回头来看,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思想传销”的味道呢?所以,从主体的角度来说,“失败”或“崩坏”的种子,其实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中世纪的帝国-殖民结构所造成的“创伤”成了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洛伊木马。
2.2、另一个经典例子即是人工智能(AI)。那些宣称人类将被淘汰或“后人类”的言论,绝对是在危言耸听,甚或是“别有用心”(例如骗经费或投资)。因为,人工智能说到底无非只是一台“计算”机器:一种“有限游戏”,一个算法系统,一个形式系统,其“计算”能力的极限即是无法“判定”(计算)自身是不是“可计算”的,这即是经典的停机问题,或判定问题,其结论是由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严格保证的,而问题核心依然是自指问题(self-referential problem)。通俗地来说即是,任何的物理性(硬件)和符号性(软件)的形式系统都不可能做到“自我超越”和“自我高阶化”因而便不可能具有“自我判定”(即高阶“自我”判定低阶“自我”)的能力,这就像是镜子或照相机无法“自己照自己”一样,但是,作为具有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的人类却可以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尽管在迄今的现实意义上而言,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达到这样的人生境界。事实上,人工智能(AI)既不是真正“独立的”(independent),也不是真正“自主的”(autonomous),它必须依赖并受限于“形而上”(meta)于自身的人类智能之建模、赋值与迭代或“转型”,比如说,AlphaGo再厉害,那也只是会下围棋而已,你让它自行改行当厨子试试,但人类却可以“不想当厨子的裁缝不是好司机”,即能够在不同的领域、范畴与层次中穿越并以“直觉”(intuition)而不仅仅是“计算”(calculation)来应对这个问题重重的世界中往往同时涌现的多样性、复杂性和非线性。所以说,人工智能本身没什么可怕的,可怕的其实是“人工智能”背后的“人工”,是“机器人”背后的“人”,例如,那些利用后门程序与系统漏洞进行恶意攻击与操纵人工智能(无人机、自动驾驶与物联网等)的黑客力量,但更可怕的是由那极少数人利用“现代”教育、资本逻辑与算法系统而把绝大多数的人类智能驯化“人工智能”(即只会计算而丧失了怀疑/反思、想象/象征、直觉/判断、创造/幽默)直至所有人都“困在系统里”而“无家可归”的数字利维坦。那么,当前最为重要且紧迫的问题,并不是在数学、物理学和工程技术领域,而是在经济学、政治学和伦理学以及背后的哲学纲领与哲学范式。
3、事实上,任何人的思想、决定和行动都不可能不是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的,也就是始终会有一个“自我”(准确地说是“自我意识/潜意识”)嵌套其中,如影随形,无可消除,或如“灵魂”般在高贵地统摄,或如“鬼怪”般在阴暗地作祟,有什么样的自我意识便会影响、塑造和限定或“决定”有什么样的思想、决定和行动,所以,每个人有必要把意识的箭头与认知的意志指向自我,从而能像苏格拉底那样“认识你自己”,卡西尔亦曾指出过,“认识自我乃是哲学的最高目标……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动摇过,它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人论》),但是,任何人的自我意识又受到所处的时代结构(包括意识形态/文化结构、社会结构和物质结构)之影响、塑造和限定甚或“决定”,不可避免,无处可逃,所以,每个人要想真正做到“认识你自己”,就不能只是停留于像传统形而上学那样的纯粹思辨,还要“认识你‘被抛入’的世界与‘此在’的时代”和“认识‘认识你自己’的认识论(意识形态或知识型)”,与此相呼应的是马克思的观点,“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产、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以及尼采的“超人”态度(“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海德格尔的“此在(dasein)的迷宫”与福柯的“知识型”(episteme)。可以说,这正是人类的“自我意识”之不应分割的两极性或者说双重性:“自然性”(导向形而上学、神学或神秘主义)与“时代性”(导向生活实践和习俗)。
3.1、理想的形态应该是这种“两极性”(bipolarity)的辩证法和“双人舞”,“二而一,一而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形如中国传统的“阴阳鱼”图式,它可以形成一种兼具自指性(self-referentiality)、他指性(other-referentiality)与互指性(inter-referentiality)并且可以不断超越自身的自玄性回路(self-reflexive loop),其形式是一种具有自相似性(self-similarity)的分形扩展结构,我们也可以叫作“非凡循环”。“玄”(reflexivity)在此的含义是“反之又反”,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前后两个“反”并不是“平权”的而是具有逻辑上的阶层差序;“自反”是自我超越和自我高阶化的必要环节,而之所以能“反”(反题),必然包含了他者的“异”与自身的“缺”(不完善),而之所以能“反之又反”(玄),中间必然产生过“同”与“合”(合题),假如能够“玄之又玄”(缘),便可度入“众妙之门”(妙不可言),我们可以假设,这便是“进化的逻辑”(logic of evolution)。但是,如果这样的“两极性”之间发生断裂并在观念中被不当地“二元对立/斗争”起来便会进一步自我强化并各自退化和固结为一种封闭性的自指性回路(self-referential loop),其形式就像是一条自我锁定和自我吞噬的咬尾蛇(Ouroboros),我们也可以叫作“平庸循环”,而这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若以一词以蔽之,即是“内卷化”(involution),一种丧失了进化力(evolution)、创造性(creativity)和主体性(subjectness)的退化状态。正如侯世达所说,“自指是一条永恒的金带”,这种自指性的平庸循环,在形式逻辑中即是“同义反复”,在经济学中即是“纳什均衡”和“囚徒困境”,在诠释学中即是“解释学循环”,在病理学中即是“自闭症”或“孤独症”,在精神分析而言即是“强迫性重复”,在大数据推荐算法中即是“回音室效应”和“信息茧房”,在尼采而言即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在中国历史中即是“治乱循环”的结构性重复或所谓的“超稳定结构”,在日常语言中即是“自以为是”、“自我重复”或“自说自话”,等等。
3.2、亚里士多德曾说“自然憎恶真空”,我们则可以说“人类憎恶平庸”,它既不稳定,也不持久,更不“可爱”,是“不正常的”,甚至是“恐怖的”,正如咬尾蛇的自我吞噬所象征的那样,或如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揭示的,它必然会朝向最大熵状态演化。那么,除非“超越这平凡的生活”(平庸循环),否则就会造成“创伤”、“躁郁”甚至是像尼采那样“发疯”——在“(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中的“超人”像不像一只困兽?但是,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陷入了这种自指性循环的自我意识,但凡想要超越自身便会遭遇人工智能(AI)那样的“自反悖论”,或者说那种想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的“主体性悖论”,这是一种形而上(meta)的真正贫困。不过,这并非完全不可解,从逻辑上来说,那就必须在大脑的神经可塑性(Neuro-plasticity)完全丧失之前重新开放性地引入“他指性”(other-reference)或“他者性”(otherness),并在异质性的“自我”与“他者”之间善意的交往、对话与共舞中发现、创造与生成彼此的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与各自的自玄主体性(self-reflexive subjectivity),正如尼采所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为什么善意是如此必要和重要并且紧迫?因为,从人的主体性视角和理性能力的生成来说,真-善-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三维一体,“真”(一致性)来不开“善”(相互性),“善”(相互性)也离不开“美”(和谐性),而在我们身处的这个“现代世界”,冷漠的利己主义与自我中心主义、文化相对主义与“文明冲突论”、霍布斯式的“人对人像狼一样”与黑格尔式的“为了承认而斗争”的范型诱导与心理预设都将导致“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博弈论困局——“纳什均衡”与“囚徒困境”,这在形式上其实是与自我吞噬的咬尾蛇是等价的(“间接自指”可以简并为“直接自指”),也许,耶稣正是看清并为了避免这样的困局才说出:“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3.3、从实践、主体和历史的角度来说,任何人从出生伊始,“自我意识”肯定是首先由原生家庭及其嵌入的时代结构所影响、塑造甚或“决定”(压抑),而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中,绝大多数的“自我意识”其实都是“被决定的”,也因此会陷入不同程度的“适应论”、“决定论”和“宿命论”,直至形成一种“客体化人格”(被物化和自我物化),作为其挫折-补偿形式(被压抑者的回归/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之“两极化”的主观唯心主义(自我神化)与虚无主义(自我虚无化)便是其症候,但也有极少数的“觉醒”与“(相对)成熟”的自我意识形成了一种主体化人格,并反过来回应、超越乃至力图“改变”所嵌入的时代精神结构,而且,这些或“伪”或“真”的自我意识与人格形式在历史上都已经形成和发展出了自身的意识形态并在现实中反过来自指性地(self-referentially)合理化与强化各自对应和“服务”的自我意识、人格类型和现实构成,当然了,其实还存在一种缺乏自身的表达能力和意识形态因而是“失语”的离散的自我意识和人格障碍的病态形式,即由于普遍存在的系统性的压抑、侵害、创伤及其病变等结构性原因而分离出的一种不成型的、人格障碍的、非主体也非客体的“贱体化状态”(abjectivation),就像是现代工厂流水线上“被抛弃的残次品”或日常生活中“被抛弃的垃圾”。人类的历史,正是在这样的主客交替、真伪互渗与循环往复中演化,或“进化”(evolution)直至升华为一种更高的社会形态,或“退化”(involution)直至崩溃以及低水平的结构性重复:一次又一次的“推倒重来”,原地打转,歇斯底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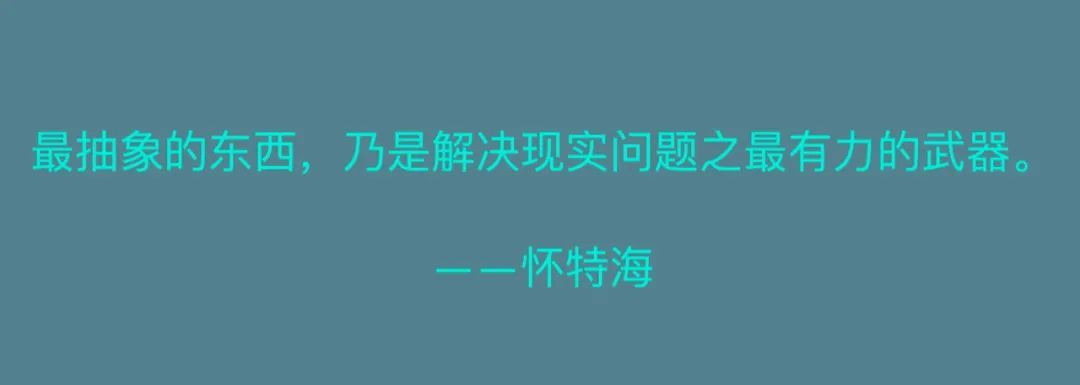
4、许多人都知道,整个现代思想和现代世界的建构,也就是从“人”的觉醒和“自我意识”出发的,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为里程碑,人类自此开启了挣脱“中世纪”状态的漫漫征程。前面已提到的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成了现代哲学的开端,自不必再说。后来,在《利维坦》(1651)中,霍布斯用了16章的篇幅来写“人”,以“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的权利原则而不再是神学原则确立了现代政治哲学的新基础。洛克写过《人类理解论》(1690)。莱布尼兹写过《人类理解新论》(1704)。休谟写过《人性论》(1739)。在《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1753)中,卢梭写道:“在人类所有的各种知识中,对我们最有用但是我们掌握得最少的,是关于人的知识。”后来,在《爱弥儿》(1762)中,卢梭又写道:“应该通过人来研究社会,也经由社会来研究人:想把政治与道德割裂开来的人,对二者都将永远是一无所知。”在《纯粹理性批判》(1781)中,康德认为对于人类理性有如下三个最重要的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该做什么?我可以期望什么?”20年后,在《逻辑学》(1800)中,康德再次回到了这三个问题,并增加了第四个问题:“人是什么?”他解释说,凡是试图找出前三个问题答案的人,最终总会遇到这第四个问题。但是,19世纪却发生了一场关于“人”的话语的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从“人性”(human nature)概念转向了“正常人”(normal man)概念,这意谓着从“自然”(physis)转向了“习俗”(nomos)的范畴,从形而上学和理性主义转向了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方法,例如,马克思的“人性论”进路就是经验主义的“现实的人”,洛克的“人性论”则是经验主义的“白板说”。哈金在《驯服偶然》(1990)中写道:“‘正常’(Normal)带有19世纪的烙印,正如‘人性’(human n ature)带有启蒙时代的烙印一样。在所有严肃的场合下,我们不再问,人性是什么?取而代之的是,我们谈论关于正常人的问题,我们会问这种行为正常吗?……研究基金会投入大量基金来寻找什么是正常的,对那些研究人性的人来说,则很少能得到资助。”后来,作为20世纪的显学的(临床)心理学与精神分析,所聚焦的对象、方法和范畴基本上是人格(尤其是病态人格)和行为,依然不再是“人性”范畴,例如,弗洛伊德的“性本能”,阿德勒的“追求优越感”,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与“自我实现”,拉康的镜像理论与“无意识的自欺关系”,等等,而所谓的进化心理学则更是野蛮和恐怖地将“人”过度地还原和降维为动物和基因层次从而“取消”(Cancel)和“Low化”了“人之为人”(human being)的类的规定性与本身之所是,这些概念、话语和范式后来都逐渐进入了时代的日常意识而成了人们理解自身的基本“原型”,尤其是在越来越严重的实证主义、数据主义和操作主义的学院化风气的裹挟下,(后)现代人类对自身的理解反而是越来越狭隘化、碎片化和阴暗化以及空洞化了,远不如中国的先秦与古希腊的人格那样更为饱满、昂扬与卓越(Arete)。
5、如今回头来看,“现代性”概念和整个“现代化”进程(倒不如说是“后中世纪性”与挣脱“中世纪”的历程),可以说是由三个维度构成的:一个是世俗化,一个是个体化,一个是科学化,但在结构上,其实依然保留着“中世纪”的神学框架与帝国结构,依赖一个作为背景的上帝(God)来统摄,诸多的“现代性”理念基本上都是在《圣经》和基督教神学内部发育起来的,“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基督教理念向世俗社会的“移情”与“投射”,例如,“天赋人权”是“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的平移,契约精神是“上帝与人之间的立约”的平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金钱面前人人平等”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移,“个人-社会”二分法是“信徒-教会-上帝”三分法隐掉“上帝”后的平移,法国大革命口号“自由,平等,博爱”是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结构与“爱邻如己”的平移,等等。
5.1、因此也可以说,“现代性”迄今并没有真正建立起自身的独立根基,正如哈贝马斯所言的“未完成的现代性”,或拉图尔所说的“我们从未现代过”,整个“现代化”进程表面上看似是批判性的和革命性的,但在深层结构上却是依附性的和“复制性”的,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中世纪”的一种逆反形式,这就像是血气方刚的少年对压抑的原生家庭的逆反或“娜拉的出走”一样,这种逆反的心理结构与所逆反对象的权力结构其实是“同构”甚至是“等效”的,结果只会是“双向强化”与“深度锁定”,只会是再一次的“解体”而不是“解放”。几百年以来,随着“上帝死了”(“博爱”也成了无源之水)、形而上学的解体与道德根基的丧失,以及大学教育的体制化、学科化和单向度化,学院知识分子和建制“精英”的思维方式也越来越“意识形态化”或曰“主义化”,直至陷入了多元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以及犬儒主义的“八卦阵”,物理学、生物学和经济学的确是发展得很快,伦理学却被远远地落在了后面,正所谓“身体跑得太快,灵魂被远远抛在了后面”,人文与社会学科的思想范式越来越自然科学化、数据化和操作化,“人”被简单粗暴地过度还原、降维和简化为原子、基因或利益(经济动物)等非人的存在而丧失了自身在“人之为人”(human being)层次上的逻辑位置、主体意志与道德原则,这也就是福柯所说的“人之死”,“主体之死”,“人终将被抹去,如同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
5.2、人类走到21世纪的今天,“现代化”的三个维度都走向了自己的极端形态,“世俗化”成了物质主义(经济主义与资本主义)与拜金主义(市场主义与金融主义),“个体化”成了自我主义(利己主义与自我中心主义)与自恋主义(绩优主义与自我优越论),“科学化”则成了科学主义(量化主义与概率主义)与实证主义(证据主义与数据主义),这三个维度在本质上其实就是一种经验主义-现实主义-结果主义的心理学进路、“成功学”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其“三维一体”的合成效应即“自我金融优势最大化”(“玩的就是杠杆儿”,“钱多才是硬道理”,“世上没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的心智模型(mindset),越是“精英”越是如此“思维”,这也即是主导当今世界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核,说白了无非就是“丛林法则”与“成王败寇”的新马甲而已,冲突而不是合作、撕裂而不是团结、“各自为政、各吃一套”成了“新常态”,社交网络也差不多变成了“社交战争”、“囚徒困境”和“信息茧房”,整个世界便陷入了自指性的平庸循环,加速朝着“最大熵状态”演化和退化。宛如“预言(理论)的自我实现”,人间真的变成了霍布斯的“利维坦”:“人对人像狼一样”,“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自由”、“平等”、“民主”、“科学”与“证据主义”/“阴谋论”等现代“(极)左-(极)右”党派化术语则往往会沦为服务“自我”(ego)、攻击对手的机会主义话术而抽离或掩盖了自指性的(self-referential)、境遇性的(situational)复杂而微妙且不可化约的自性(selfhood)与纹理(texture)。
5.3、迄今并未终结的2020年病毒“大流行”悲剧和“美国大选”闹剧成了21世纪的新寓言:人类正面临着社交网络(算法操纵)、人工智能(阶级贱斥)、生物医药(基因控制)、虚拟现实(以假乱真)和纳米技术(无孔不入)等缺乏道德原则和伦理学支撑的“黑科技”的系统性威胁,它们已经(主要)不是“人服务人”的工具而是“人利用-控制-殖民人”也就是“再中世紀化”的武器。至此,我们完全可以说,人类文明的“现代化”(不如说是“后中世纪化”)之旅已告全面失败,人类陷入了“环球同此凉热”的共同危机,无不是“困在系统里”,“内卷”到了内爆的临界状态,但这也让我们认识到,“历史”本身并未“终结”,不管是从形式还是从实践的意义上而言,“终结”的只是人类文明之现代化的“西方模式”或“西方中心主义”;“西方”(美国)不仅不再具有引领世界的象征意义、方法论和领导力,而且其本身就是问题和症候的一部分,但是,这并不意谓着人类文明的“东方模式”或“中华文化”就理所当然、顺理成章地成为“压倒西风”的新风向、新范式和“最大赢家”。事实上,“非此即彼”的现成选项并不存在,任何地方性的、局域性的或“传统性”的文化尽管尤其独立的价值但并不足以独立克服这样的全局性危机,而正确的方式方法只能是“回到人性本身”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古今西东的合璧之道(新综合)。
6、如今有不少人把目光重新投向“信仰”、宗教和神学,的确也出现了宗教的复兴和“宗教(狂)热”,但是,正如“如果奥巴马和民主党人做得好,川普就不可能进入白宫”一样,如果宗教真的“有用”的话,那这个世界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毕竟它们都已经存在并主导了人类的思想两千年左右,是吧。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没有哪个宗教是真正致力于“此岸今生”和拯救“这个世界”的,它们的用心基本上都在于“彼岸来世”、如何从“这个世界”之中解脱出来而通往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另一个世界”(恰如文艺青年式的“诗与远方”),但同时又自指性地(self-referentially)以“此岸今生”的行为之伦理学性质(善恶)为判据。迄今的历史证据也表明,宗教不仅常常并不能阻止冲突或战争,甚至还是引发冲突或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们通常是问题的构成部分而不是问题的答案。当然了,这并不是说宗教便是一无是处,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维度、精神经验和隐喻结构,它们可以为人类重新理解自身与再造文明带来无可替代的启发,但也可以肯定的是,过去的任何一门宗教或学说都不可能成为克服当前人类危机的“解药”。那么,从方法论上而言,我们应该做的只能是“回到人性本身”、立足于此生此在、从当下问题出发,并在古今中西的对比与互照所形成的“强烈的视差”(康德)中进行创造性的“大综合”与内在伦理学(与依赖神或上帝的外在伦理学相对)的新建,重新为理想、道德与正义建立基于人性的理由与动机,从而把这个乾坤颠倒的世界“正”过来。如果说,我们可以把人类文明的第一个阶段称为“神本主义”时代,作为过渡的第二个阶段称为“资本主义”时代,那么,第三个阶段便可称为“人本主义”时代,而这必定是一个必须达到如康德所期望的“人是目的”和“永久和平”的时代,而当下我们正处在“人本主义”时代的大门槛前的“资本主义”市场沼泽地里,这可以说是一场自雅思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以来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但如何才能迈过去呢?大危机需要大觉醒,大觉醒需要大讨论:如何在绝望的人间重建希望的理由呢?如何在陷入了功利主义和唯我论的全球化时代重建公共性与共同体呢?如何在相对主义、主观主义和虚无主义横行的碎片化世界里重建人生的意义感、思维的整体性、判断的有效性与道德的根基呢?
7、沿着世俗化的方向和内在伦理学的人本视角,以及在中西古今对照的“强烈的视差”之下,我们就可以轻易地辨识出中国的传统与思想的“特色”所在:西方人的世俗化才几百年,而我们中国人的世俗化却悠久得多,甚至可以说自从几千年前的殷周之变和周公制礼作乐就始露端倪了,自此底定的政治结构和儒家伦常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塑造了我们中国人的心智结构或者说“国民性”,虽然经历了晚清以来的“西学东渐”和“文化革命”,但可以说,至今我们中国人的心智结构依然是“儒家式”的,即家族主义,或自家主义。公允地说,作为一种能够以千年尺度存在的世俗化政治框架、意识形态与组织方式,它一定是抓住了人性中的某种东西,但历史上的“治乱循环”也足以表明,它也一定是丢失了或压抑了人性中的某种东西,以至于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变迁中丧失了显性的主导地位而“退居到了幕后”,西方的自由主义、马列主义和科学主义话语则以一种几乎是“词悬浮”、“蒙太奇”或“马赛克”的碎片方式进入了中国人的意识光谱,但正所谓“缺什么,补什么”,这些理念恰恰正是曾被儒家的“家天下”礼教秩序所遮蔽和吞噬的“个人”(自由与平等)、“国家”(政党与法治)与“天下”(科学与正义)三大维度的一种补偿效应,亦是迄今远未完成的“三重启蒙”,包括儒家主义在内的这“四大主义”如同传统中国的“儒释道”一样在中国人的意识光谱中其实是一种“杂居状态”而不是一个真正能够相互协调的“合一状态”,因而有时便是排斥、冲突、撕裂、纠结与互锁的状态,以至于每一个维度(主义)本身并不能真正各就各位、各安其分与各尽所能。当下,我们中国人继续的主体性重建与创造性再生产所面临的基础理论问题之一,便是如何把“个人”(自由主义)、“家族”(儒家主义)、“国家”(马列主义)和“天下”(科学主义/全球正义)四个存在性维度逻辑一贯地整合为一个内在协调、富于活力且可持续的有机整体的问题(四部和声)。但反过来说,我们中国人当前面临的这种古今中西诸思想杂居、交错与内卷的人类经验也是值得反思的独一无二的“复杂性资源”,完全有可能成为深陷危机中的人类不得不“再造文明”而亟需的新思想、新理论和新哲学的沃土,正所谓“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8、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危机,危机,危中有机。”的确,在人类文明的演进当中,危机充当着一种人类对于自我意识的唤醒、反思与超越的“南墙机制”——不撞南墙不回头。古希腊德尔菲神谕:“认识你自己”(know thyself)的本义即是“人啊,你要有自知之明”,人类要认识自身的界限,要为自身划界和立法,也就是说,人类不能“高估自己”,但同时,也不能“低估自己”,要有勇气和智慧突破那些“人为”的而不是“自然”的限制或问题。这种隐含的认识论要求和有限与无限的辩证法意谓着人类应该不断把自身再对象化、再知识化和再系统化。
8.1、但凡这样的时刻,人类的“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便分化为一种认识论上的主体(subject)与客体(object)或语言学上的主我(I)与宾我(me)的自我反思、自我对话和自我超越的二阶结构,用塔勒布的话来说,这样的主体是“反脆弱”(antifragile)的,因而能在危机和不确定性中获益,“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杀不死我的,使我更强大”。不过,在迄今的人类真实历史中,这种自我超越与“反脆弱”的能力只是例外而非常态,大多数人在危机时刻往往会陷入一种自我纠结、自我失调与自我解离的“失能状态”(主体性匮乏综合症),不少人直接就在南墙撞死了,也有不少人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索性“破罐子破摔”,“死猪不怕开水烫”,我们在现实中也会看到很多心理上“反感”反思和“没逻辑”的人,其实,他们只是缺乏反思与理性的能力而已,所以,我们可以说,康德的启蒙口号:“大胆运用你的理性”,其实是存在常识缺陷的,至少是不具有足够的“现实感”。所以说,任何一场大危机并不足以“叫醒”所有的人,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勇气和能力面对真相,尤其是关于“自我”的真相,更遑论克服危机了,但那些“叫不醒的人”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在“装睡”而是在“昏睡”(麻木不仁)或“死睡”(行尸走肉)。
8.2、需要补充和强调的是,这里的“对话”与“超越”指的是自我反思意识在“同”与“异”的辩证法中的超限、升维与进阶效应或者说“智慧”状态:“照见名智,解了曰慧”,“自知者明,自胜者强”,如数学中的纽结理论:低维(n+2)中的纽结在高维(n+3)中解结。由此也可见,假如缺少了作为差异性、交互性与合作性(善意的)的他者参与,“自我超越”便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们前面所言的自指性平庸循环,因而,“自我意识”只能是思维的起点而不应是终点,不能是自我中心主义的,或唯我论的。遗憾的是,当下的人们在唯我论语境中时髦地谈论“认识你自己”和“做自己”,却忘记了苏格拉底是在雅典的对话语境中弘扬这句德尔菲神谕的,那结果只可能是自我意识的空转与空洞化(佛系)以至于陷入前面所说的自指性平庸循环与“内卷化”。既然在“自我”(自我意识A)的超越论结构中,作为差异性的他者(自我意识B)是不可或缺的,也是无可替代的,那终究会引发“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可通约性”或“共性”或者说“自我意识A、自我意识B、自我意识C……”之共同基础与普遍结构也就是“人性”(human nature)概念的逻辑考察之必要性,也就是说,“人性”概念比“自我”概念更基本,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母体,我们有什么样的“人性”概念,便会有什么样的“自我”意识与“他者”意识以及关系结构,这反过来便会塑造什么样的“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例如,以霍布斯的“人对人像狼一样”、萨特的“他人即地狱”和“人间不值得”为信条的人性观念与政治哲学,那只可能制造一个个的利维坦、“人间地狱”和“不值得的人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亟需一场“人性大讨论”的理由,既必要,又重要,且紧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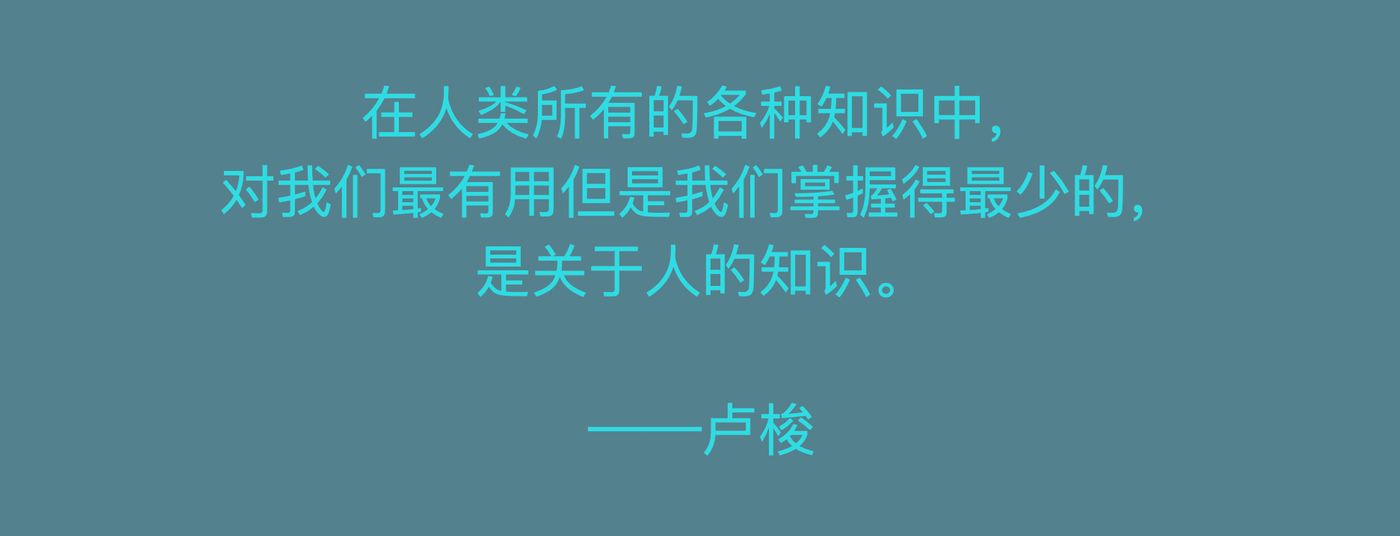
9、那么,这里引出的概念问题是:当我们在使用“人性”这个术语时,我们究竟是在说什么呢,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在日常用法中,“人性”的意思其实是不一致或者说矛盾的,例如,有这么用的:“你这个没人性的东西”、“太没人性了!”、“太不人性化!”,等等,也有这么用的:“人性太丑陋”、“人性是自私的”、“人性经不起考验”,等等。前者往往是一种更偏于感性和情绪化的表达,反而更“形而上”并接近于欧陆理性主义,隐含了对“人性”的善良预设,倾向于“性善论‘;而后者则往往是一种貌似理性和理论化的论断,反而更“形而下”并接近于英美经验主义,表达了对“人性”的悲观经验,倾向于“性恶论”。身处这种矛盾的意识或“无意识”之中,于是也有很多人持一种“性善恶混”的信念。
9.1、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矛盾而且一直未能消除,在我看来,那是因为:1)未能区分先天的“人性”(human nature)概念与后天的“人格”(personality)概念之差别而造成了范畴混淆,前者是规范性的,而后者相对于前者则只是描述性的;2)人类关于自身的理论认识,迄今也没能从“性善”与“性恶”的两极对立中走出来,这种二元对立本身反过来又会强化这种结构本身;3)“性善”说,“性恶”说,或“性善恶混”说,其实,只是持这些信念之人的自我指涉与投影罢了,这就像是人类是在以自己的形象来想象诸神、上帝、魔鬼或外星人的形象一样,很多人也只是在以自己“人格”的形象来设定“人性”的形象,而造成人们的人格向善恶的两极分化的根源未必是在先天,而(至少)应该首先从特定的时代结构中去探寻,并同时“站在矛盾之上”反过来不断重新思索和内省“人性”究竟是什么。
9.2、有必要在此介绍一下之所以如此对“人”的概念进行区分的依据和背景,以有助于理解。我采用的是加里·戈茨(Gary Goertz)在《概念界定:关于测量、个案和理论的讨论》中提出的“三层次”概念框架:基本层次(basic level)、第二层次(secondary level)和指标/数据层次(indicator/data level),由此,我们可以把“人”(human)的概念分为三个层次:人性(human nature)层次、人格层次和相貌/行为层次。人性(human nature),作为“人”的概念的基本层次(basic level),所指的是与生俱来的一种人之所是(human being)的“先天机制”和“普遍语法”、与其他物种得以区分的“类的规定性”、人类得以保持自身的“范畴同一性/不变性”,独立于后天的地理、习俗、文化、政治和语言等影响。
9.3、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中,人性(human nature)被认为既是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的来源,也给过上一种好生活提出了障碍或限制,在古希腊哲人的观念中,与习俗(nomos)相对的自然(physis/nature)乃是作为判断的权威与规范性的来源,也就是定规立则的正当性基础,例如,在政治哲学的讨论中总是有必要预设某种“自然状态”(nature state),这是“超出”(meta)于社会状态(social state)的一种形而上学(meta-physics)或元哲学(meta-philosophy)预设。
10、此外,还有必要作一下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说明:“人”的概念的形貌/行为层次是可眼见的,人格层次是不可眼见但可思辨(推理)的,人性层次是不可思辨(推理)但可直觉(或悟)的,也就是说,“人性”这种东西,看不见,也摸不着,是不可能通过目前的科学实证主义实验、机器和操作来观察、检验和证明的,只能依靠人类对自身的感受、内省(反思)和直觉(intuition)来直接把握。
10.1、事实上,直觉在我们的认知中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在知识论和认识论中也居于核心地位,无可消除,不可替代,例如,约翰·罗尔斯认为,“任何伦理学观点都必然在许多点上和某种程度上依赖直觉”(《正义论》),“哲学中最根本层次的问题通常并不是通过结论性的论证来解决的”(《政治自由主义》);侯世达从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中所阐发出的认识是,“一个人永远也不能给出一个最终的、绝对的证明,去阐明在某个系统中的一个证明是正确的。当然,一个人可以给出一个关于证明的证明,或者关于一个证明的证明的证明——但是,最外层的系统有效性总还是一个未经证明的假设,是凭我们的信仰来接收的”(《哥德尔、艾舍尔、巴赫》);亚里士多德也持这样的观点,“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被证明,否则证明的过程将会永无止境。证明必须从某个地方起步,用以起步的这些东西是能得到认可的,但却是不可证明的。这些就是所有科学的第一普遍的原理,被人们称之为公理,或常识”。
10.2、尽管我们不可能不最终依赖直觉,但也不能变成(唯)直觉主义,同时还必须对直觉所得出的命题体系进行逻辑(无矛盾)与经验(实证)的双重检验,直至最终我们在认知上没有理由不承认它,在心理上没有借口不接受它,否则,便会陷入(退化版本的作为自我辩护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泥潭。真正可以称得上“科学”(science)之名的知识是由认知主体的直觉(假设)、推理(逻辑)与检验(经验或实验)这三个基本环节或者说“三位一体”构成的,缺失了任何一个维度的所谓“思想”或“知识”都是“不科学”或“伪科学”的,但众所周知,科学知识本身并不是完备的,所以,还必须加上第四个环节——反驳(逻辑上或经验上的)直至提出新的假设而进入下一个阶段的科学循环,只有这样的科学认知之四环节(假设-推理-检验-反驳-新假设……)的非凡循环才配得上“良知”(con-science)之名,那么,我们关于“人性”概念的科学与良知显然也是同理,而在此框架中,传统的“科学”与“人文”的二元对立划分,显然也是成问题的,并得到了有效克服。
10.3、当下,我们中国人正被各种似是而非、东拉西扯且往往是自相矛盾的“意见”(opinions)所挟持和撕裂着,几乎见不到真正有逻辑、有论证和有解释力的“知识”(knowledge)并进一步可检验的“科学”(science),所以说,西方文明中的逻辑学和科学方法论是我们中国人最应该补上的“系统性缺失”和“开学第一课”,光喊“致良知”的口号是没用的。当然了,没人会认为知识(knowledge)本身可以等同于真理(Truth),但却是通往真理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的阶梯。任何人的认知与理性的确是“有限的”,绝对的真理(Truth)与完美的正义(Justice)不可能现实化(realization),但这并不妨碍人类以这样的“理想型”(Ideal form)作为参照、规范与激励从而相对正确地把握什么是知识(knowledge)、正当(right)与“好”(good)等并在实践中不断通过检验、反思和对话等手段来“超越偏见”和“跨越障碍”而得以渐进自由地沿着知识、正当与好的阶梯通往更高的人类境界(缘阶而上,更上层楼),也就是成为不断自我超越、自我迭代和自我转型的自玄主体性(self-reflexive subjectness),直至生命的尽头。从整个人类的角度来说,这是一场代代相继、生生不息的接力赛,每一个知识台阶意谓着一种意识-信息对称性水平(主客合一/人天合一/德位相配),而这也应该是“发展”(development)的真正含义,而这里所言的“主体性”(subjectness)概念,也即是一种对称性回应能力,或者说胜任力,也即是“配位之德”。
11、古今中外关于“人性”的探究、观点和著述,不胜枚举,在这个领域中,令人敬仰的先贤大哲,也是数不胜数,但也不得不说,迄今我们所获得的“人性图像”仍然是片段的、零散的,甚至似是而非的,也是越来越阴暗的,所以说,卢梭在1753年写下的如下一段话依然在有效期之内:“在人类所有的各种知识中,对我们最有用但是我们掌握得最少的,是关于人的知识”(《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无论是从概念、方法与文献,还是从认知、主体与现实的角度来说,“人”或“人性”这个词语都依然是有待深入讨论和定义的,而且,从当前的危机形势来说,也是十分紧迫的,尤为重要的是,这是人人都真正可以有权利(right)平等参与的,因而可以避免专家式垄断与独断,这也是“人性大讨论”中的“大”字之所以是恰当且可行的根本理由。但问题是,我们今天还有可能提出能站得住脚的新东西吗?
1)首先,答案是有可能的。因为,身处21世纪的我们拥有先辈们所身处的时代所没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知识与创新的基础条件——互联网,它可以带来在过去难以想象的超时空头脑风暴、智识杠杆效应和创造性大综合的可能性,这就像是在前互联网时代根本不可能想象如今用短短几年时间就能造就数千亿富豪一样,过去没有任何时代能像今天这样准备了产生“自玄性主体”或者说“大师”(Master)的时代条件,尽管绝大数人却是在循规蹈矩地浪费这样的资源和机会。
2)其次,我们还需界定一下“新”的含义,按照庞加莱和熊彼特的观点来说,创新即是有意义的新组合,“新”未必是(其实也不可能是)完全的“无中生有”,只要是“有中生新”或者说“有中合新”就行了,包括常规意义上的创新和范式意义上的创新。
3)再次,我们还应该说一下“创”的问题,创新的主体是“人”而不可能是“科技”本身,“徒法不足以自行”,徒“科技”也不足以自创,人工智能再怎么“深度学习”也不足以自行转型升级,所以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严格来说并不准确,而且也遮蔽了“人”的主体作用,尽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具有可行能力的“行动者”(agent),也并不是所有的行动者都是具有胜任力的“主体”(subject)。
4)最后,我们也有必要说一下主体的问题,作为创新之结果或“结晶”的新组合,也必定是一种具有新结构的整体,这意谓着创新者需要面对和处理的是“部分-整体关系”问题(“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也对创新者提出了相应的主体性要求,例如,至少必须得有人格的整体性(integrity)、开放性(openness)和连接性(connectedness),那些信奉“唯我论”以至于陷入了自指性平庸循环——封闭、焦虑和抑郁的精神失调与自我分裂的人格必定是自顾不暇的,因而也不可能成为创新主体,正所谓“攘外必先安内”,“人生难得是心安”。
5)当今世界之所以会陷入深重的信贷危机和“量化宽松”,表层的原因是创新赤字与创造力贫困,而深层的原因其实是这个世界陷入了“唯我论”丛林、“公共性的缺失”和“共同体的破裂”。因为,从主体论的视角言之,真-善-美其实是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缺失了人与人之间的“善”(相互性)与“美”(和谐性),也就不会有足以把握“真”(一致性)的主体性的再生产,而缺失了道德支撑的“Big tech”迟早会自我耗竭而难以为继,“科技向善”其实是科技的内生需要。一言以蔽之,人类要想克服自身的这场大危机,就必须进行一场范式大转移:从“博弈与斗争”(囚徒困境)转向“对话与共舞”(美美与共),但除非我们为这种对话与共舞范式找到客观的人性基础,否则那便只是一种空中楼阁或“南柯一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