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长租公寓暴雷,房价只涨不跌,居民如何争取居住正义(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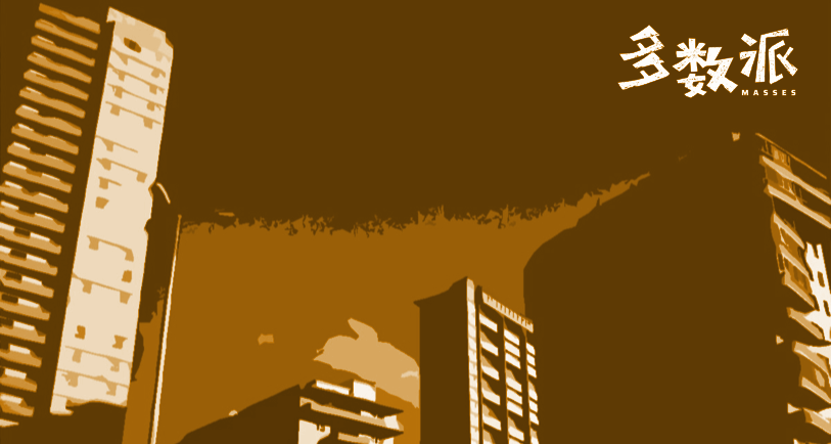
编按:2020年底,蛋壳长租公寓暴雷引发了轩然大波,有年轻的生命因此陨落,更有无数的租客、装修工、清洁工等被裹挟其中,陷入债务危机。然而,不到半年的时间,这场风波已经不留下一丝涟漪。多数派认为,在蛋壳长租公寓暴雷事件背后,无论是过度金融化的问题还是居住权的问题都尚没有得到充分讨论,而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分析、批判,并且从其他地区的反抗经验当中汲取力量,探索另外的可能性。本文上篇梳理了历史上和当下的租户行动,本篇则关注占屋运动、住宅合作社和社区土地信托等反抗市场逻辑的居住实践。
作者:张居正
租金管控、没收与占屋运动:1970年代以来与金融危机以后的德国柏林
尽管租金罢工被视为抗议住房盘剥、在经济衰退等重大事件中达成诉求的快捷工具,但这也意味着这种工具经常是短期性的。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较为平稳的阶段,租户联盟往往采取推动地方政府颁布租金管控法令的形式来防止租金上涨或过快上涨。这类法令一般规定彻底冻结租金,或是设定租金的上限(如同设定最低工资标准),或限制租金周期性上涨的幅度。
但是,无论是哪种形式的租金管控,都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认为有损住房市场的可持续供应。他们提出以租金补贴来取代租金管控,以提高房东更新住房设施和新建房屋的积极性。然而,相比租金管控,这意味着政府税收最终被用于支持地产资本,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同时也并不能起到抑制租金上涨的作用。肉眼可见的是,近五年来,越来越多城市和地方开始采取租金管控以遏制与工资水平不匹配的租金上涨。西班牙、荷兰以及美国的四个州(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新泽西州和马里兰州)实行了全境范围的租金管控措施。而德国柏林,在长达十余年的房价和租金猛涨后,也在2020年2月迎来一项严厉的租金管控法案。在该法案规定下,柏林约有150万套房屋的租金将冻结五年,并以每平方米9.80欧元为上限。
这一法案的通过是租户运动推动居住正义的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1989年两德统一后公共住房私有化、住房商品化进程所带来的持续影响,再加上德国大城市房地产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成为国际资本和投机者的绝佳避险资产,德国柏林等大城市出现了日趋严重的房地产泡沫。房价的飙升也对租金产生了影响。2009-2018年柏林住房的租金翻了一番,从2008年的5.82欧元/平方米上涨到2018年的每平方米10.90欧元。到2018年,德国家庭平均每月在住房、能源和维护上的支出为859欧元,占家庭月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而独居者则要支付月收入的40%以上作为租金和相关费用。这导致柏林每年发生的驱逐达到6000次以上。在居民租房比例达到85%的柏林,这引起了明显的社会反应。

多年来,一些运动团体(如Marx21、Interventionistische Linke等)一直反对社区士绅化,而租户的自组织团体(如Kotti&Co)则倡导“城市权”。在租金飞涨的背景下,它们共同构成了抗议“疯狂租金”(Mietenwahnsinn)的广泛运动。2015年,该运动成功举办了一次关于《柏林住房供应法》的公民投票。到2018年,有2.5万人参加了反对“疯狂租金”的集会,2019年则有4万人。该运动还提出了一项对垄断房地产私营企业进行没收的要求。这个目标最开始只是针对德意志住房建设(Deutsche Wohnen)这家德国规模最大的房地产商进行的,因而被称为“没收德意志住建” 运动(Deutsche Wohnen Enteignen)。但之后运动者援引了德国联邦法律(该法律允许在特殊情况下进行财产征收并转为集体所有权)以及柏林宪法(规定每个人都有权享有适当的居住空间),呼吁对拥有3000套以上公寓的大公司所拥有的房地产都进行征收并转为市政所有权。目前该倡议已经进入全民投票征集签名的第二阶段。可以断言,如果没有这些活跃的租户权利运动,我们就不可能看到柏林租金管控法案的通过以及后续可能的进展。
在同一时期,随着住房危机的加深以及新增移民住房权利被漠视,柏林的占屋运动也出现了新的延续。尽管社会环境和成因不同,历史上西柏林与东柏林的占屋运动曾分别于1980年代和1990年代达到高峰。这些占屋运动一般是针对长期囤积而导致空置的私人或公共房屋进行的。占屋者们出其不意或秘密地占领这些房屋,自主更新并使用房屋设施,促使房屋所有者最终允许他们低价或免费使用住房。大部分时候,为获得使用权的法律承认,占屋者不惜与警察发生对抗。在西柏林,青年学生、流浪者、工人和原住居民进行占屋,除去表达对社会住房政策的不满以及对市政腐败的抗议,也是受到1968年以来激进左翼和亚文化运动的影响,试图建立属于自己的替代空间,因而带有十分强烈的反建制色彩。而在东柏林,直到柏林墙倒塌以后,居民才开始采取类似的行动。与西柏林的住房紧张不同,东柏林的公共住房供应充足。占屋行动一定程度上是被官方视为一种有助于瓦解住房集体所有权的现象,而被短期合法化的。但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柏林警察局定期开展大规模的清理占屋行动,自那时起新的占屋行动就很难取得成功。而保存下来的占屋,大多在与占屋者签订租约的形式下得到承认,但也为日后的分散清理埋下了隐患。近年来,在城市士绅化与租约到期的情况下,许多历史悠久的占屋消失了。
而新一轮的柏林占屋行动主要与前文提到的租户抗议运动以及难民运动相关。例如在2012年5月,由克罗伊茨贝格的一群社会住房居民(主要是来自土耳其的难民)组成的租户自组织Kotti&Co就在当地的一个公共广场中间搭建了一座木屋,以抗议由于市政部门撤出补助而导致的住房租金上涨。尽管这座木屋最初只是作为集会的临时建筑搭建的,但是它很快就被当成了永久性的抗议营地。而在2018年5月,80位占屋行动者占领了柏林两座拥有40个房间的空置公寓楼(由国有住房企业Stadt und Land所有),以抗议柏林无家可归以及经济适用住房短缺的现象。尽管房主与占屋者进行了租约谈判,但在价格协商不一致、谈判破裂后,占屋者很快被警察清退。尽管这次行动并没有以占领成功而收尾,但复兴的租户权利运动的确使得占屋重新成为一种抗议和争取权益的手段。占屋者不仅旨在争取具体的住房权益,而且试图延续上世纪的做法,采取书店、咖啡馆、电影院、花园、日托中心、画廊等形式,将它们打造成自治的社区空间和行动网络。
而在西班牙、希腊、意大利、美国等地,占屋也正在重新成为工人阶级实现住房正义的方式。

住宅合作社与社区土地信托:在自我管理中实现反剥削
除了组织各种形式的租户权利运动来反对政府和资本对住房的垄断之外,工人们还通过合作社、社区土地信托等方式,以土地和建筑设施的集体所有权来实现住房权益,并获得自我管理和组织的权利。
早在19世纪60年代,德国就出现了第一个工人住宅合作社。这种最早的住房合作社由工人集体筹资、自主建房和管理,按照合作社的通行原则——罗奇代尔原则组建。这个原则以英国的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命名,并成为世界各地合作社的运行原则。原则上,每个工人或家庭享有平等的股份,对土地和房屋享有集体所有权,在社区决策上有相同的投票权。这种方式可以降低住房成本,保证住房布局和社区公共服务按照个人和集体协商意愿来安排,并能有效防止住房的投机性交易。不久之后,出现了社员对住房不享有所有权的租赁合作社。这些最早的住宅合作社无疑是工人运动的产物。
但在二战后,为了解决住房短缺的问题,住房合作社成为欧美许多国家接受的一个方案,从而被吸纳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当中。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尽管住宅合作社有诸多好处,筹集资金毕竟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相比由房地产公司来建筑和售卖房屋,住宅合作社的建房成本已经降低了很多,但许多工人仍然无法一次性支付股金。恩格斯曾经批评英国早期出现的建筑协会(一种住房众筹组织)总是由中产阶级参与的,而工人无法负担。住房合作社也有这个窘境。因而,许多合作住宅是在国家通过土地和税收优惠、租金补贴、银行贷款支持等多种形式的支持下兴建的。例如,在二战刚刚结束的西德,住房合作社占新建住房的比例达到20%,是由政府直接出资建造的公共住房以外的主要住房形式。如今,德国柏林的租赁市场仍然有30%左右的住房由住房合作社拥有。
但是,政府1990年代对住房合作社的支持力度减小并通过了立法改革,住房合作社的非营利性质改变了。合作社被允许追逐利润,一些纯投资目的股东得以进入,从而使其与一般房地产商同质化。这个过程表明,尽管国家支持下的住房合作社具有改善工人阶级住房条件的目的,但与住房合作社诞生的初衷——工人阶级实现互助和自主管理——存在偏差。它仅仅只是作为资本主义住房市场的补充形式而存在。对于政府而言,它既不如公共住房给居民带来的好处那么直接,也不如商品房可以给富人投资保值的机会。它仅仅是调控市场的一个元素,在不必要的时候就会得到抑制。
另一个原因是,住房合作社已经完全从工人运动中脱离出来了。在美国,尽管早期出现的一些豪华型住宅合作社是由富人开发的——方便筛选住户以设置封闭性,但随后大量中低收入工人负担得起的住宅合作社大多是由强大的工人运动支持的。在1926年,纽约合并服装工人工会(ACWA)主持了本地第一批合作住宅的建造。第一家合作社位于布朗克斯区,有303个单位,不仅向工会工人公开出售股份,而且由工会拥有的合并银行提供贷款。入住以后,合作社居民还集体兴办了一系列社区业务,成立社区杂货店合作社,提供牛奶运送服务,还有将工人送往地铁的巴士服务。为了普及与其他工会的合作发展并开展更大规模的住房项目,1951年联合住房基金会(UHF)得以成立,由包括19个工会组织的机构和个人联盟组成。如今,在纽约,仍然有超过10万名居民居住在1926年至1974年之间由工人运动建造的公寓中。这一时期由工会支持的合作住宅约有4万套,它们今天还是抵制纽约城市士绅化的堡垒。尽管这些合作社住房后来被认为顺应了种族隔离的策略——居民主要是白人工会工人,但它们仍然证明了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为自己营造住房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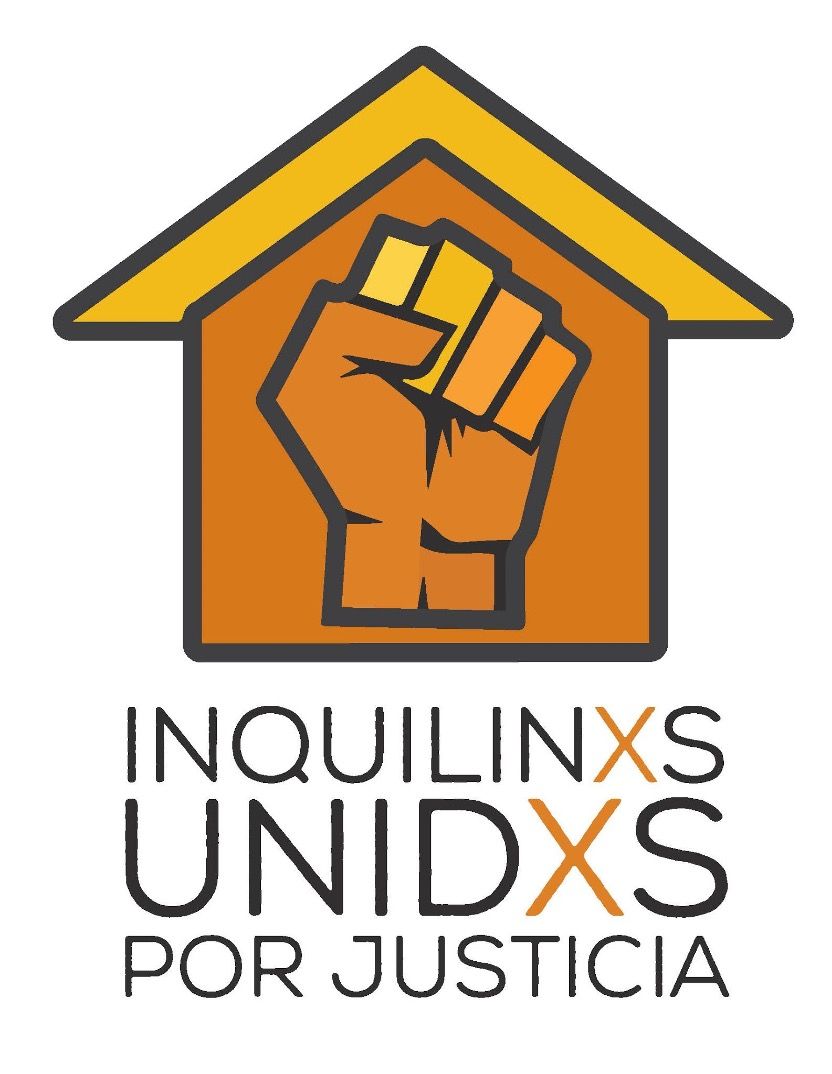
今天,最活跃的部分住房合作社仍然是和草根运动紧密联系起来的。一些占屋运动者在行动成功后,将占领的空间改造为合作社,由集体进行运作。而在租户权利运动中,一些租户向房东赎买住房并将其转型为合作社,以抵抗租金上涨。例如在2019年,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些租户(主要是少数族裔)就从私人房东手中买下了居住的柯克伦五公寓大楼。这场斗争实际上从2016年持续到2019年底,租户先后动用了反驱逐、租金罢工以及推动市议会剥夺违法房东的租借许可证等手段,但仍然没有摆脱纠纷。在租房者正义组织(Inquilinxs Unidxs por Justicia)与土地银行双子城(Land Bank Twin Cities)的帮助下,他们最终实现了赎买目标,土地由土地银行所有,而房屋建筑则转型为有限资产合作社,从而得以使租金在50年内降低至少20%。
在住房合作社之外,从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民权运动中,黑人逐渐发展出一种社区土地信托的土地使用形式,以与住房合作社相配合。尽管最早的社区土地信托是由美国南方黑人农民发明的,通过集体购买土地并成立信托基金,他们得以保留地价上涨的收益并控制租金,而不是定期向白人交租。但是,这一创新很快被运用到城市中。由于种族歧视性的贷款政策以及按照房型和地块大小进行划分的严格分区规定,美国许多大城市不同种族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贫富差距。由于黑人往往没有房屋所有权,租金的上涨常常使得他们持续贫困化,乃至无家可归。社区土地信托则通过将租户需要支付的地上建筑的租金与土地价格分离,使得少数族裔可以享受低于市场价格的住房使用权,或者获得房屋所有权。信托基金首先是将社区土地买下,然后对土地上年久失修或破旧的建筑进行翻修,再把住房售卖或出租给居民,许多住宅因此被转型为合作住宅。由于其非营利性质,土地的溢价以及其它收益可以被用于投资社区内的公共设施,并由居民民主控制。这也避免了一些住房合作社可能存在的问题:随着地价上涨带来租金上涨,或者初始社员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在地价上涨后将合作社解散并售卖资产——这也使得后来的租户面临严重的租金上涨问题。因而,社区土地信托+住房合作社的模型可能比单独的住房合作社更能防止士绅化,从而巩固少数族裔和种族融合社区的发展。而在轰轰烈烈的BLM运动中,社区的集体所有权作为一个核心诉求,成为遏止黑人社区贫困化、争取种族正义的行动方向。社区土地信托与合作社,无疑为黑人运动实现这些目标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尾声
在资本主义持续的生产利润危机中,房地产和建筑业已经成为资本越来越流行的逃避危机的“回路”,以此倾销剩余并获取租金和利润。在这种背景下,金融化作为一种工具,必须将城市、社区和房屋这些原本的公共物品设计成花样翻新的金融产品和活动的组成部分,并让劳动者以各种形式买单,来延缓整个系统的崩溃时间。而工人在按揭贷款和房租中支付的工资比例越大,家庭受到的挤压就越多,结果是越来越多国家出现所谓的生育危机。而工人阶级在再生产上投入的增长,也可能大大限制他们在生产领域上的斗争,促使他们难以采取脱离和反抗体制的行动。
在许多国家,我们迎来了住房运动的复兴,这是全球阶级斗争复苏的一部分,已经变得与反对工作场所剥削的斗争同等重要。但是,这些斗争会带来什么深远的影响,可以将我们带到哪里去,是否会随着经济危机的退却而渐渐消弭,一切还有待明晰。然而,毫无异议的是,运动的参与者已经为自己和他人带来了生活的改变,并提供了进一步斗争的工具。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回过头来看,会将这些行动视为重要的进展。而在尚未发生改变的土地上,我们能做的绝不仅仅只是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