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翻译社会学的角度看文科生与理科生的互相鄙夷
最近由于央行一篇论文中,夹杂了一句“东南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文科生太多”掀起了轩然大波。又激起舆论关于“文科是否无用”的激烈讨论。众所周知,我国理科生与文科生素来不睦,前者蔑视后者没逻辑,后者鄙夷前者没文化。不过在网上的论战中,理科生底气更足一些,毕竟不少文科生选文科的原因只是理科不好,辩论起来未免少了些“理论自信”。

我可能比较另类,中学最擅长的课是语文、历史和数学。虽然考进复旦数学系,但数学没考好,反而是语文作文拿了最高分。数学系毕业后先读统计,最后又转回历史系中。这两天不少朋友问我怎么看这次舆论之争,“文科生是不是真的没用?”。我倒不想辩论文科或理科的重要性,一无新意,二太空泛。但我认为大部分人在为文科或理科辩论时,似乎默认双方对文理的内涵并无异议,而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前置问题:
“文科”与“理科”这两个翻译准确么?如果不准确,错在哪里?其中的误差又如何误导了我们对于文科与理科的想象?
“文科”与“理科”之误及其成因
当代文科与理科的划分,虽然参照西方的教育系统,但在英文中却并不存在一个标准的对译。比如文科似乎囊括了英美学校的Art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理科则包含Natural Sciences,Applied Science,Mathematics。这些分类之间也有模糊地带,比如数学算不算科学,人类学算Humanities还是Social Sciences都有争议。不过我们就文科的全称“人文社科”来看,似乎是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的对译。那么文科的“文”,应当源于Humanities(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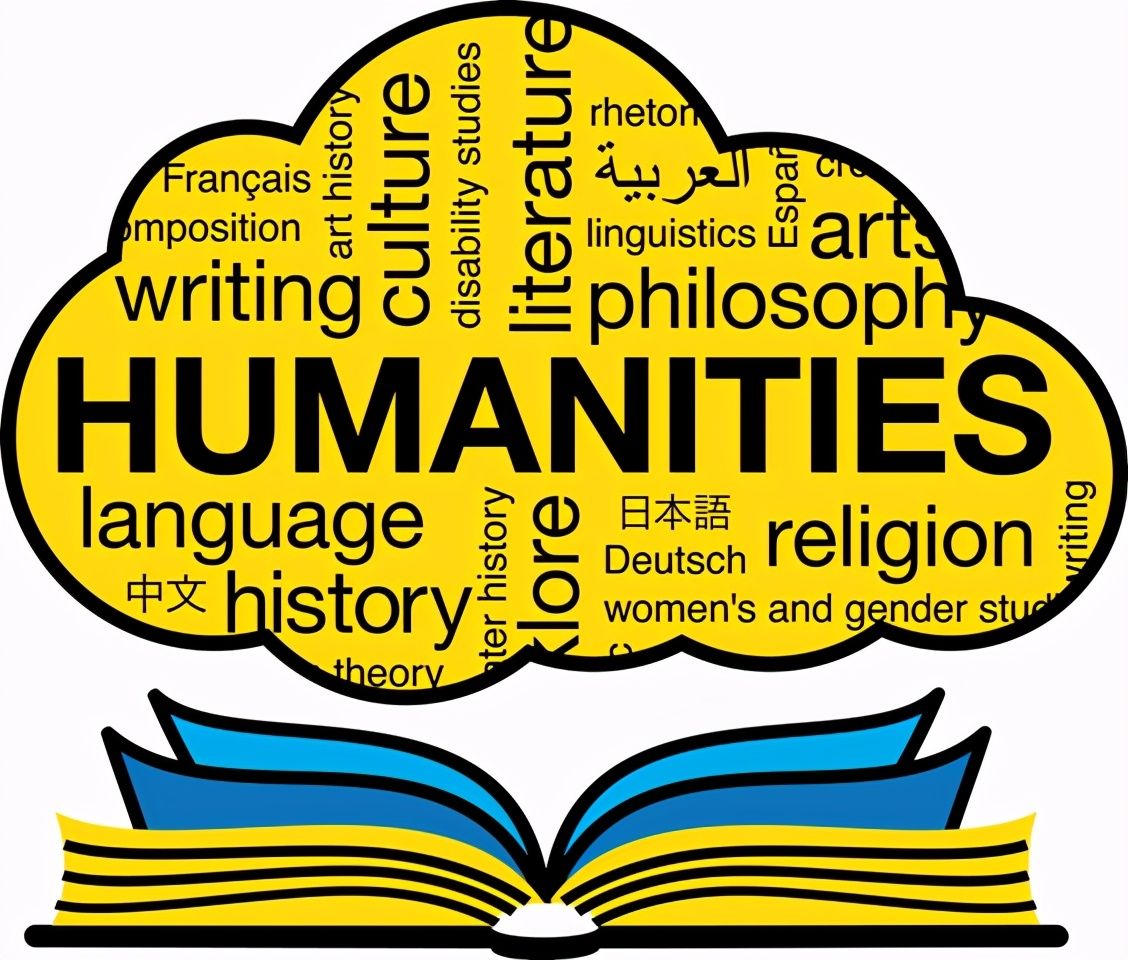
但“人文”一词出自《易经》:“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和天文一样,属于偏义复词,重点在于“人”和“天”,而非“文”。古文中也有水文和地文,均是研究水流与地质的学问,与“文化”无关。其实文通“纹”,因而关于星象、水流、地脉的活动,都缀以“文”这样一个表示脉络的语素。因此我们可以说,把“人文”简化成“文”,已经错了,毕竟我们并不把天文学、水文学、地文学也视为“文科”。如今所谓之“文科”,其内涵应当是“人科”,这倒与Humanities的精神相符,后者在文艺复兴时,被用于指代世俗社会中的活动及文化,与神学研究相对。
理科的“理”也有类似的问题。俗语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里的文与理其实是近义词。地理与地文在古文中内涵类似,只是现代文中地理用以翻译geography,地文用于代指physiography,才形成了差异。文与理在古文中并不构成一组对立,与“文”对立的是“质”(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或者“武”(文武双全),与理对立的是“欲”(存天理、灭人欲)。“理”也并不跟科学方法论所强调的实证主义有什么关联。

但语言是个积非成是的过程,历史学者不能简单地说某个现象或概念“错了”,而应该进一步追寻其何以如此。具体到“文科”与“理科”的翻译,其成因在于绵延千年的科举制度。虽然今人把“文科”视为“人文社科”的缩写,但“文科”同“人文”一样,古已有之。科举体系把考试分为文、武两榜,大众认知中皓首穷经的“科举”统称“文科”。有趣的是,在科举初期,唐代一度将“算学”纳入科举,即“文科”。而清末迫于时局,清廷推动瀜记忆”而非“理解”教材内容。教材说的是“原子是保留物质化学性质的最小单位”,就好比人也可以一分为二,但后者不能作为社会人而存在,所以“人体是保留社会人性质的最小单位”,但并不意味着绝对意义的不可分割。当然,“原子(atomos)”这个词的本意确实是“不可分割”,源于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世界由不可分割的最小单位组成)。但这并不是物理学意义下的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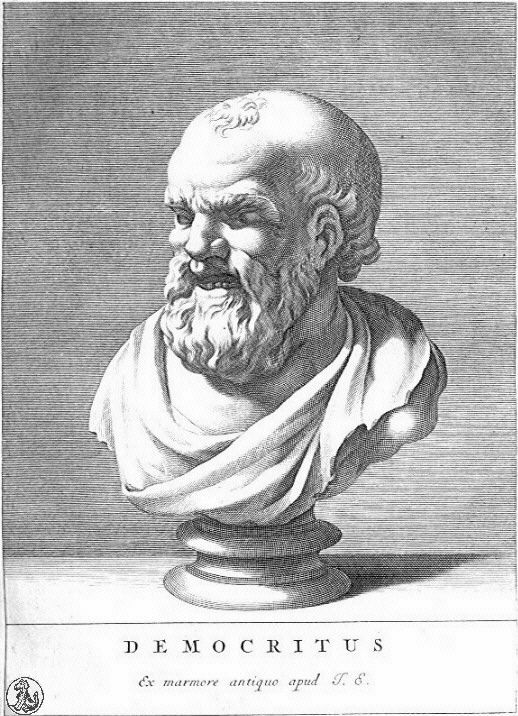
如果说上一个例子可能是把哲学原子论与物理中的原子混淆,还情有可原;下一个例子则更让人无语,也更典型地体现出“文科轻逻辑”的偏见带来了怎样的恶果。在一节社会学课上,要读布尔迪尔的场域(field)理论。我发现场域和电磁学的场用的都是field这个单词,便有意地把电磁场的性质与布尔迪厄的分析相对照,发现颇为类似。在《为何阅卷组长成了小镇做题家》一文中,我分享了这一对比:
“场域”常见于社会学理论,如文学场域、政治场域等。对这个概念最常见的质疑是,场域和通常说的领域有什么区别?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视角的转换。当我们说领域时,强调的是领域中的行动者,如“电影领域的陈导李导 ”,这句话的主体是导演,电影只是他们工作的场所。但若要研究电影场域,那就不是研究电影人,而是针对一个抽象的电影圈子,研究它如何对具体的电影人施加影响,以及这个圈子自身的权力结构、流动性等特征。 这是因为场域借鉴自物理学的电场(二者原文都是 field)。布尔迪厄认为场域能对其中的行动者造成宏观上的影响,但行动者本身仍然具有一定的能动性(agency);这对应了电场对微观上不规则运动的电子产生作用力,使其宏观上沿着电场方向产生电流。 此外,电场作为客观物质,其自身是物理学的研究对象。因此社会理论家提到场域,研究的也是场域的主体性,而非作为表演舞台的领域。
课上教授问起如何理解场域时,我也以此作答,随即招致一位国内文学博士的反对。本以为她有什么理论性的批评,没想到其理由竟是“我刚才翻了Introduction,没看到布尔迪厄说他参考了物理学。”看来我在分析场域与电场理论结构的相似性时,她一字没听,而是去前言里看作者的原话,仿佛这才是正确且唯一的研究方法。那一瞬间,我感觉她似乎在从事圣经研究。这个例子无疑体现了国内文科教育诉诸权威、而轻视分析的倾向。后来我在布尔迪厄其他著作中,看到他确实承认受到了电磁场的启发,不过对我来说,观察和分析场域与电场理论的相似性,远比考据布尔迪厄说没说一句话重要地多,后者是传记作家、文献学或版本学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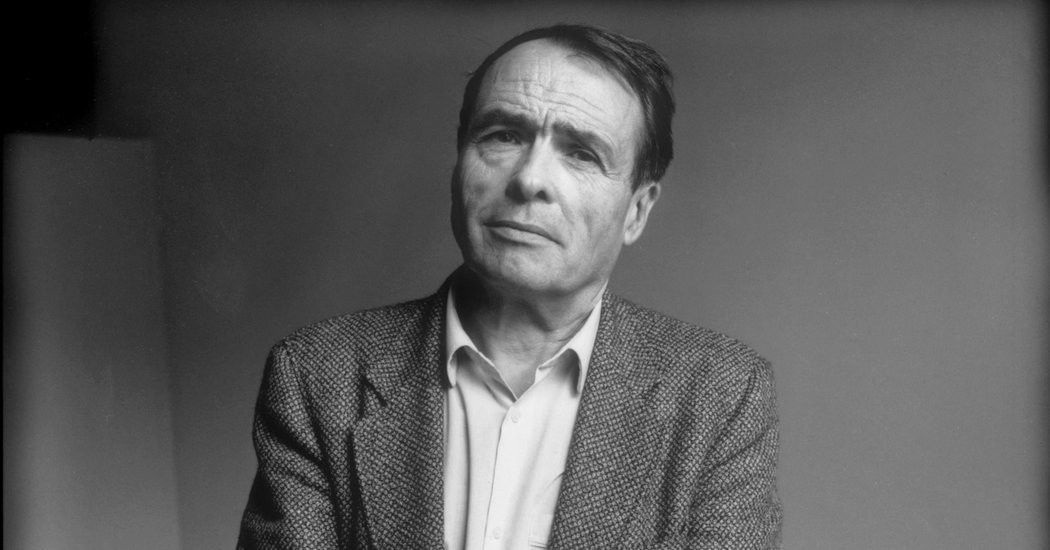
结语
其实人们之所以对“文科”与“理科”望文生义,还有一重原因,就是古文与现代文的隔阂。今人看到人文之文,已不会想到天文、水文、地文中的 “文者纹也”,而自然地将之与文化、文明相联系。类似地,由于“理”被用来翻译“rationality 理性”、“reasonable 合理”,也在语感上与“文”渐行渐远,而侧重逻辑思辨。我们似乎很容易就能接受“理科生”讲逻辑这一观点,却并未质疑它的逆否命题“文科生不讲逻辑”是否成立,而是下意识地默认。反之“理科生没文化”也是一样的望文生义。这或许是文理互相鄙视的根源,然而逻辑也好,文化也罢,本就无所谓文理。从这个意义上,晚清科举改革把人文社科、理工知识一同纳入“文科”,反而有着歪打正着的启示作用。
我提出“人科”与“物科”的分类,倒不是为了取代“文科”与“理科”。在翻译问题上,我始终持保守态度。唐玄奘曾提出“五种不翻”,其中就包含“顺古故不翻(顺应之前的译法,不另加翻译)。”文科与理科的提法,已有近百年历史,一朝颠覆,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但是倘若在思考“文科”与“理科”各自的侧重与价值时,引入“人科”与“物科”,或者说“异质化”与“同质化”的概念,很多问题或许不言自明。
就我自己的经验而言,国内与国外文科教育的差距,恐怕远比理工科的差距大得多。这或许有点反直观,因为我们坐拥各种“国学大师”,理工科诺奖却寥寥可数。然而这种错觉源于学科性质不同:理工类的差距是显式的。有个段子说,“世上只有数学不会辜负你,因为数学不会就是不会。”理工类的定理证不出就是证不出,零件造不了就是造不了。因而面对美国的围堵,我们时常感到自己科技实力的差距。但人文类的差距却是隐式的,胡适所谓“敢开风气不为先”,虽是自谦,也是事实。五四之际,只要能把西方人文学问嫁接到中国,不论是否准确,至少也有一代大师的名号。理工类就难多了,因为他们本来就要跟全世界在同一套标准下竞争。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之前吐槽大会范志毅吐槽男篮,引发男篮反扑,骨子里觉得“你国足也配骂我?”其实很多人忽略了,篮球在世界范围内相当小众(中美比较热门所以让国人产生了错觉),国篮排名世界29,亚洲第4,最多就跟国足排名世界79,亚洲第9半斤八两。只是在篮球本就无人问津的亚洲闭门造车,所以感觉良好。文科同样如此,当人们把“中国哲学”与“外国哲学”、“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并立时,文科已经立于不败之地。然而即便不谈文学、哲学这些与语言高度相关的学科,只看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这些社科领域,相对于华人在理工类的成就,依然乏善可陈。
其中的原因既有教育的原因,也有美国与英语在知识生产层面的霸权原因,已非本文所能承载,最后就以我在一个群中的留言做结吧。这段话是回应一位群友认为“文科生至少在马哲等大学基础课比理科生强”的观点,也算点出了我认为“文科”教育落后的部分原因。
马哲这些“基础课”可以对标高数。有的文科不用学高数,或者只学高数c,但马哲也没有a、b、c,在高中准备比较多的文科生肯定有优势。但就研究而言,悲剧在于,高数还是那个高数,马哲却不见得是那个马哲。比如找一个理工科(数学、物理、统计)之类的硕博士,功底再差,高数基础概念微积分之类的总是完全掌握了;但人文社科的研究生,虽然理论上国内从高中就学马哲,还有大学四年,没读过原文或者误读的比比皆是。这当然也不怪学生,一方面是学科属性决定的:国内数学教材虽不如美国苏联,但副作用最多就是学得慢一点,启发性差一点;一个理工科学生不用读牛顿的原著也能学会牛顿三定律和微积分;文科就不一样了,很多人批判的马哲可能只是列宁主义,或者列宁主义都不算,不阅读整个系统的谱系,只能南辕北辙,但这恰好是高中教育没法承载的。如果把文科窄化成古诗词、训诂学、文献学这些与中文强相关的,那中国还是有优势的;但那样的文科就不足以与理科并列了,人文社科中历史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这些都离不开理论。但知识生产的上游不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