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校园乐队主创姜如璋:我的T恤上写着“浪漫主义接班人” | 围炉 · RUC


如果有人曾在一天前与姜如璋在放着温柔爵士乐的咖啡厅里进行了一次访谈,一天后再次在音乐节的舞台上看到他和乐队的演出时,他一定会感到震惊。如点燃的炮仗般抱着话筒架蹦跳的主唱,用嘶哑的烟嗓唱着:“我就是这新世纪的穷光蛋”;双手在桌面上交握着端坐的大个子,说话低沉柔和,偶尔垂头沉思——很难想象这两个是同一个人。
姜如璋,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专业研究生,能够演奏吉他、架子鼓、键盘多种乐器,每周五参与学校爱乐人社团的吉他角演出活动,独立作词作曲创作有《他的猎枪》、《想和你在草坪深潜》、《一篇关于美好的田野笔记的摘要》等9首作品。2020年10月与同校另外五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组建校园摇滚乐队"草坪深潜",担任乐队主唱兼主创。乐队目前拥有《新世纪穷光蛋》、《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醒来》等共4首原创音乐作品,曾参加2020青巢大学生音乐嘉年华。

H=黄哲敏
J=姜如璋
H | 你能不能先和我们讲讲你和音乐的故事,一开始你是如何和音乐结缘的,然后又怎么一步步发展到开始进行音乐创作?
J | 小时候爹妈给我报了钢琴兴趣班。当时其实挺不喜欢,因为它占用了很多玩耍的时间,但是学琴的经历可能无意间打开了我在音乐方面的某些技能或是天赋。从小开始,我的不管是音感、音准还是唱歌的节奏感,都比较好。刚开始时我学得可带劲了,因为别人都夸我弹得特别好。我还作为我们那一批学生中的代表登上音乐厅演出过。但我对具体怎么“好”也没有什么概念。后来可能是到了干啥都没兴趣、都特别浮躁的阶段,变得越来越不喜欢学琴。
学琴期间我练习的强度比较大,我妈一直在边上看着,有的时候我俩就一小节一小节地抠那个曲子。现在回看,我觉得这段经历对我的心性从积极方面说可能是磨练,从消极方面说也近似于泯灭或者压制。
只有一次我真正感受到了弹琴的快乐。那一次我弹了一首歌,正好我姥姥也在,她直接跟着唱了起来。后来我才知道,我姥姥年轻时是吕剧演员,我弹的正好是他们曾表演过的一首歌。那次是关于弹琴我唯一记得的非常非常快乐的回忆。可能也只有那一次。
但是在小学毕业结束了学琴之后,我没有走上什么特别的创作的道路。初中的时候音乐对我来说没有多么特殊的意味,就和大家差不多,当作业余爱好,闲时就听听。
开始自己搞点东西是在高中的时候,我一直很喜欢听Westlife,于是就着手把他们的英文歌词翻译成押韵的中文。在高三的日子里,翻译歌词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调剂方式,是一定能让我感到很轻松与享受的一件事情。这时候我开始了有一点自主性或者是主体性的尝试。
H | 为什么把翻译歌词视为你在音乐方面的“主体性萌发”?
J | 因为在翻译的过程中,哪怕你再忠实于原文,你总是要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H | 你又是怎么从这个你所说的“主体性萌发”的阶段过渡到真正开始尝试创作的阶段的呢?
J | 我高中足球队的一个哥们儿,他会玩吉他,后来我们俩凑到了一次,他弹琴我打鼓。受到他的启发后我开始去自学吉他,发现自己虽然不具备什么乐理知识,但还是可以自弹自唱一些东西。所以更多是受到了身边的人的刺激吧:我身边的人都可以玩儿,他们好帅,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他们能玩我也能玩!所以从大一下或是大二上开始,我更多地想要写一点自己的东西。那时候我感觉还挺好,硬凭感觉就可以往下写一些歌或是词。
那时候还有一件事情:我的腰受了挺严重的伤,在宿舍躺了一个多月,看着人来人往,有的跑着去打球,有的匆匆去上课,只有我一个人在宿舍养伤,对比起来落差感还是挺明显的,所以心理状态不是太好。那时候正好民谣比较火,我偶然间听到了其中一些非常丧的作品,受到了很大的触动。由于只需要一把吉他、几个简单的和弦以及抒发情绪的歌词——也不难押韵,便可能创造出一首比较简单的民谣,于是我就想:我的文字功底不差,音乐感觉也不差,那试试能不能也整把吉他稍微划拉两下。我在音乐方面的主体性也在这个尝试的过程中逐渐被激发了出来。
H | 你的创作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进步和变化的过程?
J | 写出第一首歌的时候,还挺激动的。我前面创作的几首歌,比如《匿情于黄昏》、《亲爱的那不是浪漫》,是非常典型的民谣。但是民谣听多了之后,我个人感觉有点腻,因为民谣的数量比较多,主题也大都以远方和理想为主。我自己写的词一开始则呈现出非常情绪化的倾向,完全表现我的个人感受。
对民谣感到腻了之后我对自己的作品也有了更多的反思:是否可能往其中注入一些更深刻或更丰富的东西。这时我恰好听到摇滚,而摇滚正是很多乐器配合在一起;它还可以有很多主题的呈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大约从大二开始,我觉得摇滚可能比民谣更适合我,它是我下一步想去玩的东西。我现在还不知道摇滚往后会不会有更适合我的东西出现。
转向摇滚后,差不多就是现在这个状态,也注重一些感情的抒发,但更多的是在追求一种深度。不管是词还是曲子,都希望它可以不那么口水。这也是我为什么希望和乐队一起玩,因为大家聚在一起,想法能更多一点,汇聚在一起就可能会诞生一些新的东西。
H | 你是怎么从个人化的歌词转变向更深刻的主题的?
J | 我觉得这和我对于自己所学的专业的理解有关,比如我本科时所学的社会学。当对专业知识的学习越来越深入,就会开始试图——我觉得这也是不可避免的——用所掌握的专业知识来观察生活中的一些现象。当我开始用社会学的思维来观察生活、思考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时,就发现之前的歌词可能有点窄,过于个人化。尤其是学了后现代社会学理论之后,知道了这么多伟大的思想家对社会有如此深刻的批判和独到的思考,觉得他们很了不起。
除了专业的影响以外,还有一点是:随着自己听的歌越来越多,开始听小众的和所谓政治不正确的歌,进一步意识到其实歌词还可以有很多深刻的内容。这两个因素刺激了我,让我决定一定要写些不那么个人化或情绪化的歌词。
H | 纵观你的作品,所涉及的内容的确比较广泛:《你好二十岁》是在生命的一个节点上有感而发,《想和你在草坪深潜》唱的是校园的毕业季,《他的猎枪》则是受到了顾桃的纪录片的激发。你在创作时是否有意识地从某些地方取材?往往是什么“刺激”你进行创作?
J | 我一直坚持的原则就是我要写真东西。我在追求这种“真”的时候,比较固定的主题首先就是在我身边、让我感觉不舒服的事情或环境氛围。我会用稍微有些隐晦的歌词把它描绘出来,然后批判一番。
再一个比较固定的主题就是通过看各种纪录片——尽可能真实地反映他人生活的纪录片,用这些纪录片来丰富自己的精神体验,然后像写观后感或影评一样来写歌。这种写歌方式我一定会坚持下去。
H | 是什么促使你想写这些“真实的东西”?
J | 我希望我的歌可以让大家得到暂时的解脱,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到大家,比如认清些事情。我这样说有点自大,但这的确是我的初衷。比如说我之所以写那首批判内卷的歌,是因为我真的看到好多朋友,由于期末考试低了零点几个绩点而非常难过。我真的替他们难过,我觉得事情不该是这样的,或者说太残酷了,而这种残酷不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我也知道一首歌不会改变这个大家因出路有限而拼得你死我活的现状。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朋友们能看开一点:这件事情尽力就好。我希望他们别那么难过。
H | 你曾提到“如何过音乐以外的生活”,这样的说法让我感到好奇,它似乎喻示着:音乐在你生活中占据了超乎一般人想象的、相当大的一部分。
J | 有段时间演出比较多,音乐自然而然就成为了生活的重心,占据了生活中比学习都要大的一部分。并没有刻意地实践,当时的生活就是这样的节奏,让你自然而然就觉得:音乐真的是我很重要的一部分。和音乐有关的生活分为线上和线下两部分。线上的生活是在群里定我们排什么歌、统计大家什么时间有空,然后再和排练室老板进行预约。
线下的生活则是排练,我们一般都在晚上排练,排练一次至少要两个小时。排练的时候,我们会随时打断,讨论某一部分是否设计得不够好、大家是否有新点子,就这样一点一点不断尝试。当然这主要是我的乐手伙伴们的工作,我则负责不停地唱。弹奏乐器的是他们,所以他们更有发言权——他们更知道怎么弹会听着更好听、更动人,或怎么弹更容易。而他们伴奏的旋律怎么和我这个人声的旋律相配合,这是我和他们商量的内容。

H | 当音乐不再是你生活的重心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
J | 虽然演出没那么多了,但心里仍然会觉得音乐还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在演出之外,你还可以听歌,可以在平时自娱自乐。
不过确实也有这种情况,当演出变少之后,或者说就是在演出结束走下舞台的那一瞬间,当你回到你日常生活中的那一刻,会有一点失落。有一个词叫“演后抑郁症”,专门用来形容这种现象。在全国巡演的歌手和乐队,他们会出现这种情况:在演完之后突然变得非常失落和空虚。我也出现了,但没有那么严重。
青巢音乐节的表演结束之后的第二天我们接受了《新闻周报》的采访。那天再次见到伙伴们的时候,我甚至产生了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突然觉得面前的他们有些陌生。虽然只相隔了一天,伙伴们在我心中的形象却已经不一样了:高大了许多,但同时又感觉更亲切更熟悉了许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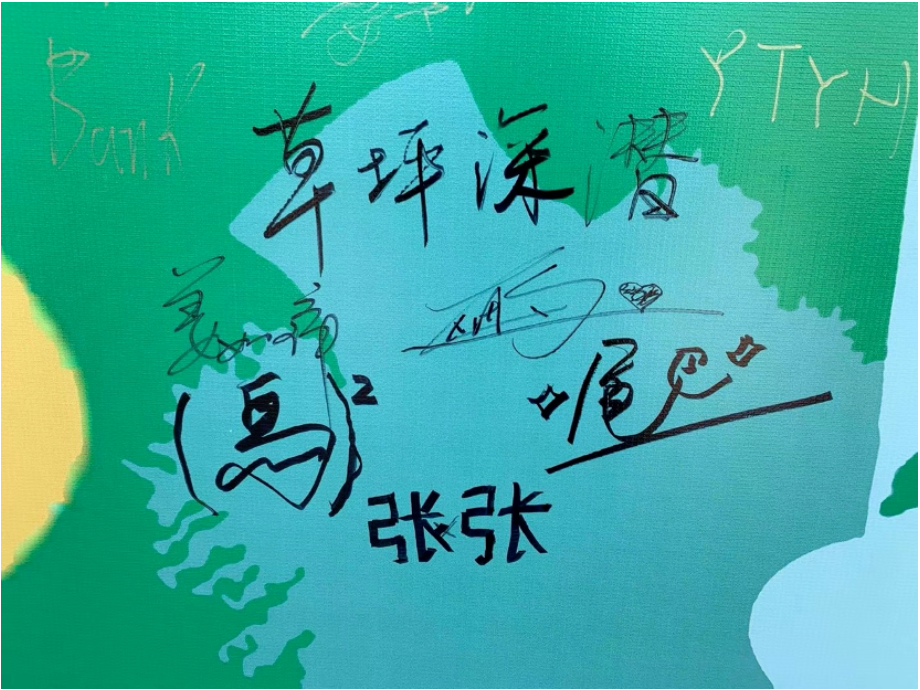
H | 你不仅听歌、唱歌,也创作和演奏音乐,在这个与音乐相处逐渐深入的漫长过程中,你对音乐形成了什么样的个人化理解?
J | 我觉得音乐带给我的——我不想说得过于崇高——但确实是一种被拯救的感觉,或者说是真的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感觉,挺让人高兴的。
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做的是摇滚乐,我借机顺着历史脉络把摇滚乐从头到尾听了一遍。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一些艺术史或是美学的教育、熏陶和感染。就像马尔库塞说的,艺术是对异化的异化,对否定的否定,我觉得这确实发生在了我的身上。
我可以举个例子,就在几天前,我的心情突然就崩溃了。那一周要做两三个展示,那天就有一个。我在宿舍想趁展示前睡两三个小时,但愣是睡不着,脑子里净是乱七八糟的事情。宿舍里兄弟们都还在呢,我就突然在床上开始大喊大叫、捶桌子。舍友们都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但也震惊。如果换成别人,大家可能觉着这人疯了,但如果是我表现出这样,大家一看就知道我肯定是又不太爽了。
我让一个兄弟帮我把吉他拿到上铺来,然后我就一边躺着一边开始即兴创作,脑子里想到什么词就唱什么词,并且顺着弹旋律。唱着唱着,我的情绪好像就稳定了一点,然后就爬下床准备展示去了。甚至即兴写出来的这段词我也觉得还不错,后来还记录了下来。
音乐让我的情绪有一个突破口,或者就像个减压阀一样。沉浸在音乐中的我看起来是处在一个非常危险和高压的状态,写的歌有不少也是比较激烈的,但其实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得到了释放,变得不那么紧绷。
我在歌里不管是追求浪漫,还是讽刺和批判,我的出发点都是爱。
H | 我感觉到你的情绪一旦累积起来,就似乎会比大多数人都更加激烈。你也提到音乐给你的情绪提供了一个突破口,那么我能不能理解为,恰恰是你非比寻常的激烈情绪及其带来的充沛感受赋予了你创作音乐的能量?
J | 是的。草地音乐节那天我们乐队的演出你也去看了,我的其他五个队友在台上都没我“疯”,是吧?在球场上也能看得出来,其他队友也没我“疯”。我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容易上头的人,即使我暂时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之后也会发现这些情绪全都“内化”了,我的思维会非常激烈地翻涌。我可以接纳这样的自己,但也有意识地尽量不让自己的情绪给周围的人添太多麻烦。
我很愿意把很多事情都当成一种生命体验来对待,其中就包含了与这些事情紧密相连的情绪。我也会带着情绪去创作,甚至会刻意收集这些情绪——刻意去记住情绪部分失控的那种状态。比如说,当我大喊大叫的时候,我知道自己现在失控了,同时我也会意识到,如果把这个瞬间记录下来,说不定会成为艺术创作上的灵感。所以当我冷静下来以后,或者是正在冷静过程中,还没完全冷静下来的时候,就会尽力去记录和捕捉。
H |《浪漫伦理与现代消费主义精神》一书在将浪漫主义源流追溯到了以丰富的情绪为乐、放任强烈情绪流露的情绪主义和感性伦理,指出了一种将开心、愤怒、感伤等各种情绪全都视为享受、甚至有意去创造出丰沛情绪的特质和伦理,具备这种特质的人往往也心地善良、具有较强的同理心。你觉得自己属于这种情况吗?
J | 我有件T恤,上面就写着:浪漫主义接班人。我觉得我本质上是个浪漫主义者,但可能没有那些最激烈的浪漫主义者那样夸张;而我对待情绪也与你刚刚提到的情况不同,我的态度是:let it be——让它出现吧,出现了我就会有意识地去记录;而不是说我会刻意让自己生成某种情绪。我会觉得它可能对我的艺术创作有用,但很难说我享受它,我不敢说我享受它。
H | “出发点都是爱”应该怎么理解?前面提到,你为“内卷”现象及被卷入其中的人感到难过,可以将这种“难过”理解为“爱”吗?
J | 当看到日常生活中与我关系亲近的人遇到不好的事情时,我就会不断地想: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这个事情就不该是这样。理想的生活中怎么能出现这种丑陋的、让人极其不舒服的东西?它们的出现会让我非常不舒服,虽然这并不是我的过错,但还是会成为我难过的来源。我会生出强烈的愿望,希望遇到难处的朋友们哪怕能稍微舒缓一点点。
不管是创作还是演出,我都不仅仅是希望我自己,而是更希望听到或看到的人能够因此而减少哪怕是一点点的负面情绪。即便我写的是一首非常批判或者忧郁的歌,出发点也是希望大家在体验过歌中的悲伤之后,在现实生活中能得到一些缓解。
借用人类学的思想来说:虽然主张发展会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论一直被批判,但多线进化论我还是认可并坚持的。也就是说,我还是相信,对于好和美的东西的追求,对于爱的追求,是我们要坚持的。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可能会有多种多样的途径,文化相对主义便体现在多样的途径上。其他的朋友可能是通过文学、戏剧,或单纯就是游戏,这些都可以。但对我来说,是通过音乐这一途径来达成上述目的。

文 | 黄哲敏
图 | 来自姜如璋
审核 | 李文轩
微信编辑 | 蔡佳月
Matters编辑 | Marks
围炉 (ID:weilu_flame)

文中图片未经同意,请勿用作其他用途
欢迎您在文章下方评论,与围炉团队和其他读者交流讨论
欲了解围炉、阅读更多文章,请关注本公众号并在公众号页面点击相应菜单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