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趁着517国际不再恐同日的今天,我们来聊聊“跨”和“排跨”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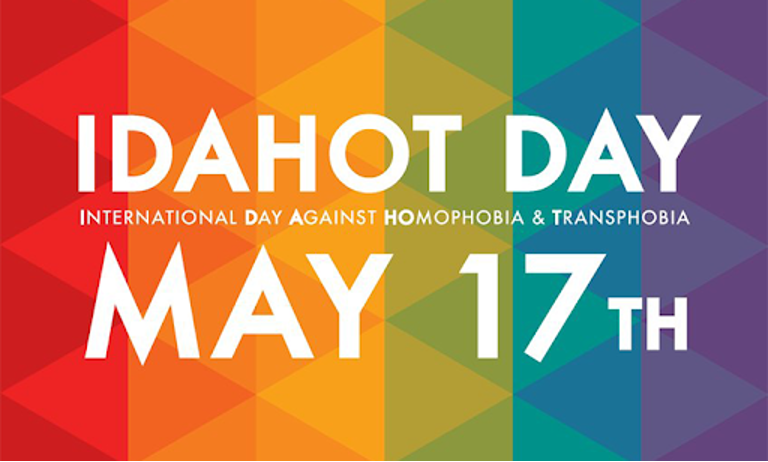
参与者|Snoopy、凉、Becky
国际不再恐同恐跨恐双日(IDAHOTB),全称为国际不再恐惧同性恋、跨性别与双性恋日。1990年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分类大会决议将“同性恋”从精神病名册中删除,这标志着一个多世纪以来医学界恐同的终结。自此,517国际不再恐同恐跨恐双日便被寄予了望唤醒人们对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群体的恐惧的反思,以及加诸于这些群体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暴力及不公平对待的厚望。
此前多数事务社出过一篇《豆瓣激进女权的迷思与困境》,文中以豆瓣的破产版雅典学院小组为代表对豆瓣社区中的激进女权的共识进行了一番梳理。当中,“反对跨性别的概念”引起了不少的争议,被直指为TERF (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 排跨激进女权主义者)。值此517国际不再恐同恐跨恐双日,我们邀请了三位朋友一起聊聊“TERF”。下文中,Becky, Snoopy和凉分别从三个不同的视角对TERF的概念、议题和争论作了多维度的讨论。其中一些核心问题可以启发我们进一步的思考,例如TERF与其他女权主义流派以及排外主义之间的关联,以生理决定论为基础的TERF背后的话语权力和性别政治、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的辩证、位于TERF战争核心的卫生间问题在未来是否有去性别化的可能、如何理解跨性别身份与对抗父权和异性恋正统主义之间的关系。本文试图通过TERF议题去呈现性与性别思考中的多元立场与理论焦点,更希望引导读者观照中国跨性别运动的状况和设想一个可行的更具进步性的性/别运动,亦望有更多人能参与到当中的反思乃至进一步发展成行动,打破附加在我们身上的枷锁。
参与者:
Snoopy:友跨研究者,跨性别权利支持者
凉:一个酷儿赛博格 & A queer feminist (酷儿女权主义者)
Becky:可以算是一个TERF,不代表所有TER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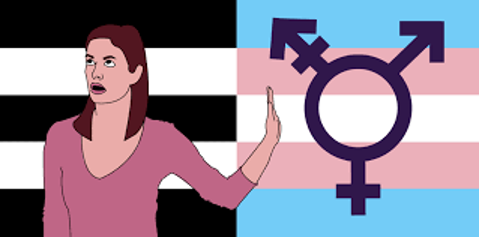
TERF在不同语境下的涵义、概念争议以及流变
Snoopy:TERF这个词最开始是由一些顺性别激进女权主义者在十多年前为了区分自己与排跨激进女权主义所创造出来的词 (Smythe, 2018),这个缩写很快在西方语境里询唤出了围绕”跨性别女性算不算女性”等问题的不同女权主义思想和流派之间的论辩,并成为一种颇具争议的政治身份。被称为TERF的排跨女权主义者则认为TERF这个标签有污名之嫌,是主流女权主义和跨性别平权人士”gender ideology” (性别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的体现,因而更多使用“gender critical”来作为替代性的身份和政治符号。但所谓的“gender ideology”实际上也被右翼团体用来攻坚性别运动,也是对trans-inclusive feminism (不排跨的女权主义)的多元和多义性的无视。而“gender critical”,正如Pearce(2020)等人指出的那样,实际上仍是基于极端生理决定论来界定性别。
凉:TERF一词进入大众视野源于J·K·罗琳一系列排跨推文。典型地,罗琳在她的推特账户里写道,“如果生理性别不是真实存在,全球女性的生活现实就被抹去了。我认识并喜爱跨性别者,但是消除性别观念会消除许多人有意义地讨论其生活的能力”。将跨性别女性排斥出“女性”的范畴,拒绝跨性别女性进入激进女权主义者所声称和拥护的专属女性空间,这代表了被标记为TERF群体的核心主张。这背后关涉这整个女权主义理论和运动的一个关键问题:何为女性?(what is ‘woman’?)。对本质的生理性别的坚持,是TERF将MTF(ma le trans female)跨儿群体排除出“女性”的根本性原因。同时,我也并不认为TERF的称谓构成一种污名化或诽谤性的称呼。那些自我认同为女权主义这并且同时坚持将跨性别女性排除出女性空间的人,这样的称呼正是对其身份的指涉。
TERF和恐跨(transphobia)应该联合起来考察,并做出区别。认为跨儿女性不是女性仅仅是TERF中的一个构成条件。那些自我认同为激进女权(或认同激进女权的主张)并且同时排除MTF为女性的人,才能被称为TERF。激进女权虽然同时有着不同的流派,但对于基于性别的压迫构成最本质的压迫形式的承认,是一个共同的核心主张。而其他形式的压迫,如种族主义,异性恋霸权主义,阶级压迫等都与对女性对压迫有关。因此,激进女权并不一定排斥跨儿,而恐跨的人也并不一定是TERF。恐跨,对跨性别群体的恐惧、排斥、误解、厌恶、暴力等现象,相比TERF群体,更容易在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和现实生活场景中发见。
Snoopy:TERF实际上并不是多么新鲜的政治身份,更不是J.K.罗琳带火的文化现象。早在1979年,Janice Raymond写的 《The Transsexual Empire》就把transsexual women视为侵占女性身体进行性施暴的男性。我认为无论是排跨还是恐跨,都是基于一种本体论的不安全感所产生的恐慌与排斥,都是基于将一个固定的、确切定义的女性作为女性运动的根本。但正如Judith Butler在《身体之重》中所说,女性主义对于对生理性别和物质性不可化约的执着与倚重,可能正是对女性的排斥和降格(exclusion and degradation)。
Becky:在中国语境下很难真正找到一群自称TERF的女权主义者,如果要严格地符合“排跨”和“基进女权”这两项,应该只有lesbian feminism(性别分离主义)的社群会积极讨论跨性别的问题,这或许和一些女同性恋在约会时不愿意遇到跨性别女有关。其余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在中国语境下,反婚反异性恋、希望建立单女互助的女权主义者一般会将自己归类为激进女权),其实很少对跨性别问题进行讨论,因为在中国尚未出现任何涉及跨性别的政策改变。
在我观察到的简中互联网上,TERF这个词基本已经被用来代指所有有排跨倾向的女性,而不是“排跨人士”或“gender critical”。且不论TERF这个词本身是否带有贬义,它本身代表的预设非常奇怪:一个女性如果拒绝承认跨性别,她就是激进女权。或许在这个词被流传、广泛应用的过程中,TERF里的“radical”已经无意判断排跨者是否为女权主义者、属于哪个流派,只是想表达贬义。这带来的误导性是十分严重的。我本人可以接受TERF这个称呼,因为我确实认同激进女权的理论和实践,也确实不认同性别存在被“心理认同”的过程。但事实上,在接触激进女权理论之前,作为一个所谓的“顺性别”女,我已经对跨性别这个概念带来的性别观产生了质疑。我身边对女权议题不甚关心的朋友,从自己的生理女性的立场出发,也会产生同样的疑问。

如何理解TERF对于“女性”的定义,你所理解的sex(生理性别)、gender(社会性别)等性/别核心概念是如何与这种定义对话?
Snoopy: 我认为应当承认人在染色体、性激素、和性征发育等各方面的生理差异而避免滑入一种反自然主义的立场,但这种差异不应当以一种先入为主的男女二元框架来理解,而应该扩展到更广阔的范畴从而认可这种差异是个体层面的。父权和异性恋正统主义正是基于一种本质化的和二元化的生理性别来建构和行使特权,女权主义的一个伟大贡献就在于打破这种压迫的基础,并揭示了sex/gender如何都在生命形式的最早期就被社会和文化赋予意义。兼/间性人(国际阴阳人组织)与广义上的跨性别群体的实践与经验,虽然并不天然就是反抗的激进的,但为我们进一步展现了人类性与性别存在的丰富性。
凉: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的区分与二元体系,和认为生理性别是天然的、本质的,都是社会与历史建构的结果。将生理性别标记为前于社会性别的建构,按照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中的分析,是男权-异性恋中心的规训权力机制最擅长的倒果为因。作为酷儿,坚持反对性别二元体系,反对异性恋中心主义,同时也在体认性别与性向都是流动且多元的。必须说明的是,反对二元的性别权力机制,并不意味着否认性与性别的差异。相反,是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反对生物本质主义(biological essentialism),并试图创造出更加包容的(inclusive)与更加自由的生活。将性别还原为生物本质论,将社会的人缩减为身体生理器官机能的一部分,因而拒斥跨儿群体实在的性别意识与体认,是错误且糟糕的。
Becky:排跨激进女权认为sex是二元的,而gender是一个光谱,主张坚持生理性别的区分,而抵制社会性别,并在理想状态下将社会性别消除。女权主义者与其说排跨,不如说首先排斥的是“顺性别女”的身份。顺性别的定义是:gender与assigned sex相同。跨性别女在将自己与生理女区分的时候,默认了生理女性全盘接受了自己社会性别。恰恰相反,女权主义者在以实际行动拒绝“实践性别”(doing gender):不化妆、不穿会令行动不便的裙子、剃头——事实上,没有人真正承认过自己的社会性别。我是女性是因为客观的生理构造(依照目前科学给出的定义),并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成为”女性,也不需要主观上的认同。
先将非二元性别放在一边,因为很多跨性别人士也并没有持此观点,一部分男跨女只是希望社会承认他们是女性,并参与到女性的话语讨论中。在他们眼里,不仅生理性别是二分的,社会性别也是二分的,且社会性别凌驾于生理性别。反对TERF的人总是质疑她们所说的生理性别是否二分,却完全忽略了“男跨女”、“女跨男”这种词汇本身已经默认了男与女是对立且完全不同的两个性别。
在我了解到的跨性别人士的心路历程中,很多人都在以刻板印象定义自己的性别,并向往改变自己的生理性别。例如从小喜欢玩洋娃娃等女孩的喜好、性格和行为举止被说“娘”、向往女性的美感等,这些原本就是社会强加于女性的特质,构成了他们对女性的想象。他们不认为男性也可以留长发、化妆打扮、性格文静,却认为只有改变了生理性别才可以合理地进行这些行为,在我看来是非常遗憾的。这是父权制对男女的规训对他们进行的迫害,他们通过改变自己的身体默认了这种迫害,并进一步强化了它。他们通过刻板印象对自己原来的性别产生不认同,对另一个性别产生认同,这种认同本身就是过于主观的。在这里提到的都是社会性别,完全不涉及生理性别。如果一个人因为自己的生理特征对assigned sex产生了质疑,确实是值得讨论的,但上述例子完全不是这样。以上观察并不代表全部跨性别人士,但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并且这些观感来自一些主流的跨性别权益关注机构所呈现的内容,并不是被排跨者污名化后的二次解读。
再来谈谈多元性别。之前就说到,gender是一个光谱,一边是男性气质一边是女性气质,这当然可以说是多元的,甚至不需要被贴任何标签。但是如果说生理性别是多元的,甚至是可以被消解的,就非常值得警惕了。
激进女权认为,父权制建立在对女性的生育价值与性价值的剥削上。目前国内女权关注的核心议题,例如性骚扰、职场歧视、离婚冷静期,都与这两者、尤其是前者无法分离。如果说性欲是被构建的(基进女权论述过女异性恋的性欲是政治的,而非天生的;我认为男性的性欲也是如此),也可以被消解,那么男女在生育功能上的差异是不能被消解、也不能被忽视的。如果男性有一天也可以用子宫生育,那么性别确实可以被消解,激进女权理论的语境也会被完全瓦解。但在此之前,任何消解生理性别的意图都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有人认为女性的弱势来自于生育成本,拥有子宫这个生理构造造成了女性的弱势地位,所以消解了性别就可以达成性别平等,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理解。女性拥有孕育生命的功能,本身是一项能力,而不是劣势,只有在父权社会的统治下拥有子宫才成为了一种“负担”。这本身是引人深思的一点。在没有用科学手段消除生育功能差别的情况下,消解性别等同于将女性对自己子宫的话语权剥夺了。另外,名义上的称呼不应在社会现实未改变的情况下直接改变。在大部分女性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实践性别(do gender)的情况下,女权主义者拒绝社会性别只是一种刚刚开始的努力,而不是一种普遍现象。比如现在走在街上,还是可以凭外表轻易区分出生理男性和女性,强奸犯、随机杀人犯也会因此选择目标,直接否定生理性别的存在为时过早,过于乐观,反而会将已经建立起来的反抗话语一并消解。
国内激进女权虽然反婚反育,但不意味着忽视了自己是一个有子宫的女性。也正是因为有子宫这个事实,反婚反育才会成为一种需要坚持的选项,而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选择。6b4t对于性欲、爱情的解构,本质上都是在解除父权社会对女与男的绑定,而这种绑定最初存在的原因就是父权社会对女性生育功能的觊觎。
当然,目前科学定义下的女性生理特征不止有子宫,还有染色体、性激素、性征等。有人也会提出双性人的存在,来反驳binary sex的合理性。我个人认为除了生育功能以外的性特征或许是有分布性的,而不是严格二分的,且科学研究也是有主观导向性的,对此我保留疑问。并且跨性别女通过手术和激素注射,确实能获得一部分的女性生理的外表上的特征。当跨性别女的外表和打扮接近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女性时,确实存在遭遇强奸、性骚扰等男性对女性的特定暴力行为的风险。如果TA们的身份证上的性别也改为了女性,确实也会遇到教育、职场资源的倾斜。在这个意义上,跨性别女也应该作为女性参与女权议题的探讨。
因此我个人的观点是,当一个跨性别女进行了变性手术(放弃了供精能力)、改变了官方证件上的性别,应该被社会承认为女性。与此同时,女权主义者在某些具体话题上,尤其是婚育话题,应当保留对“经血姊妹”的门槛,即只接受有子宫的女性参与讨论,不该被视作对跨性别群体的恶意。但如果是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改变,或仅仅是注射激素,且声称自己为女性,则不应该被接受,否则生理性别将没有任何意义。
Snoopy: 这里你提到因为传统意义上女性外表而受到男性性暴力、身份证上女性性别标记导致的系统性性别歧视实际上都是在社会性别范畴去讨论女性身份的,我是认可的。而实际情况是,目前在医疗手段获取和身份证变更等方面的法规相当严苛,导致许多想要通过性别肯定手术(gender affirmative surgery)等医学手段成为法定意义上的女性的跨性别者(注意并不是所有跨性别女性都想要或需要这样做,因为医疗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想要完成你上述所说的这些准入门槛难如登天。而对医学手段进行等级划分,比如只注射激素不能被接受只有手术后才可,在我看来是谬误的。激素注射一定时间年限后,所谓的“供精能力”便可能丧失(当然我并不是认为没有供精能力就是女性了,我反对的就是这种生理决定论的性别认识,更不认为应当将生育能力视为性别划分的唯一准绳),更不存在所谓的“试行男性性暴力”,相当一部分跨性别女性是厌恶生殖器的,这些顺性别女性的担忧虽然可以理解,但我认为是出于不了解和因为本质化生理性别导致的恐惧和排斥。生理性别并非没有意义,但其意义来自社会建构。
Becky: 我不明白在男女生育功能有明显差异的情况下,生理性别的意义为何是社会构建的?上文中我不是在讨论男人如何才能成为女人,这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在我看来男人在无法改变生育功能的情况下没有必要成为女人,变性手术本身就不应该存在——正如Snoopy所说,其余的意义都是社会构建的。目前的所谓变性手术,除了消除生育功能,其余都是整形手术罢了。乳房是哺乳器官,放硅胶进去只是改变外观;阴道是产道,做一个阴道出来只是能够进行纳入式性行为。
但是目前社会性别还没有被解构。虽然生理女是无意识或被迫在do gender,男跨女是自愿do gender,但我愿意承认二者都在社会性别为女的情况下确实遭遇了相同的压迫。因此以我个人的想法,在谈论女权时,可以接受承认一部分男跨女确实为女。上述的划分不是一个标准,而是一个底线。超越了这个底线,如果一个因为恋童而被化学阉割(相当于注射激素)的男性因为失去了供精能力就被称作女性,那么不如取消男女的称呼。激进女权认为目前无法取消二元化的性别称呼是因为1)生育差别无法消除,2)根据社会性别产生的打压和犯罪仍然普遍。但如果跨性别人士的支持者们认为性别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为何又执着于让女性承认男跨女为女呢?
凉:作为社会建构论的支持者,作为跨性别人士权利的支持者,作为酷儿,并非是认为性别没有任何意义!相反,正是认识到生理与社会性别本身作为历史构建与其携带的社会意义,与对个体的持续不断的规训,所以在努力挑战性别作为历史范畴被固定下来的意义!同时,承认并同时试图创造更多元的性别形式,并对其未来所有可能形成的新形式与社会意义保持开放的态度!我们反对男性气质才能表达所谓男性,(反对)女性气质才能表达所谓女性的二元规训权力体系,我们反对以性器官作为最本质的性别区分形式,同时我们也反对性器官的快感作为性快感最为中心的形式,而不断地试图挑战、撬开、打破这些被确定为牢不可破、被认知为自然、被塑造为正统的身份范畴,探索更多元的生活可能。

如何理解TERF的核心议程?
Becky:国内对于“具体议题”的讨论并不是很多,主要还是对sex和gender的讨论以及关注西方的新闻。国内的女权人士对例如厕所、体育赛事等问题并没有产生一个可以被观察到的共识,毕竟这类政策的改变在中国是很困难的。
一定要说厕所问题的话,我个人的想法是,厕所本身就是依据生理特征(尿道结构)划分的,男女厕的设施有所不同。之前国内行动派女权发起的“占领男厕所”,提出的诉求也是因为生理特征导致如厕时间不同,希望建立更多女厕所。厕所隔间都是封闭的,隐私性较好,身份认同在这里不是重要因素。但如果一个男性在没有改变自己的生理特征的情况下,因为声称或认同自己是女性就进入女厕所,我认为没有任何合理性可言。如果一个男性去男厕所会造成“心理负担”,那么他应该以心理治疗的方式解决这种问题,而不是挤占女性的资源。
至于更衣室一类更没有隐私性、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生理男性对女性的潜在威胁确实不应该归于跨性别女(前提是真的改变了重要的生理特征,而不是声称)对女性的威胁。但如果开放了相关措施,任何人只要“认同”自己是女性就可以进入属于女性的single-sex space,带来的安全隐患最后还是女性买单。这种问题不是女性臆想出来的,而是有犯罪率佐证的,又该如何解决呢?
Snoopy:我认为TERF某种意义上也是议题导向的,其中最为显著的自然是对跨性别者进入女性空间(如卫生间、更衣室等)的不加分辨的排斥。在这样的脱离实际体验和语境的话语里,出生时指派性别为男性的跨性别女性和非二元人士被再次定位为男性以及潜在的潜在的性侵害者。生殖器、欲望、性取向、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在TERF的话语里被本质化地理解,这不仅忽略了多样化的跨性别主体经验,也混淆了一部分非跨人士的违法犯罪行为与作为性别身份的整个跨性别群体。当然这些议题其实并不是完全无解的死胡同,我所接触到的一些跨性别人士也在积极地思考如何推动单一化性别空间的政策倡导,从而服务于不同的个体需求,如孕妇、残障人士、儿童等。在这些议题的背后,狭隘的排斥主义和借助“科学”话语但又缺乏基本的对性别物质性和建构性了解的极端性别本质主义的幽灵实际上更需要我们的警觉。
之所以说是议题导向,因为我认为TERF作为女性主义流派实际上并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其对生理性别二元论述的依赖实际上在医学上也站不住脚,在社会意义上又否定个体的独特生命体验。“科学”的话语是TERF话语中常常倚重的概念工具,科学的政治性在此就不多加论述了,但是借助科学话语TERF在诸如跨性别体育运动参与等问题上试图获取对女性的定义霸权。英国TERF对于女性的定义和想象还被批判为是白人中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比起一种女权主义流派,我认为TERF还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基于科学知识权力话语的排外主义。
凉:TERF拒绝将跨性别女性纳入女性的范畴,并进入拒绝她们进入女性的空间。卫生间的划分与使用,确实是一个最常被讨论的问题。由拉康提出和被无数后拉康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论辩的尿道分离法则(Laws of Urinary Segregation),本身就是二元性别化的体系物质化进入现实生活的结果。标识为男的空间,仅由生理性别男性进入,而标识为女的场域,则仅由女性使用。同时在另一方面,当我们意欲挑战语言与现实勾连起的传统性别秩序的管控时,卫生间本身构成一个重要的场所。当然,我本身会更加支持多元性别友好的卫生间的建立,而非像现有男女的绝对划分与分离。

作为对当前TERF话语/观点的回应,你如何看待当前跨性别权利与性与性别少数运动之间的关系?你如何展望一个更具进步性的性/别运动?
Snoopy: 我与跨性别活动人士的交流中发现,跨性别群体对于TERF的认识程度和态度也是多元的,大部分跨性别者对于TERF可能只有朴素的认知甚至并不了解,而一部分跨性别女权主义者也指出,TERF与跨性别之间的冲突本质是一个弱势群体对另一个更弱势群体对其仍未获得的权利平等可能产生的威胁的一种想象。这种想象的致命之处在于有意无意忽略了房间里的大象,即处于压迫结构中心之处的父权制度和异性恋正统主义。因此对于我来说,一个progressive(进步的)的性与性别少数群体的运动一定是求同存异的,容忍不同的论述,而把将性/别桎梏清除、让性别不再是区分彼此的藩篱作为最终目标而努力。
Becky:“一个弱势群体与另一个弱势群体”这个表述让人误以为女权主义者和跨性别人士在进行一场零和游戏的争夺,而父权渔翁得利。激进女权的理论全部建立在对父权制的批评上,怎会将父权制视为房间里的大象?
求同存异是一种运动中的策略,其舍弃与获得的多少只有当事人才有资格判断。例如国内的女同性恋群体,在观察到台湾LGBT团体推动同婚合法后紧接着试图推动代孕合法的举动之后,有意与男同性恋解绑,以L的名义发出自己的声音。此外,如果从具体议题来看,即使排跨女权不承认一个“女性化”打扮的跨性别女可以算作女性,在发生值得广泛关注的性骚扰案件时,两者的利益还是客观上绑定在一起的。任何抗争中最主要的力量都是出于人对自身权益的维护,而不是出于所谓弱势群体之间的共情和关怀。相反,如果“求同”求到放弃了对生理性别的坚持,消解了女权运动已经建立起来的话语,反而得不偿失。(例如,声称自己是女性或非二元性别的生理男性对其他女性进行的性犯罪,就不是性别问题了吗?我们可以直接通过想象多元性别,否认目前社会中性别问题的存在吗?)
另外,跨性别究竟是对父权社会的挑战,还是对刻板印象的服从和放大,仍然值得质疑。如果说在保留对生育功能的二分化的事实尊重的基础上,消解性别是一种进步,那么很多跨性别者因为社会性别而厌恶自身生理性别的本末倒置就另当别论了。在这里我不想干预或评论他们对自己身体进行改变这个选择,而是认为社会应该正常化与本身性别“不符”的行为,鼓励男生可以喜欢粉色、女生可以不温柔娴静,从这个角度解决他们心理的困惑,而不是鼓励他们去改变自己的身体来适应父权社会的规则。否则不免有种父权社会在清除异己的嫌疑——父权社会要求男性刚强、好胜、不花时间打扮、不产生充沛的感情以维持经济、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对于做不到这些的男性,与其打破或放低这些要求,不如将他们“驱逐”入女性的队伍,以维持性别规则。
Snoopy: 我认为在中国的语境下,从各方面来看社会都没有鼓励改变身体来选择性别,或者将不符合的“男性”“驱逐”入女性队伍。相反,社会通过政策法规、刻板的性别文化等等结构性力量在压制和惩罚身体和性别的改变。性别更不是二元的两列队伍,可以通过选择站位轻易变更。既要认识到个体在追求自我认同的身份和生活方式的道路上遭遇的结构远比能动复杂和强大,同时作为一种性别身份的跨性别不能简单地用挑战父权或者服从刻板这两个标准来进行是非判断论功行赏。这种对包括跨性别在内的性与性别少数的经验进行submission(顺从)/resistance(抵抗)的二元化思考不仅是僵化的而且是一种认识论暴力(epistemic violence)。跨性别的经验和身份是极其复杂多元的,这种多元的个体实践本身并没有办法天然地承载抵抗性的力量,但多元的存在可能可以指示一条包容性的前路。
最后想说的是,目前TERF话语中所想象的跨性别,是刻板而偏僻的,也并没有考量跨性别和跨性别运动的现实情况和有限条件。这也是我为什么认为TERF是不同女权主义流派之间有点阳春白雪的讨论,而跨性别的视角则几乎失声。跨性别个体,以及跨性别作为一个movement,TA们所面临的并不是可供任性选择的性别光谱可以随意宣称自己是某个性别身份,而是具体的复杂的生命体验和非常限缩的经济、政策、社会和文化空间。在有限的空间里面挣扎出一条勉强可得的道路。TA中许多人也告诉我性别也不是最为重要的关切,而是经济负担、校园职场霸凌、精神健康状况等。脱离了这些现实和物质性的考量,TERF借助很难站得住脚的本质主义论调去认定完成何种程度医学身体变更的跨性别女性才能被承认为女性是不妥当的。
凉:首先在这里,我想强调本土知识(indigenous knowledge)生产的重要性。这意味着,对于跨儿群体真正的生命体验的关注。对于跨儿群体本身,不应该抱有一种刻板印象式的态度,将其视为一个同一的稳固身份认同。事实上,正如Snoopy所强调的,TA们的主体性与经验是异质的且多样的。更重要地,要在跨儿们的个体与社群之内,去观照他们的性与性别意识,去探索从跨儿群体出发的一个更加多元且自由的性别光谱。其次,作为一个酷儿,所期待与想象的是去中心化的非二元性别体系。基于性别、性相差异产生的歧视、暴力与种种不平等都被消除。所有人都能真正地拥有性/别自由,而非在传统的性别规范下,被强制地按照指派的性别,在异性恋中心的规训下压抑难捱。这所有个体都能够自在地生活,而不必担心因为性别与性相的差异会遭受任何形式的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