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资本手中的)算法不会解放工人——反驳FT中文网刘远举一文

文|小新
最近,搜狐新闻旗下极昼工作室发布了一篇报道,采访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陈龙,请他聊了聊算法与平台经济中的劳动控制。在当下中国数字经济被发展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的话语主导的情况下,这本是从普通劳动者角度对这种发展方式的难得的清醒反思,是帮助坚守各个岗位的劳动者理解自身处境的一个好机会。但是即便是如此温和的反思,也引来了一些人的不满,FT中文网近日发表的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刘远举研究员的《算法、劳动力与劳动:兼与陈龙博士商榷》一文(以下称“刘文”)便是其中之一。

简单来说,陈龙的研究是关于平台企业中,资本如何利用算法进行劳动控制的,他的论述基本上围绕劳动过程展开,这是劳工社会学再经典不过的命题。他的观点也简单明了,一方面,相比传统工作场所中肉眼可见的管理团队在办公室或车间实行管理,平台劳动体制下,算法和消费者成为了表面上的“管理者”,而平台资本虽然是实际上的控制者但却吊诡地“隐身”,甚至在一些时候充当消费者与骑手矛盾看似公正的调停者;另一方面,平台公司所采用的算法是以机器学习技术为基础的,这就意味着平台公司可以通过收集、分析外卖业务开展过程中,来自骑手、商家、消费者等多方数据,按着利润最大化的原则,不断更新和“优化”算法机制,从而“优化管理”,达到不断缩短配送时间的效果。陈龙认为,与传统工作场所的管理方式相比,这种基于算法的、不断自我生产和更新(self-generating and self-updating)的管理方式可以削弱骑手的反抗意愿,蚕食其自主空间,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到对自身的苛刻管理当中。
刘文虽然题为商榷,但一上来就通过咬文嚼字、偷换概念的方式,给陈龙的论文扣上了“同意反复”、“缺乏洞见,以学术迎合庸常,反而误导了社会”的大帽子。通读下来,用很多网友的话来说,刘文“思路清奇”,不值一驳。但刘文如有任何可取之处,那便是在于,相比陈龙的论文聚焦微观的劳动过程,刘文把视野扩大到了平台经济在整体经济发展中的位置,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本身很重要,是值得讨论和澄清的。此外,作者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所有关于资本的批判性思考的污名化,虽然很常见但危害性极强,这样的观点有FT中文网这样的主流媒体为其提供发声平台更是令人担忧,亟需反驳,以正视听。
是算法让工人变得更自由,还是对“自由”的追求让平台得以壮大?
刘文广受网友诟病的一个观点是,当下很多骑手之所以会感觉到平台工作比较自由,是因为算法虽然在劳动过程中体现为对劳动者的高度控制,但同时也释放出了更多的人身自由。据此他认为算法解放了劳动者而不是加强了对其的控制。
为论证这一点,刘文引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力(labour power)和实际凝结在所生产产品中的劳动量(actualised labour)的区分。这个区分认为,资本家以一定的价格购买劳动者的一定量的劳动力,通常以劳动时间衡量,但在不同的生产安排和管理方式下,劳动者在特定的时间内能提供的劳动量是不同的,可能有很大的差别。在刘看来,算法的精妙之处正在于大大提高了生产和管理效率,进而提高了资本在单位时间内从劳动者身上提取劳动的效率。他认为,这一效率的提高,在两个方面解放了劳动者:一方面,它减少了劳动过程中对劳动者人身自由的约束;另一方面,在单位劳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它使得骑手只需要花更少的时间,就可以获得在非算法的劳动条件下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赚到的报酬,劳动时间的缩短让劳动者的人身自由得到解放。
首先,算法提高了资本在单位时间内从劳动者身上提取劳动的效率吗?这涉及如何定义劳动时间的问题。从刘的行文中不难看出,他把劳动时间等同于工人执行生产劳动的时间,而不包括工作间隙的休息、上下班通勤或其他完成某项工作所必须的时间。在一个工厂里,这是工人在流水线上从事组装工作的时间,在骑手那里,这是从系统接收到消费者下单到骑手在系统里确认订单送达为止,至于订单与订单之间的等待时间,以及骑手为满足其生存所必须的休息、吃饭等时间,对于作者而言并不算劳动时间。但是我们知道,无论是我国的劳动法规,还是世界通行的标准,工作时间都不限于作业时间,还包括准备工作时间、结束工作时间以及法定非劳动消耗时间。也正因此,午餐、午休时间才应该被算计入工时,上下班路上通勤过程中手上才会被认定为工伤 。
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算法是否提高劳动生产率真的就需要打上一个问号。就笔者了解较多的网约车行业而言,经常司机师傅是一天接十几二十个单,有一半的时间在路上,一半的时间在等下一个客人,很多原本开出租现在转网约车的司机师傅认为,同样的单量他们的工作时间实际上是延长的。算法确实提高了资本提取剩余价值的效率,但这效率不是——起码不完全是——通过提高生产和管理效率实现的,相反, 基于算法的生产安排将本应由资本从劳动者手中购买的劳动时间和准备时间,转嫁给骑手,让其无偿提供这部分劳动时间,由此来提高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效率。
其次,算法减少了劳动过程中的对劳动者人身自由的约束吗?为了论证这一点,作者将算法与奴隶制、泰勒制、国企的劳动体制作比较,认为相比于之前的这些劳动体制,算法因为技术进步,从劳动力提取劳动的效率进一步提升,所以很多工作要求的人身自由更少了,作者举的例子是在家办公、骑手和网约车司机。这乍看没什么问题,但只要稍微想一下,就会发现作者故意忽略了不同行业的生产过程本身的差异性。这里作者暗含的比较是奴隶制时期的农场庄园、泰勒制下的制造业工厂和算法劳动体制下的骑手、网约车司机和白领工作之间的比较,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生产过程本身就非常不同,没有算法的时候,餐厅服务员的工作在很多方面也比工厂工作来的更“自由”,这种比较本身就没有什么意义。更有意义的反而是没有算法时的骑手和有了算法的骑手的劳动过程中的控制,这两者哪个控制更多,我想无需赘言。制造业的情况更是如此。自9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已经在不断引进和更新管理软件对员工进行“科学管理”(例如严格控制离岗时间,包括吃饭午休、甚至上厕所的时间),可以说是算法的前身。我国近年来也有类似的发展,珠三角地区的服装业、LED产业和汽车产业在近十几年来都经历了一个向“精益生产” 、“升级”的过程,其过程多采用信息技术,而研究者发现,伴随着产业升级的是对劳动过程的更严格的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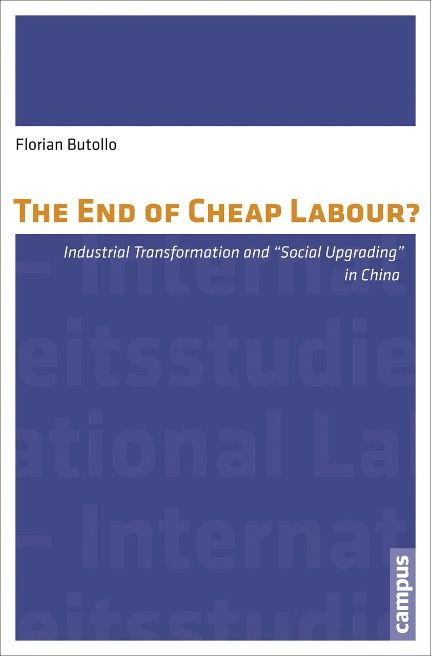
再次,算法会提高平台工人时薪从而减少其工作时间吗?作者认为算法提高效率进而可以提高骑手的时薪,这一点也并不能站住脚,前面说过这是基于对工人作业时间和工作时间的混淆。即便把这个混淆放一边,生产效率提高会提高劳动者的时薪这一论断成立的前提,如作者所言是单位劳动的价格不变。而事实上,因为资本对利润的无限渴求,生产效率的提高反而往往会导致劳动者的单位劳动价格的下降和劳动时间的增加;此外,单位劳动价格的变化还受到一系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劳动力供给。事实上,无论是美团、饿了么还是滴滴,在其短暂的发展过程中都曾数次降低骑手送单的单价,这构成了很多骑手、网约车司机抗争的原因。
所以算法一方面加强了劳动过程中的控制,另一方面也不会减少工人的劳动时间,又何谈“解放”工人呢?
如果不是算法让工人获得更多自由,那应该如何理解骑手所说的“自由”和围绕算法产生的新生产组织和管理模式之间的关系呢?多数事物社之前就这个问题,曾基于对网约车司机的调查做过连续的讨论。简单总结,虽然算法加强了劳动过程中的劳动控制,平台工人还是感受到了自由,但这并不是工作时间的缩短和在工作过程中拥有更多的人身自由,他们感受到的自由更多的是免于(freedom from)之前在工厂、建筑工地、饭店等工作场所中感受到的种种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限制(如很难请假),而不是平台劳动体制给了他们多大的自由来(freedom to)实现工作自主。实际上,很多骑手都表达过对算法和平台限制的不满,尤其是由于平台对送餐时间的不断压缩所带来的道路上的人身安全威胁,以及平台算法对骑手劳动过程进行的全方位的监控、限制,和一旦未能完成平台规定所带来的罚款和其他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讲,平台对工人的人身和劳动控制确实与传统的工作场所不同,但并不必然减少。
相反,平台经济之所以可以迅速在中国崛起,除了政府的支持和资本在拓展市场的时候大量烧钱之外,一个庞大而稳定的劳动力队伍(reserve army of labour)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之所以平台经济在疯狂补贴和价格战后还能够持续不断地吸引和留住工人,与他们在平台经济中可以免受传统工作场所中本就不合理、不合法的种种限制密切相关。在这个意义上,平台经济的成功和持续发展的动力,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大量劳动力“被剩余”的前提下,对这种“自由”的商品化的。
算法或信息技术反而增加了工人的权利吗?
刘文的另一个饱受争议的观点是,信息技术的使用增加了企业管理能力,但从未增加企业的管理权力,因为作者认为权利是由权力决定的,而与资本无关,所以资本也无法从信息技术的使用中获得权利。而工人的博弈权利则不降反升,作者的理由是,骑手的工作之所以得到比农民工、建筑工更多的媒体关注,是因为它是互联网产业,而媒体关注的增加了工人的博弈权利,因此他认为,技术的使用反而是为工人赋权的。
按照作者的逻辑,这里的权力应该是国家权力,是权利的唯一来源;资本不掌握国家权力,所以也无法决定自己的权利;但吊诡的是,作者认为媒体的关注可以增加工人的博弈权利,如果国家权力是权利的唯一来源,难道作者认为,媒体是国家权力机关的一部分吗?那这么多年,中国媒体的市场化进程、文化经济的发展和权力机关试图保持文化领导权的努力可都一笔勾销了。这种逻辑谬误的背后,不难看出作者的屁股坐在哪里。我们需要重申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资本当然是权力。这里根本不需要长篇大论的论述,只需要想想为什么那么多的产业工人和白领“社畜”被工厂和公司逼得不得不加班就能明白一二。
回到算法与工人的权利上来看,算法和技术本来都是可以为解决特定的问题服务的,它可以设计成不同的样子,用来解决不同的问题。陈龙的研究已经让我们看到,在平台经济中,算法或信息技术的使用更多的时候是掌握在资本家手里、为资本家的市场竞争和利润最大化服务的。工人当然可以砸烂机器或学习并试图超越算法,但机器学习的强大之处正在于它和它背后的数据分析师和程序员们可以不断地学习工人如何试图超越,并迅速作出反应。在这个意义上,如陈龙所揭示的,在微观的劳动过程里,算法不仅通过自身的设计限制工人权利而扩大管理人员(和资本)的权利,它也压缩了工人的协商和反抗空间。

在劳工权力和劳动保护方面,前面提到,平台经济在中国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政府政策对平台经济从市场准入、审批、用工、用地、融资、金融化等各方面的去管制化,这背后固然有应对08年前后不断发酵的经济危机的考虑,但推动去管制化、鼓励金融资本在各个领域迅速攻城掠地从而推高经济增长的数字只是应对危机的一种方式,是一种政策的选择。这个选择是以劳工权力为代价的。事实上,08年《劳动法》修订之后,面对制造业、建筑行业日益恶化的阶级矛盾,政府颇有一段时间在这两个行业内大力推动工人社保、规范合同,学者研究也显示这一动作效果显著,很多人也是在这段时间慢慢亲身体会到社保的好处,开始有劳动权力的意识。甚至美团刚刚开始开拓市场的时候,都以雇佣关系去处理自己与骑手的关系,骑手得以享受最低工资和社保。反而是其在扩张的过程中,为了降低用工成本,才慢慢采用“众包”和“分包”的形式,疯狂地以侵害劳动者权力为代价降低运营成本,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出于就业的考量并没有出面制止,如此发展下去,日积月累才导致了今天骑手合同和社保福利“裸奔”的局面。虽然近两年,互联网经济发展异常宽松的政策环境逐渐成为过去,政府已经开始探索如何规制日渐庞大的互联网企业,但目前为止动作更大的仍然集中在互联网金融和电子商务领域的反垄断,其背后的关注点是金融安全和消费者利益,而在庞大的平台劳工的权益上,讨论才刚刚开始且仅限于工伤保险;就目前已经出台的相关政策来看,众包骑手在南京等地出台的新规中众包骑手被一刀切地踢出劳动关系,广东骑手能不能上工伤保险要看公司“自愿”,在政策和国家制度的框架内,平台工人的劳动权益几为真空。 试问,这又要怎样曲解,才能解释成是“算法和技术增加了工人的权利”?
再退一步,从平台工人凝聚团结、进行抗争的可能性上来讲,算法使得对一个跨越了地理空间的、无形工作场所实施控制成为可能,很多研究指出,这大大增加了骑手个体化的程度,降低了骑手之间形成有意义的关系和联结的可能性,从而削弱了团结和抗争的基础。
至于作者提到的媒体关注,这当然有利于工人争取自己的权益;但因为现实中的劳动关系日益紧张,劳工权益一直都是中国媒体上主要的话题之一,所以平台劳工获得较多的媒体关注,并不是因为作者所言“与互联网有关”,更谈不上什么技术带来的“权利红利”。另一方面,更应该看到并不是有媒体曝光就意味着权利的增加。事实上,从媒体曝光到改变,往往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大公司会公关,政府会用自己的方式思考创造就业和GDP的问题。过去了一年,我们经历了《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刷爆朋友圈,经历了处长体验送外卖和北大博士后批评算法,但得到的是美团让消费者多等8分钟,是各地单价持续下降,干更多的活,挣更少的钱,是配送时间依然紧张,是外卖员自焚讨薪... 当然,这里还有媒体以什么样的方式曝光和呈现平台劳动者的问题,之前多数事务社派也有撰文讨论影视剧中的劳工形象,媒体对劳动剥削情况的呈现也并不总是真实和批判性的。
总而言之,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就目前的发展而言,都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算法或信息技术的使用“反而增加工人的权力”,相反的证据倒是很多。
批评算法加强了劳动控制是反对技术进步、抑制年轻人当骑手,从而让中国陷入严重就业与经济危机吗?
论述完算法是如何为平台工人赋权之后,刘文又在没有真正理解作者——和腾讯主办的论坛上呼吁大家反思外卖行业所谓“便利性”是否必要的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项飚——想说的东西的情况下,直接给两位的反思——后来这攻击面扩大到了整个社会学对资本和技术的批判性反思——贴上了“反市场”、“反对技术进步”、“抑制年轻人当骑手”的标签,随后给这种批评戴上了颇有民族主义煽动性意味的“让中国陷入严重的就业与经济危机”的大帽子。
将围绕劳动体制和技术进行的批判性反思扭曲为反市场、反技术进步和抑制生产发展并不稀奇。但是即便是马克思本人也不会想象一个生产和科技倒退、饿殍遍地的共产主义社会。批判的社会科学或更广泛的批判性思考之所以会对资本主义下的市场、技术和经济发展进行批判,往往是因为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架下的发展催生或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与剥削,批判的目的不是消灭市场、否定技术、放弃经济发展,而是让市场、技术和经济的发展真真正真为每个人服务;其目的不是回到原始社会,而是建立一个公平、平等、先进的社会。以对算法劳动体制的批判为例,批判的目的不是否定算法本身所带来的效率的提升,而是指出当前算法的设计和应用扩大了资本和劳动者权力之间的不平等,指出其原因,提出改善的方案。对外卖行业的聚焦也是如此,它必然不是要消灭外卖行业,而是希望去想象一个更好的外卖行业,而不是一个资本攫取利益而给社会留下巨大阶级矛盾的外卖行业。
同样的,这种批评也绝对不是要“让中国陷入严重的就业和经济危机”。事实上,真正让中国陷入严重的就业和经济危机的,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和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所揭示的那样,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避免的阶级矛盾和内在危机。这一点,过去40年的发展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恐怕即使中国有“社会主义遗产”,也难以幸免。
我们需要什么样关于发展的思考和论述?
因为工作的关系,笔者有时会阅读FT中文网的相关文章,也每每为编辑记者的分析和对事态发展的及时把握感到佩服,所以看到刘文时,笔者一度认为自己看错了。这篇文章也引发了不少人的气愤和哀叹,不少读者直接在网上爆粗口,一些人则感叹“怪不得今年五四青年人会如此愤怒”,直言“这就好像对那些‘内卷’得喘不上气的人说,卷是为了给你释放更大的空间”。
不过,笔者很快注意到,这并不是FT中文网第一次发表刘远举反驳批评平台经济的声音,去年9月,当《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刷屏朋友圈时,FT也发表了刘远举对此文的批判。从刘在FT专栏的文章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其从各个角度为平台做的一系列辩护工作。这些文章和刘的专栏之所以能发表出来,可见它代表了一些人的想法,在FT的目标读者群——知识和经济精英——中的有一定的市场。 虽然多数事务社先前的文章已经多次论及,但笔者认为还是值得在这里重申:今天中国的普通劳动者正处在一个由国家支持、高技术支撑的资进民退的过程,一个中国资本主义从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一个劳动被“降格”(downgraded)、劳动者权力和权益和工作的意义在方方面面遭到挤压的时间节点。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是更多个陈龙来对中国当下的发展与未来进行批判性地、深入的观察与反思。至于刘文及其代表的思潮,任何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媒体,都应该警惕;任何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读者,都应该看到要看到其背后的意识形态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