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升即走”制之下的悲剧

6月7日,39岁的复旦大学数学学院教师姜文华,持刀杀死本院书记王永珍。直接导火索是事发前几天,王代表单位通知姜,学院决定合同期满之后不再续聘,要求他即日办理离职手续。
事件发生后,国内的舆论两极分化:一派归咎于行凶者,或明或暗地强调此人心理有问题;另一派则认为这是不正常的机制所造成,“青椒”(青年教师)在“非升即走”制之下承受着过大的压力,被辞退只是压断骆驼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
耐人寻味的一点是:论战双方都援引美国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只不过,反方强调美国的大学远没有国内这样严酷的高淘汰率,可以人尽其才。一位据称是姜在美国留学时的室友就在论坛上发文说:
依我对他的有限了解,给他足够的时间和一张安静的书桌,他可能就是第二个陈景润,或者下一个张益唐。我们能不能查一查, 是陈景润还是张益唐在小姜这个年龄时比他出的论文多?他已经展现出出色才华,为什么不能多给他一点机会?各种各样的混混,塞满中国成千上万所高校和科研机构,为什么就不能挤开一条微缝让他栖身?又是什么事情把这样一个安静、羞涩、胆怯而单纯的人逼到无路可走,继而暴起杀人?他的性格多少有一些问题,可是我在美国见到过多个比他的性格更偏颇的人,他们却都工作顺利、生活幸福。什么时候,中国也能变成这样?
反过来,正方则强调,美国也有相似的例子:2010年,44岁的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分校生物学助理教授Amy Bishop在被拒绝授予终身教职(tenure)后,持枪造成三死三伤,死者包括其系主任。事发后,舆论普遍认为是行凶者自身的心理问题和认知偏差。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发生在中国的就不能是这样?

确实,“六年非升即走”这套制度起初就是从美国引进的,旨在避免高校人才工作安稳之后“混日子”,但就像很多国外的事物一样,一旦引入中国的环境,就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
本来,这么做的出发点可以说是好的,尤其教育、卫生是改开之后唯一未触动的两大领域,以往那种“单位体制”下的心态保留得最多。美国生物学家乔治·夏勒1984年来到中国,他后来回忆:“我在中国遇到的生物学家,大多年满五十岁就在心理上宣告退休,一心一意保护既得的地位,避免被年轻人夺走,尽量不引人注目,等着领退休金。”
然而,与此同时,这些年来像大学排名等机制,又促使管理者必须设法在短时间内提升绩效。此时,他身兼双重身份:既是贯彻教育政策的官员,又是一个推动业绩的CEO。
鉴于高校特殊的环境,很难骤然对老教授们采取新的考核机制,那这就势必造成一种双规制:有些老资格的可以没有论文项目压力,悠闲自得,但那些议价能力更低的青椒却不得不接受“非升即走”的劳动条件,实行“大进大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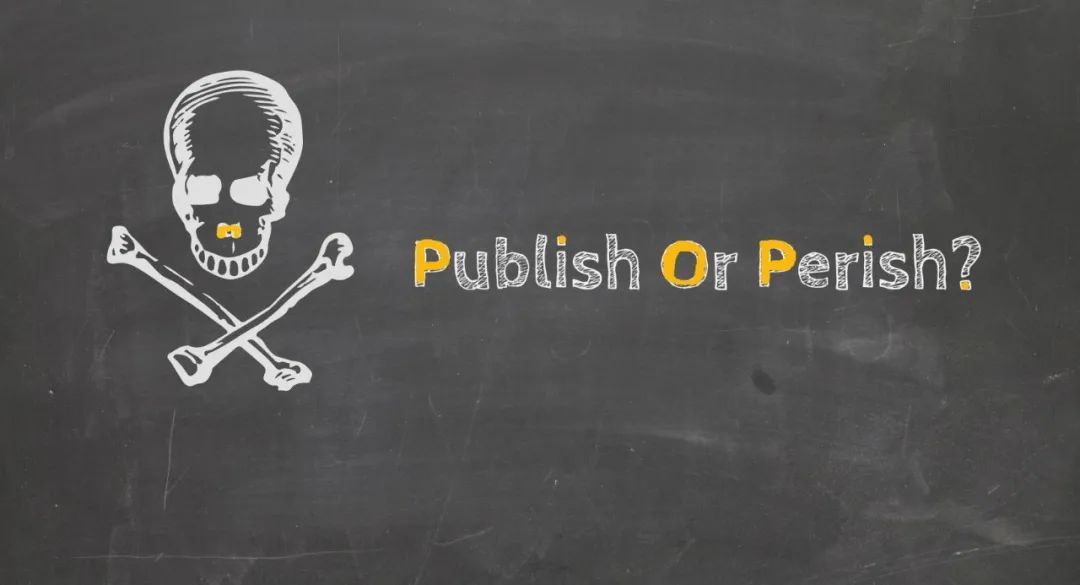
这样,青椒实际上是在缺乏保障的条件下,承受了大得多的压力。甚至除了基本科研能力外,还要强大的抗压能力、厚脸皮和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能力。自身就是青年学者的马华灵总结了一下:
青椒六年非升即走的压力:教学(新手需要大量时间备课)+科研(期刊以向大佬约稿为主,小讲师发论文太难了)+辅导员(通常带满一届4年)+行政(领导和大佬让你做事你不做吗)。青椒的家庭压力就不说了,三十好几的人上有老下有小,还在租房。
这些压力,设计这一机制的决策者只怕是不会考虑的,相反,他要的就是强大的压力迫使你不得不拼尽全力。这本身体现出一种把人工具化的倾向,和对人自治、自律的不信任,因为它潜在地假定:如果给你足够的安全感,那你就会混日子,唯有施加强大的外部压力,才能驱使你不遗余力地拼命工作。
反过来说,这一机制要能顺利运转,取决于三点:充足的人力(你不干,有的是人);有限的选择(尽管有压力,但你别无选择);缺乏组织的个体(就算不满,你们无法联合)。
唯一的漏洞,就是绝望的个体可能走极端。 甚至这一点也不成大问题,因为如果真有人走极端了,那只要保证社会舆论相信,都是这些人自己心理病态就行了——毕竟做出这种事,一般多多少少确实在某些方面异于常人。

像这次的事一出来,就有人说:“合同到期不续聘,职场人士基本上都遇到过。在996福报企业里,合同不到期被解聘的工程师比比皆是。”这话的潜台词是:这些“都是正常的”,难道被辞退就要杀人?
我想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表面上的起因,而在于背后有没有一套良性机制支撑。如果你所在的行业里,能让你重新开始的机会很多,辞退时做法规范、赔偿也很丰厚,那你接受起来也就不那么难了。反过来,假如对你而言,前期投入了巨大的心力,你也没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但最终不但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且你又别无出路,那这就是毁灭性的打击。
更何况,有时你还会赫然发现,这套机制本身就未必是公平合理的。像“末位淘汰制”原本也源自美国,著名企业家杰克·韦尔奇以此来激发良性的内部活力,然而在引入国内后,且不说被淘汰者缺乏保障、没有尊严,而且他们被列入淘汰清单的原因往往只是因为不会搞关系、不被上面所喜欢而已。换言之,这竟有可能蜕变为清除异类、激发效忠的极好借口。
我刚入行实习时,有同事因为掉了客户,当即被辞退,并且是从会议室谈完出来,HR看着他收拾东西立刻离开,不许再动电脑,带走任何资料。这对我是名副其实的文化震撼。看到我的神情,公司的HR总监后来还私下跟我慨叹:“我以前在国营单位,那时要辞退一个人,得费多少口舌啊,还有人一哭二闹三上吊,不断来吵闹的,要做无数工作。外资企业真是冷酷无情。”
听她这一说,我反倒意识到一点:人们之所以能平静地接受这一点,是需要一系列条件的,包括事先的知情同意、规范的流程、合理的赔偿,以及有选择的退路。因此,任何文化移植都不是孤立的,你可以引入某个理念、做法,但却没办法把支撑它们的一整套社会机制都搬过来。

国内在引入这些机制时,往往只看到它达成的结果在管理上是好的,却很少在意它配套的程序,更别提复杂长期的社会机制建设了,在现实中,这实际上意味着个体要默默消化制度缺失带来的种种酸楚。
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长久生活在一个封闭、稳定的圈子里,从来也没想过要离开,更无从想像失去眼下这一切会面临什么,也没有保障,那么很自然地,失业对他/她而言将是极大的恐惧。这就是为什么当年推动改革、让大批工人下岗时,上上下下做了那么多工作,否则鲁莽推行,那是要出事的。在历史上,更危险的是军人转业,他们丢了饭碗之后哗变,曾是许多事变的导火索。
张五常在评论姜文华事件时说,姜的学术生涯本来不错,如果在复旦教书不好,那让他去主持一些研讨班就是;即便不续聘,那上司也“应该在两三年前就给他信息,让他知道获取终身雇用合约的机会如何”。且不说纯数学研究的人很难找到出路,39岁“非升即走”比35岁程序员被大厂辞退惨烈多了,意味着他将很难再找到别的高校入职,可以设想,对姜来说,自己顿时就到了生死一线的绝路上。
说这些,不是要“同情凶手”,而是因为只有理解其处境,我们才能完善机制,避免悲剧再次发生。事后来看,这一悲剧看似是偶发的,但其实却内在于机制本身:它之所以能施加强大的压力驱使你内卷,就是因为看准你选择不多,此时一个人的抗压性几乎是无限的(想想看,疫情之下为了保住饭碗,一个人可以干两三倍的工作量,还不敢有怨言);但又因此,一旦人们幻灭,后果也将格外严重。
当然,机制再完善,或许都难免会出事,但如果机制本身就有问题,那出事的概率就高得多了。这未必是行凶杀人,也可能是绝望中自杀,又或是不断内卷后过劳死,但其背后的根源都是相同的:身在其中的个体没有退路,只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如果此人个性又容易钻牛角尖,那就更不易看到其它出路的可能性了。
不难看出,这里有一个矛盾的死结:正因缺乏选择,人们才不得不忍受;但一旦出了事,人们却又会惊诧为何出现这样的极端行为,仿佛你明明可以不这样。
造成这种困境的条件,“缺乏联合的个体”在短期内无法改变,“充足的人力”造成的“僧多粥少”说不定还将更严重,因而对个体来说,最现实的途径就是尽力让自己多几个选择。也只有当机制保障了人们有足够的选择权时,我们才能说,个人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因为你不是没有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