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包法利夫人》译本看许渊冲的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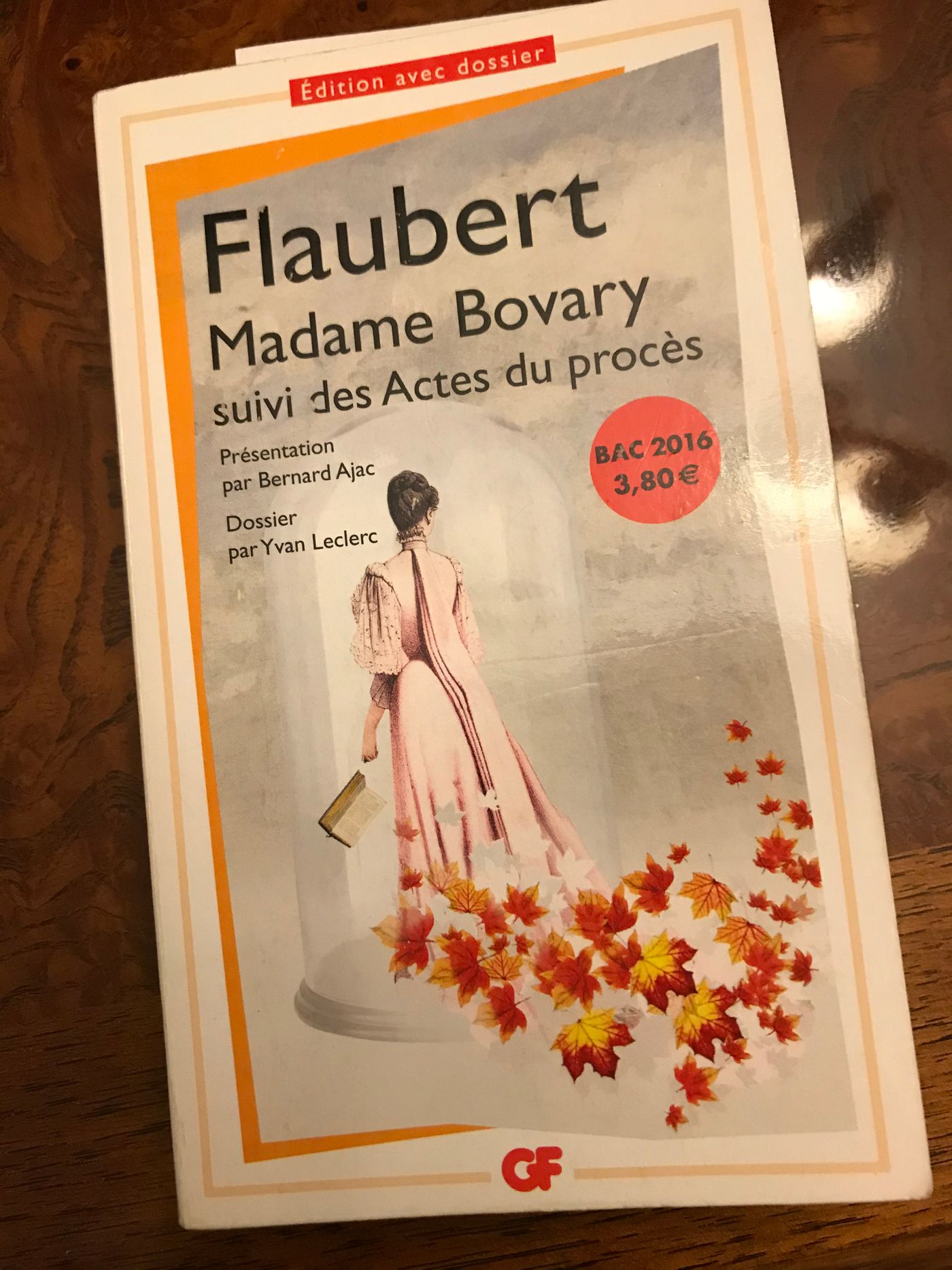
(注:中国大陆的翻译家许渊冲以100岁的高龄去世,官方媒体和民间对其翻译和翻译理念赞美有加。其实,许的翻译以及翻译理念以陈旧落伍和俗不可耐著称。不过,这种赞美倒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大陆的翻译何以烂译横行。瓦釜雷鸣的另一面必定是黄钟毁弃。与上述这一现象配套的是,完全是认真讨论文学翻译、讨论许渊冲的文章如本文两年前在中国大陆发表后遭封杀,现在重新发表又被遥遥无期地地审核难以发表。这种局面也可以很好地说明只有在讨论或辩论不能正常进行的环境中,许渊冲这样的学问半吊子才会被吹捧为大家和权威。本文将以具体的事实展示许渊冲的翻译如何不堪,以及他显然对什么是文学语言茫然无知。)
假如要挑选毫无争议的以文字精致而见长的世界文学杰作,那么,十九世纪法国小说家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必定属于其中的首选。
福楼拜以字斟句酌、推敲再三、刻画细微、呕心沥血的写作方式而广为人知并被传为美谈。他的作品多是靠精雕细凿、富有微妙暗示的细节描写取胜。
《包法利夫人》可以说是福楼拜的代表作,是他的写作方式的广告和样板。世界各国一代又一代的作家悉心研读它,试图从它那里汲取营养和启示。
在当今中国,《包法利夫人》的一个流行的译本出自许渊冲。
非常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许先生显然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他的乌龙翻译给读者造成了困惑。不懂法文的中国读者若想通过阅读他的翻译来鉴赏福楼拜的这部精致的作品会被误导,或无意中陷入难堪的境地。
毫无疑问,上面这段话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说法。按照已故的美国著名科学家、天文学家卡尔·萨根(1934 - 1996)的说法,非同寻常的说法需要有非同寻常的证据。否则,就是忽悠,就是欺诈,就是不负责任,不道德。
本文要提出的证据取自许先生翻译的《包法利夫人》第一章的一段文字。
这里需要声明的是,指出翻译的种种错误,目的不在于指出错误(但凡是翻译就难免有错,翻译错误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多少的问题,程度有多严重的问题),而在于通过翻译错误看到名著原文的精妙;假如读者不在乎名著原文的精妙,就大可不必在乎名著翻译的错误。这是阅读外国文学的一种辩证法。
为了方便法语专业的学者和学生参与讨论,本文附上了讨论所需的法文原文。但不懂法文的读者也可以参与这里的讨论,因为本文为讨论所需的法文材料提供了足够多的而且是足够忠实于原文的翻译。
***
文学名著的开头是作者用力最大的地方,也是最能体现作品特色、作者功力的地方。名著开头的翻译因此也是最能体现翻译者功力的地方。
但笔者多年来一直没来得及研究许渊冲的翻译。笔者对许先生的《包法利夫人》翻译的研究起始于友邻安提戈涅发表的非常有趣的文学鉴赏和批评文,其标题是《包法利的帽子》。
在其鉴赏和批评文中,在大学教授外国文学的安提戈涅从小说《包法利夫人》第一章的包法利的帽子的描写谈起,探讨了工于精雕细凿的细节描写的小说的现代性特征。
作为例证,安提戈涅引用了许渊冲翻译的《包法利夫人》第一章开始不久一个著名段落,那一段文字描写的是大龄小学生包法利的帽子。
顺便说一句,在《包法利夫人》第一章的开头,福楼拜描写的法国调皮捣蛋的学生在自习时偷懒,看到校长进来,“那些正在睡觉的人警醒了,每个人都直起腰来,好像是正在用功时受到意外的打扰”(Ceux qui dormaient se réveillèrent, et chacun se leva comme surpris dans son travail),这种描写大概会让许多中国读者不禁想起鲁迅在他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结尾时所描写的调皮的私塾学生。
以描写学生的调皮开头之后,福楼拜接着又描写了那些学生的一种约定俗成的调皮把戏,这就是,每次从外面一进教室就把帽子扔到地上,以便腾出双手;而且扔的时候还要把帽子用力摔到长凳下面,碰到墙壁,激起一片灰尘。
然后,就是那段包法利的帽子的描写。以下是安提戈涅所引用的许渊冲译文:
不知道这个新生是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一套,还是不敢跟大家一样做,做完课前的祷告之后,他仍把鸭舌帽放在膝盖上。他的帽子看不出到底是皮帽、军帽、圆顶帽、尖嘴帽还是睡帽,像是一盘大杂烩,反正是便宜货,说不出有多难看,好像哑巴吃了黄连后的苦脸。帽子是鸡蛋形的,里面用铁丝支撑着,帽口有三道滚边;往上是交错的菱形丝绒和兔皮,中间还有条红线隔开;再往上是口袋似的帽筒;帽顶是多边的硬壳纸,纸上蒙着十分复杂的彩绣,还有一根细长的饰带,末端吊着一个用金线结成的小十字架作为坠子的饰带。帽子是新的,帽沿还闪光呢。
***
安提戈涅在引用了上述的许渊冲翻译之后紧接着写道:
在这个著名的开篇片段里,引起最多兴趣的问题是“我们是谁”?这涉及到讲故事的人到底站在什么立场上描绘现场,...
安提戈涅在这里提了一个很有趣也很重要的问题,但非常不幸的是,假如对照原文,则可以说她提得文不对题,显得无的放矢。
作为中文读者,安提戈涅之所以陷入这种尴尬被动的境地,是因为她相信了许渊冲的粗率马虎的翻译,因而被许译所误导——查原文可知,在《包法利夫人》这个著名的第一章片段里,“我们”或“我们的”(法文nous,或nos)的字样并未出现。
为了让懂法文的读者可以进行认真的比较研究,不妨把这一段的法文原文抄在下面:
Mais, soit qu'il n'eût pas remarqué cette manoeuvre ou qu'il n'eut osé s'y soumettre, la prière était finie que le nouveau tenait encore sa casquette sur ses deux genoux. C'était une de ces coiffures d'ordre composite, où l'on retrouve les éléments du bonnet à poil, du chapska, du chapeau rond, de la casquette de loutre et du bonnet de coton, une de ces pauvres choses, enfin, dont la laideur muette a des profondeurs d'expression comme le visage d'un imbécile. Ovoïde et renflée de baleines, elle commençait par trois boudins circulaires; puis s'alternaient, séparés par une bande rouge, des losanges de velours et de poils de lapin; venait ensuite une façon de sac qui se terminait par un polygone cartonné, couvert d'une broderie en soutache compliquée, et d'où pendait, au bout d'un long cordon trop mince, un petit croisillon de fils d'or, en manière de gland. Elle était neuve; la visière brillait.
这一段话开头的第一句,严格遵循原文的翻译是:
然而,或许是他没注意到这一套(摔帽子的)把戏,或者他不敢这么玩,祷告结束了,这新生还是把帽子放在他的两膝上。
无论是读法语原文还是读严格遵循原文的翻译,读者都可以看到,福楼拜在这里并没有使用“我们”或“我们的”之类的字眼。
对精致的文学描写敏感的读者读这里的严格遵循原文的翻译可以还可以注意到一个更有趣的问题,这就是,福楼拜用“这新生还是把帽子放在他的两膝上”这种陈述,来展示头一天上学的包法利循规蹈矩、老实得令人感到可笑甚至可怜。
读到这句话,读者马上可以在心目中看到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画面——那个15岁的大龄小学高年级男孩正襟危坐,规规矩矩,两腿并拢,帽子一直放在他的两只膝盖上。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而法文原文在这里写得清清楚楚,le nouveau tenait encore sa casquette sur ses deux genoux,【这新生还是把帽子放在他的两膝上】。
但许渊冲的翻译却抹掉了这至关重要的细节,随随便便地翻译为【...放在膝盖上】。
读者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福楼拜的的文字精致精细、精准精确,许渊冲的翻译则粗糙粗疏,马马虎虎。
***
虽然不懂法文原文的人很难看出这种粗糙粗疏,但许渊冲的翻译太粗糙,以至于不懂法文的读者都可以明显地看出问题,至少是不由得感到生疑。
例如,“他的帽子...说不出有多难看,好像哑巴吃了黄连后的苦脸”。看到这种翻译,不懂法文的中国读者就难免要问:难道福楼拜或法国人也跟中国人一样有黄连最苦、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面相难看的观念和习惯说法吗?
换句话说,假如中国人看到一个意大利译者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翻译为“谁知盘中意大利通心粉,根根皆辛苦”,一定会感到可疑和可笑。
与此同时,一个不懂中文的意大利人读到这样的意大利文翻译也会坠入五里乃至五十里雾中,也不禁要问:莫非一千多年前意大利面就出口到了中国、中国人就开始吃起来啦?
很不幸的是,许渊冲的翻译与这个虚拟的意大利文翻译有异曲同工之(不)妙。
跟许渊冲翻译的“他的帽子...说不出有多难看,好像哑巴吃了黄连后的苦脸”对应的法文原文是,
... dont la laideur muette a des profondeurs d'expression comme le visage d'un imbécile.
严格遵循原文的翻译是:
那帽子的沉默的丑陋有一种犹如傻瓜面容的表情深度。
读法文原文或严格遵循原文的翻译可知,福楼拜在这里使用了一系列脱离常轨、标新立异的说法,并由此打造出一种非常奇异的形象/意象。
这是一种信息量很大、含金量很高、非常引人注目的说法,其中的每一个词、每一个词组都是明显的、甚至是炫耀性的、欢欣玩乐的匠心独运,而这正是认真的文学读者要特别感兴趣、要特别关心和关注的文学/文字艺术表现。
作为文学翻译,许渊冲将原文不同寻常的标新立异的说法偷梁换柱、改换为他自己所喜欢的中式陈词滥调,这应当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不称职、不合格、不专业、笨拙的做法。
这种以次充好、以俗代奇、挂羊头卖狗肉式的翻译实使正规的、严肃的文学讨论变得极其困难,甚至干脆不可能。
以这里的“那帽子的沉默的丑陋有一种犹如傻瓜面容的表情深度”为例,其中的“沉默的丑陋”,“傻瓜的面容”、“犹如傻瓜的面容”、“表情的深度”,这些意象每一个都是标新立异,令人惊讶,每一个都令人匪夷所思,令读者感觉耳目一新,感觉有许多话可说。
相比而言,“好像哑巴吃了黄连后的苦脸”则是中文世界的一种耳熟能详的俗套比喻的变体,类似于把“雪中送碳”改说成“大雪中获得薪炭时感觉到的身心温暖”,可以说毫无新意,而这种毫无新意的俗套比喻说法跟福楼拜的脱离常规标新立异的说法可谓南辕北辙,判若云泥。
换句话说,这种俗套说法跟福楼拜原文的说法完全是两码事,普通的读者根本就不可能由这种俗套的说法推导出或想得到福楼拜所要传达给他们的概念、形象或意境。由此可知,不称职的翻译不是有助于而是有损于中外文学的交流。
就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而言,翻译问题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无法绕过的问题,因为翻译问题跟外国文学文本的诠释直接相关——任何严肃的诠释必须是基于可靠的翻译,而不是错误的、不可靠的、或荒唐离谱的翻译。
因此,外国文学研讨必须有国际的眼光,文化交流的眼光,从事翻译和讲授翻译文学不能以中国特色为由来自拉自唱,不能将错误的翻译说成是合法的翻译,将挂羊头卖狗肉说成是狗肉就是羊肉,甚至比羊肉味道还好。否则,就必然闹出国际笑话,制造国际笑料。
很悲催的是,挂羊头卖狗肉而且声称狗肉即羊肉就是眼下中国的文学翻译惨不忍睹的现状。
***
在这段文字翻译中,许渊冲还有其他明显的翻译问题或错误。例如,“他的帽子...像是一盘大杂烩”,但原文并没有这么说。原文的说法是,C'était une de ces coiffures d'ordre composite,严格遵循原文的翻译是:
那帽子是一种由多种成分构成的复合体。
这里的问题是许渊冲把ordre composite翻译“大杂烩”。
众所周知,中文所谓的【大杂烩】是暗示乱七八糟的杂凑而成的东西。但我们由法文composite一词的同根词动词composer(写作文,作曲,组装配件构成一整体,...),名词composition(组成、结构、构造、建构、由部分构成整体的平衡的秩序)可以得知,composite的意思是【由井井有条的元素/部分组成的】,因此,将法文的ordre composite翻译为【大杂烩】是基于误解的误译。
如此指出许渊冲在这里的误译并不是小题大做,不是没事找事吹毛求疵揪住一个词大做文章,而是这种讨论涉及严肃和细致的文学研究和解读,这个词语在这里牵一发动全身,涉及作者福楼拜对整个小说的布局安排,涉及读者对整个小说的阅读理解。
读者必须时刻记住,福楼拜是精雕细凿的大师,他笔下的每个用词都是精心推敲、冥思苦想的结果;他在这里表面上是在描写包法利的帽子,但其实是在声东击西,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福楼拜使用ordre composite(由多种成分构成的复合体)这种措辞来来形容包法利的帽子,来暗示和预示包法利其人的未来发展,暗示包法利是一个井井有条的琐碎琐屑之人,无聊得令人发疯,他越是有条有理井井有条,他就越是让人、让可怜的包法利夫人发疯,让包法利夫人感到压抑得要死,感到有必要出轨才能透一口气。
实际上,在这一段里,我们已经看到了福楼拜为小说情节今后的发展所布下的草蛇灰线,而这种草蛇灰线就是福楼拜十分精心的遣词造句,其中包括ordre composite(由多种成分构成的复合体)。
因此,任何误译或脱离原文的翻译都会损害乃至破坏、毁坏原文的精妙。这就是为什么任何一个专业的、称职的文学翻译都会以小心谨慎的态度对待原文,十分忌讳脱离原文导致这种损害或毁坏。
非常悲催的是,中国的文学翻译界翻译标准很烂,很低,甚至没有标准,导致乱译和烂译横行,而且乱译和烂译常常被认为是汉语流畅地道,是文学翻译的正宗。这种翻译观和文学观其实是不懂文学也不懂翻译的人瞎掰。
文学的语言追求的是新奇,常常是流畅地道的反面。福楼拜在这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例子,无论是“那帽子是由多种成分构成的复合体”,还是“那帽子的沉默的丑陋有一种犹如傻瓜面容的表情深度”,它们的法文原文根本就不是流畅地道的日常语言,而是标新立异的语言。翻译把这种标新立异的语言改写成读者司空见惯的流畅地道的俗套话,实际上是佛头着粪,暴殄天物,是糟蹋好东西。
应当指出,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文学的误读,而是翻译的误读;翻译的误读是更为基础的、更为技术性的东西,这种误读影响或扭曲我们的基本阅读、理解、阐释。
翻译的误读常常是黑白分明的,总是不合法的(是公认的错误);文学的误读则常常是灰色的,对错难说的,甚至时常可以是合法的(是突破窠臼的创造性解读)。
***
关于《包法利夫人》开头的包法利的帽子的描写,似乎还可以进一步申说。
应当说,福楼拜费那么大的力气描写帽子,其实是“别有用心”,他写的是帽子,但心在别处,他只是拿帽子来当道具,用帽子来暗示,来作比喻,作暗喻,来暗示和暗指包法利其人——以后包法利的种种不是或劣迹,都可以从这帽子的描写当中找到伏笔,找到蛛丝马迹。
或者,福楼拜如此描写帽子其实是作为一个写手的抒情,写手的撒欢,是玩弄文字游戏。文学大家或文字高手常常喜欢玩这套游戏。
俄罗斯作家果戈里在他的著名短篇小说《外套》和《鼻子》中,在他的长篇小说《死魂灵》中,更是把这一套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果戈里动辄就鬼使神差般地逮着一个话题、一件事情、一样东西一路说下去,说个没完没了,说得天花乱坠。他的言说整体匪夷所思,不合常理,荒诞不经,荒谬至极,但细节又顺理成章,头头是道,丝丝入扣,严丝合缝。
在优秀的小说家和杰出的文学研究家、评论家纳博科夫看来,果戈里的这种笔法是天才的文笔,是一个优秀写手的最佳表演,是货真价实的优秀文学。果戈里的文学手腕、文字杂耍表演有些像是高超的体操运动员,在踏板上一踏脚就可以飞腾空中,在空中进行令看客眼花和惊叹的身体翻转,然后再两脚稳稳落地。
无独有偶,英国十八世纪的词典编纂家、学者、诗人、文学批评家约翰生博士对莎士比亚也有类似的看法。但约翰生是以贬斥的口吻说莎士比亚,说他像是个小孩子,遇到一个双关语像个孩子看到一个不可抗拒的的玩具,就会忍不住玩起来,玩个没完没了,忘记了该说的正事。
然而,在纳博科夫看来,文学的精髓和真谛就是文字游戏,游戏就是文学的正事;一般人心目中的文学正事(深刻的思想之类)则是文学可以用来借题发挥的借口,是文学可以借以起跳的踏板;思想对文学来说是可有可无的次要的东西。
***
许渊冲对《包法利夫人》 第一章这个著名段落的翻译还有一些问题可以讨论。但样的讨论最好是保留给法-中文学翻译专业研讨会。
对一般的读者来说,将许渊冲的翻译跟在互联网上看到的另一种翻译作一个对比,可以得出一个很有趣也很悲催的发现。
为了方便读者进行对比,在这里我们再把许渊冲的翻译跟网上可以找到的翻译并列出来:
不知道这个新生是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一套,还是不敢跟大家一样做,做完课前的祷告之后,他仍把鸭舌帽放在膝盖上。他的帽子看不出到底是皮帽、军帽、圆顶帽、尖嘴帽还是睡帽,像是一盘大杂烩,反正是便宜货,说不出有多难看,好像哑巴吃了黄连后的苦脸。帽子是鸡蛋形的,里面用铁丝支撑着,帽口有三道滚边;往上是交错的菱形丝绒和兔皮,中间还有条红线隔开;再往上是口袋似的帽筒;帽顶是多边的硬壳纸,纸上蒙着十分复杂的彩绣,还有一根细长的饰带,末端吊着一个用金线结成的小十字架作为坠子的饰带。帽子是新的,帽沿还闪光呢。(许渊冲译)
不知道这个新生是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一套,还是不敢跟大家一样做,课前的祷告做完之后,他还把鸭舌帽放在膝盖上。他的帽子像是一盘大杂烩,看不出到底是皮帽、军帽、圆顶帽、尖嘴帽还是睡帽,反正是便宜货,说不出的难看,好像哑巴吃了黄连后的苦脸。帽子是鸡蛋形的,里面用铁丝支撑着,帽口有三道滚边;往上是交错的菱形丝绒和兔皮,中间有条红线隔开;再往上是口袋似的帽筒;帽顶是多边的硬壳纸,纸上蒙着复杂的彩绣,还有一根细长的饰带,末端吊着一个金线结成的小十字架作为坠子。 帽子是新的,帽檐还闪光呢。” (网上发现的译文,被误称为周克希译)
读者在这里清晰地看到,许渊冲和网上的翻译高度相似乃至高度重合,两者只有屈指可数的微小差异或个别词组的前后次序调整。翻译的明显错误和问题在这两位译者的翻译中完全一样。
不懂法文的中国读者若想通过阅读这两种的翻译来鉴赏和品评福楼拜这部精致的作品便必定会被误导,或无意中陷入被动难堪的境地。
有翻译经验或写作文经验的人都知道,如此高度相似乃至高度重合、尤其是错误也完全重合的文本,只能是来自逐字逐句的抄袭甚至是电脑文字处理的剪贴作业。
***
笔者在此不拟对许渊冲和网上的译文究竟谁抄袭谁做出评论。网上的这种翻译据说是来自著名翻译家周克希。但笔者后来得到一读者提醒,得知并不是周克希的译文。
在这里,不妨就翻译的借鉴和抄袭的区别问题做一点解说。
随着中国出版业的重组、外国文学作品的版权问题的发展,以及外国文学名著出版市场的变化,如今有不少中国出版社在谋划并进行外国文学名著的重新翻译和出版。有一些出版社在约稿时明确规定,译者不准借鉴先前的译本。
这种规定显然是专门针对当下中国文学翻译界所流行的把剽窃抄袭旧译当作新译的恶劣做法而制定的,因此,提出这种规定的初衷是可以理解的。
但毋庸讳言,这种规定也是一种纯粹外行的规定,因为制定这种规定的人显然不知道,翻译事业跟科研事业一样需要借鉴前人,需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推进。翻译和科研一样,不借鉴前人已有的成果是外行的表现,其结果只能是在低水平上的徘徊和停滞不前。
因此,优秀的翻译家从来不忌讳借鉴了前人的翻译成果并公开声明这种借鉴。例如,二十世纪中国的著名翻译家、诗人卞之琳就公开声明,他翻译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就借鉴了前辈曹未凤的翻译。
但就翻译而言,如何判定一个译者是借鉴前人还是抄袭前人呢?很简单,就是看后来者是否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推进。
具体说就是,前人的好东西是否得到了后来者的继承(而不是弄出新的差错)?前人的错误后来者是否给予了纠正?
假如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大都是yes,那就是借鉴。假如后一个问题(是否纠正了前人的错误)的答案大都是no,那就很可能是抄袭。假如后来者的翻译文字跟前人的高度一致而且错误也一致,便可以肯定是抄袭。
不劳而获的抄袭犹如盗窃,是一种可耻的行为。
***
这个问题还可以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这就是,从事翻译或从事文字工作的人都知道,每个人的文笔/文风都不一样。就文学翻译而言,读者期待译者表现出自己的独特风格,对外国文学文本有自己的独特解读和表达,抄袭则是辜负读者的期待,实际上是一种诈骗。
每个自尊自爱的翻译,每个自尊自爱的文章写手都会回避瓜田李下之嫌,都会顾忌读者的谴责或鄙视。实际上,从事翻译的人要想避免跟别人的翻译雷同实在是非常容易,只要自己翻译一遍,不要逐字逐句抄袭即可。
本文所讨论的福楼拜的著名段子为例,一千个译者就会有一千种明显不同的译法,假如两种高度雷同,就必定是发生了抄袭。这种问题不需要很高的智商或很高的专业水平就可以做出正确无误的判断,甚至小学三年级学生就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
非常不幸的是,当今中国文学翻译界除了缺乏专业标准和操守导致烂译横行之外,也有抄袭横行,其中不乏所谓的著名翻译家原封不动地抄袭他人来冒充自己翻译。
抄袭的翻译总是不可靠的,是劣等的,无价值的。为什么?研究版本学的人都知道,假如一部文学作品的版本是抄袭另一个版本,抄袭版是无价值的,因为抄袭版只能是在抄袭过程中增添错误,不会增添好东西。抄袭的翻译也是一样。
参考资料:
安提戈涅,《包法利的帽子》,见,https://www.douban.com/note/684682939/)
许渊冲译文,见译林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许译《包法利夫人》第4页。
网上不知名译者(但被说成是出自周克希)的译文,见https://www.thn21.com/Article/chang/fuloubai/2.htm
《包法利夫人》法文原文,见http://www.gutenberg.org/cache/epub/14155/pg1415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