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adie Smith的《搖擺時代Swing Ti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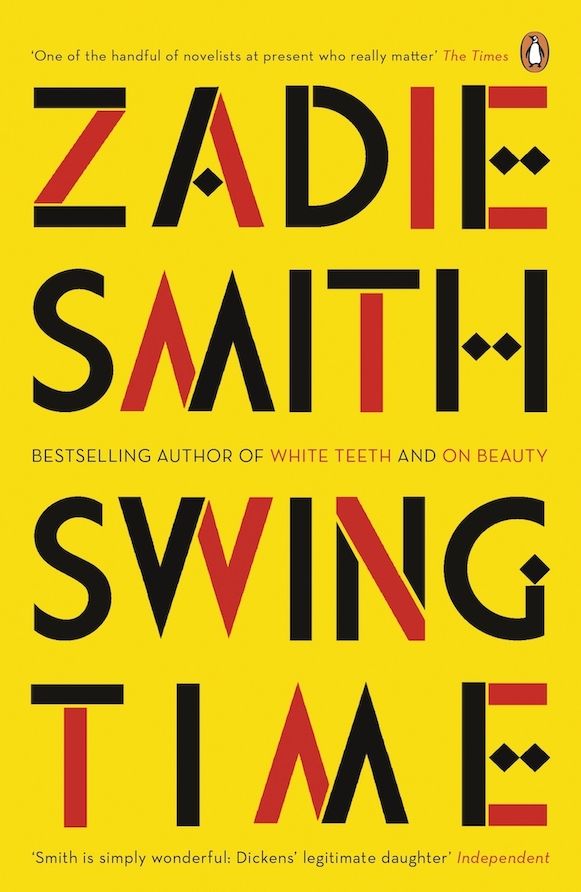
小說開場時,敘述者是"Aimee"的特助,她捅了一個天大的婁子(我們還不知道是什麼婁子),正在倫敦的某個旅館裡避風頭....。
在她接下來的回述裡,我們會聽到一個很大的敘事,關於種族、階級、流行文化、音樂與舞蹈、跨國娛樂產業、殖民與後殖民,從倫敦到紐約,乘著私家飛機到西非貧窮小國的故事。
但包裹在這個故事的核心,是一段友情:當七歲的敘述者在社區的舞蹈課裡與Tracey相遇時,她們立刻認出彼此:她們都是咖啡色(brown)的。她們都是一黑一白父母生出的孩子,她們都住在公屋裡;皮膚的顏色,像物種的DNA般,註定了有些事,她們永遠無法讓彼此以外的其他人懂。
那是一種類似同類相認的物種本能:比方說兩人似乎都對舞蹈有超乎班上其他女生的天份與熱情,她們在Tracey家反覆看著Fred and Ginger的歌舞片錄影帶——Fred Astaire與Ginger Rogers是黑白歌舞片時期的黃金拍檔,他們在1930年代合作了九部電影,包括這本小說的同名電影,1936年的Swing Time——也只有彼此能當對方的舞伴,儘管Tracey才是天生的舞者,而敘述者其實更擅長唱歌。
同時,她們也迅速在對方身上辨認出彼此的歧異:Tracey的爸爸是黑人,媽媽是白人;而敘述者則反過來,媽媽是黑的,爸爸是白的。Tracey的媽媽沒有工作,爸爸在牢裡。敘述者的父親在郵局工作,媽媽也沒工作,正透過開放大學(Open University)的遠距課程,在家裡自學。
敘述者不懂,為什麼Tracey的媽媽所有注意力都在女兒身上,總是替她精心打扮,甚至穿上正式的芭蕾舞裙tutu去上課,自己的媽媽,明明也沒有上班,卻沒有把100%的心思都放在自己身上?連舞蹈課也是爸爸陪她去。週六的舞蹈課是媽媽「自己的時間」,爸爸總是隨身攜帶他永遠讀不過20頁的《共產主義宣言》——父母當年是在某個左翼運動集會上認識——在進行舞蹈課的教堂外面抽煙,那個時間,媽媽在家啃著一本又一本的學術書籍,然後在餐桌上吐出父女都聽不懂的詞彙。
Tracey房間有數不清的玩具,在Tracey家,兩人愛幹嘛就幹嘛,但媽媽總是跟自己說:你和她們不一樣。她們,是Tracey,也是公屋社區的其他小孩。媽媽來自有十個小孩的牙買加家庭,她發誓永遠不要回到那裡...。
兩人在學校也這樣形影不離,在課堂上不停犯規、從校園到課室和男生玩把手伸進褲子裡的遊戲、在同學的十歲生日派對上表演十歲小孩不該知道的舞蹈體位....母親跟她說:你比他們更好;Tracey的叛逆與諷刺笑容卻彷彿提醒她:你永遠也別妄想....。
兩人如同雙子星般,被彼此的引力拉扯靠近,但同樣的引力也終將把彼此推上註定分歧的軌道。母親脫離了因為種族與階級而往往已被預寫的人生:她在開放大學完成一個又一個學位,她離開父親,她成為國會議員,她甚至找到同性伴侶....。而敘述者,也如同母親以強韌意志力所預言的:你不會變成公屋長大的孩子。她從大學畢業,她進了YTV(其實就是像MTV的音樂頻道),她成為超級國際巨星Aimee的助理。
(而這些年Tracey在幹嘛?Tracey在短暫的音樂劇舞群人生後,回到了同樣的公屋,和她母親一樣發福而臃腫,帶著她和三個不同的男人生的三個小孩...。)
雙子星可能因為在不同的軌道上,背離彼此航行多年,但總會在什麼時候,再度交錯。多年來,敘述者還是一直想著Tracey,而她的過去仍然跟著她,直到來自澳洲小鎮、同樣拋棄過去而成為超級巨星的Aimee,決定把她的巨額財富,投注一小部分在解決貧困問題上。Aimee透過敘述者的議員母親,相中西非一個舉國GDP略遜於自己財富總額的小國,決定在那蓋一間全女子學校,她派她能幹的特助前去做籌備工作....
她的母輩先祖當年戴上腳銬,被送上奴隸船隻前往加勒比海的蔗田前,正是從那裡、或者鄰近相類似的港阜出發,在那裏,敘述者的軌道開始逆行,她彷彿回到童年的課室,回到公屋社區,直到她好像終於應證了Tracey過去的預言:你沒有辦法不一樣,你無法擺脫你真正的身份.... 她捅下了天大的、足以讓Aimee拋棄她的婁子....
Zadie Smith的母親是牙買加人,父親是白人,她父親長她母親三十歲,她父母在她青少年時離婚,她從小就喜歡踢踏舞....。她去了劍橋,讀了英文文學。她在25歲出版了第一本小說《White Teeth白牙》。
我知道Zadie Smith多年,《White Teeth白牙》當年太紅了,圖書館出清舊書時我撿了一本回家,放在書架上很多年沒打開,那時我不常看英文書(直到她第三本小說《On Beauty論美》入圍了2005年布克獎決選時,我都還沒開始讀英文),但這不妨礙我知道她的(白人)老公Nick Laird很帥(他們在劍橋相遇),兩人堪稱文壇金童玉女(而Zadie Smith名氣更顯著)。當年我還在部落格貼了篇名為美女作家的沒營養文,把她列進去...。
開始用英文看書後,我忙著補十九世紀廿世紀前葉的小說,當代作家的小說我讀的很少,幾年前我開始會在走路時跟移動時聽有聲書,在圖書館電子書櫃找到《Swing Time》的有聲書。終於在這麼多年後,讀(聽)了Zadie Smith的小說。
一個移民、新住民的小孩,要經過多少時間,才可以掌握國家的語言,或者說,才可以突破作為移民,作為種族與階層上的相對弱勢以及缺乏資源者的限制,找到自己的聲音,甚至讓自己的聲音被聽見?
近幾個禮拜,再度聽《Swing Time》的英文有聲書時,我重新思考這個問題,還有:Zadie Smith的小說對台灣人、中文世界的人有什麼意義。
從一個語言,跨越到另外一個語言,本來就是一件很艱難的事,縱使是土生土長的語言,話語權、主權文化的藩籬仍然很難突破。
我要在讀英文多久以後,才可以在聽到敘述者說,她和Tracey都來自estates時,知道在英國\英語語境下,這個詞指的是公屋、社會住宅?這些需要投注功夫與時間,但可以支撐這些心力的,也需要資源——因為生長環境而能夠擁有、獲取的資源。
我離開台灣太久,台灣的移民、新住民,對我來說幾乎是完全隱形的。如果我在現場,我至少還會在現實中看見他們(不管那個「看見」多麼有限),但我隔著遠距,只透過網路、並很限量地接收台灣的訊息時,他們幾乎是不存在的;我不太會在文字、文化中看見他們。和人說起這些,才會知道並不是他們缺席或隱形,在某些領域裡,在移工文學裡,他們是存在的,也有作家是這樣的身份,只是我沒有特別去找、或是去看見。
也許不要說新住民,單只是台灣的某些階層、族群,對我來說也幾乎完全是隱形的,要不就是,當我知道、讀到他們時,是別人在說他們的故事,之前和L聊起《做工的人》,大概有點像那樣。
我的小世界裡只有我看得見的人、事、物,這當然是我的錯,或者說侷限。如同Zadie Smith的小說,她必須要主流到一個程度之後、或滲透到那個文化成為令人不假思索的一環,可能才會映入我的眼簾。我讀英文書,到現在一直都還不會特定去找用英文書寫的華裔、亞裔作家的書,用英文讀其他文化、族裔作者的書,可能要書的題材吸引我,或者因為其他什麼原因(得獎、評價斐然、作者名聲響亮),我的閱讀口味是否很保守、很反動、很狹窄?也許。
但Zadie Smith的小說寫的真好,幾乎有十九世紀小說裡那種極廣的視野,把當代的重要元素都寫進去了,但同時,她寫身為一個「有色人種」小孩,在長大過程中經歷到種族、性別、階層如何交互作用,一道又一道地,把自己與同儕割成許多種色塊不一的身份——乍看之下差不多,但每一塊又有著細微的色差。這只能來自親身經驗與觀察,是現成論述很難捕捉到的細微差別、nuance。這些色塊有時候群聚,有時候壁壘分明,如同我們的身份,隨著我們和不同的群體發生關係,也隨著我們自身的改變,總在不停地流變;同時既想突圍,又彷彿永遠無法僭越那些疆界。
噢,而且Zadie Smith的筆法還同時幽默而詼諧,幾乎也有點像她喜歡的、小說格局也很恢宏的約翰法蘭岑(Jonathan Franzen)....
Zadie Smith身上的多重身份與脈絡豐富、滋養了她所隸屬的英語文學地景,在文學的領域,我總是追求美,和其他什麼標準無干。(或者說我也在意對人的拂照,我喜愛的作家,幾乎都很humane,我不太能喜歡「討厭人」、跟站在制高點俯瞰世界跟筆下人物的作者。但對我來說這也是美的一部分、一種體現)
和不列顛群島一樣,台灣亦是群島,英國曾經透過航海、貿易與殖民,擁有日不落帝國。而各色人種,也從帝國的四角,群聚到島上,包括一批批從非洲輸送至加勒比海再輸送至歐洲的奴隸,包括英國人自非洲殖民地撤離時,因害怕繼任政權而尾隨的非洲人、印度人。台灣沒有過殖民帝國,也不需要有,台灣如果天生是海洋文化,也許在她的近代史中,曾經歷過內封的、大陸性的、大國式思維,那她是否能重新找回自己張開的、流動的、收容的、廣褒的基因屬性?
雖然我是一個很懶也很不主動向外覓食的讀者,但我還是期待能夠看見這些不同的聲音,從台灣的文學地景裡生長出來,不止作為某種點綴、或在多元欄位旁打勾滿足某個標準,而是,真正地成為那個地貌的一部分,因為,這些都是文化的養分,也是對美的追求——只有一個有豐富文化底蘊的地方,才可能永續地創造有形無形財,繼續創造美麗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