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辉煌的美国汽车工业,为何一蹶不振?

作者|陶孟元
今年3月,新任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了超过2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并将电动车等新制造业作为支持重点。拜登把这一计划称之为“二战以来对美国就业的最大单笔投资”,期待它可以提振遭疫情重创的美国经济。与此同时,拜登和哈里斯会见了美国的大型汽车制造商、汽配公司和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 Union,简称UAW)代表。劳资双方的代表共同敦促拜登支持“全面”的电动车计划,包括提供税收优惠和购车补贴等。此举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美国汽车工业在新一轮能源革命中拔得头筹,我们不得而知。
然而,美国汽车工业早已不复当年勇,却是不争的事实。如雷贯耳的美国汽车资本三巨头——通用汽车(GM)、福特和克莱斯勒,诞生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经过20世纪上半叶的发展,三巨头在1962年达到巅峰:当时的通用汽车占据了美国汽车市场一半的份额,三巨头加起来更是达到了惊人的87%。但是,在之后的50年,三巨头便由盛转衰,其市场份额不断下降。2008年金融危机后,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更是靠奥巴马政府的输血才逃过破产的厄运。2019年,通用汽车只占据了美国国内市场份额的17%,三巨头加起来也不过是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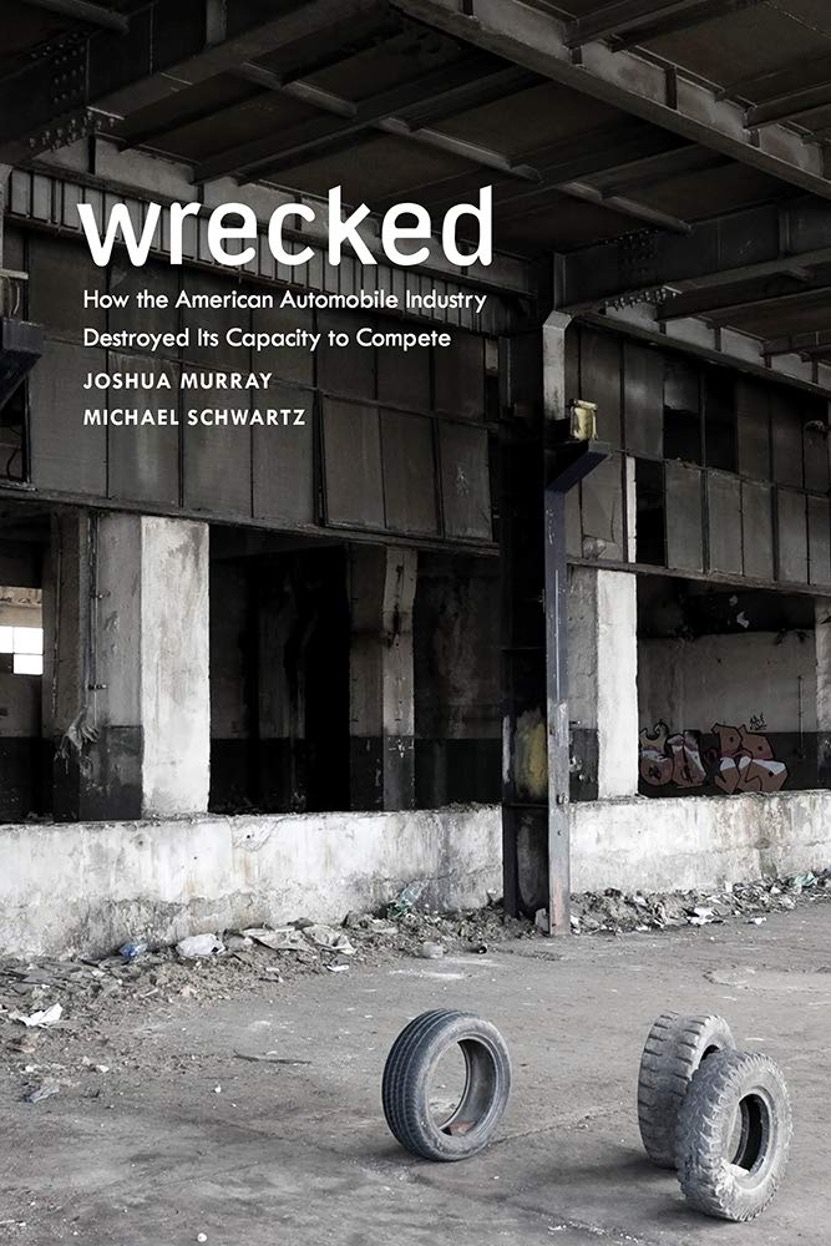
那么,这50多年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能让看起来这么“结实”的三巨头变成“弱鸡”?如果说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信贷收紧只是它们濒临垮塌的导火索,那真正的“炸药包”又是什么?2019年,美国社会学家Joshua Murray和Michael Schwartz的著作《毁灭:美国汽车工业怎么摧毁了自己的竞争力》(Wrecked: How the American Automobile Industry Destroyed its Capacity to Compete,以下简称《毁灭》)问世,为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
讨论美国汽车工业成败兴衰的著作很多,尤其是在商业和经管领域。然而,《毁灭》不同意主流舆论常见的三种解释,转而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探讨这段历史。最终,两位作者得出结论:“作死”美国汽车工业不是别人,正是三巨头资本家自己。
对三种常见看法的反驳
作者首先回顾了以往三种针对美国汽车工业不断衰颓,尤其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被日本车企赶超的解释。
第一种理论是产品生命周期论。这种理论认为,每一个产业都有其生老病死的阶段,这是由市场的力量塑造的生命周期。当产业的技术升级跟不上市场需求,生产难以扩张,资本就会主动减少人力支出、寻求廉价劳动力以节约成本,增强竞争力。表面上看,这个理论对美国汽车工业的衰落很有解释力:最早的汽车产品问世后(初生期),在大萧条时期技术得到长足进步(创新期),随后是二战后标准化生产的成熟以及美国汽车生产在国内外的扩张(成熟期)。最终,日产汽车利用廉价劳动力进军美国市场,击败美国汽车工业(衰退期)。这是产业的命,我们得认命。
作者认为,这个理论不符合他们对各国汽车工业的观察。第一,日本和欧洲的车企生产历史比美国更长,但也不见它们像美国一样或者更早步入衰颓的阶段。而且,美国汽车产业是在全球扩张生产之后,才出现创新衰颓,而不是反过来。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日本汽车产业的竞争力,主要来自它们的生产技术和流程创新,而不只是来自廉价劳动力。这一点其实也是绝大多数商业分析的共识。
那为什么日本汽车企业有这么强的创新能力呢?我们又看到了两种常见的解释:美日汽车工业不同的管理文化和工人文化。
持管理文化论者认为,日本车企的成功是因为日本传统宗族、禅文化和日本传统书画艺术影响,因此日本汽车工业的管理层非常谦卑、非常重视细节,也非常愿意承受创新带来的风险。相反,美国汽车产业厌恶风险、管理文化非常傲慢、对细节不重视。所以日本/美国车企的创新/不创新是不可避免的,都是根植于其文化中的。然而,作者认为,汽车工业创新与否,是由生产系统的结构性决定的,管理文化只是对这些物质条件的一个回应。
而美日两国车企的生产结构是由阶级斗争、当时当地的事件和历史路径依赖决定的。日本车企创新的关键是灵活生产系统,这套系统其实是从美国二战前类似的生产系统学来的。美国汽车产业用这套系统的时候,美国的分析师认为美国汽车工业很创新、很愿意承担风险。后来美国汽车工业弃用这套系统后,创新减少,各种“管理文化”论也来了。
除了管理文化论,工人文化论在主流舆论中也很有市场,尤其深得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欢心,是抹黑工人运动的常见话术。这种理论认为,美国汽车产业衰落,都是因为美国汽车产业以UAW为首的工会太强大了。工会通过和资方谈判,使得工人工作只达到合同的最低标准,却不断要求更高的工资和福利,这些因素都阻碍了美国汽车工业创新。而且,因为这些又贪婪又懒惰的工人,所以美国车企在面对拥有更廉价劳动力的日本和欧洲车企时没有竞争力,因此美国车企的市场份额从1960年代开始落于下风,最终奄奄一息。
作者也不同意这个说法:以1981年的通用汽车和马自达美国工厂对比为例,通用汽车超过一半生产线在墨西哥等非工会廉价劳力地带,时薪拿的是“高”工资的美国工人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因此它的劳动力成本远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高。而马自达相比通用节约的生产成本,只有四分之一是来自更低劳动力时薪,剩下的四分之三都是来自灵活生产:日企工人的劳动时间更少、零部件的成本更低、库存更少、运输费用也更低。因此,即使有了高昂的关税,日本车企还是能以更低的价格卖出质量更好的汽车。

灵活生产系统:日本汽车工业打败美国同行的关键
那么,在两位作者看来,是什么造成了美日两国车企竞争力的分野呢?答案是:不同的生产结构。美国汽车工业为了压制劳工的力量,因此选择了和日本汽车工业不同的生产结构,最终把自己活活作死。
两位作者总结,日本车企(以及一些欧洲车企)采用了灵活生产系统。这种系统的特点是地理上的集中生产、机器灵活、长期单一供应商以及零库存/及时交货。这个系统能够保证产品设计和生产的持续创新,实现生产和组装的协作,以及增加工人的生产效率。美国车企则相反,它们采用了僵硬的大规模生产系统。这种系统的特点是地理上分散生产、零部件和机器都是固定的,以及大库存,结果是阻碍创新,降低生产效率。
那么,为什么灵活生产系统会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创新呢?在进一步讨论美日车企的选择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灵活生产的四大要素及其意义:
- 零库存/及时交货(just-in-time delivery)。这是指上游和下游供应商同时开工,使得零部件可以在不需要库存的条件下及时到位。如果整个链条顺畅运行,车企就可以更低的成本及时试验、调整和创新。
- 机器灵活(machine flexibility)。二战后主流的量产方式,是一台固定作用的机器在一个环节固定待着,工人也是在工程师的安排下,在这个固定的生产流程中固定地各司其职。灵活生产系统则改装或者代替原来的机器,使其可以在不同的作业步骤中灵活变换,车间工人也随之灵活调整。这不仅可以改善零部件供给中的配合和调整,减少库存,也可以增加产品的多样性。
- 地理集中(geographic clustering)。零库存决定了供应商和组装厂在地理上的集中。这一集中以圈层分布,核心层是最终的组装厂,产出面向消费者的最终产品;中间层是一级供应商,主要生产组装成车的零件;外层则是二级供应商,主要为一级供应商提供原材料和次级零件。由于成功的创新依赖长期、面对面的互动——包括管理层、工程师和技术工人,所以地理集中也为创新提供了便利。
- 长期单一供应商(long-term sole supplier relationships)。相对少而更集中的供应商,对于稳定品控和降低成本有利。这种关系也便于零部件创新和试错。因此,地理距离近和互相信任在这一要素中继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这四个要素里,工人的投入都是保证灵活生产顺畅运行的决定性条件。因此,灵活生产系统赋予了工人较强的议价能力。一旦一两个环节(尤其是重要环节)的工人停工,整个生产链条都会停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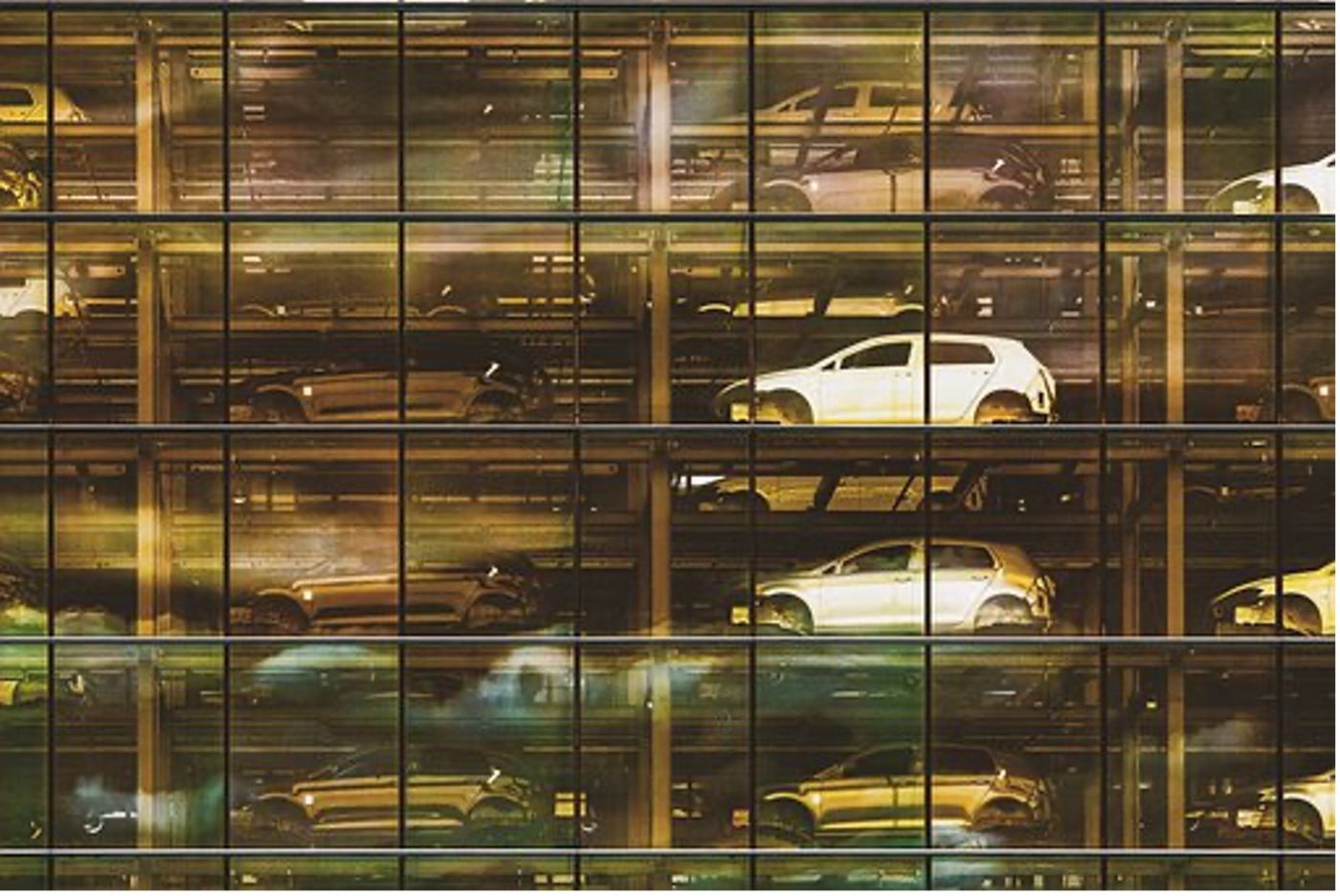
为什么美国车企放弃灵活生产?
如果灵活生产有这么明显的优势,为什么美国车企后来会放弃呢?如果资本都惮于劳工的力量,那为什么日本车企又愿意向工人妥协呢?以及,既然后来美国车企都看到了日本车企因为采用了灵活生产而后来居上,为什么它们还是没有拾回这个自己原创的“杀手锏”呢?为了回答这三个问题,作者认为,我们需要回到美日汽车工业的阶级斗争去寻找答案。
事实上,泰罗制和灵活生产并非日本汽车工业的原创。恰恰相反,日本车企其实是从美国车企那儿学来的。一战前,亨利·福特就采用了灵活生产系统,从而实现了持续的技术创新,降低了劳动力等生产成本。这种生产系统对工人的剥削很严重——不管是当时的美国还是后来的日本工人,都对劳动过程的去技能化和高强度非常不满。
但灵活生产在地理上的集中和零库存制度也增强了工人的议价能力。1914年,福特工人罢工,导致福特公司瘫痪。因此,福特向工人妥协,用5美元日薪和提高的福利待遇来换取工人对恶劣劳动条件的容忍。这一做法后来也扩散到了通用汽车等行业巨头,并演化成一种劳资之间的“社会契约”:工人接受因为技术革新带来的失业、被迫无薪放假、降薪等后果,以换取技术革新后提升的物质激励(如公司返聘之前因技术革新而下岗的工人,开的工资比之前更高)。当时美国汽车产业流行的口号是“同甘共苦”——虽然“同甘”时,资方拿“甘”的大头;“共苦”时,工人吃“苦”的大头。
到了大萧条时期,美国经济万马齐喑,车企也大规模裁员、降薪、“放假”。尽管如此,这时的劳资“契约”其实还没破裂。“契约”的真正破裂是在1936年:美国汽车三巨头的利润回到了大萧条前的水平,但工人工资却没有回到相应水平。换言之,资本家忽悠了工人。因此,工人发起反抗——从数百名工人加入UAW,在厂区静坐,逐渐演变为13.6万名工人共同参与的弗林特大罢工。这是美国历史上汽车工人第一次利用他们的议价能力成功实现的组织化斗争。四年后,美国汽车工人以组织程度高而闻名全国。
弗林特大罢工震惊了美国汽车三巨头,它们也因此开始想办法瓦解工人的力量。这个计划被二战延迟了。而且,尽管二战期间,工会和罗斯福政府达成了“不罢工承诺”,但基层工人还是不断发起零星的罢工,持续斗争。二战后,汽车产业巨头不愿接受工会提出的加强版“社会契约”——这时的工会不只要求继续增加工人的劳动所得,而且要求工人对生产流程的安排有一定话语权。因此,资本家希望降低工人的议价能力,增加他们发起集体行动的难度,从而“一劳永逸”。他们决定放弃灵活生产系统,转而采用零散平行生产:分散生产,可以增加工人组织反抗的难度,减少像弗林特大罢工那样的一厂起事、周边数厂响应的可能性;平行生产,可以保证每个环节的生产都有替代方案,一厂停工无法“锁喉”整个生产链条;大库存,可以保证上游的停工不会马上影响下游的生产。这个系统确实有效隔绝了罢工,但也隔绝了灵活和创新。最终,美国汽车三巨头在日本汽车涌入美国市场后便完全败下阵来,从此一蹶不振。即使眼看着日本汽车工业靠灵活生产发家,自己也无能为力,因为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僵硬和惰性已经积重难返。
那为什么日本汽车工业没有发生类似的情况呢?作者也是从日本汽车工业的阶级斗争史中寻找答案。和20世纪初福特的罢工不同,最早采用灵活生产系统的丰田经历过有组织、有力量的工会运动。这些工会主要由日本左翼力量组织,从1950年到1953年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的丰田工人罢工。但是,1954年,亲资方工会击败了左翼工会,从此开启了日本汽车工业资方工会系统的历史,也开启了日本汽车资本和工人的“社会契约”——资本为工人提供高工资、终身雇佣和高福利。日本工人之所以会接受这个妥协,一方面确实是因为1954年的失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战后日本工业的腾飞提供了物质基础、日本工人长期忍受低工资和恶劣劳动状况的历史,加上资本对于工人未来的晋升和技能提升的承诺,日本工人也没有经历过像1936年美国资本家“背信弃义”的情况。所以,丰田工人接受了资本的妥协,资本也因此得以继续采用灵活生产系统。作者认为,同样内容的“社会契约”,如果发生在别的时间、别的地点,可能结果也不一样。

思考和总结
《毁灭》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通过扎实的历史研究,以美国汽车工业为例,将资本和劳动这一个矛盾的两面搞清楚,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阐述阶级斗争,从而有力地回击了主流舆论中对美国汽车工业衰落的错误解释。笔者认为,这是值得我们所有舆论工作者学习的严谨态度和论述方法。
其次,《毁灭》从宏观和微观角度,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工人运动的洞见。从宏观来说,作者将美国和日本汽车产业在国内以及全球的扩张,还有美日汽车产业工人运动史一并考虑,动态地考虑工人运动在当时当地的得失。从微观来说,作者在书中详细回顾了美国劳工运动的不少细节,如由左翼政治力量主导的弗林特大罢工是如何组织、如何抗争的,适合所有组织者一读。碍于篇幅,这里就不具体介绍了。
当然,《毁灭》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书中对美国汽车工业历史上的劳资斗争复杂性阐述不够。历史上,UAW曾和资方达成协议,成为控制工人以及为美国民粹主义站台的工具。另外,工会领导层的保守性和基层工人斗争性之间的矛盾,美国工人运动和民主党建制的矛盾,这些矛盾如何左右美国汽车工运的历史,以及这些历史对我们思考中国工人运动的意义在哪里,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去了解。笔者不才,只是抛砖引玉,还望各位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