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者的執著(靈異 / 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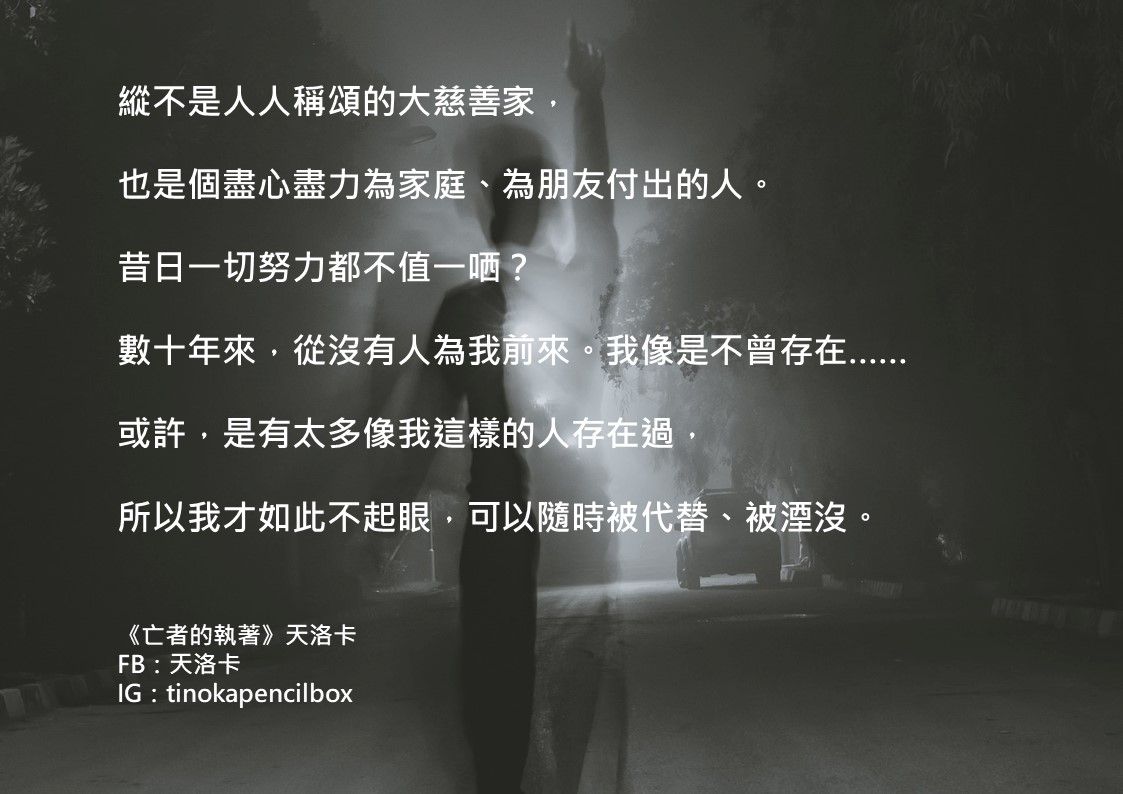
我,男性,中年。某天上班時,遇上交通意外,命喪當場。身體已死,魂魄不散,跟著屍體到殮房去,眼巴巴看著妻兒親友哭成淚人,卻沒能加以安慰,內心異常悲傷。人潮散去,我尾隨妻兒回家,默默守在他們身邊。稚子年僅三歲,終究未明世事,很快重拾正常生活;倒是妻子日夜哭過不停,教我擔憂無比。
慶幸日子有功。妻子由每天哭得雙眼紅腫,到慢慢走出陰霾,結識新歡。對方是個條件優裕的好男人,沒有不良嗜好,對我妻兒體貼無比。我應該替妻兒感到高興,找到能夠倚靠的家庭支柱;但看著妻子再婚、親兒稱呼別的男人作「爸爸」,我心裡總是不是味兒,可恨欲哭無淚:我的淚腺早在那場車禍中灰飛煙滅。妻兒搬到新居去,舊居亦放售予素未謀面的陌生人。我的家庭就此徹底捨棄了我,無論我願意不願意。
我到自己的骨灰龕前坐坐。我沒有確實數算自己在此呆坐了多久,只見每年到來鄰龕拜祭的小伙子,由步履不穩的小娃長成禿頭粗腰的中年胖漢。數十年吧。躺在鄰龕裡的魂魄早已離開,沒有受過後人的一香一燭,但前來拜祭的家庭一直懵然不知。為報先祖之恩,他們帶來的祭品甚至越來越奢華,令眾人眾鬼張口結舌。
可能,鄰龕的魂魄生前有救國救民大功績,值得受到如此厚待。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只是一個平凡的上班族,沒能與他比擬。不過……我真的卑微得不值半炷清香?縱不是人人稱頌的大慈善家,也是個盡心盡力為家庭、為朋友付出的人。昔日一切努力都不值一哂?數十年來,從沒有人為我前來。我像是不曾存在……或許,是有太多像我這樣的人存在過,所以我才如此不起眼,可以隨時被代替、被湮沒。
我離開龕場,漫無目的地一直走。不需吃喝,不需休息,不知疲累。沒有活著的感覺,卻有活著的煩惱。喜怒憂懼愛憎欲,纏繞心頭,縈迴不散。
徒步來到某山山頂。夜空陰沉,銀月耀眼。強烈的對比,像利刃,割斷我最後一道繃緊神經。我縱身一躍,由山頂滾下山腰,沿途被無數樹身石塊穿過。一陣混亂後,我最終在一個涼亭旁邊停下。「身體」絲毫無損,心緒更為煩躁。
涼亭下,有兩隻穿古裝的魂魄。他們時而吟詩作對,時而高歌詠唱,逍遙自在。他們見我悶悶不樂,於是主動打開話匣,逗我說話。
「人已死,還有何話可說?」
「魂魄未散,可以和我們一起風花雪月!」
「我沒有心情風花雪月!我想死,徹底地死去!」
「傻孩子!身體早已滅亡,魂魄純粹是生前的殘念。你想『徹底死去』,就要放下生前的一切啊!」
我呆立當場。
放下一切?包括我的人生、我的愛、我的恨?我的一切都是由昔日種種組構而成。放下一切,不就是放下自己?若然放下了,不就是沒有我?沒有我,就是「徹底死去」……說到底,原來是我不想放下、不想死……
今時今日,我還未懂放下。
請問,有誰可直接來將我打個魂飛魄散,免我執著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