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港第八日
8.23,这是我到到香港的第八天,解除隔离的第一天。
本来在上海时就决定到香港的隔离期间必须要写点什么,结果在无数的拖延症和理由之后成功糊弄掉了这件事,但是在今天,香港以它的各种威逼利诱的姿态告诉我必须写点什么。
早八半,这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早晨,但是对我而言不一样:这是我来港以后起得最早的一天,尤其是前一天晚上还睡得很晚。
不过这都是小事,毕竟明天开始我又能继续睡懒觉,情况好的话这个学期都不用早起了,夫复何求。
于是开始理东西。结果发现我的收纳能力和我妈还是差了一大截:从上海来时带了这么多东西,装进了两个箱子里,刚刚好好;现在还是这么多东西,是怎么也装不下了。更何况在我的强烈要求下,我妈还给我寄了半箱子书,整个隔离期间我都没看过一眼,现在根本带不走...
不过反正都是同酒店搬来搬去,大不了多跑几次就是。
打电话和前台商量好下午四五点回来checkin去新的房间,并告知不用送午饭了就上街压马路了。
几日前收到学校发的邮件,说可以去拿学生证了,隔了一天又收到一封邮件,说上一封邮件是错发的,忽略即可。借着我半吊子的英语水平和理解能力,看了多遍还是横竖看不懂以后决定还是去实地探查一下,顺便去看眼学校。邮件上著名要自行打印一份邮件的纸质版,问酒店打印12hkd一面黑白A4,扣b我决定自己在外面找打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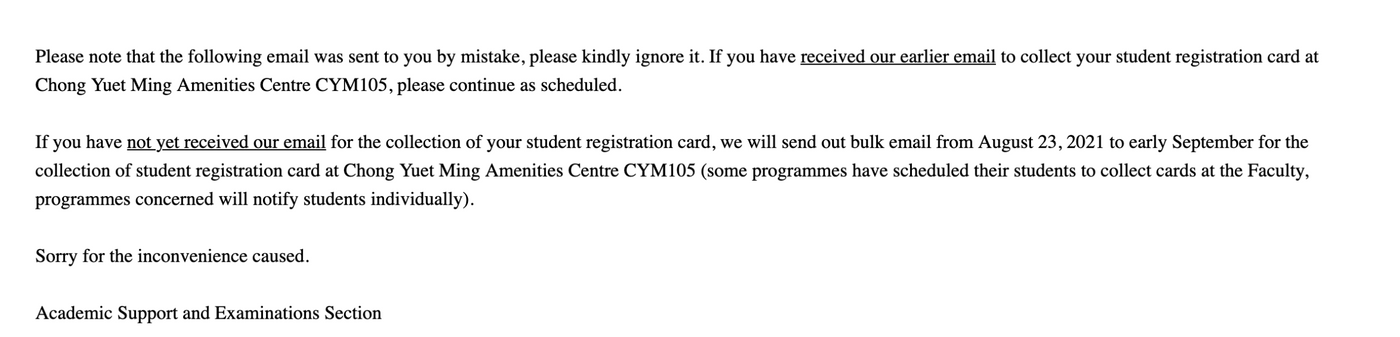
关于我扣b这个问题,以前在内地未曾有过这种见解,甚至还嘲讽过某小友是扣b,不过后来事实证明,只是我扣b的内心未曾拥有一个足够华丽的舞台得以展现,hk一顿外卖10khd的运费我都觉得简直是贵得离谱!更不要说外面一顿饭随随便便就是60+hkd,于是我还是老老实实吃完了这难吃的隔离餐...(小友今天问我为什么ins照片这么少,因为我是一个没有手机VPN的穷b啊!)
话说回来,出了酒店门以后鉴于对高德深厚的喜爱和信任,果断选择了高德找路并搜索附近文具店(有人告诉我文具店一定有打印🙄️)。在比上海临近赤道1488km的香港的八月烈日下我走了100米去找寻第一家文具店,走到门口在街上反复确认再三得出结论:它关门大吉了。更离谱是在我刚出门准备找店时,高德就给我了一个相反的方向,路的尽头是大海。好在我会看地图,在出发之前就意识到了此事,因而并没有放在心上,通过地图(而不是导航)找到了这家文具店。
其实我早该意识到,今天高德地图把我往海里导,就是这不幸的一切的开端。但那是的我还天真,还是用高德继续找了第二个距离400米的文具店,一路上在不同便利滴蹭了空调,才顶着烈日走到了第二家文具店的所在地。但在街上反反复复走了三遍以后同样以失败告终。好在对面就是地铁站,太阳简直把我晒成一滩水,融到地心里,免费的空调岂能不蹭!于是我就坐了地铁,去到身份证的地方。
入境事务处一看就是在市中心,大排面。此刻的我还心心念念想着要打印,于是用谷歌继续搜了一个文具店,辛辛苦苦过去以后被告知没有打印。路上遇到三联书店进去逛了一会,很遗憾没有找到西西(香港书店怎么能没有西西呢!),价格和上海的书贵得相当,于是吹够了空调就溜号了。

大众点评一搜,发现附近有家收藏了的川菜馆。隔离饭过分清淡吃得我对川菜饥渴难耐,于是兴致勃勃要去找这家川菜馆。可惜地址写的“xx街28号地下”,把整个街区兜了个遍都没找到地下的入口,倒是在路上遇到了一个打印店,终于把打印的事情解决了T~T。只要3hkd,比酒店便宜了75%,也不枉费我走了这一路。在打印的时候有一个流浪汉撞了我一下,我有点愣,想要说些什么却还是没说出来,老板和另一个打印的人早已见怪不怪。香港的流浪汉是真多,在cbd的街头和人行街道也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流浪汉。我在上海已经好几年没见过流浪汉了,刹那想到NYC据说也有此番情景,是不是健全的福利保障制度让无家可归的人都有了保障,因而便出现了更多这样的人?这个话题太大了,打住。
大太阳下街上人还是很多,大都走得很快,我想用往常的方法跟着一个人找路都行不通。就像一大盘沙一样填满了在高楼大厦之间的每一个缝隙,但所有人都走的那么那么快片刻间就消失在一栋楼里或是一个转角处,他们走得快而清晰,都朝着自己的道路走去,只有我走得茫然而毫无目的,不知道哪里才是正确的路。我想跟上其中一个人,但发现他们走进的高楼需要刷卡,而并不是我想去到的地下商场。于是我站在马路上,看着相互重叠的大楼,感觉自己仿佛也是最远处的那一栋,被其他所有所压盖着,难以呼吸。
这不是一种静态的压抑,它是会动的,就仿佛眼前的楼都移动了起来,你走向哪里它就跟往哪里,深怕让你放松一丝一毫。

我走到人行天桥,耳边传来都是异乡方言,因而不敢用语音输入暴露出自己身为他乡之客的惶恐和不安。走进一家M记,人群挤挤攘攘,不论是等餐的地方还是自助点餐的地方都是排队的人,自动点餐共三台机器,每台机器后都有五到六人的排队。是我见过人唯二多的M记,另一次是在午市时间在上海的几幢商业办公楼边上的时候。
你就是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陌生的环境里,哪怕身边经过的人长得再熟悉,无数的声音、文字、语言、街边的便利店、甚至垃圾桶的形状都能不断提醒你:你是一个异乡客,你不熟悉这一切。这种割裂感于我每走一步便加深一些,一致于要吞没我。
但是肚子还是饿的,于是在路过一家看似生意不错的冰室时便果断溜了进去。心里还窃喜到都是香港的茶餐厅肯定好吃,何况还有这么多本地人!
想着说不定能吃到此生最好吃的港料,踏着愉悦的步伐走进了店里。冰室生意确实好,一楼座位全部坐满了,服务员向我确认完我只有一人后便邀请我上楼就餐,而上楼后就没有服务员领路了,于是找了个角落的四人座就做。
角落的位置一直是很难叫到服务员的,作为一个90%吃饭都是single的人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一点。上海多是扫码点单,在服务员送菜的时候说上两句话就行了,因而对我也并无大碍。然而香港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城市,吃饭都叫服务员,餐后结账都是拿到前台用现金付。虽然小友也曾说我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但是我仍不认为我习惯于此。
首先在叫服务员时我就陷入了难堪。服务员很忙,难能有机会理我,在我两次同他示意以后才来拿着点单的笔和纸问我要点些什么。饭店里多是本地人,少有看菜单的,大都是直接告诉服务员想要吃什么并在十秒内结束点单。我想吃虾滑蛋,但是又想吃面,于是还是叫服务员帮我把菜单拿来,服务员从隔壁桌顺过一本菜单丢给我就忙去给别的桌上菜了。我对着菜单满是图片和繁体字颇有信心,想到又是中文汉字又是图片,这我还能点不成?
可我还是错了。在我第二次叫服务员过来点单后,我指着奶茶说“milk tea, cold”,但是他只听到“milk tea”,于是反问我“ice or hot”,我没有听清。他便怒吼似地问又问了一遍我“ice or hot”。我答“ice”。虽然这只是我耳背的误解罢了,但很明显我在他忙碌的工作中又增添了一点怒气。而后我翻到Noodles一页,想问xx是汤面还是炒面,在我犹豫时分由于我刚刚的耳背已经时他十分生气,他变大声怒吼着问我到底要吃什么,隔壁桌6个人公司聚餐的人转头齐望向我,我除了尴尬就是慌张就是恐惧,对着菜单随便指了一个steak牛肉相关的东西(隔离期间没有牛肉,我太想念牛肉了)就说this one. 他问我了一遍“r u sure”(其实我已经迷迷糊糊忘记他说什么了,已经被吓懵了)我还没来得及想明白他就收走菜单走了。
换做以往,我只能专注做一个干饭人来缓解这一切的尴尬了。但是在这一个从服务员到顾客都是香港人听不到一句英语或普通话的店里,我的单子一直没有上来,仿佛过了几百个世纪,我的手机从满电玩到低电量模式,都没有来。比我晚来,晚点单的人的菜都已经上来时,我的订单还没来...
我要感谢手机的发明,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发明让我避免了那漫长的等待,好在后来我还是等到了我点的东西,虽然在它上来后我只剩下瞠目结舌的能力。
我无法形容我看到那盘“面”时 的惊讶,它用我已知的食材拼凑出了一道我未曾想象的料理。我从未想到一大块steak可以和通心面配在一起,尤其是这个通心面还是浸泡在胡椒汤里。想来这种“中西结合”地如此精妙的菜品也只有出现在香港才能略显出一点“正常”吧。本以为上来的多是一碗出前一丁(我想吃汤面。。),就算不是汤面也是一碗炒粉,能难吃到哪里去呢!
结果这玩意儿甚至不如我的隔离餐。。。

胡椒汤太咸,肉嚼不动,唯一尚可的只有那杯港式奶茶,但是我的心永远只爱台式奶茶。“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大概说的就是我身在异乡对台式奶茶一点点的怀念。
对了,这个东西叫“牛扒通粉”,其实它名副其实,我的错。
说实话,在它最初被端上桌的那几分钟,我都不敢吃这个东西。是我从餐单上点出了什么离奇的东西,生怕刚刚看我被服务员骂的那几个人再次转头过来,用眼神的乜斜就足矣让我焦虑地想哭。
我坐在桌前,对着那道菜,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最后在那桌人走了以后才扒拉了两口,吃到后来,味道竟也能接受了。
但是在吃的时候还想着刚刚服务员莫名对我来的怒火,想到找不到文具店的彷徨,想到烈日骄阳的辛辣,耳边都是听不太懂的语言,还是觉得委屈觉得伤心。我以为我是一个还算坚强的人,但自从来到这个地方的第一天起我便感到了各种或明或暗的歧视,这不同于与一个人相处后由于它笨拙的行为而对它的偏见,这是一种带有民族主义的,从你出生开始就仅仅因为你的国籍、性别就对你带有的歧视。你无法摆脱它甚至自证清白,不论你是否从客观条件上优越于此,你都会难免遭受这种歧视。这种由于政治意义所导致的歧视更近似于一种洗脑,但谁相信的就一定是真理了呢?尽管我一直觉得歧视是一个很虚无缥缈的概念,因为其本身所带有地位不平等的潜在条件,但这条件可以是主观的。因此在你看不起我的同时,我也可以看不起你,谁也不必谁高贵。
后来在入境管理局碰到四个工作人员,三个人很友好,其中一个和善到我甚是感动,身在异乡,哪怕陌生人只施舍出如抽丝般薄弱的温柔都能触动一个人内心最深处的情感。唯一的一个工作人员不知是由于我的耳背(我是真的耳背,熟悉我的人都知道)还是Nationality原因对我很不耐烦。
Anyway,很难不发出“沒有疫情的時候,怎麼會有人選擇來香港讀書,這不是自讨苦吃吗”这样的感慨。
后来又去了港大,香港山形的地势确实不太熟悉,在平原地带从未走错过的我今天基本没怎么走对过,真的是找不到,該怎麼下到地下。
我还没有习惯于过马路先看右再看左,就像我无法习惯从手机支付到现金支付,每天上学都是在走山路(上坡或下坡)。我以为七天隔离积攒的雀跃和期待已经可以掩盖过对陌生的水土不服,我还是高估了自己。
它把我对自己的所有自信同认知一并打碎,把我的头按向水面让我认清自己的样貌。我尖叫挣扎但是都无法逃离它。我想是我适应能力太弱了吧,就像我初进高中时那般迷茫。
这座城市就像是它所拥有的风景那般:高楼密布,逼仄难耐,路上的人都步履匆匆,他们像唱歌一样准时准点对准了每一个音符和音调,在每一个停顿处停留地恰到好处而在我刚反应过来时就倏地走进了下一个音符,而我唱歌跑调,更难以熟悉这首歌的旋律。
当我以为一切都结束了,到酒店才发现因为我不喜欢给鼻子涂防晒霜,外加带了口罩闷了一天,我此时的鼻子和面包超人一模一样!除了我缺少了两块高原红。。希望明天不要疼地蜕皮,虽然我已经感到这个趋势了sigh
回想到中文选课没有选到,以及各种经历云云,总有一种窒息感拂面而来。更像是全身被埋进沙里,只露出了一个头看似可以大口呼吸着空气,殊不知每呼出一点气,沙便压缩一点空间,久而久之再难以完整的吸到一口气,烈日下的沙子吸干了我身体内的为数不多、残存的最后一点水分,也让我感到一种全身心的压迫及窒息。我看着我自己走向一个绞肉机,它搅碎的是梦想。
其实这一切的一开始也许就是错误的,这已不再是一个“向左走向右走”的问题了,是我是否还能再回到原点重新做选择。可是你又怎能让离弦的箭停下呢?它太快了,抓不住的。
“日子每天都很难过,但有些时候特别难过。”还会好起来吗?也许吧。
(一年后再来更新,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