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牛記(靈異 / 動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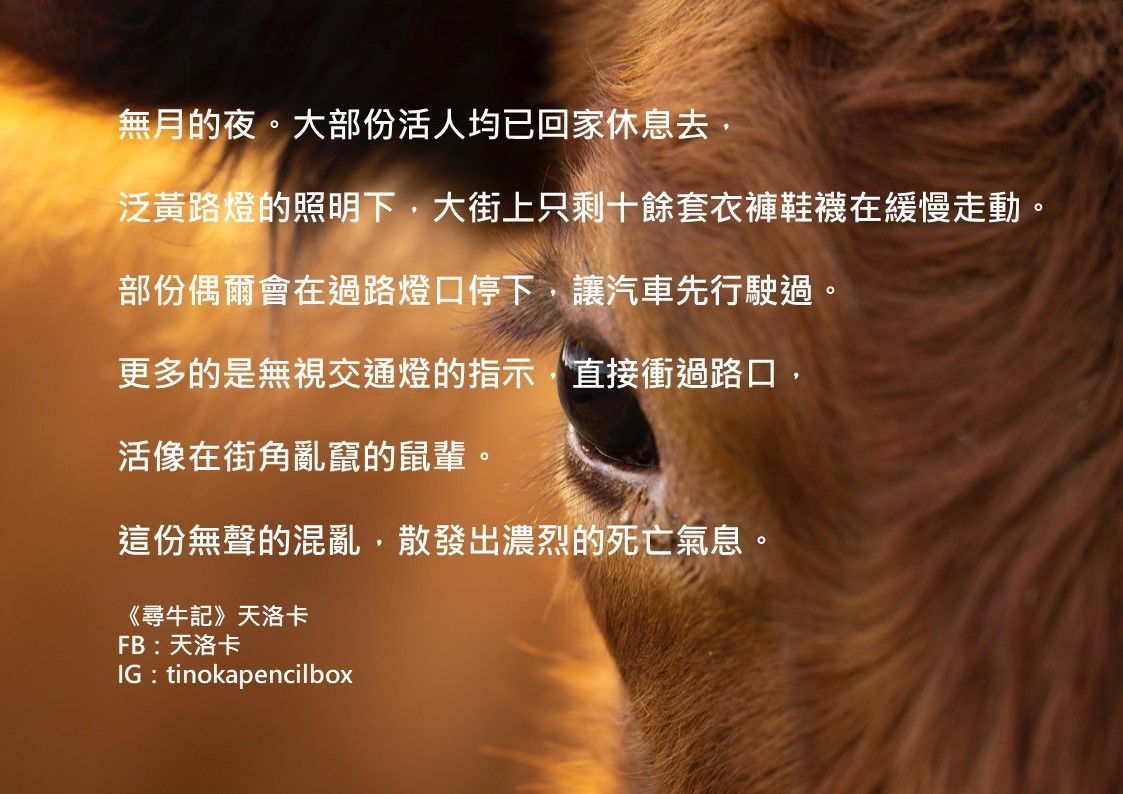
燃起盆內的炭後,我連忙狂灌紅酒。本以為要兩支紅酒才夠我不省人事,豈料一支經已綽綽有餘。很高興,我能在感受到熱力前昏睡過去,免卻更多痛苦……
不知過了多久,我漸漸恢復意識。
真是失敗的傢伙!連自殺亦告失敗。
我目光散渙,緩緩掃視四周。我正躺在地面,在床和房門之間。估是從床上滾下來。我望向火盆和剩炭的位置。咦?怎麼不見了?難道包租婆到來過?除了我,只有她有鑰匙。難道是為了免卻報警帶來的麻煩,乾脆取走火盆和剩炭作罷?我要控告她「擅闖民居」和「盜竊」!噢!我在亂想甚麼?我仍拖欠她租金……
勉力撐起身子,才驚覺自己一絲不掛。我徹底驚醒,連忙檢查身上有沒有傷口或甚麼的。沒有。挺直腰板站起來,金睛火眼環視四周。自己留在房內的行李袋、日用品、衣物、雜物等等,統統不見了。十分不對勁!難道我真的死了,自己正身處死後的世界?我是鬼魂?昔日看過的鬼電影,讓我很快就意識到自己已然死亡,是「鬼魂」。
可喜可賀!終於死掉了!我難掩興奮,馬上測試自己有沒有獲得甚麼超能力。
穿牆過壁!我直衝房門,不痛不癢就穿過門板,來到門外的走廊。冷不防,背面有「東西」撞來,利落地穿過我的身體,繼續開步走。一頂純黑色鴨舌帽、一件灰藍色男裝汗衣、一條深灰色三角骨褲、一對白襪和一對破爛波鞋,各安本分,併湊出一個人形,一個活生生的「東西」。
驚魂未定,我呆站原地,眼巴巴看著那「東西」掏出門匙,扭開門鎖,進入附近的單位,關門。十分平凡的舉措,以萬分不可思議的形式呈現出來。我意識到那「東西」是活人。他看不見我,而我亦算不上看見他。
我心神稍定,穿牆進入他的房間去。基本格局和我的房間一樣。一張鐵製碌架床、門後一個趟門衣櫃、門側一張小桌子、天花吸頂燈、窗口式冷氣機,沒啥特別。
他沒有開冷氣(包租婆徵收的電費貴得出奇),逕自坐在床上清衣落褲,甩鞋脫襪,只剩下一條內褲。內褲對上的位置,有一堆泥狀流體,沿著既定軌道排隊。位置較高的,色彩繽紛,依稀辨別得到是三絲炒麵的食材碎料;位置較低的,彎彎曲曲盤踞著,卻紊而不亂,由淺至深呈現令人不安的啡黑色,以濕潤至乾癟的質感訴說它能產生出何等嚇人的惡臭。
我轉身到其他單位參觀去。目不暇給。杯麵麵條被無支點的筷子扯到空中,自動輾碎成糊;鉛筆在書簿上飛舞,留下歪歪斜斜的醜字;一根香菸被火機點燃,在空中來來往往,將白煙硬推入無形的管道、兩瓣墨黑的氣囊。當白煙經管道和兩條小管逃出生天時,香菸亦慢慢消逝成灰……
單是遊覽大廈裡的單位,已花掉我大半天時間。到我下樓到大街時,天色早已入黑。街燈黃光依舊黯然,身邊卻是一番有趣的風景。無數衣褲鞋襪四處遊走,甚至穿過我的身體;車輛彷彿有思想的,懂得自行看交通燈號,適時開車或停車;商店的門自動開開合合,讓無人的輪椅安全內進;超級市場的貨品,佻皮地由貨架飄入購物籃,或是悠悠直接飄往收銀處,由旁邊的銀包為其付款;餐廳的廚房裡,刀起刀落,食材慘被利落砸斷……
我在廚房的角落看見正在溶雪的牛肉塊。淡紅的血水流在工作台上或滴在地上,再悄悄溜到溝渠裡去。肉塊是啡白色的,該已雪藏半年之久,死氣沉沉的。但就是這堆毫無生命跡象的肉塊,讓我再次察覺生命的「存在」。
這堆肉,是來自多少頭牛?那些牛生前會吃甚麼,糧或草?住的地方會否很逼狹,就像我住在劏房裡那樣可憐嗎?牠們會親眼目睹同伴被屠宰的過程或親耳聽見牠們的悽厲叫聲嗎?會傷心嗎?
「請問,有沒有見到一頭小牛走過?」有一成熟女聲從後傳來。
我初時沒有意識到對方是跟我說話,未有理睬她。但無視對方半晌後,我才猛然醒悟:怎麼我會聽到「聲音」?自我醒來一刻,我就沒有聽到過任何聲音。要不有如斯精彩的世界在眼前,恐怕我早已被這份異樣的寂靜嚇破膽。
我猛然回頭,和身後的一隻黃牛對上視線。我十分肯定,牠是看得見我,但我不肯定說話的是否牠。牠也是鬼魂嗎?曉講人話是牠的超能力嗎?
我搖搖頭,連退幾步,心生見鬼的恐懼。
「那真可惜。」黃牛沒精打采地搖搖尾,轉身穿牆離開,消失於我的視線範圍。
心神稍定,我才開始後悔。我該跟上去!可能會遇到其他鬼魂,從中得到更多關於鬼魂的資訊,甚或是知道「投胎」的方法。
衝到大街,已不見黃牛的身影。
牛!牛!牛!你在哪裡?我扯大嗓子,高聲喚叫。聽來很白痴,但我無所顧忌。該不會有認識我的「人」會看見我的滑稽相吧。
沒有回應。
我隨意跑向右邊。一直跑、一直叫,苦無回應。昔日由街頭行至街尾,需時二十分鐘;現在用上跑的,時間則更短,估計要十五分鐘。我這疏於運動的瘦削青年,一口氣接連跑了十五分鐘,竟沒有喘過氣,大腿小腿均不覺痠軟或抽痛,全然沒有肉體的負累。我會否還有甚麼未被發掘的超能力,可以有助我找到那頭黃牛?
飛?飛上半空,該可以看見牠的身影!我模仿小鳥的拍翼動作,拍動雙手,上下上下上下。可惜,雙腳不曾離地。難道我太重?難道雙手的力量不夠支撐身體?難道我根本沒有這種超能力?
「哈!」黃牛的聲音在我身後傳來:「你在學飛嗎?」牠面帶笑意,從不遠處緩緩走向我。
我被牠突如其來的現身打亂了思緒,變得語無倫次。是……不是!
牠的笑意更深。
真糟糕!我被一頭黃牛恥笑!
我在找你!我連忙換個話題,避開窘況。
「我知。我聽到你的喚喊聲。」黃牛收起笑意,換上鄙夷的眼神:「不過你一邊叫、一邊跑遠,教我該怎麼回應你?」在牠眼裡,我該是個愚笨的傢伙。
你可以大聲回答我,或是直接跑過來。我教牠。
「是你在找我,怎麼要我主動方便你?你又不是要給我甚麼好東西。」黃牛毫不客氣:「看你的狼狽相,該是剛斃命不久的。想要找個前輩來倚靠吧。」
被說穿了,我語塞。
靜默了好一會兒,牠率先邁步離開。沒奈何,我如喪家之犬一樣跟在牠身後。
不需再細分人行道和馬路,想走在哪就走在那。黃牛喜歡走在馬路中央。牠沿著兩條行車線中間的白色油漆記號走,四蹄故意踏在記號上。無聊又可愛。
「你不需要害怕。這裡沒有誰能傷害你。」黃牛心情愉快。
全世界只有我倆在?沒有其他鬼魂?我不明所以。即便細小如我城,按道理,每秒也該有數以千計的生命消逝。人類、黃牛、狗、貓、老鼠、蟑螂……醒來至今,早已過了大半天。除了這頭無禮的黃牛外,我沒有遇見過其他鬼魂。
「不!當然有其他鬼魂。不過,沒有緣份就沒有溝通的機會。」走在前頭的黃牛狀甚感慨:「此時此刻,我倆除了被『活物』穿過,同時被無緣份的『鬼魂』穿過。鬼魂的數量遠比活物多,但我們感覺不到對方的存在,亦溝通不了。」牠故意走上人行道,任由衣褲鞋襪穿過身體。「這是『朋友』告訴我的。牠無所不知。」
我跟黃牛有緣份?我想像到自己正被無數鬼魂同時穿過,但我無法想像到自己如何跟一頭素未謀面的黃牛有緣份。
「我有要事在身,不能照顧你太長時間。」黃牛想起了甚麼,眼神顯得落寞。
我強擠笑容。不如你介紹「朋友」給我認識,我就可以直接向牠了解更多,不需再麻煩你。
「你朝著那個方向一直走,就可以看見牠。」黃牛冷冷地用尾巴指往某個方向。
在清楚了解狀況前,和有經驗的黃牛分開,是不智的事情。我連忙想個動聽的藉口,好讓自己能繼續跟著牠。你要辦甚麼要緊事?需要我幫忙嗎?當是報答你的指導。根據剛才的對答,我相信牠有一定的智商和歷練,不會提出天方夜譚的要求。
黃牛愣住,仔細端詳我的表情,似乎沒料到我會主動提出幫忙。但我很有信心,牠會留住我:當智商去到一定程度,動物就會懂得使用工具,包括身邊的同伴。
「我在找兒子。」黃牛很感動:「我生前眼巴巴看著牠被人類帶走,沒能找回。現在失去肉體的束縛,才可以了無拘束去尋找。」
我馬上想到一個關鍵問題。假設相遇是必須講求緣份的話,黃牛找不到小牛的唯一原因,只會是「緣份已盡」。若是有緣份,無論如何都會碰上的。在約二千七百平方公里的我城,高樓林立的環境裡,我和黃牛在某小小餐廳的廚房裡相遇。除了緣份,還有甚麼能解釋茫茫宇宙中的遇見。
我沒有將這番話說出來,還裝模作樣地詢問更多有關小牛的事。
我們可以去牠逝世的地方試試看,看牠的鬼魂會否留在原地。小牛在哪兒去世的?
「不知道。」
我們可以去相關的地方看看。小牛生前有沒有甚麼喜好?
「用尾巴驅蒼蠅。」
小牛被人類帶到哪裡去?
「運牛車……」
基本上,所有線索都斷了。只能靠緣份。
每提及小牛一次,彷彿往黃牛內心插一刀。牠的步伐越益沉重,眼神越見哀傷,牛頭越垂越低,四蹄不再執著於馬路上的記號。我於心不忍,沒有再詢問關於小牛的事,甚至為了轉移黃牛的焦點,主動講述生前的見聞……
無月的夜。大部份活人均已回家休息去,泛黃路燈的照明下,大街上只剩十餘套衣褲鞋襪在緩慢走動。部份偶爾會在過路燈口停下,讓汽車先行駛過。更多的是無視交通燈的指示,直接衝過路口,活像在街角亂竄的鼠輩。
這份無聲的混亂,散發出濃烈的死亡氣息。
生前,總渴求死後世界的安寧;死後,卻覺得生前的世界更接近印象中的死亡。
生前,除了工作時間需要說話片刻外,其餘時刻都不需要溝通,枯燥乏味得與困在棺材等死無異;死後,我和一頭新相識的黃牛談天說地,分享活著時的所見所聞。
牠說牠的兒子右後腿有一塊紅色的胎痣。不愛吃草,但愛嚼草;我說我唯一的女友有一頭烏亮順滑的及腰長髮、精緻脫俗的五官、姣好的身材、白嫩緊緻的肌膚。性格單純可愛,善良正直……
「既然你愛她,為何你會選擇自殺?」黃牛畢竟是一頭牛,不懂得複雜多變的人類世界,沒能理解人類的思路。
有數之不盡的原因。我不打算詳述,以免對牛彈琴,白費唇舌。
「你已經死了,沒有肉體的束縛,你現在可以全心全意去愛她。」黃牛是單純的不明白,沒有批判之意。
還不行啊!我苦笑。執著於沒有好結果的感情,是很痛苦的事。所以,即便和女友的感情再深,我也決定將其埋藏心底作罷。
「原來人類的問題不會隨肉體消失?」黃牛衷心同情人類:「那可真糟糕!」
我無言以對。怎麼說?人類的問題確實沒有消失,但將我逼上絕路的問題已然全部消失。住屋、金錢、前途、道德、倫理、政治、家庭、事業、健康、生活環境……統統不復存在。
很悲哀。人生的基本事項,竟是我尋死的主因。而更令我感到痛心的是,世上絕大部份活人仍然需要面對它們。他們有沒有能力解決這些問題呢?如何解決呢?
不!我不該再為這些東西動腦筋。這不再是我的問題,而是活人的問題……
「或許,你可以守在她的身邊,直至她逝世。只要她一死,你不就可以馬上和她相見,永遠待在一起!」黃牛的腦筋挺靈活,很不錯。縱使牠漏算了人類沒有「一生只愛一人」這特質。
我正要開口否決牠的建議時,眼角瞥見藍中帶紫的天際泛起一片淡紅朝霞。頃刻間,來到唇邊的說話被莫名的寧靜驅散了。黃牛似乎看穿我的感受,領我去一個「好地方」看日出。
寬闊的大馬路上,四蹄兩腿齊齊拔足狂奔。無視迎面衝來的汽車,無視交通燈號,無視規則,只知向著日出的方向跑。跑著跑著,我突然發現自己是一隻正在跑道加速的飛機。跑到前邊那個交通燈口,我就會自然而然飛起來。
對!我一定會飛起來!
跑、踏、跳、飛!
雙腳離地,輕鬆趕上拋離我十多個身位的黃牛,還在牠面前來個花式飛翔表演。
「哇!」黃牛被迷住了,興奮大叫。亢奮的身影,在車水馬龍的鬧市中尤其奪目。
我回身俯衝,雙手一抱,將整隻黃牛帶離地面。牠比我想象中輕盈得多。是沒有肉體的關係嗎?管他的!快樂就可以!
朝霞顏色更見鮮豔,火紅鵝黃亮橙,誘人耀眼。黃牛驚恐至極,又叫又喊。我懶理牠,逕自飛得更高,高過附近所有大廈,得到一個遼闊無邊的視野。朝霞變淡,取而代之是一片無瑕的魚肚白。懷中的黃牛忽而安靜下來,靜待主角登場。金黃亮光先行開路,將眾生靈的注意力聚焦一點。太陽冉冉升起,令天上其餘色彩啞然失色。沒有肉體的限制,我放膽直視太陽。
純粹的白,純粹的光,純粹的能量。純粹的情感,純粹的快樂,純粹的愛。
「小牛!」黃牛高呼兒子的名字。
我高呼女友的名字。
明明知道對方聽不見,偏偏就是想叫喊出來!明明知道你再感受不了,偏偏我就是愛你!
太陽高掛半空之時,我們亦回到地面去。馬路上,並肩漫步,相顧無言,無視心裡頭的大量疑問,享受日出帶來的美妙餘韻。日正當空,我們來到海濱長廊。踱步,閒話家常,享受海面的粼粼波光。
「我決定了。」黃牛露出罕有的溫柔微笑:「帶你到『朋友』身邊後,我才繼續找兒子。你可以在『朋友』身上得到很多資料。那會對你找尋女友下落很有幫助。」牠竭力以自己有限的所知去理解我的世界,為我操心籌謀。果然是當媽媽的好料子。「我起初以為你在漫無目的地遊離浪蕩,現在才知道你也有想念的人。思念是很痛苦的事……」牠將自己失去兒子的痛苦,代入到我身上。
我眼眶濕潤,掃掃黃牛頭上的短毛,加以安慰。料不到,與這頭認識不到廿四小時的黃牛,會有如此深刻的情感交流。
「好!坐言起行!」黃牛立即換上一副精神奕奕的模樣,衝向護欄,四蹄一蹬,直墮海面。
風平浪靜,水花沒有為牠濺起。四蹄平穩地直立水面上,不受波浪影響,如履平地。牠回頭喚我跟去。
我望望大海,再望望自己雙腳,不期然憶起兒時遇溺的苦況:雙眼澀痛,刺鼻的泳池水無間斷湧入鼻腔口腔,四肢激烈亂舞卻抓空撲空。掙扎無果遠比一擊致命的痛快更見殘忍……
雙腳猶如釘在地面,久久不提步。陽光很美,大海很美,奈何我不敢上前。
恐懼面前,時間彷如無物。我的思維、大海的波浪、粼粼的波光,都靜置在恐懼當中。明明知道自己已然死亡,不會再經歷那種苦痛,為何就是放不下?
黃牛沒有催促我,輕輕抬頭莞爾一笑:「怕水?」
我點點頭。
「騎在我的背上吧。」黃牛前蹄曲下,半伏下來:「算是答謝你帶我飛天看日出。」
我毫不忸怩,馬上跳到牛背上起行。牛步四平八穩,不會顛簸。
我問黃牛,你怎麼能水上行走。
「覺得自己做到,就會做到。」
甚麼?
「覺得自己曉飛,就曉得飛;覺得自己能夠水上步行,就可以水上步行。」
你怎麼不自己飛起看日出?
「我畏高。」
我笑了,黃牛也笑了。
的確,起飛當刻,我純粹覺得自己可以飛,並沒有質疑過自己能否飛起,就像我認為鬼魂定能穿牆過壁那樣理所當然。
茅塞頓開。
我雙手一撐,躍下牛背,站在水面上。沾沾自喜,一臉得意:「好。到你!」
黃牛愣住,浮游於恐懼和快感之間。
說不定,你將來可以教小牛飛,看盡世界的好風景!
黃牛笑了,臉露神采,四蹄稍稍離開水面。
就是這樣!我鼓勵牠。四目交投,要牠忘卻高度,記住小牛精靈眼眸的深度。
「小牛!」牠高呼兒子的名字,就成功飛起來。
我尾隨牠,飛越港口,在離島著陸。
烈日當空,遊人稀疏,商戶店員在簷下陰影搖扇乘涼。我和黃牛浩浩蕩蕩來到古舊的廟宇。無人。香火疏落如禿子頭上殘餘的髮根。我抬頭望向那莊嚴卻滄桑的木雕神像。這自身難保的傢伙,就是黃牛的朋友?
「小牛終於回來了。」祂的聲音像柔和的風,又像滋潤的雨,是聆聽者心中的風鈴。
「不。還未找到小牛。只是發現一個人類鬼魂。」黃牛狀甚灰心。
「這是小牛。」神像肯定說:「小牛投胎多次,早已忘記曾經的『小牛』身份,亦忘記了你。」
不知是否我的錯覺,總覺得木訥的神像在望著我,以一種極其謐靜的目光。
「我怎會不認得小牛?」黃牛激動地喊嚷:「黑白分明的圓眼,右後腿有一塊紅色的胎痣,時刻擺個不停的牛尾巴,左額角有道小刀鎅成的疤痕……」
「記得你家的風景嗎?」神像的淡然,反襯出實相的殘忍:「柴枝和枯草搭成的棚,棚前的碩大黃枇樹,樹下的大片青草地……」
黃牛點點頭。
「它們還在?」神像以簡單的一句話,引出黃牛晶瑩的淚珠。
「不在……棚主老死後,子孫將地方賣給一個富翁。富翁僱人拆掉牛棚、斬掉黃枇樹、清走草坪,在空地上築起一間漂亮的大磚屋。後來磚屋被拆卸,先後改建成學校、住宅、大廈……」黃牛頓了頓,轉頭望向我,一臉不敢相信:「現在是一間餐廳……」
眼神相交,我大概估到黃牛在想甚麼:這就是我倆之間的緣份。
整個空間倏忽靜默起來,彷彿只有我和黃牛的存在。
我們的緣份並不是始於今世,亦未必始於黃牛知道的當世之中。很有可能是更久遠的過去。在地球誕生之前嗎?是在宇宙其他角落發生的事情嗎?不過,那全都不重要,因為我們連眼前狀況亦沒能弄清楚。
「昨天在街上流連,突然感覺到小牛在附近。我隨著感覺走,走到餐廳裡。找不到小牛的身影,卻看見你。我只把你當作和我有緣份的人類,沒料到你竟是小牛……」黃牛破涕為笑:「真糟糕!我竟認不出小牛。我真是個很糟糕的媽媽!」
不!不糟糕!世界時刻在變,認不出來,很正常。
「謝謝。」笑著笑著,黃牛的身影隱去了,消失無蹤。
心頭若有所失,眼淚在眶裡打圈轉。我轉身望向神像,冀祂能指點迷津。
黃牛到哪兒去?
「黃牛到了下一個階段去。」神像說。神情似笑非笑,既冷漠又仁慈。
我沒再多話,隨意找個幽暗角落躺著,好好整頓思緒。呆望漏光的屋簷,看見空氣中的微塵,有光又有影。它們緩緩飄落,穿過我,落到地面。渺小卻必然。和我一樣。
甚麼是「下一個階段」?
「投胎。」
甚麼時候會到下一個階段?
「當你不在這裡時。」
我如何不在這裡?
「當你不想留在這裡,你自然會離開這裡。」
我已不想留在這裡……
「不。你想。你仍然緊緊抱著這世界。」
甚麼?
「你認為鬼魂一定能夠穿牆過壁,所以你在死去不久已懂得穿牆過壁。當你覺得自己會飛,就馬上由不懂飛變成懂得飛。當你明白在水面行走的原理,你就可以立即踏步於在水面上。表面上,你接受了自己失去肉體這事實。
可是,移動時,你會用腳走路或用腳跑;你感知周邊環境時,會依賴眼睛;對黃牛說話,你依賴嘴巴和聲帶。事實上,你的肉體經已滅亡,你沒有腳、眼睛、嘴巴、聲帶。你只是習慣性地以為自己正在使用身體。你仍然未真正拋開你的『肉體』。」
那我就忘掉自己的習慣吧。行!
「要拋開你慣用的思考模式。例如,你一直聽到黃牛在講人話。但我告訴你,牠不懂講人話,純粹在吽吽叫。你聽到牠講人話,是因為你認為自己只聽得懂人話,加上牠是鬼魂,該有超能力。『懂得講人話』亦算得上是超能力的一種……諸如此類的。你仍然下意識地將自己在人類世界得到的觀念活用出來。」
那我就忘掉這些觀念吧。行!
「最後要放下執著。就像黃牛放下小牛一樣。」
我驀地想起黃牛的說話:思念是很痛苦的事。頃刻間,我分不清黃牛的最後表情孰悲孰喜,抑或是當中不包含悲喜。我亦分不清自己是否要堅決放棄那痛苦的事。畢竟捨棄痛苦的同時,對立的快樂亦會消散。
黃牛失去小牛會感痛苦,是因為牠擁有小牛時會快樂。
當初我選擇捨棄生命,是因為生存讓我感到痛苦。生存讓我感到痛苦,是因為我沒能擁有那些讓我感到快樂的。惟失去生命以後,我卻發現「那些讓我感到快樂的」大部份只是過眼雲煙而已。
無論生前或死後,唯一穩佔我心頭的只有女友一人。
昔日與她分離,是因為我自覺沒能照顧她。在這亂七八糟的城巿裡,人類能活得像樣已是很了不起的事情,養活父母、照顧妻兒更是人生的豐功偉績。我的人生結局,證明當日的分離是最正確不過的決定……不!不正確!決心分離和自殺才是真正斷絕緣份的方法!斷絕了人與人之間的緣份,亦斷絕了人與可能性的緣份!
我告訴神像,我決定多留一會兒。我想待女友死亡後,給她講解這裡的規矩,就像黃牛照顧我一樣。
「未必可行……你們之間的緣份已因你的自殺而變得極為淺薄。除非,你們之間互相存有十分強烈的思念。就像黃牛對於小牛的百年執著。」
原來黃牛已尋找小牛一百年……
「明白了沒?」
明白!無論結果如何,我這就去她的身邊,開始我的執著!心念一轉,眼前景觀立即粉碎成細末,瞬間重組成一個小小的睡房。床頭櫃上的相架,放有一位高貴婦人的相片。我認得那溫柔的笑容,屬於我曾經的女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