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帶到底有多憂鬱?
壹 憂鬱的熱帶
前段時間偶然聽聞了著名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的著作《憂鬱的熱帶》,這個書名頓時讓我沉陷了進去。
我個人其實對人類學並沒有什麼興趣,但是沒辦法,這個書名簡直絕美得讓我無法忽視它。
但是我對這本書的觀感其實並不太好,感覺全篇都是各種不明就裡的碎碎唸。但是後來我看了相關書評才發現,這其實並不是我的問題,而是這本書的中文版翻譯本身就不太好,就是會讓人看不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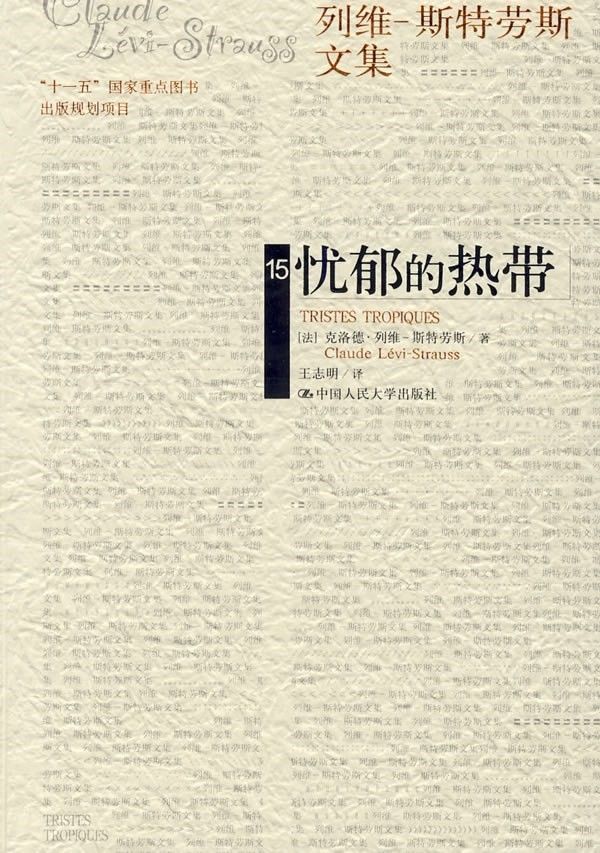
自新冠疫情一來,我就再沒出過國。也是因為自身消費水平的原因,我目前還沒有走得多遠,我絕大多數的腳印都印在了熱帶。
啊,熱帶,又是熱帶。
這可能正是《憂鬱的熱帶》吸引我的原因,我可能不知道熱帶有多憂鬱,但我確實在熱帶留下過很多快樂的回憶,並且因為無法回到熱帶而倍感憂鬱。
所以從頭到尾憂鬱的可能根本不是熱帶,而是我。
我記得我第一次自己出國大約是在2019年的年初,去的馬來西亞。
我最初抵達吉隆坡機場的時候,第一次看到了禱告室的存在。
我出去旅遊有個習慣——或者也可以稱之為惡習——我很不愛做攻略。一方面是因為我懶,另一方面是因為我覺得不帶攻略的旅遊最能看清一個地方的真實面目。
但我當時沒做攻略的程度實在是誇張到了一個新的境界。
事實上我也是前一年聽到朋友隨口說了一句馬來西亞有很多穆斯林,我才知道原來馬來西亞是一個信仰伊斯蘭教的國家。如果不是聽到朋友這麼說的話,我甚至可能會驚訝於吉隆坡機場居然有禱告室的存在。
當然不可避免的,我還是被驚訝到了。
因為接待我的海關大姐姐是個印度人,事實上在抵達海關之前我就已經看到了很多印度人。然後我查了一下才知道,原來印度人居然是馬來西亞的第三大族裔,僅次於馬來人和華人。
當然也是因為對於當地過於不熟,擔心會錯過很多別樣的風情,所以後面像這種懶到連主體民族和基本歷史都不去查的情況也基本被我自己杜絕了。

因為是乘坐的紅眼航班,我到達民宿的時候天都才蒙蒙亮,天氣也還算涼爽,似乎是熱帶特有的一種鳥兒一陣一陣地叫著。
這種鳥的叫聲就像口哨一樣,但是音調卻是像拼音中三聲一樣的變調。這種鳥叫在我去過的每個東南亞國家都有遇到,讓我一度以為這是東南亞特有的鳥類,也一度成為我對東南亞的一個記憶印記。
後來有一次我去樂山的時候也聽到了類似的鳥叫,勾起了我很多旅行的回憶。
但是後面事情走向其實有點超出控制。
我當時租住的民宿是一個兩室一廳的房子中的其中一間臥室,房子位於吉隆坡市中心,一晚上卻只要90人民幣。
房東是個中國人,她當時已經回國,而她的一位朋友暫時借住在她家。
所以這個時候我就遇到了一個問題——因為兩間房的房門都是關著的,我並不知道他朋友睡的哪間房。
我沒有辦法,只有在早上大概八點鐘的時候給房東發消息,但是她似乎還沒起床,並沒有及時回我。
最開始的等待還算比較平和。
這棟公寓的過道是開放式的,所以開門就是室外,還可以聽到各類鳥鳴。那時太陽還沒完全升起,熱帶的濕氣還沒有顯現出它的威力。當時已經有一些老年人起床晨練,運動的喘息聲和踏步聲配合著鳥叫,一度讓我覺得待在這種濕噠噠、黏糊糊、又帶點清涼的空氣裡是一種非常難得的悠哉的體驗。
但是隨著太陽的升起,一切都變得不太對勁。
我感覺空氣仿佛是一瞬間熱起來的,清涼和愜意瞬間消失不見,只剩下濕噠噠和黏糊糊。
因為當時我還穿的冬裝(我十分沒有經驗地沒有在機場提前換好衣服),甚至與我而言,連黏糊糊都成了一種奢侈。我只感覺自己仿佛處在了一個巨大無比的烤箱裡——不是蒸籠,而是烤箱,比蒸籠還要讓人窒息的烤箱——仿佛每一吋皮膚都要裂開一樣。

眼看著氣溫向著30度狂奔,我實在忍不了了,只有給房東打了個電話。隨後房東掛掉了我的電話,終於開始給我回消息。
當我終於入住了屬於我的房間之後,我立刻換上了夏裝、打開了空調。
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的熱帶確實是憂鬱的。早上的愜意就像是空中略過的一道閃光,甚至連影子都來不及留下,就被熾熱的陽光瞬間摧毀,剩下的就是一片燎原的烈火。
這種憂鬱是別緻的,它不同於那種陰冷的、灰暗的感覺,而是一種仿佛被黏在了加熱的罐頭裡,無法脫身的絕望感;是一種好像在美國西部公路上狂奔了一夜,抵達了一個連風滾草都懶得光顧的墨西哥小鎮後狂飲一杯啤酒過後的頹廢感;是一種粗糙的壯碩男子渾身帶著黏膩的汗液,赤身躺在沼澤冰冷的水塘裡,卻仍然無法擺脫那種空虛感時產生的無助感。
總之,它熱,它狂躁,它野蠻,它憂鬱得別緻。

在我換掉衣服過後,空調把房間的溫度降下來之前,我終於變回了熱帶應有的樣子——濕噠噠、黏糊糊,而不是像烤箱裡考過頭的老麵包。
我當時翻了個身,終於意識到自己正處在亞洲大陸最南端的一個小角落裡,離自己的家鄉已經有了十萬八千里。彼時家鄉的人們正穿著棉服在通勤的路上奔波,我卻穿著短袖短褲,把空調調到了26度,家鄉的一切似乎都與我切斷了。
“你在南方的艷陽裡,大雪紛飛。我在北方的寒夜裡,四季如春。”《南山南》的歌詞這樣寫道。
可是我在的南方沒有大雪紛飛,我所在的南方,它熱得一匹。
貳 沒有鴨店的城市
我在吉隆坡呆了大概三天,但卻想不到有多少可以寫的東西。
這個城市怎麼說呢,我當時不知道怎麼形容,現在想來也還是只有用“憂鬱”來描述。
我有個喜歡環球旅行的好友這麼形容吉隆坡:發達但無趣。
馬來西亞畢竟是穆斯林國家,處於伊斯蘭教義的限制,國內能消受的娛樂活動並不多。
踏遍整個吉隆坡,能逛的無非就是柏威年商場、吉隆坡塔、石油雙塔這類總歸是偏於現代、沒有太多文化積澱和娛樂渠道的地方。
不過要想在熱帶完全逃避世俗,我覺得還是挺困難的一件事。
當一個地方一旦被悶熱所籠罩,人們的情緒就會不可避免地曖昧起來。這種曖昧可能是下巴上凝聚的一滴汗珠,可能是嘴角被黏住的髮絲,也可能是冰冷酒杯上滑落的一滴情愫。當熱烈的氣氛一旦被烘托起來,世俗就會像潮熱的濕氣一樣無孔不入。
我住的民宿就在吉隆坡的酒吧街附近,每晚我都會去那裡逛一逛,稍微驅散一下這座熱帶城市的憂鬱氣息。
我其實想說的是,即便是以伊斯蘭教建國,這裡至少還是保留住了一些燈紅酒綠和超短裙。
但我確實不感興趣。我對酒不感興趣,對超短裙妹子更不感興趣。當媽媽桑們帶著熱帶的世俗氣衝上來圍住我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倉皇逃跑。
不過,吉隆坡可能沒有鴨店,但是它卻有絕味鴨脖。
唉。

叁 腦子裡的小人
我曾經在網上看過一個問題,討論熱帶為什麼沒有發達國家。後來有一篇文章指出,熱帶氣候會讓人沒有幹勁,地區發展也就比較慢。
烈日下的吉隆坡確實沒有一丁點生氣,城市裡幾乎所有的碳基生物都躲在室內或是陰涼的地方。但即便是躲起來,他們大多也是沒有什麼活力的,這可能也是熱帶特有的喪感。
照這麼說來,那篇文章確實有它的道理。

不過印度人確實算其中的例外。
印度人總是能在各種惡劣的環境裡表現出他們的活力,即便熱如吉隆坡,我甚至都在獨立廣場這種被陽光暴曬、沒有一點遮陰的地方,看見兩個印度人在烈日下打架。
我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會選在太陽下打架,可能只是因為這樣比較有儀式感吧。
在過去我就對印度人的奇怪性格有所耳聞,我很多見過印度人的網友都說印度人性格極其跳脫,且不靠譜。
在印度的電影中,裡面的人們隨時隨地都會跳起舞來。我不禁在想,這種畫面描繪的其實並不是印度人的生活,因為並不會有人走著走著就開始唱歌跳舞,但你要說這事印度人的內心世界,我大概是相信的。
印度人的思維之所以跳脫,我想可能就是因為他們的腦子裡有一群小人。這群小人每天什麼都不幹,但興致來了就會開始唱歌跳舞,而此時此刻的印度人,也會開始做一些跳出常理的事情。
我在吉隆坡的小印度打車的時候,毫不意外地打到了一位印度大叔的車。
說他是大叔其實並不完全準確,他應該叫大哥。
大哥梳著油亮的大背頭,戴著墨鏡。他上衣穿的是一件緊身的白色襯衣,漏了兩顆釦子,露出了一點點胸口,他下車來迎接我的時候我看到他的胸肌向我撲面而來。他手臂上的肌肉也剛剛好,剛好把襯衣撐滿,但又不會讓人覺得肌肉過量而顯得油膩,手腕上還戴了看上去似乎很貴的手錶。他把襯衣扎進了緊身的黑色西裝褲,緊身的褲子讓他的大腿看上去粗壯有力而修身的版型則顯得小腿十分修長。
總之,一切都非常完美,一個自律中產精英的形象呼之欲出。
直到我的目光繼續下移,我兩百度近視的眼睛,看到了一雙
人,字,拖。
當時我多麼希望我的眼睛是兩千度,這樣我就會看不到他的人字拖,然後我的記憶就會止於他的緊身西裝褲。
可是我看見了,我看見了他的人字拖,他中產精英靈魂背後隱藏的人字拖。
而我唯一能想到他會這麼搭配的原因,可能就是他在出門穿鞋的時候,腦子裡的小人突然跳起了舞,然後他的眼神突然渙散,全身仿佛不受控一樣,如同一個提線木偶一般,全身僵硬地從鞋櫃裡拿出了那雙人字拖···至於為什麼會拿出人字拖,他們可能自己也不知道,畢竟這些事情都是無意識的,就像被下了迷藥的受害者,反正他們就是這麼做了。
啊,我懂了,那些小人其實是印度人的祖先給他們下的蠱,可遺傳的那種。
肆 廁所裡的大草原
不久後我離開了吉隆坡,去到了檳城。
檳城這個地方,我對它的了解比吉隆坡還要少。我很早以前在一個朋友那裡偶然聽過檳城這個地方,並且聽說這裡很有特點。
但至於有什麼特點、好不好玩,我一概不知。我只是在訂機票的時候發現從吉隆坡往返檳城只要人民幣120塊,我就決定了去檳城(實際上我都買貴了,前一天我看的時候只要90塊)。
檳城的民宿的房東是一對華人夫婦,為人非常熱情,對檳城的各類特色如數家珍,我到的當天就給我洋洋灑灑地講了一個小時的旅行攻略。
你要問我為什麼會聽那麼久,可能真的只是因為我對檳城一無所知,而他們也沒想到真的會有一點攻略都不做的大傻子來這裡玩,所以把檳城介紹得無比詳細。

房東最驕傲的當屬檳城的美食。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檳城確實是東南亞知名的美食之都。
不過話是這麼說,但我在吉隆坡的一些經歷實在讓我對馬來西亞的料理有些提不起興趣。
我當時在吉隆坡的一家燒烤店吃晚飯,在店家的推薦下點了一份生蠔。
當時店家問我:生蠔是要烤的還是生的?
內地的學生在以前都學過一篇課文,叫《我的叔叔於勒》。在這篇文章中,於勒叔叔的工作就是在輪船上賣生的生蠔給富人們享用。
文章中描述的生蠔對於內陸的孩子來說有著十分致命的誘惑。這不僅是因為內陸的孩子很少能吃到生蠔,而是莫泊桑描繪出的,生蠔那種爽滑、細嫩、直接從喉頭滑進胃裡的內容,對於貪吃成性的小孩來說實在是太要命。
我真的太好奇生的生蠔的味道了。
“要生的吧。”我說。
然後我發現,莫泊桑真的是一個非常棒的美食帶貨博主。
這裡並不是說莫泊桑的描繪有多麼精準,恰恰是因為我發現他居然能把這麼致命的食物描繪得這麼美味···
當然,也可能是因為我這種內陸來的小孩兒吃不慣。即便是加了檸檬,那股把我天靈蓋都掀翻的海腥味還是讓我無福消受。
緊隨而來的,是生蠔對我的復仇。畢竟我吃掉了它們,卻在心底貶低了它們,是絕對的得了便宜還賣乖,所以遭到了生蠔慘烈的報復。
在晚飯後的三個小時裡,我一共去了四趟廁所。
但我第四次坐在馬桶上時,我看到廁所的墻壁開始一點一點地淡化,然後逐漸變得透明,旁邊的洗臉池、花灑、梳妝鏡也慢慢地消失,唯一沒有變化的只有我座下的馬桶。
墻壁的背後不是廁所隔壁的臥室,也不是一篇虛無,而是一片大草原。草原一望無際,放眼望去是一大片有點發黑的草綠。草原上有一些微風,耳畔是風兒在曠野中穿梭形成的輕微的呼呼聲。
我整個人就坐在這口曠野中的馬桶上,微風把頭髮絲吹進了我的眼睛,讓我有些看不清遠處。但我能聽見,能聽見青草在風中搖擺的聲音,就像我的髮絲一樣。
我曾在雨後空無一人的北京地壇公園裡漫步,曾在夏夜海濱酒店的陽台上聆聽蛙鳴和浪湧,也曾在只有山泉流動聲音的密林裡穿梭,但其帶來的放空感都不及這個大草原上的馬桶。
電影《猜火車》裡,在全蘇格蘭最臟的馬桶下有著最蔚藍的海洋。而在吉隆坡,最便宜的民宿的馬桶旁,是世界上最空曠的草原。

再說回檳城吧。
老實說,檳城的美食,或者說房東給我推薦的美食而不是那些我自己去找的奇奇怪怪的美食,確實味道都還不錯。
但是各位讀者,請不要忘記了這篇文章的主題——憂鬱。
這趟旅程我所踏足的這些熱帶城市,都是憂鬱的,我也是憂鬱的。所以我的覓食之路,一直都走得並不算特別順暢。
當時在房東的推薦下,我在第二天中午去嘗試了一家印度菜餐廳。
啊,又是印度。這麼說來,我在檳城所經歷的一切憂鬱都起源於印度人,印度人才是其中的罪魁禍首。
我當時並不能看懂他們的菜單,只是簡單地對店員說了一句:你給我推薦一些吧。
後來他大概給我推薦了二十多馬幣的菜,我都唏哩呼嚕地吃完了。味道,確實還是很不錯的。
但我下午就遭遇了嚴重的消化不良。
我很早以前就對與印度菜對消化系統的不友好程度有所耳聞。印度菜大多喜歡製成糊狀,而且還會有很多菜是非常乾硬的麵食,這就導致印度菜非常管飽——以及難以消化。
總之,那天一直到了晚上七八點我都仍然感覺肚子很脹,晚飯也沒有吃。後來迫不得已,我去找房東要了一些助消化的藥物。
當時房東順口問了一句:你到底吃了多少啊?
我說:二十多塊錢吧。
房東當時愣了一下,說:我平時去那裡也就吃個十來塊錢。
所以那個店員是直接給我上了雙人份的量,而且,我還全都給吃完了。
反正那個店員和我,我倆之中肯定至少有一個腦子不正常。
到了第二天中午的時候,我的肚子仍然很脹,但我全身卻沒有一點力氣。
嚴格說來我已經有三頓——也就相當於一整天——沒有吃飯了,我身體的能量已經透支,但我卻絲毫不覺得餓。
所以沒有辦法,就算肚子很脹,我也得強忍著去吃飯。
出於對腸胃的考慮,我決定去吃房東推薦的椰漿飯,因為它聽上去就很清淡。
但我萬萬沒有想到,椰漿飯居然是辣的。
我更沒有想到的是,提供餐位的華人大媽會把我說的“牛奶”聽成“牛奶冰咖啡”。我原本是想點一杯牛奶養養胃,然而她卻給了我一杯咖啡,還是冰的。
總而言之,原本就嚴重消化不良的我,在吃過冰火兩重天的午飯過後,渾身近乎虛脫,每走一百米就得坐下來休息一下。
也許是因為沒有坐在馬桶上,吉隆坡的草原並沒有再次襲來。但是那種把靈魂都放空的憂鬱感,卻一路從吉隆坡追到了檳城。
伍 憂鬱的尾聲
這場旅行不長不短,剛好一周,三天吉隆坡三天檳城,剩下的一天送給了機場。
我變得了解馬來西亞了嗎?沒有,我甚至連吉隆坡和檳城都不甚了解。
我變得熱愛馬來西亞了嗎?沒有,因為它並沒有給我留下很多印象深刻的好印象。
我因為此次旅行變得更加博學了嗎?可能有,畢竟不是每個地方都能看到正裝配人字拖的印度大哥和坐落於大草原之上的馬桶。
其實我知道,給這樣一趟平平無奇的旅行冠以“憂鬱”的名頭並且將其作為貫穿全文卻又顯得完全不必要的主題來妄圖讓這篇文章變得高端一些的操作,似乎是顯得有些裝逼了一點(第一章可能算是個例外)。
這樣一個主題也並不好,因為它讓我錯失了能夠寫有趣的事情的機會,導致我只能將內容放在了人字拖、嫖娼或是腹瀉之類的屎尿屁的事情上。
但是沒辦法,當我看到《憂鬱的熱帶》的時候,我腦子裡蹦出來的第一個地方,就是馬來西亞。
至於馬來西亞是不是真的很憂鬱,其實已經不重要了。當我第一反應是馬來西亞的時候,就說明它在我潛意識裡的形象就已經是憂鬱的了。
馬來西亞人可能也沒想到,自己居然會因為嫖娼或是腹瀉之類的事情被一個外國遊客冠上了“憂鬱”的名頭。
“你才憂鬱,你全家都憂鬱。”
馬來西亞人如是說。
“靠北,你們怎麼知道我和我媽都有憂鬱症。”
我也如是說。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