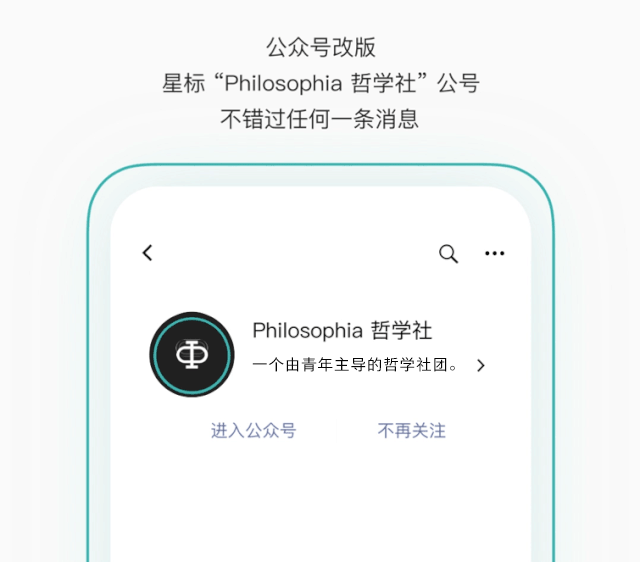汉娜·阿伦特的政治学 / 哲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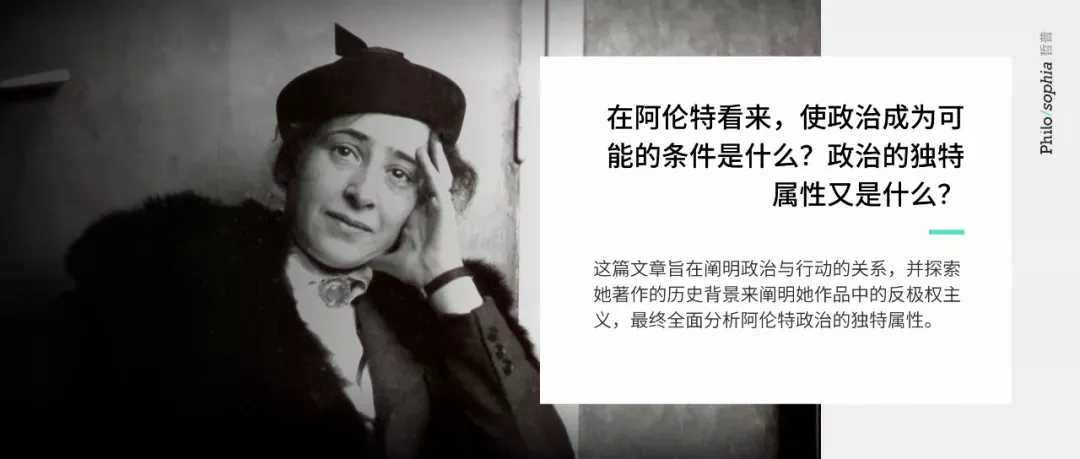
「本文于 2021.7.3 原载于公众号philosophia哲学社」
作者 / 乌断
1 概述
汉娜·阿伦特对政治的定义可以被最好地理解为对人类多元性和自然性的捍卫,及对抗现代性的极权主义倾向,而这只能在掌握她的哲学体系后才能充分理解这一点。她的政治取决于公共自由和对必要性的掌握。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自发的、表达性的、交流性的,但也是不可预测的、捉摸不定的和脆弱的。在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我将解释阿伦特关于人类境况的三元理论,然后通过阐明政治与行动的关系,将她的政治理念置于其中,并最终概述其前提条件。在第二部分,我将通过考察她的方法和探索她著作的历史背景来阐明她作品中的反极权主义,在她的各种作品之间建立联系,并最终全面分析阿伦特笔下的政治的独特属性。
2 政治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
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认为,人类境况是三方的,包括劳动、工作和行动。由于政治取决于人类的多元性,虽然自然性是「政治思想的核心范畴」,但政治与行动领域的关系最为密切。[1]
劳动对应于人类生存的生物层面,包括无休止的重复性生产和消费。[2] 在劳动领域,人类是劳动的动物(animal laborans),他们的时间概念遵循自然界的周期性节奏,因为他们像动物一样追逐无休止的必要性循环。[3] 然而,人类的存在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其运动的直线过程」[4],它贯穿了「生物生命的循环运动」,而这种直线性反映在人类独特的工作和行动领域。 [5] 在「工作」领域,人类是技艺人(homo faber):「世界的建设者和事物的生产者」,能够驾驭自然,制造出比自然的消费循环更持久的人造物品;因此,在「工作」中,人类能够展现出自己与动物的区别。[6] 然而,「工作」的产品获得了一种异化并外在于生产者的线性生活,因此「工作」是人造的,但不完全是人的。只有在「行动」领域,人类才会通过「行动和言说」在同类中宣称自己的个体身份:「工作」证明了人类创造能力的集体伟大,而「行动」则允许多元性,即人类的独特性,而不是集体的「人类」,这使得个人的故事可以得到讲述。[7] 更重要的是,通过允许多元中的独特性,「行动 」实现了「人类的自然条件」,这意味着正是通过言行,每个人都能够采取意想不到的行动,具有自发性,并为世界带来一些「独特的新事物」。 [8]
「行动」抓住了人类生存的直接性、动态性和自发性,这是政治的基石,而它劳动和工作中基本没有。[9]尽管政治不能脱离劳动(生存)或工作(人造),但只有行动才是政治活动的精髓,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没有明确区分政治和行动,可以说是反映了它们在概念上的接近。[10] 如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科学教授Andrew Norris指出,正是在政治行动中,人们宣称自己的公共身份,并在此过程中将自己与其他人类联系起来,从而赋予「作为人」的意义。[11] 此外,只有在行动中,权力才会产生:对阿伦特来说,权力的实现「只有在言行未分离、言谈不空洞、行迹不粗暴的地方」才可能,也就是说,当言语和行为本身就是目的的时候;权力是一种动态的潜力,在人与人之间「当他们一起行动的时候」涌现,「在他们散开的时候就消失了」。[12]阿伦特对暴力和权力进行了区分:暴力是工具性的,它本身不能获得任何政治合法性,而权力则是从集体行动中产生的,是合法性的根本来源。[13] 这对韦伯的「目的论」框架提出了挑战——韦伯认为暴力(胁迫)是政治的核心,因为它是实现政治目标的基本工具。就此,她提出了另一个强调集体协议和团结的「交流性」框架。[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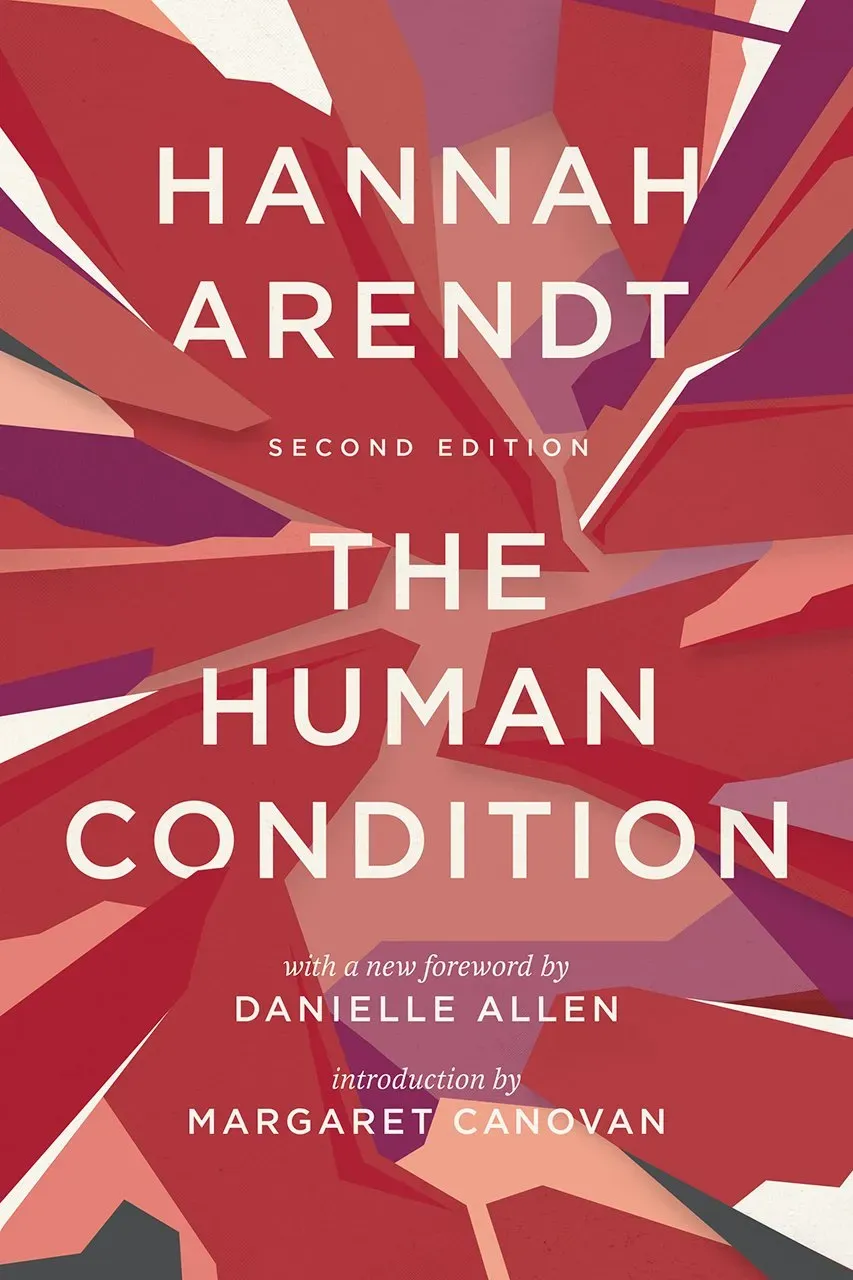
在《人的境况》中,阿伦特断言,从古希腊的意义上理解,政治本质上是行动和言说,[15]其前提条件是自由。自由一方面需要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另一方面需要一个掌握必需品的私人家庭。[16] 古代意义上的自由既意味着摆脱困境的自由(freedom from necessity),也意味着与平等同伴交往的自由,[17]这对政治来说是必要的,因为前者将人从劳动的维度中解放出来,而后者则使人能够从事行动的维度。在《政治与自由》中,阿伦特认为,「如果不谈论自由,就不能谈论政治,」她强调了后者,说自由是「把以前不存在的东西召唤出来的自由」。公共领域是与同伴交往的自由的先决条件,因为它是一个允许人们「被他人看到和听到」的舞台,并允许「无数的观点和方面」来说明「一个共同的世界」;换句话说,它是人类多元性的体现,意味着公共性和多样性,而自然性(行动)只有在有多元性的地方才可能。[18]公共领域反过来又要求存在一个隐秘的私人领域,阿伦特将其等同于私有财产[19],因为一方面,古代的私人领域,即家庭,是一个人的必需品被管理的地方(通过对妇女和奴隶的统治),没有它,人就无法超越劳动,进入共同的自由公共世界。另一方面,从更形而上和不那么残酷的意义上说,只有从私人领域,人们才能「升入视线」,进入公共领域。如果没有私人领域庇护人们免受无尽的宣传,不仅生活会变得「浅薄」,而且公共本身的意义也会丧失。[20]
如牛津大学国际关系教授Patricia Owens所说,阿伦特关于政治的论点是「主要通过否定来构建的」[21],并且最适合被视为对现代政治或者现代性的批判。她在《人的境况》中对政治的论述具有独特的难以捉摸和形而上学的特点,这不仅是因为它植根于对人类状况的整体哲学分析,而且还因为她独特的注重语源学的方法。她没有给政治下定义,而是探讨了与政治有关的各种词汇的古希腊、罗马和教会的起源及其应用;她不以历史为例,而是倾向于分析政治生活(bios politikos)和积极生活(vita activa)的含义变化背后的含义。这主要是因为,如政治理论家谢尔顿·沃林所说,她打算找回在现代化过程中丢失的「过去伟大的政治理论」,以「照亮现在的困境」[22]。尽管她并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想找回「佩里克利斯式的民主」或「荷马史诗般的集会」[23]。在《人的境况》的序言中,她声称她并不打算「提供一个答案」或参与「实际的政治」,而是「从我们最新的经验和我们最近的恐惧的制高点」来重新考虑人类的状况[24]。她通过「对古希腊政体的理想化描述」来阐述她的政治概念[25]——沃林批评她「歪曲历史」是对的[26],但她关注的是现代政治世界的不足和偶然性,而不是历史本身。她对政治的描述更多地反映了现代政治中缺乏的东西,而不是历史中真正原先存在的东西。

她对现代政治的批判(以及对更广义的现代性本身的批判)在她对霍布斯、马克思和韦伯的批判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对她来说,现代性的错误在于把工作归于劳动,把行动归于工作,而这两个错误往往是相互关联的。阿伦特认为,霍布斯的政治概念建立在政治对「社会」的错误征服上:她声称,霍布斯的政治所保护的东西,正是一个由无情的收购者组成的社会。[27]他忽视了关键的「公共和私人」的区别,将与「维持生命」有关的事务公共化,因此将政治变成了以保护为目的的行政管理,通过用工作建立一个伟大的利维坦,使得行动屈从于劳动。[28]其结果是,积极的政治被理性主义的、工具性的技艺人的工作所取代。[29]
同样,马克思也是政治屈从于社会的产物:在阿伦特看来,政治只是社会利益的反映这一说法,本身就体现了家庭(自然-劳动)的「非自然增长」;而马克思本人也生活在霍布斯之后的现代,其中公共领域已经「消亡」(wither away)并成为行政管理。[30]此外,马克思将工作归入劳动之下,并主张通过发展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以从劳动(必要性)中解放出来,其结果并不是解放,而是将悠久的工作技巧瓦解在无情的消费循环中,因为大规模生产只会创造更多的贪欲。[31]在阿伦特看来,马克思的现代性是对消费主义社会的治理。
她对韦伯的批评没有那么直接——但是,在她对官僚机构「作为最社会化的政府形式」的批评中[32],以及对潜藏在「技艺人」思想中的暴力工具性的批评中[33],韦伯所描述的以国家垄断合法暴力和官僚机构为特征的现代政治显然是被指涉的对象。[34]简而言之,对阿伦特来说,这三位哲学家的政治概念中(以及延伸到整个现代政治中)都没有自发性和多元性这一根本性的人类维度。
3 阿伦特政治的独特属性
阿伦特对多元性和自然性的再次强调,以及她对现代政治的批判,都可以说是源于她对极权主义的反思。她亲身经历了纳粹主义,并观察了斯大林主义的恐怖,这是现代社会中两个最令人发指和最没有人性的政治制度。她的著作中从未缺少对现代哲学的怀疑,而现代哲学使得这种恐怖机器成为可能。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认为,正是对任何行动的可能性的破坏,以及通过将所有人捆绑在一起成为「大写的单个人」( One Man of gigantic dimensions)来消灭人类的多元性,才使得极权主义恐怖与一般暴政区分开来。[35]因此,极权主义的危险性并不仅限于其残酷性,因为它不仅摧毁了人的肉体,还通过阻止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自发性来熄灭公众身份的可能性,从而使每个人都可以被替代和摧毁,并在这样做的时候否认了人类个体的人性。[36]而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她认为大规模屠杀的核心是在纳粹官僚机构中的人放弃了个人自主性和良知——极权主义恐怖的实施者往往是拒绝思考和行动的「正常得可怕」的人,而不是虐待狂。[37]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诊断为极权主义所缺乏的东西,正是她在《人的境况》中加以肯定的政治的本质,因此可以说她的政治概念从根本上是反极权主义的。[38][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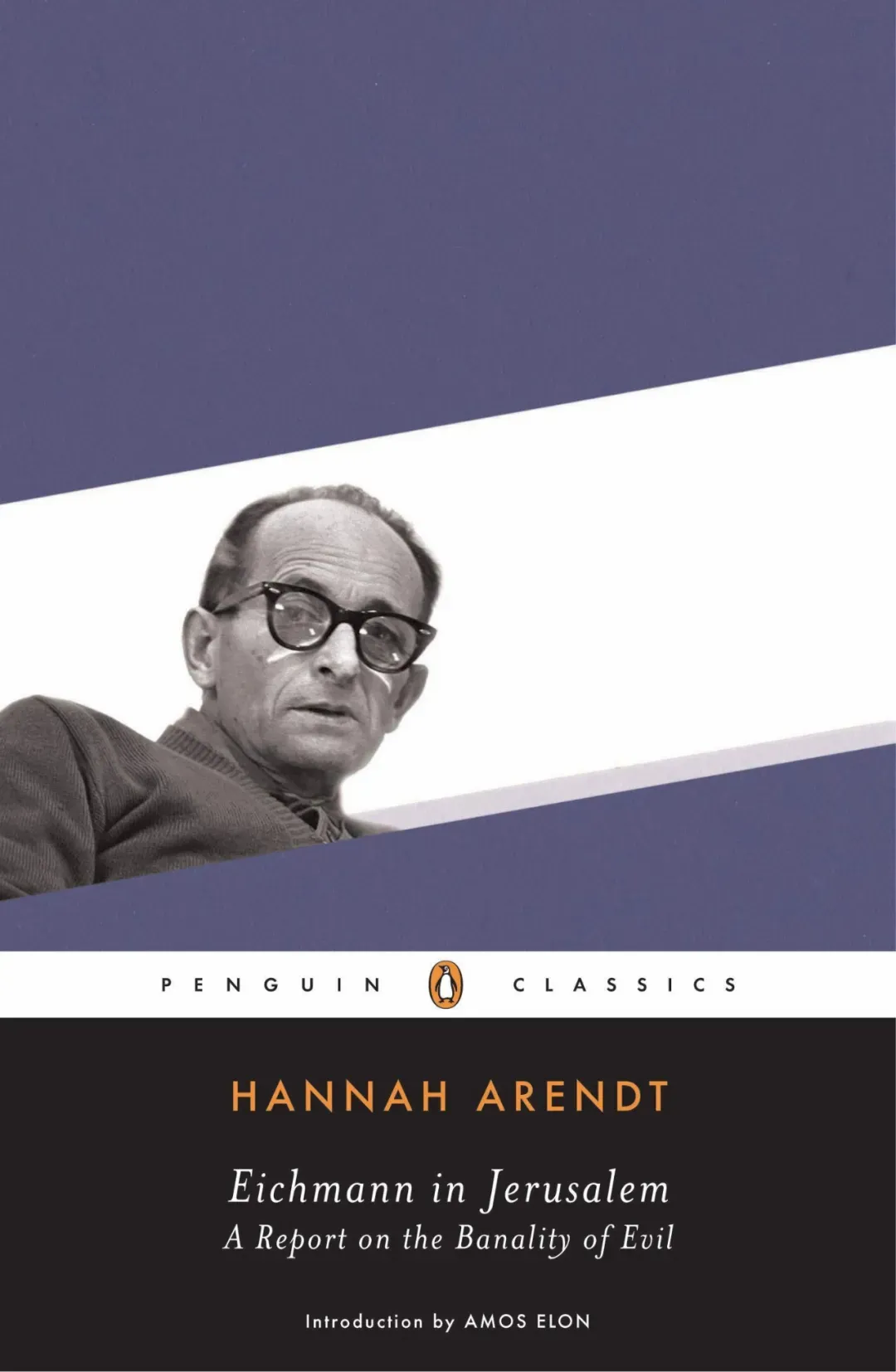
然而,这种隐含的反极权主义也限制和削弱了她的政治概念。一方面,在拒绝现代世界中潜藏的非人性的极权主义倾向时,她的历史叙述往往忽略了「社会的兴起」背后的原因,她没有解决如下这一恼人的古代悖论:即为了让一些人从事行动,其他人必须被暴力放逐到私人家庭,接受无情的劳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John Levi Martin正确地指出,阿伦特「明知故犯地从一个奴隶制社会中获取她的概念装置」,这很令人感到奇怪[40]。 而且,也可以说,霍布斯和马克思的理论所捕捉到的现代性也可以被看作是对少数人的排他性和残酷的古代自由的反叛,通过将更多的人从劳动领域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正如沃林所批评的,阿伦特的政治常常显得过于「纯粹」,因为它本质上脱离了经济动机和社会目的,接近于美学领域,因此常常显得贫乏。[41]现实中的政治行动很难脱离社会或经济目的:政治抗议通常涉及某些社会经济问题,甚至政治讨论也必须涉及某些东西。如果公共参与/行动本身不涉及任何更广泛的社会经济问题,而只是关注表达,那么这种行为是否会有价值就值得怀疑了。诺里斯准确地指出,她对公共行动本身的赞美使公共道德判断变得困难,这本身就可能是危险的。[42]
阿伦特的哲学体系本质上是反极权主义的,而她的政治理念,作为保护极权主义及现代性试图摧毁的人类要素的尝试,是独特、自发、表达、交流的。在阿伦特看来,政治或行动在本体论上是必要的,因为它允许人们超越海德格尔式的「向死而生」的绝望,因为共同的公众将个人从孤立的死亡中解救出来,而自发的行动与潜在的不朽的言论一起,通过「开始新的东西」,可以打断毁灭的循环。[43]用她自己的话说,「政治和行动」提醒我们,「人虽然必须死亡,但不是为了死亡而出生,而是为了创始而出生」,因为它允许个人通过人类世界的故事来表达他们的人类尊严。[44]尽管他们生物意义上的生命是脆弱而短暂的,行动还是拒斥了将个人还原为可替代的部分的极权主义倾向。
此外,尽管这一点在《人的境况》中没有一贯的阐述而且经常被忽视,但共同的政治世界以及作为政治行为的言论是与「思考和谈论我们能够做的事情」的能力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的——而这种能力是针对极权主义无思想性的解药。[45]可以说,政治或行动所保留的基本人类要素是面向公众领域的思考(与之相对的是面向自我的个人沉思),而对一个共同的客观世界进行独立思考的能力是良知的先决条件,使人即使在极权主义条件下,在一切都被绝望吞噬、每个人都被暴政隔离的情况下,也能做出分辨是非的道德判断。[46]诚然,她的政治观念也的确是不可预测的、难以捉摸的和脆弱的,因为人们无法知道自发和多元的行动的后果,而「行动」本身的纯粹性使它难以独立于其他事物存在。[47]然而,正是这种难以捉摸的对人类条件的脆弱维度的表达将人类与工具区分开来,并赋予人类某种尊严,这可能会「在罕见的紧要关头防止灾难的发生」。[48]
4 结语
总而言之,对阿伦特来说,政治是通过自发的言论和行动来表达个人的公共身份,这重申了人的尊严。尽管这种政治只有在建立了公共领域和满足了个人需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而且也是一种难以捉摸和脆弱的表达方式,但它是人性的基本条件。如果没有它,人类很容易沦入丧失人性的极权主义。 /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2nd ed.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7-9
[2] ibid, 96-99
[3] ibid, 160
[4] ibid, 18-19.
[5] Arendt in 3 talks about the life story of individuals and distinguishes eternity(Cyclical) from immortality(linear), which I assume distinguishes the natural/animal from the human. But here she also talks about the life story of individuals, which only corresponds to the domain of action, and I do not quite know where does Work fits in here: it is obviously distinctively human and linear, but it is almost linear on a collective rather than individual scale. Could we maybe discuss this in supervision?
[6]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137-140, 154-160.
[7] ibid, 19, 176-179.
[8] ibid, 178-179
[9] This aspect of human existence described by Arendt reveals much influence by Heidegger’s theory of time captured in Nature, History and State, I really do not know whether I have done it justice but I should be able to unpack it more if necessary in supervision.
[10]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8-9
[11] Andrew Norris, ‘On public action: rhetoric, opinion and glory in Hannah Arendt’s The human condition’, Critical Horizons, vol. 14, no. 2 (2013), 212-213.
[12]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199-200
[13] 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 Pelican Book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3. 81-82.
[14] Jürgen Habermas, ‘Hannah Arendt’s communications concept of power’, Social Research, vol. 44, no 1 (1977) , 3-6
[15] To be sure, Arendt did not clearly define politics in THC for the most part of it but instead resorted to exploring ancient notions and etymology, which I will discuss later in the essay
[16]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30-32
[17] ibid, 31-33
[18] ibid, 56-58.
[19] not private wealth
[20]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60-72
[21] Patricia Owens, ‘Hannah Arendt: violence and the inescapable fact of humanity’, in Hannah Arendt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thony F. Lang and John Williams, eds.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50-51.
[22] Sheldon S. Wolin, Fugitive democracy: and other essays, Nicholas Xenos, e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251-255
[23]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239-240.
[24] ibid, 4-5
[25] Norris, 202-204
[26] Wolin, 240.
[27]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31
[28] Hannah Arendt, ‘Politics and Freedom’, in Hannah Arendt, Thinking without a bannister: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53–1975, Jerome Kohn, ed. (New York, NY: Schocken Books, 2018). 246-250.
[29]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299-300
[30] ibid, 76-80.
[31] ibid, 131-133.
[32] ibid, 40.
[33] ibid, 156-157
[34] Max Weber, “The Profession and Vocation of Politics” in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ed. Peter Lassman and Ronald Spei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310-313
[35]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2nd ed. London: Allen & Unwin, 1958. 609-611
[36] Arendt,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612-615; Politics and Freedom, 267
[37] 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Penguin Classics. New York, N.Y.: Penguin Books, 2006. 276-279.[38] To be sure, the notion of totalitarianism is not very accurate in historical analyses of the Nazi regime or Stalinism, but her theoretical analyses of totalitarianism still stand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r analyses of totalitarianism and her notion of politics/human condition remains a fundamental one.
[39] However,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in THC, her definition of totalitarianism expanded to refer more broadly to the deprivation of human identity and the common world, thus of the ability to act and think, which may eventually lead to murderous rule and utmost inhumanity. (THC, 3-5)
[40] John Levi Martin, “The Human Condition and the Theory of Action” in Philip Baehr and Philip Walsh. eds., The Anthem companion to Hannah Arendt (London: Anthem Press). 68
[41] Wolin, 245-247.
[42] Norris, 215-218.
[43]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245-247.
[44] ibid, 246.
[45] ibid, 2-3.
[46] Hannah Arendt, 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3. 189-192.
[1] Arendt, Hannah. The human condition, 2nd ed.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2] Arendt, Hannah. On Revolution. Pelican Book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3.
[3] Arendt, Hannah, and Jerome. Kohn. 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3.
[4] Arendt, Hannah. Thinking without a bannister: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53–1975, Jerome Kohn, ed. (New York, NY: Schocken Books, 2018).
[5] Arendt, Hannah. Eichmann in Jerusalem :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Penguin Classics. New York, N.Y.: Penguin Books, 2006.
[6] Arendt, Hannah, .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2nd ed. London: Allen & Unwin, 1958.
[7] Baehr, Philip and Philip Walsh. eds., The Anthem companion to Hannah Arendt (London: Anthem Press).
[8] Canovan, Margaret. ‘Introduction’ to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9] Habermas, Jürgen. ‘Hannah Arendt’s communications concept of power’, Social Research, vol. 44, no 1 (1977), pp. 3-24
[10] Owens, Patricia ‘Hannah Arendt: violence and the inescapable fact of humanity’, in Hannah Arendt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thony F. Lang and John Williams, eds.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p. 41-65.
[11] Weber, Max. “The Profession and Vocation of Politics” in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ed. Peter Lassman and Ronald Spei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12] Wolin, Sheldon S. Fugitive democracy: and other essays, Nicholas Xenos, e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