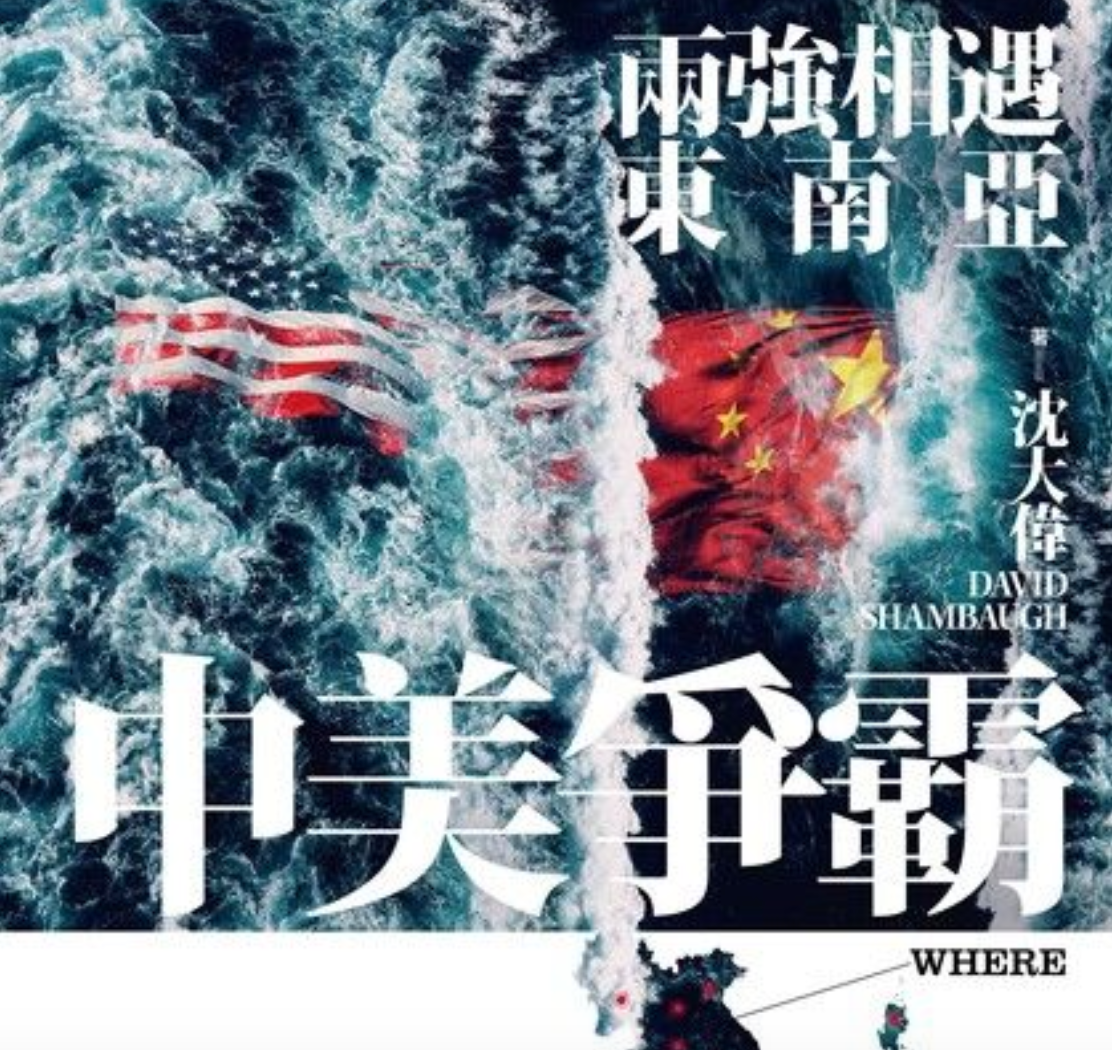《中美爭霸:兩強相遇東南亞》導讀: 大國競逐的東南亞進行式
作者/蔡宏政(國立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
本書電子書介紹與連結,請點此
是新冷戰嗎?
沈大偉,美國著名的中國與亞洲事務教授以及政府智囊,在本書《中美爭霸:兩強相遇東南亞》中,提供一個細節與宏觀兼具的全面分析,來說明東南亞在美中霸權對抗中的進行方式與未來可能的場景。
按照沈大偉的說法,美中「競爭」(霸權對抗的外交辭令)與過去的冷戰方式並不盡相同。冷戰是美蘇在政治、經濟、軍事上劃分出涇渭分明的兩個陣營,雙方從事作用—反作用式的直接競爭較量,是一種以牙還牙,甚至於你死我活的報復性行為。但中國是先透過經濟全球化融入國際體制,因此它的影響力不只出現在政治、軍事與外交上,也廣泛分布在商業、媒體、技術、公共治理、文化與意識形態上。換言之,現今的美中對抗是一種柔性的總體戰(soft total war),戰場從國家機器穿透到公民社會的各個層面,但雙方的活動旨在推進自己的利益,而非直接反制或削弱對方的地位。在本書中,沈大偉從三方行動者(美國、中國與東協)的強弱之處來分析這個柔性總體戰的可能推移力量。
美國與東南亞
根據沈大偉的研究,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長期根基依舊穩固。就經濟上而言,從一八七三至二○○七年,除了二次大戰時期,美國一直是東南亞的最大貿易夥伴,而東協整體則是美國的第四大貿易夥伴,同時享有對美八百多億美元的貿易順差。美國在此地區的直接投資額,至二○一八年為止累計達三二九○億美元,比中日南韓三國的投資額加總還多!二○一七年美國的直接投資達二四九億美元,比中國的一三七億美元多了將近一倍。東協事實上是美國在整個印太地區最大投資目的地。
就軍事安全關係來說,東南亞諸國的軍隊幾乎全與美軍有廣泛的歷史連結。其中,與新加坡關係最為密切,儘管與傳統盟邦泰國、菲律賓的關係在近年來有所逆轉,但與越南的關係也同樣因為地緣政治的轉變而大有改善。自歐巴馬政府重返亞太以來,美國印太司令部已成為在資源、裝備、訓練、演習、防務夥伴關係、部署等各方面更為重要的地區性司令部。二○二○年時,已有六成的美國空軍資產、五成的最新式戰鬥機(F-22與F-35),以及六成的美國海軍船艦部署於此作戰區。
就教育文化而言,在整個東南亞地區,美國依舊是鼓舞、吸引人心的柔性實力大國。美國貨、美國媒體、美國觀念、美國教育人員和英語老師、美國運動賽事、美國電影依然是該區域主流文化的象徵。美國國務院的公共外交局、教育暨文化事務局繼續推行一系列公共外交計畫。這些公共外交和教育事務、文化事務策略,針對東南亞社會、公共機構、媒體的不同切面,鎖定當前和正要冒出頭的外國領導人、編輯、記者、智庫成員等,來美做三星期的參訪。這些活動為美國在該區域創造了「戰略性好感」。
不過美國從未把東南亞列為主要關注對象,對該區域的關注是配合其他更重要的戰略利益進行工具性的操作,因此外交活動呈現一種斷斷續續的狀態,經常在長期的冷漠之後,突然造訪,發表一些宏大願景的言論,達成美國想要的目的之後,轉身走人,再次陷入長期的冷漠。因此對東南亞人來說,美國讓人覺得自我中心、傲慢而善變。這個全球地緣政治弱點在一九九○年之後,隨著中國與東南亞地區的關係日漸升溫,美國的傳統優勢因而大大折損。
中國與東南亞
過去三十年以來,中國靈活地使用總體戰滲透進東南亞國家,提高其影響力。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危機後,相對於美國主導下的多邊組織所提供的救援與財政縮減方案,中國的經濟支持更加實惠而沒有附加條件。一九九八至二○○八年可以說是中國深耕東南亞的黃金十年。中國自二○○九年起就成為東協的最大貿易夥伴。到了二○一九年中期,東協已超越美國,成為中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然而,隨著中國經濟量體快速變大的過程,東協各國對中貿易比例持續上升,呈現對中貿易依賴程度增加的趨勢。即使是全部東協國家的加總,其人口、經濟與軍力也難以跟中國匹敵。這使得東協各國難以單獨跟中國處於平等的談判地位。沈大偉稱呼二○○九至二○一○年是北京的「強勢年」(year of assertiveness),中國政府在這期間開始出現咄咄逼人的行為,從而大大抵消其取得的成果。
北京對東協國家的拉攏與恐嚇太成功,以至於中國即使做了東南亞人不喜歡的事,整個東南亞也很快讓步,這使得中國猶如在該區域享有「否決權」。東協各國固然從一帶一路計畫中獲得投資,但伴隨這些開發計畫進入的是債務陷阱、環境衝擊、中國移工問題、黑幫入境、洗錢、毒品與人口走私。對湄公河下游國家來說,中國在上游攔水築壩已成一大問題。中國在南海造島,建立軍事化設施,急劇擴張其海軍勢力,令整個地區深感憂慮。但中國官方對於東南亞人的憂心幾乎不當一回事,甚至於懷抱著傳統納貢體系的尊卑觀念,視為「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
中國的強勢作為終究引發了東南亞一些國家的對抗。二○一三年菲律賓向海牙國際法庭提出南海仲裁案,在二○一六年國際法庭常設仲裁法院作出最終裁決,判定中國在南海被「九段線」涵蓋之海域內所主張的歷史性權利、或主權權利、或管轄權之主張,與《國際海洋公約》牴觸,不具法律效果。同時,南沙群島所有海上地物均為《公約》所指之「礁岩」,而非島嶼,因此不能主張專屬經濟區或大陸礁層。
另一個直接的衝突對峙發生在二○一四年,中國海洋石油集團有限公司在距越南海岸線僅一二○英里(位於越南兩百海里專屬經濟區內)的海域,無視越南反對,建置了一個超大型深海鑽油平臺。雙方為此陷入嚴重僵持,各自部署海防艦船,向對方發表不畏一戰的聲明。中國最終撤走鑽油平臺,但此事已在越南引發大規模反中示威,也讓海洋東南亞國家見識了中國在該區域行事肆無忌憚的程度。
沈大偉引用新加坡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的〈二○一九年東南亞狀況〉調查報告,針對「政治上和戰略上哪個國家/地區性組織在東南亞有最大的影響力?」一問,四五.二%的受訪者回以中國(美國居次,三○.五%)。就經濟影響力問以同樣題目時,中國拿到更高分(七三.三%)。但中國在東南亞「受信任」程度卻敬陪末座:日本(六五.九%)、歐盟(四一.三%)、美國(二七.三%)、印度(二一.七%)、中國(一九.六%)。反之,就「不信任」程度來說,中國拔得頭籌(五一.五%)。因此,儘管中國多管齊下要說好中國故事,塑造中國正面形象,但就中國在東南亞的情況來說,中國的存在感和影響力愈大,受信任程度反而似乎愈低。
東南亞與美中
在美中軟性總體戰的爭霸中,東南亞國家因此暫時獲得可以兩面下注的「避險」(hedge)操作空間,也就是在完全的扈從(bandwagon)與抗衡(balance)之間游移,藉以取得最大的利益。但由於東協具有複雜的地緣政治、族群與宗教文化,為了尋求一個比較容易的起步,它的制度運作核心內涵是「協商、主權獨立與不干預」。但這也導致東協作為一個區域組織,既無充裕經費,也缺乏強有力的領導核心來產生有效的集體政策與行動。中國對該區域採取的戰略立場:堅持南海主權、拒絕多邊協商、對東協進行雙邊談判以便分而治之,就是針對東協的組織弱點而有的策略。因此南海爭端仍有賴於美國的介入領導。
沈大偉的結論是,美中戰略性競爭如果變得愈來愈劇烈,那麼美中的地緣競爭會愈來愈以東南亞為中心來升溫。目前北京和華府都未要求哪個國家選邊站,但隨著兩強對抗愈加緊繃,東協諸國要繼續兩面下注、見風轉舵並沒那麼容易,也愈難以維持自己行事的自主性,保住自己的國家主權。「令人遺憾的是,東南亞國家不願面對不愉快外在事實的心態頗為強烈,而且過度埋頭於內部事務。這會使它們看不到正在自己周邊上演的更大變化。」
對臺灣的啟示
本書的優點在於提供一個涵蓋範圍廣泛的堅實經驗內容之外,同時能夠給出具有分析力,也就是穿透經驗資料的洞見,從而形成一個對該區域的獨到觀點。這使得作者既深入理解東南亞地區的在地經驗,但又可以從美中全球對抗的高度來理解與解釋東南亞在地經驗變化的意義。所以本書既是一種學術研究成果,也有助於實際政治決策時所需要的具體解決方案之形成。這正是臺灣新南向政策所需要的研究。
比起東協諸國,臺灣的避險空間因為國家地位(statehood)受到中國更嚴厲的壓制,根本無法與東協或國際多邊組織發展任何官方關係,以至於在這一連串的區域變局中,被排除在所有正式的談判之外,僅能藉由參與一些非正式會談來表達自身立場。臺灣在中美爭霸下的國際處境甚至於連選邊站的資格都沒有。對中國而言,最理想的狀況是臺灣在國際體制(international regime)中會愈來愈靠近香港的位置。但臺灣具有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的國家主權,這個國家認同(state identity)一直是戰後臺灣的主流共識。這就是為什麼隨著中國力量的擴張,臺灣內部的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會因為中國的打壓而增強,乃至上升到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的層次。這個民族認同也就驅使臺灣社會與民選政府選擇跟美國與日本進行戰略結盟。所以這個國際爭霸的格局轉變很好地定義了臺灣過去二十年來內部政治發展的外部參數,也很好地說明中國政府為何能夠熟練地使用柔性總體戰的方式來改變臺灣內部的政治生態(在臺灣被稱為「中國因素」)。
雖然受到中國的國際封鎖,但臺灣因為擁有連結東北亞與東南亞的戰略地位、南海兩大島礁主權、相對較強的經濟與技術實力,以及日漸穩固的民主多元精神,照理說新南向政策還是可以讓我們擁有不小的「避險」操作空間。不過既然是兩面下注的避險策略,臺灣與東南亞國家交往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弄清楚交往國家的核心利益為何,以及臺灣能夠在什麼議題,滿足對方到什麼程度。這樣才能談到精準下注。如果再加上中國干擾的因素,那麼臺灣避險策略的具體議題就必須尋求同時滿足下述條件:(一)符合東協國家的個別國家核心利益;(二)臺灣具有相對較強的能力可與之互動者;(三)不易因政治理由而受中國干擾者。
在過去的經驗中,我們知道第三個條件很不容易滿足,但也不是全然沒有機會。聯合國所提倡的十七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都是立基在全球平等發展、健康與環境永續等「四海一家」(cosmopolitan)的普世價值,較不易受政治理由影響,也攸關東協國家核心利益,亦即易於滿足第一與第三條件。其中的醫療(Goal 3)、教育(Goal 4)、環保(Goal 13、14)等項目都是臺灣的強項,符合第二條件,可以彰顯臺灣特有的人文精神與民主多元價值。同時,「永續發展目標」(SDGs)作為聯合國決議,各國政府都設有相應的專屬機構在負責,新南向的行動方案其實馬上就可以進行組織連結。因此,這幾個分項議題之下的各種子議題就是臺灣可以具體操作的措施。
舉例而言,臺灣是一個海洋國家,四周的國土邊界就是海洋,與東南亞發生直接接觸者就是南海。隨著東南亞國家經濟的日益進展,光是環繞南海的海洋東南亞國家高達五億的人口,就需要高比例的水下蛋白質。如何避免捕撈漁業的過漁現象,以及養殖漁業的環境汙染,這正是符合糧食安全永續生產與消費,以及海洋發展(Goal 2、12、14),在理想的情況下甚至可以創造出在地國產業鏈,促進該國就業、消除貧窮與社經不平等(Goal 1、8、10)。
但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FAO)並沒有南海漁業資料,臺灣之所以能夠在南海漁業資源調查上有所貢獻,不只是我們的科研技術能力,而且是因為東南亞各國對臺灣具有基本的信任感(相信臺灣不會採取擴張性戰略),這就是沈大偉在前面提到的,長久累積下來的「戰略性好感」。
但即使有完整的漁業資源調查資料,也會因為各國宣稱的專屬經濟區互相重疊、漁民越界、海巡執法過當而時有糾紛。近來更因為中國的人工造島與武裝漁船而火上加油。如何透過良好制度的安排與實踐以促進最大的漁業收益,這件事情顯然會上升到各國海巡業務的協調。從現實主義的觀點而言,東南亞各國之所以對臺灣具有基本的信任感,乃是因為臺灣並無能力單獨進行這樣的制度安排,因此結構上臺灣必須選邊站,與美、日、紐澳等區域強國合作,因為比起東南亞國家,我們更沒有兩面下注的避險空間,這是中國強勢單邊主義所造成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