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种人不擅长短跑?一个存在主义视角的解读

本文的“存在主义”主要援引萨特的部分观点(不涉及他对自由与不良信仰的阐发),即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陌生与离奇,一旦摆脱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或认知逻辑,便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高度的偶然性与荒谬感。接下来请跟我一起咬文嚼字,重新思考这一命题中的两个关键字:短跑与黄种人。
为什么100米短跑是体育赛事之王?
在舆论对苏炳添的赞叹声中,有人指出,苏炳添的50米、60米成绩均在世界前列,可惜奥运会没有引入这两个项目,不然苏炳添或许真的可以在奥运短跑称王。(苏炳添60米成绩现役第三,鉴于第一名Christian Coleman今年已被禁赛,确实很有竞争力)那么为什么奥运会没有50米、60米呢?这个问题下的网友的答复以嘲弄“50米太短”为主,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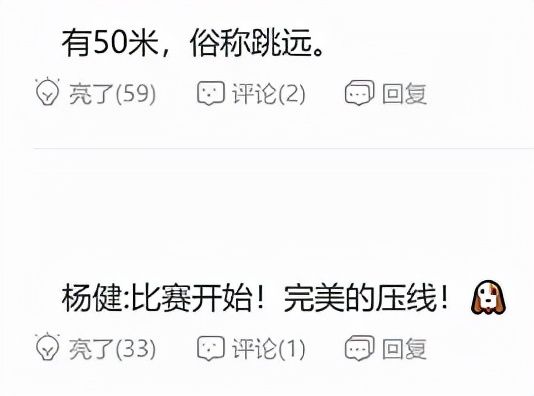
这种看法无疑是先入为主了。50米固然短,100米难道就够长了吗?我在海外看央视转播,网速不稳定,刚好100米决赛英国选手抢跑时,电脑卡了。等到缓冲结束,只听到解说员说“苏炳添应该……是第6!”让我郁闷许久。顶级100米选手用时9秒多,50米则是6秒多,后者并没短到哪去。何况50米与60米并未因为“太短”而缺乏职业比赛,只是未进入奥运会罢了。
当然,回帖中也有相对专业的回复,指出“许多运动员在50米以后才达到最高速,因此50米最多只是个比较加速过程的运动,不能体现最高水平”。这个说法仍有待商榷:毕竟100米比赛的前半场处于加速阶段,也不能代表“100米最高水平”。人类历史上跑完100米的最短耗时是8.7秒,也就是博尔特跑200时,在速度达到顶峰时的后一个百米。(博尔特4*100接力时跑出过8.65秒,但4*100最后一棒实际上不足100米)换言之,如果考察巅峰速度下的短程赛跑,200米比100米更合适;而如果侧重考察选手起步加速的能力,则应该比50米或60米。
排除上述两种理由后,我倾向于一个看似荒诞的结论:奥运会乃至全人类,之所以把100米视为短跑的桂冠,本质上是因为,我们采用了10进制。十进制的社会,很难不对10的倍数特别是100情有独钟。不仅百米赛跑如此,百分制考试如此,许多法币的最大币额也是100。
然而在人类历史上,8进制、12进制、20进制、60进制都曾主导过不同社会(比如英文计数中不规则的eleven和twelve以及中文的地支都是12进制残余)。如果我们仍处于12进制社会,那144米自然会成为奥运短跑赛事的皇冠,100米则因为100这个数字过于不规则而根本不会举办比赛。有语言学证据表明,原始的印欧语系,可能采用的是8进制。在8进制时空中,64米赛跑显然会取得100米赛跑一样神圣的地位,不仅是短跑之王,也是体育之王。
如今体坛虽无64米跑,却有60米的职业比赛。苏炳添曾在2018年跑出6.42的60米成绩,世界第5,现役第3,比他的百米排名高出不少。而且榜单中排第一的Christian Coleman由于禁药丑闻被本次奥委会禁赛。可以说在8进制时空中,苏炳添将是短跑之王的有力竞争者。(题外话,这一榜单不包括博尔特,他百米赛跑时前60米快至6.31,但不参加60米赛事)

什么是一米?
如果有兴趣读到这里,想必不会介意我继续钻牛角尖。实际上,100米有多长(适不适合黄种人发挥),除了取决于100这个数字以外,也取决于“一米”有多长。一米、一秒这些测量时空的基本单位由于过于基础,往往让人们忘记了它们本身也是被人为测量、规定的结果,而非某种超越历史的普世尺度。
具体到1米而言,1671年Jean Picard提出把周期为2秒的单摆(即秒摆)的长度定义为一个基本单位(Toise Universelle)。但随后人们意识到秒摆的长度与重力加速度有关,并不恒定。1790年,法国科学院决定将子午线的四千万分之一定为一米。至于为何不是三千万或五千万分之一,只是因为前者的长度更接近于秒摆。但由于勘测队误算了地球的曲率,导致实际测得的“一米”比理论上子午线定义的少了1/5毫米,但这个误差版作为米的尺度被沿用至今。至于后来用原子跃迁及光速定义的“米”,也不过是对上述测算结果的精确表述。

因此严格来说,一米的长度受到了秒摆与勘测误差的共同影响。其中仍不乏十进制的影响,不然法兰西科学院不会选择4千万分之一这个单位,但同时也受到12进制与60进制的影响——因为定义秒摆的秒源自我们对于一昼夜的划分,其中小时为12进制,分秒却是60进制。再推一步,米的定义也与地球的自转周期有关,假如周期变短,那么一昼夜以及一秒所度过的时间会更短,秒摆的长度、以及“一米”的尺度也会相应缩短。
说得耸动一些,百米赛跑之所以对“黄种人”如此不利,除了老生常谈的种族劣势外,10进制、地球的自转周期、子午线长度、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如今的100米并不是“黄种人”擅长发挥的距离。
当然,或许有人会问,设想这些与地球不同的possible world有何意义,在那些世界,有没有奥运会都不一定,谈何100米冠军?我的回答是,本文并不是机械地改变初始条件,而是试图消解一些本体论意义上的“真实”。我们把百米当成理所应当的短跑之王,因此苏炳添在决赛只能敬陪末座。但是100米赛跑之所以比50米、60米、200米更伟大,只是因为10进制,跟跑步、飞人、或者更高更快更强都没关系。不可否认,在如今地球的限制条件下,我们确实可以客观地讨论谁是100米的王者。但是这些限制条件的形成,无疑具有偶然甚至荒谬的成分,或者至少与短跑这项运动本身无关。
谁是黄种人?
在“苏炳添是黄种人之光,证明了黄种人也可以出现在百米决赛”这样的叙述中,“黄种人”本身又是一个值得商榷的概念。
有留学经历的朋友不难发现,白人的白并非绝对成立,他们往往皮肤发红,而地道的中国人中,却有一些远比白人更白,大概就是古人所谓“肤如凝脂”。口说无凭,就以这次奥运会游泳比赛为例,100米蝶泳冠军张雨霏就是我所谓的比白人更白的“黄种人”。游泳比赛一无p图,二无化妆,下面这几张截图都出自nbc转播的女子100米蝶泳,熟白熟黑一目了然。



凑巧(或者说不巧的是),女子游泳也是中国传统强项,因此虽然张雨霏勇夺2金1银,但观感上倒不至于冠上“黄种人之光”的名号。设想一下假如女泳是传统弱项,抑或苏炳添像张雨霏一样皮肤白皙,那大众恐怕不得不面对一个比白人更白的“黄种人骄傲”了。
那么为什么一个与事实相悖的“黄种人”概念会被提出,甚至风靡至今呢?近年来学界有一部著作Becoming Yellow: 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便处理了这个问题。从副标题不难看出,“黄种人”的发明,与18世纪以来愈演愈烈的种族歧视关系密切。在早期欧洲传教士笔下,中国人同样是白人,当时被西方观察家视为黄皮肤的,则是如今归为白人种之列的印度人。1758年,植物学家林乃首次把亚洲人的颜色由fuscus改为luridus,意为枯黄、蜡黄。林奈本人也曾说过,植物呈现luridus时意味着可疑与悲伤,因而把亚洲人冠以“luridus”中的歧视含义不言自明。
“黄种人”的概念随后披着科学外衣进入中国,实则是种族主义下的伪科学。正因如此,日本人至今拒绝承认自己为黄种人,中国倒是欣然接受——这又是一个巧合:“黄”的概念在中国传统中有崇高的含义,国人便阴差阳错地引以为傲。
如果考虑到黄皮肤所蕴含的歧视性,以虚构的黄种人自居无异于一次自我东方化(self-orientalism)。这里的orient(东方)同样具有贬义,代指西方中心视角下作为愚昧、野蛮的他者的那个“东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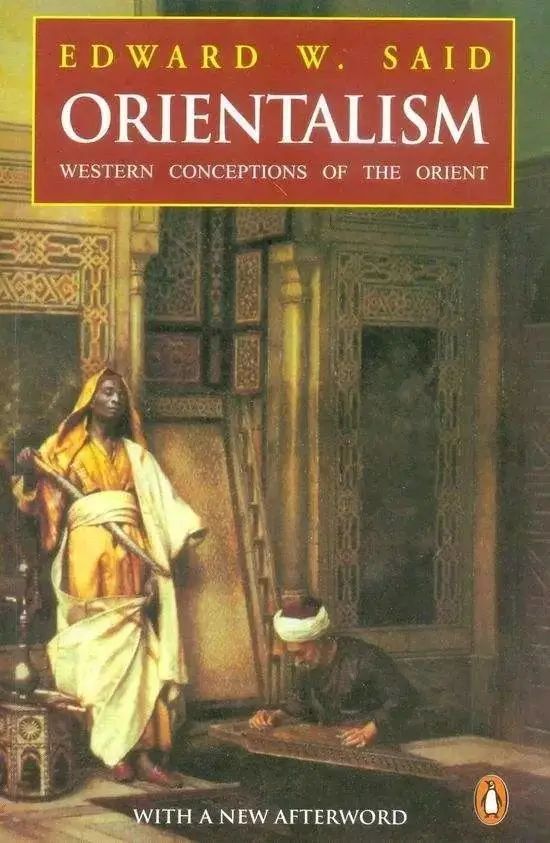
自我东方化最典型的一幕,莫过于这样一句中国人人传诵的歌词: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就叫长江。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它的名字就叫黄河。”
这句话吊诡的地方在于,“遥远的东方”是站在谁的视角上的叙述?只能是作为世界中心的西方。然而西方视角的龙可是喷火吃人,等待勇者斩杀的怪物,绝无普降甘霖的功德。但创作与传颂这首歌的显然又是龙的传人自己——可见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歌唱者,都内化了西方中心的视角而不自知。在这种范畴错乱之下,下面这句话倒显得莫名自洽起来: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我们可以是龙的传人,但并不是黄皮肤,不仅引申层面不是(枯黄、败破、乃至病夫),事实层面也不是(横跨南欧、北非、中东、印度的地中海人种(Mediterranean race)肤色普遍比东亚更黑,但他们居然是白人,甚至发明了dark whites一词)。时至今日,海外在填写族裔时早已放弃yellow race这样一个歧视性概念,但国内却将“黄种人”塑造为某种与西方白人相对立的,超越国界的种族纽带,把“黄皮肤的中国人”的概念不断内化。这个早已被始作俑者惭愧废弃的伪概念,却在一次次奥运赛场中国歌升起时被国人不断强化,实在令人五味杂陈。
结语
熟悉我文章的朋友不难看出,我有一定怀疑论及解构主义倾向,质疑绝对意义上的真或客观(无论是宗教、历史或科学层面上的绝对真理);又有喜欢文字游戏的癖好,本文算是结合二者过了一把瘾。但本文的解构,既非消解奥运健儿拼搏的意义,也非消解荧幕前观众们油然而生的自豪感,而是挑战我们习以为常的常识背后,那些被认为是恒定、客观、严格成立的本质。很多常识往往只是偶然事件的路径依赖,例如铁路轨道的宽度,追根溯源却是因为罗马军团战车所需的两匹马的屁股宽度如此。
当然,这样的消解也可能因一句so what?而被怼地哑口无言。毕竟毁掉一个笑话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追问so what,而这类萨特式的脑洞其实正与笑话异曲同工:试图以陌生化的视角重新审视周遭熟悉的一切,点出其合理性背后诡异的一面。
当我把上述脑洞跟朋友分享时,他恰好有个长辈是山东省200米及400米纪录保持者,也有类似的想法:他觉得应该测试一个人类平均短跑速度最快的距离(他推测在150-160米左右),以此为准。不过这个均值显然难以测量,遑论群体的均值对于运动员个体也不公平,因而并不现实。
这个叔叔大概笃信“更高更快更强”,认为高快强都有其客观不变的尺度。但实际上正如本文所揭露的,这些概念的生成都有不少繁复且充满偶然的历史背景。大量看似毫不相干的因果关系,错综复杂地构成了我们如今习以为常,并且看起来非常有秩序感的世界。这也正是存在主义哲学,对世界荒诞性的揭露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