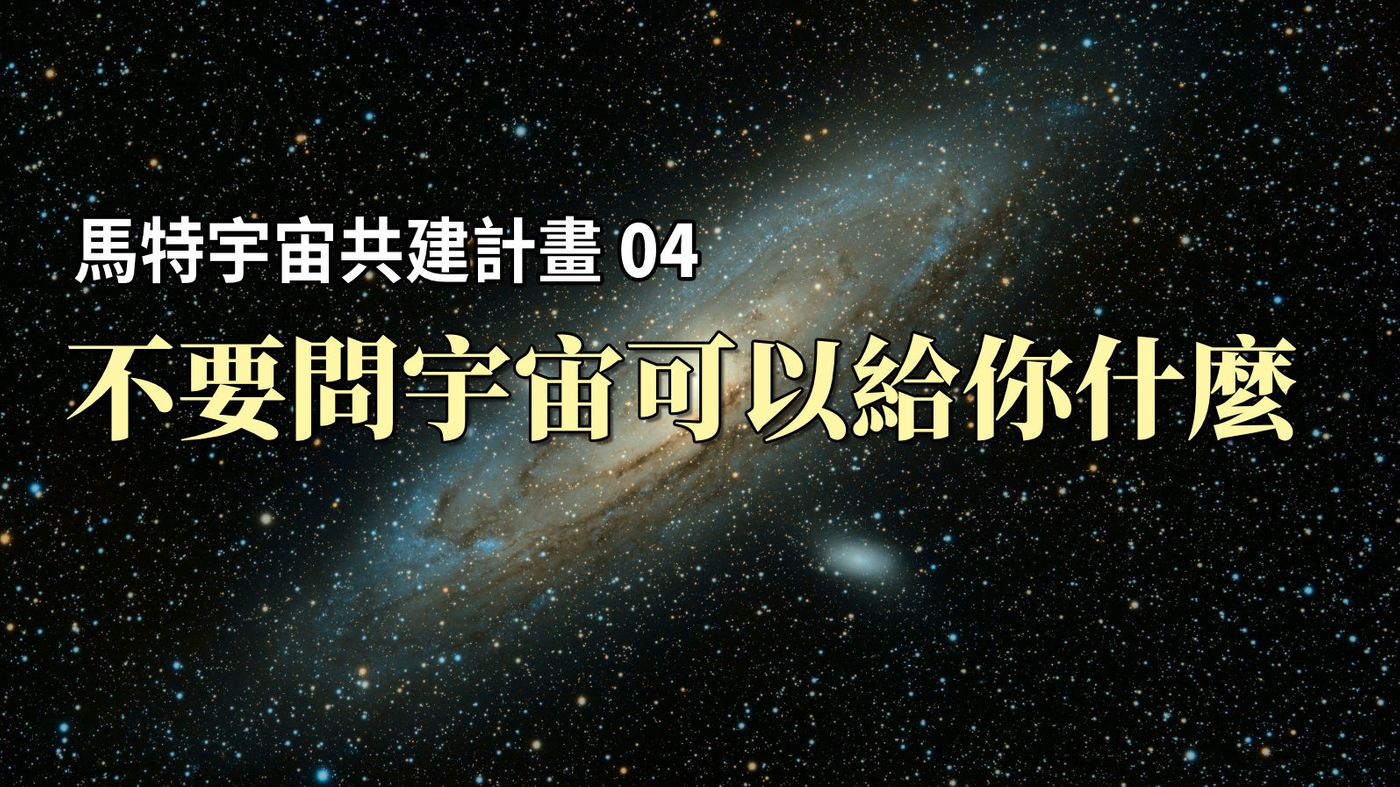馬特宇宙共建計畫04|不要問宇宙可以給你什麼
呯~呯~呯~
叛逃者應聲倒地,背後三個彈孔,隱約傳出滋滋的烤焦聲音;孔中冒出的煙,正好被汩汩流出的血澆熄了。
我還是喜歡這種老舊手槍,震耳的響聲,實體的子彈,比那些什麼激光什麼高頻電殛要酷得多了。沒有這種嚇破膽的巨響和噴發的鮮血,敵人怎麼會害怕?怎能殺雞儆𤠣?
你看,連沒有中槍的那個叛逃者,都嚇得跪在地上,不斷的發抖。
我對身旁的兩個手下打了個眼色,他們馬上衝前,逮捕了叛逃者。
叛逃者看着中槍的同夥,急得哀號:「你們快去救他啊!他可能還沒死的......嗚......」
「救?在我眼皮底下,沒有一個叛逃者可以活着離開,你還有其他的遺言嗎?」
叛逃者知道再沒有活命的機會,抬頭面向我,以空洞的眼神,看着我手中槍管的空洞,說:
「若有來生,我要到宇宙的另一端.....」
呯~
講什麼廢話?宇宙另一端,不就是腐敗的銀河宇宙,不就是一幫被自轉鐘操控着的半人半機器嗎?他們那曉得黑洞的偉大?
若有來生,我還是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蝸星人!繼續守住鐘樓,當一個稱職的時間監控員!只是,「來生」也是腐敗者的概念,我們蝸星人,只應活在當下,為黑洞盡忠職守!
「好渴⋯⋯」被拷在病床上的叛逃者緩緩醒來,可能還沒了解自身的狀況:「我⋯⋯死了嗎?」
「還沒。」我拍了拍叛逃者的臉:「想死得乾脆一點,就老實回答我的問題!」
我拿出一疊信件,是從叛逃者身上搜出來的。剛才,在開槍的一剎那,我瞥到叛逃者的口袋,露出信件的一角,一個分神,子彈就打偏了,叛逃者卻嚇暈過去。
「這是什麼?」我抖了抖手上的信。
「情書⋯⋯」叛逃者語音沙啞:「可以給我一口水嗎?」
我遞上水杯,繼續問話:「情書?為什麼用手寫?」
喝了水後,叛逃者看了看周圍,發現只有我一個人,神情放鬆了一點:「你是鐘樓裡的人,還用問我嗎?打字的話,你們能看到。」
「不讓我們看,明顯就是心中有鬼!我有理由相信你意圖通敵賣星⋯⋯」
「這是穩私!」叛逃者還狡辯:「我是情書作家,有責任為我的客戶保密!」
「哈哈哈~」實在太可笑了:「我第一次聽到這麼牽強的理由!寫情書有什麼好遮遮掩掩的?對蝸星的愛、對黑洞的愛、甚至對我們鐘樓總指揮的愛,都可以大聲的說出來,沒有人會阻止你!」
叛逃者白了我一眼,彷彿我說了什麼荒謬的話一樣,哼!光是這一個眼神,就可以提告侮辱監控員罪!
「愛情,不只有一種⋯⋯」叛逃者似乎沒有一絲悔意,還很認真地想說下去。
我忍不住要指正:「不!鐘樓早就頒佈了規則——愛,只能有一種,就是對蝸星、對黑洞、對鐘樓總指揮的愛,因為蝸星、黑洞、和鐘樓總指揮是三位一體的,所以是一種!」
鐘樓的規則,我背得爛熟,休想質疑我。
「你知道為什麼蝸星是紅色的嗎?」叛逃者突然拉開話題。
「因為紅色是宏偉、榮光、純正的顏色,代表⋯⋯」
叛逃者用力搖頭,打斷了我的話:「蝸星本來是彩色的,在黑洞出現之前⋯⋯」
叛逃者的眼神,漸漸變得清澈,好像對自己的話,有十足的信心,儘管聽聽你想胡編亂造什麼——
「蝸星本來有各種各樣的顏色,有各種各樣的聲音和音樂,有和其他星體對應的時間⋯⋯蝸星,也曾經有來自其他星球的旅客,甚至有一段和其他星體,一起搭建宇宙航道的歷史。」叛逃者沉醉於這段所謂的「過去」裡:「可是,自從黑洞出現之後,一切都變了⋯⋯黑洞吸收了所有的顏色⋯⋯」
「胡扯!我們明明是紅色的!怎麼會沒有顏色?」我憤怒了,要制止這些歪曲事實的謊言。
叛逃者又一次搖頭:「紅色,其實不是我們的顏色,是因為黑洞的吸引力太大了,它把附近的一切都吸收進去,而還沒吸進去的東西,因為高速摩擦碰撞燃燒,從外面世界看過來,才會以為我們是紅色的。」
叛逃者的話,好像有一點點的理據,我有一點點想聽下去⋯⋯
「你知道嗎?我們本來也安裝了自轉鐘,和其他星體用類近的時間......」
不是吧?自轉鐘不是銀河宇宙推銷員用來忽悠我們的垃圾嗎?
「當所有星體逐漸接受蝸星,開始和我們頻繁往來時,沒有人想到,也沒人注意到,黑洞慢慢地、悄悄地改裝自轉鐘,一步一步的,把自轉鐘改成了......」
「鐘樓?」
「沒錯。」叛逃者第一次點頭:「就是我們...就是你效忠的鐘樓。曾經,在自轉鐘還沒完全變成鐘樓之前,有個港口的居民,看出了端倪,耗盡力氣提醒過大家,再這樣下去,總有一天,我們連愛一個人、連寫一封情書的時間都沒有。可惜,大家都聽不進去,而港口居民,凡是年青的、有理想的、有小孩的,都爭先恐後的逃離,於是,鐘樓下令,把蝸星這個唯一對外星開放的港口,堵死了。
「當其他星體一一組合、連接,成為銀河宇宙時,鐘樓只能適應黑洞的緩慢時間,因此與其他星體完全脫節,蝸星,也漸漸被推到銀河宇宙的邊緣。你以為我們鎮守在宇宙深處嗎?不!我們是給所有星系遺棄了!」
「夠啦!不要再侮辱黑洞了!你知道這是死罪嗎?」我拿起叛逃者那疊信件,用力擲在病床上,散落一地。「私自寫信、非法離境、侮辱母星,每一條都是死罪,你知道我可以馬上把你槍決嗎?」
「如果講事實就是侮辱,如果去找一個可以有自己的時間寫作、可以用自己的時間去愛的地方,也是違法,你殺了我吧!」
「你知道這麼多有的沒的假歷史,很明顯是非法使用了踢踢機,接收銀河宇宙的糟粕,這一條,也是死罪!可惜你只有一條命,要不然要死四次⋯⋯」
我拔出正義的手槍,指向這個嘴硬的叛逃者——
忽然,我看到地上一張信紙,猶豫了一會,還是忍不住把它撿起來。
這信紙有點陳舊,上面的筆跡非常的稚嫩。
我很驚訝,為什麼叛逃者會有這一封信。
「這封信,你是怎樣得到的?」
我推開醫院的後門,外面和平日的清晨一樣,霧氣沉沉,應該沒有人會看到我們。
我把換上了醫護人員制服的叛逃者帶出來,解開了手銬。
「走吧!」我說。
「為什麼⋯⋯」叛逃者不敢相信,我竟然會冒這個險。私放叛逃者,好明顯,也是一條死罪。
我把那封陳舊的信塞進叛逃者的手裡。
「因為這封信。」
「這封信,是我當年努力成為情書作家,一次又一次的失敗,被退稿、被刪除、被警告,感到絕望想放棄的時候,收到的一封情書,它讓我相信,我們還是有愛⋯⋯難道⋯⋯」
我默默地點頭——
很久之前,我剛剛進入鐘樓,成為初級時間調控員,負責檢查文字時間,經常看到她的文字,可是,她的內容越來越單調、越來越乾枯。後來,幾乎不用檢查都能通過,卻不知為什麼,她的情書再也不好看了⋯⋯於是,我模仿她原本的筆觸,寫了這封信給她。
「趁天還沒全亮,快走吧!」我催促她離開。
「你......不會有事吧?」
我拿出一顆無憂:「你走了之後,我會吃一顆,把時間調回正軌,我不會記得你⋯⋯」
她按住我的手:「我想你記得梨梨⋯⋯和我一起走吧!」
我笑了笑:「我不覺得銀河宇宙有多了不起,沒有鐘樓,還不是要給自轉鐘控制?我知道,自轉鐘現在被四大星體掌控,銀河宇宙的居民,都受他們擺佈。」
「誰說我要去銀河宇宙了?」
「你說,若有來生,你要到宇宙的另一端.....」
叛逃者,不,梨梨指向天際:「我要去一個新的宇宙,叫馬特宇宙!」
「馬特宇宙?和銀河宇宙有什麼分別?她能給你什麼?」
「不要問宇宙給你什麼,問問自己,可以為這個宇宙,創造什麼。」梨梨嫣然一笑: 「聽說,馬特宇宙的每一個星球,都是自己創造出來的;你,就是自己星球上的小王子。你要做的,就是不停地創造,和其他星球連結起來,織出一個不斷創新的宇宙⋯⋯」
她遠眺未來的眼神,充滿期盼和希望。
「謝謝你,將來,我也會給你寫一封信,這封信,將會永遠存在於馬特宇宙。」
「永遠?」
她堅定地點頭:「永遠。」